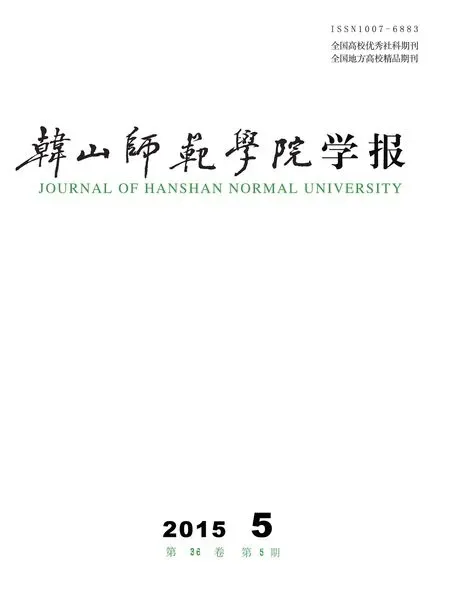马礼逊与中英早期官方交往
——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为中心
2015-03-27伍玉西
伍玉西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马礼逊与中英早期官方交往
——以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为中心
伍玉西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广东潮州 521041)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作为东印度公司派出的代表之一,加入了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任中文秘书兼译员。他参与了此次出使的全过程,且表现得比较活跃,在双方的语言沟通和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礼逊坚持国家交往过程中的平等原则,反对英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礼,在那个时代英国人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诸多评议中,他把问题抬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上。
马礼逊;阿美士德使团;官方交往;中英关系;平等
一、引 言
在1834年英国向中国派驻商务监督之前,中英间有过两次正式的官方交往。一次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来华,另一次是1816年的阿美士德(William P.Amherst)使团进京。①乾隆六十年(1795)和嘉庆十年(1805)进贡过方物,由广东督抚代为呈进。参故宫博物院辑:《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63页。两个使团均为经贸利益而来。英国对华贸易始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已居西方各国对华贸易首位。自1757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人在华贸易被限于广州一地,且处于一系列既定规条的严密控制之下。英国政府最初想通过外交途径和谈判手段来解决中英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并借机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但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无功而返,几乎没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进入19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英国摆脱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由此导致两国在贸易、军事、司法等领域的矛盾加深,冲突时有发生。每当冲突一起,广东督、抚总是以封仓相要挟,并随即出台更为苛严的规定来约束在华外人,这样就使得广州的商贸环境越来越恶化。在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下,1816年英国政府向中国再派使团,这就是阿美士德使团。使团旨在通过前往北京觐见中国皇帝,以改善英人在华贸易环境,为他们“消除一向受到的种种冤抑,免除将来这种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情况继续发生,并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避免地方当局任意侵害,并受到中国皇帝及钦定章程的保护”[1]。他们的诉求主要有:贸易不能间断;中国官员不得随意闯入十三行英国商馆;可以用中文与中国官府通信;争取允许让一个英国人长驻北京,或者允许在北方海岸的某个港口进行贸易。[2]275-278
中英官方交往首先遇到的是语言沟通问题。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教授中文,当时来广州贸易的各国商人极少有人会说哪怕是一知半解的中文。在广州和澳门两地,替中国官府做事并承担了一定翻译职能的是通事,美国人亨特(William Hunter)说他们“只通中文,并不懂外文”[3]。虽然不至于如此不堪,但以他们所受的低层次文化教育和不伦不类的“广东英语”,是无法胜任两国政府交往这种庄重场合里的翻译工作的。马戛尔尼出使时为翻译问题大费周折,最后是天主教传教士以拉丁文为中介解决了问题。阿美士德出使时情况有所改善,英国人中已有少量懂中文的人才,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马礼逊是伦敦传教会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传教士,1807年9月7日来到广州,寓居十三行商馆。通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他的中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809年初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为中文译员,1811年又被雇为中文秘书,直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独占权被取消。东印度公司是一家从事东方贸易的商业公司,1716年在广州设立商馆,1773年在澳门建立属下公司,由特选委员会全面负责对华贸易事宜。阿美士德使团成行后,东印度公司对此高度重视,承担了使团的所有费用,并抽调了公司里包括马礼逊在内的几乎所有懂中文的人员,该年度的特选委员会主席小斯当东(George T.Staunton)出任第一副使,其他人或担任中文秘书,或提供健康服务。[2]257
与马戛尔尼使团一样,阿美士德使团也陷入到外交礼仪的纷争之中。在天朝人看来,阿美士德勋爵来华又是一次“纳赆输诚”[4]54的朝贡行为,按清朝礼制和惯例,使节必须行使相应的朝贡礼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面圣时行三跪九叩礼,即所谓觐礼。英方全权大使阿美士德在听从了小斯当东等人的意见后,拿定了主意,哪怕使团不被接见,也不会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最多只能单膝下跪,鞠躬三下,如此重复三次。双方几番商议,最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由于觐礼问题悬而未决,也由于中方官员和世泰的昏聩(他向嘉庆帝和英使各隐瞒了部分真相,把事情弄得更糟),英使觐见未成,遭到了嘉庆皇帝的驱逐。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是中英官方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中英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马礼逊在使团中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中文秘书兼译员,但因他表现得“非常活跃”[5],甚而在一些中文文献中,他被误当成“副贡使”①参(清)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5页;(清)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8页;赵尔巽:《清史稿·邦交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17页。,可以说,他在使团中是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的。在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研究,特别是有关马礼逊的研究中,有一些提到过马礼逊与使团的关系,②如清洁理《马礼逊小传》第六章“董事的反对与北京之行”,费佩德、杨荫浏译本,广学会,1935年版;英人海恩波《传教伟人马礼逊》第十三章“撤职而不去职”,简又文译本,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年版;英人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的先驱》第九章“北上京师——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王振华译本,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一章中的“马礼逊的政治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顾梦飞《早期来华传教士活动特点及其影响——以马礼逊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及其参与英国对华外交政治为例》,《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1期;陈才俊《马礼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贾永梅《早期来华传教士的“非传教行为”研究——以第一位来华新教士马礼逊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江滢河《英国的全球战略与澳门——以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等。但它们都只有简略的叙述,未做专题性的深入探讨。本文在充分挖掘中外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他在这次中英官方交往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总结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从礼仪问题入手,分析他的国家平等交往观。
二、马礼逊随阿美士德使团进京
马礼逊最早接触使团事务是在1816年6月初。英国出使的确切通知晚至这年5月25日才到达澳门,此时使团已经启程三个多月了。28日,东印度公司澳门特选委员会致函广东巡抚兼署理总督董教增,报告英使来华之事。30日,该年度的特选委员会成员梅特卡夫爵士(Sir TheophilusMetcalfe)又带来了一封印度事务部主席白金汉希尔伯爵(Earl of Buckinghamshire)致两广总督的信件。因是政府机构间的往来公函,不能像特选委员会的禀帖一样由行商转交。在小斯当东的安排下,梅特卡夫爵士以“英吉利公使”的身份亲自到抚院衙门递交函件(总督蒋攸銛不在广州)。马礼逊作为公司译员和中文秘书,与一位皇家战船的船长、一位公司职员一起,陪同梅特卡夫爵士前往。他们于6月4日到达广州,同日交函,随后在商馆区停留几天,回答了广东官府关于使团情况、欧洲事务及英国政府等方面的咨询。[6]143
阿美士德等从欧洲动身的使团人员没有在广东登岸,而是直接走海路上北京。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其他代表于7月10日在南丫岛加入使团,7月28日抵达白河口外,8月9日在塘沽登岸,12日到达天津。在天津停留期间,长芦盐政广惠奉命接洽,嘉庆帝又派工部尚书苏楞额到天津赐宴,双方就觐见礼仪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14日离开天津,20日到达通州。嘉庆派出总管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和世泰以及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到通州指导英使的觐见礼仪。28日离开通州往北京,29日清早被安排觐见,不久即遭驱逐,走陆路南下,1817年1月1日到达广州。马礼逊参与了此次出使的全过程,记录了这六个月他在内地的行程和见闻,并以《1816年英国使团出使中国纪实》(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Year 1816)的书名于1819年在伦敦出版,成为记载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的几种原始资料之一。①此外还有副使小斯当东的《1816年英使往北京纪事》(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另一副使埃利斯(Henry Ellis)的《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首席医官阿裨尔(Clarke Abel)的《中国旅行记(1816-1817年)》(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使团中文秘书之一德庇时(J. Francis Davis)的《中国纲要》(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 between Peking,Nanking, and Canton;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Present War)。除了有关使团事务外,该书还留下了不少有关内地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社会风貌方面的记载,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独有的观察视角。
在此次出使过程中,马礼逊承担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翻译工作。使团中共有6人懂中文,均来自东印度公司,他们分别是副使小斯当东、医生皮尔逊(Pearson)、中文秘书曼宁(Thomas Man⁃ning)、图恩(Francis H.Toone)、德庇时和马礼逊。小斯当东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伦纳德·斯当东(Leonard Staunton)的儿子,1793年他12岁时随父来过北京,后在东印度公司任事多年,是一位中国通。但他的身份是使团副使,一般不进行具体的翻译工作,在双方会谈时他尽量避免干扰马礼逊的翻译和取代他译员的地位。[7]44其他5人均是因懂中文而被小斯当东选为使团成员的,但真正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只有马礼逊一人。皮尔逊是医生,全程不见他进行过一次翻译。曼宁最早于1806年来华,是董事部派来的译员,但他喜欢浪迹天涯,无心于中文学习,他的翻译很糟糕,“只有将英文本读透并能辨别汉文原意的人,才能全部了解”[2]101。图恩是马礼逊的学生,学中文已有6年,但长进较慢,在进京途中“主要借助于汉字”与中国人进行交流。[8]47德庇时也是马礼逊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但他那时才20出头,学中文仅有3年。相比之下,作为首席译员的马礼逊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就高得多,不论是口语(包括粤语和官话),还是书面语,他都能运用自如。使团另一副使埃利斯在见到马礼逊后,感慨地说:“我万万想象不到,欧洲人竟然能够把这种最难学的语言掌握到如此熟练的程度。”[8]43因此,马礼逊得到授权,为使团翻译中英两国的官方文件,并作为译员出席双方所有的会谈。由于他对中国文化有比较精深的理解,他的翻译是比较准确的,他对1816年8月30日嘉庆帝颁给英王敕书的翻译就很能说明问题。英使得到的敕书有中文和拉丁文两种文本。拉丁文译本不知出自何人手笔,很有可能是由担任内阁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南弥德(Louis-Francçis-Ma⁃rie Lamiot)所译,南弥德在翻译时,把原文中那些表示中国皇帝君临天下和对外国人表示轻蔑的地方,或加以省略,或改为轻微平和的辞句,这种处理方法本是善意,但不利于英国人对中国皇帝文书的准确把握。马礼逊从阿美士德勋爵那里抄录了汉文本,把它细心地译成英文,并对其中的一些关键性字眼加以解释,因此英国人非常“珍视马礼逊更准确的翻译”。[2]295
中国方面,因天津和北京没有懂英文的人才,广东巡抚董教增从广东遴选了一位“熟悉英吉利国夷字夷语”的通事,派员伴送到直隶总督衙门。[4]55但天津方面迟迟不见此人的到来,晚至8月28日这位叫阿周(Achow)的通事才出现在北京。[8]126也就是说,从7月29日使团与天津官员第一次接触开始直到8月28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中方没有自己的译员。当双方代表正式会谈时,中方官员的陈述只得由英方译员代为翻译。广惠在见到马礼逊后,发现他“言语尚为通晓”。广惠在1816年8月1日(闰六月初八日)的奏折中称,“该国译生言语尚为明白,而天津别无通晓夷语之人,只可暂令该国译生传语”。[9]正因为如此,在某些特殊场合里,马礼逊就成为了中国官员发泄和倾吐的对象。例如,英使担心嘉庆帝只允许他们在中国作短暂停留并由原路返回,为了不让有任何这样的机会出现,他们在塘沽登岸后即让船只离开泊地,南下广州。广惠获知英船离开的消息,惟恐遭嘉庆问责,心急如焚,忙向英使追问船的去向并声明事态的严重性。阿美士德反唇相讥道:既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告知呢?广惠无奈,情急之下把怒火发泄到译员身上,他转身对马礼逊说:“不应该责备特使,错误在于你没有忠实地传达我们的话。”此语一出,视诚实为生命的马礼逊甚感委曲,声明道:如果广大人这样认为的话,他拒绝再进行任何翻译。广惠自知理亏,在小斯当东的解释和要求下,当场向马礼逊道了歉。[8]79再如,使团在通州时,和世泰为说服英使接受中国礼仪,讲了一番“大皇帝是天子,所有的王都得跪倒在他面前”之类的天话,并说三跪九叩礼自有朝代以来就有了。为了证明自己说话有据,他把脸转向马礼逊,说:“你是知道这事的。”[6]170和世泰把马礼逊当成了熟读中国经书的学者和自己的知音,想从他那里寻找支持。又如,在使团遭驱逐的8月29日早晨,九门提督的一位部下奉命通知英国人离开,他气势汹汹地来到英国人的住所,嚷嚷着要找译生,接着就在马礼逊面前大吹特吹起九门提督的权势,并顺便把英国特使数落了一番。[10]
除了为中英双方翻译外,马礼逊还是英方的主要联络人,是“与中国人交往的主要媒介”[8]43。他不时与中方负责联络的天津兵备道张五纬和副将寅宾会面,进行一般性的意见交换和信息沟通,也答复中方官员的询问,对相关问题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例如,中方接待官员抱怨使团人数过多,连卫队和乐队加在一起达到了75人。马礼逊说:“对一位如此伟大的皇帝而言,这点人数简直就不值一提。”天朝官员听后很得意,就默许了他们。[11]34再如,接待人员对使团名单心存疑惑,因为广东官府提供的名单中有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而没有托马斯·斯当东(Thomas Staunton)。马礼逊解释说,托马斯是小斯当东孩提时代用的名,乔治是他现在用的名,“由于这种情况符合中国人的观念,中国官员们表示满意”[8]74。关于礼仪问题,他向张五纬解释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个朋友派他的仆人向另一个朋友问侯致意,这两位朋友家里各自的习惯做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接受致意的这名朋友不应该坚持让另一个朋友的仆人遵守他家里的特殊规矩。”[8]106-107
马礼逊很清楚,中英关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他所能解决的,但他又非常渴望两国政府能够保持正常的交往。他认为英使觐见中国皇帝不是解决中英商贸问题的唯一途径,他曾向张五纬提出,如果因为礼仪问题皇帝拒绝接见英国特使,还可以派出官员与他就相关事宜进行协商,“以此来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8]1079月15日,离京不久的使团从邸报中得知,嘉庆把此次不能成礼的责任归于中方办事官员瞒报实情,并没有责备英使。马礼逊认为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建议把特使在被召见的情况下想要提出的请求列成条款,进呈给皇帝。但他的提议遭到了否决,理由是:即使得到了召见,他们的请求大多(不是所有)也会遭到拒绝。[11]205实际结果可能会是这样。不过,此时使团决策层考虑的是如何向国内舆论交差,中国官员的舛误让他们摆脱了礼仪困境:既不会因为遵行叩头礼而有损英国的国家尊严,也不会因为拒行叩头礼而危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利益。他们高兴得忘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连提书面请求这样的事情都不愿去尝试。
使团成行后,东印度澳门公司前任特选委员会主席益花臣(J.T.Elphinstone)预感到马礼逊“将会是这个使团的重要人物”,特写信给他,希望通过他的努力,“使双方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12]466事实证明,在此次出使过程中,马礼逊确实尽了自己的力量,至少在双方的语言沟通、信息传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马礼逊的国家平等交往观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有关礼仪问题的争执最早出现在1816年6月4日。当那一天梅特卡夫爵士在广东抚院衙门呈递书信时,中国官员要求他“拜伏”、“如陪臣礼”,但他不从,商议再三,许行英式免冠鞠躬礼。当时参与接见的副都统张永清大为不悦,“据案不少动,意殊拂然”。[13]168在天津和通州,中英双方为觐见礼仪问题反复争论,终无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礼仪之争不仅发生在中英两国之间,还出现在英国人内部,是执行还是拒行中国礼仪,英人意见并不一致。
在英国政府给阿美士德的训令中,觐礼问题似乎是可以通融的,“为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之故,可以遵守这样的礼仪”。[7]30使团另一位副使埃利斯也认为,“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在这样的场合对抗这样一种被认为属于东方野蛮习俗的礼仪,从而牺牲使团更为重要的目标,也不能被看作是明智的做法”。他还说,“如果中国人在其他方面对待使团的态度还算令人满意的话”,叩头对于维护英国的国家尊严“决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使团的远期目标要取得成功,唯一的机会在于给中国皇帝留下一个好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在合理的自尊所允许的范围内,结合策略的考虑,“尽可能地顺从中国皇帝和国家的特殊习俗”。[8]38,39-40,105
然而,东印度公司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来自董事部的指令是:“最重要的是要考虑使团对广州产生的效果”;“在礼仪和接见问题上,不能退让,因为有可能导致在那个地方(广州)损害英国的国家尊严”。[11]56作为公司代表,出任使团第一副使的小斯当东“此时已赚取足够的财富,并早有回英的打算,东印度公司在华利益虽重要,但不希望因遵行叩头礼而对其名誉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反对行三跪九叩礼。[14]他公开的理由是:
即使不去考虑我们原本就反对这种礼仪,……(屈从)不仅有损于国家尊严和丧失国格,而且也会伤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和利益。这种服从(从我对中国人品性的基本了解和经验来看,尤其是从1795年荷兰使团的结果来看),将不会有助于实现我们正在筹划的任何一个目标,或者以任何方式惠及我们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7]31-32
在小斯当东看来,英国特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跪拜礼,不仅有损大英帝国的尊严,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会危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利益,因为广州的官员们会因此更加瞧不起英国人。除马礼逊之外,东印度公司的其他代表持有跟小斯当东同样的观点,认为“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会严重伤害公司的利益”,“要维护广州商馆的尊严以及这种尊严带给他们的效能,就必须使中国人相信,他们总是坚定不移地遵守那些已经确定的原则,而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在如此重要的场合里向中国人屈从,必然会彻底破坏他们的这种信念”。[8]117
作为使团成员之一,马礼逊在觐礼问题上也有自己的态度。跟东印度公司的其他代表们一样,他反对英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礼,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由上可知,无论是埃利斯认为可行中国礼仪,还是小斯当东等人反对行中国礼仪,都是建立在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之上,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利益立论的。马礼逊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拒行中国礼仪可能会损害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现实利益,但他又从一般的原则出发,认为“屈从是不恰当的”,[7]103因为在他看来,这种礼仪违背了国家间的平等原则。
马礼逊指出,礼仪实际上涉及到平等问题,它们不仅是形式,而且是一种像话语一样可以理解的语言,有些礼仪是中性的,没有不平等之意在其中,但有些礼仪则是“以身体姿势的不同来表达服从和忠诚(意义)”。[6]141马礼逊列举了中国人行礼的多种方式,认为其中的三跪九叩礼是“这个注重礼仪的民族所能发明的表达效忠和臣服的最为强烈的外在表现形式”[12]450。他宣称,“有些民族天性不愿遵行那些明显具有屈从意义的礼仪”。[6]141言下之意是:不列颠人不应也不会在中国皇帝面前丧失自己的天性。
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都有过这样的提议:如果一定要让英使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礼,那么必须让一位与英国使节官阶相等的满洲官员在英国国王的画像前完成同样的动作,或者让他亲往欧洲,在英王面前如此。也许是受到了这种提议的影响,马礼逊提出了国家交往过程中的礼仪对等原则,他说:
提出以下问题或许并不恰当。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行这样一种表示完全屈从的礼仪时,无论以何种形式,哪怕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只要是相互的,就不妨碍平等或者彼此的独立;如果不是相互的,那么这些仪式最后就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屈从和效忠。就此而论,现在统治中国的鞑靼家族把这种礼仪称为“三跪九叩”,就是三次双膝下跪,九次以头抢地。那些认为自己是中国藩属和有效忠义务的欧洲国家,就可以行这种鞑靼礼仪;如果认为自己不是,则不应该如此行礼。[6]141
在乘船北上途中,他奉命翻译了英国摄政王(Prince Regent)致嘉庆皇帝的国书、礼品单、使团人员名单及其它文件,为体现中英两国平等,他把特使译为“王差”而不是“贡使”,把送给皇帝的物品译为“礼物”而不是“贡品”,把摄政王的国书译为“书”而不是“表文”。[6]141现场翻译也是如此。当使团在天津与中国官员进行觐礼问题会谈时,苏楞额说:如果英使拒行中国礼仪的话,英国“在广州的贸易可能会因皇帝不悦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失”,又说皇帝陛下可能会对英国国王发怒。马礼逊认为后一句话过于冒犯,因此“非常得当地拒绝加以翻译”。[8]668月27日在通州,和世泰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们的国王可能会有麻烦。对此,马礼逊“以其惯有的敏锐判断力,拒绝予以传达”。[8]115
客观地说,马礼逊的平等外交主张并没有现实的根据。对长期受宗藩观念影响的天朝人来说,礼仪对等相比于简化礼仪更具冒犯性,理事官员甚至不敢据此上奏。与此同时,平等也不是英国外交的现实原则,它本身“并未以平等态度对待其它较弱势的国家”,“每当时机成熟且力量足够时,就常展开掠夺和殖民的行径”。[15]实际上,他的国家平等观是源于他的人类平等这个一般性的原则。
1824年7月,正在欧洲休假的马礼逊应邀到利物浦的一座教堂做了一次题为《民族间的血亲关系》(“The Kindredship of the Nations”)的布道。他针对一些人吹捧自己个人、家庭或民族比其他同类更为高贵的论调,以《使徒行传》第17章第26节即“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为依据,提出了人人平等的主张。他的依据是:“因为上帝从一本造出了世上的万民;因为全人类只有一个上帝和一个父,并且他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同样的材质,因此明显只有一种血缘关系,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呼吁人们一起来反对那种血统高贵论,他说:
我们应该从神圣的宗教中得到支持;我们应该反对现存的血统高贵现象,这种现象是:让一部分人在地位上高于他们的其他同类;或者让他们免除我们人类本应承担的责任;或者把他们抬到异教神那样的地位。长久以来形成了某个人尊贵、某个家族荣显以及某些国家有权支配另一些国家的错误观念;走上歧路的民族主义让人们不是相互憎恨和伤害,就是彼此轻蔑和鄙视。面对诸如此类的人,我们今天宣布:人类都有血亲关系,所有的人都是兄弟。[16]
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早在17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Hu⁃go Grotius)就提出了国家主权独立、平等的学说。马礼逊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出发,推演出民族平等与国家平等的结论,可以说是对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平等观念的一种神学注解。
马礼逊的国家平等交往观虽不属创见,但他从这个视角来看待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的外交礼仪之争,相比于一般的英国商人和政客而言,“把问题抬到了远比肮脏的商业得失要高得多的高度上”[17]。引文出自德庇时,仔细回味当时英国人关于中国礼仪的各种言论,德庇时对自己老师的这种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四、余 论
在新航路开辟后西方的海外殖民活动中,传教士虽与商人结伴而行,但一般不直接卷入商贸
活动。受清政府严厉禁教政策和一口通商制度的制约,作为传教士的马礼逊被迫与垄断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深度结缘。东印度公司不仅从事对华贸易,还与英国对华政治、军事、外交、司法关系牵扯在一起,因此任事于东印度公司的马礼逊参与了大量与中英关系有关的事务,加入阿美士德使团只是其中之一。从主观上来说,他也是很愿意参与使团进京觐见皇帝这样的政治活动的。因为这样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为传教服务,还可以为改善中英通商条件尽上自己的力量。马氏倡导正常的商贸往来,他说:“因为人类劳动产品种类数量巨大,且地域广阔,一般来说,一地的某种产品过剩而另一种产品稀缺或完全没有。通过物品交换或商品贸易,可以改善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生存条件。”一个地方的所有事务会受到商品交换的有效影响,人们在自由和友好的交往中彼此受惠。他还注意到,商业活动有助于平等观念的形成。他说,正如人们在进行小规模商品交换时容易滋生平等和互惠观念一样,国家间的交往和商业往来也容易产生两国平等和互惠的观念,“一方对另一方感恩戴德,或屈服于另一方,这样的观念很可能损害两国间公平的商业往来”。因此,他支持英国政府的重商政策,认为:“那些以真诚之心推进不同民族间友好交往的政府应受到人们的赞赏。他们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推进了整个人类的福祉。”“农民、工人与商人都是同样有用的职业。就像鼓励和保护国内的工农业一样,为了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对外国统治者施加影响也许是政府职能的必要部分。”[6]140-14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礼逊才积极参与了旨在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以保护英国商贸利益的阿美士德使团,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姚曾廙,杨志信,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60.
[2][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第三卷[M].区宗华,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3][美]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M].冯树铁,沈正邦,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8.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郑天挺.马礼逊父子[C]//列岛.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三联书店,1958:356.
[6]MORRISON ROBERT.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J].Substance of the Speech of the Right Honorable,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on Finance;Comprising the Finance Resolutions for the Year 1819,1819,15(29).
[7]STAUNTON GEORGE T.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 in 1816[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8][英]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M].刘天路,刘甜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9]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484-485.
[10][英]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M].刘海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04.
[11]DAVIS J FRANCIS.Sketches of China;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Four Months between Peking,Nanking,and Canton;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Present War vol.1[M].London:Charles Knight&Co., 1841.
[12]EILZA MORRISON.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M].Landon:Longman,Orme,Brown,Green,and Longmans,1839.
[13](清)王之春.清朝柔远记[M].赵春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168.
[14]游博清,黄一农.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中英关系(1793-1840)[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69:18.
[15]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7,第78本第1分:37.
[16]MORRISON ROBERT.A Parting Memorial:Consisting of Miscellaneous Discourses Written and Preached in Chi⁃na;at Singapore;on Board Ship at Sea,in the Indian Ocean;at the Cape of Good Hope;and in England[M].London:W.Simpkin and R.Marshall,1826:170-171.
[17]DAVIS J FRANCIS.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1[M].New York:Harper&Brothers,Cliff-Street,1836:100.
Robert Morrison and Official In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in the Early Time——Focusing on the Amherst Embassy to China in 1816
WU Yu-x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anshan No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dispatched by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Robert Morrison, a missio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joined the the Amherst Embassy to China in 1816,taking the post of Chinese 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He attended actively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mbassy to Beijing,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between both parties.Morrison insisted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in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intercommunication,and objected to British en⁃voy’s‘San-kwei-kew-kow’before Chinese emperor,which brought the question up on a higher ground than other opinions on Chinese ceremonies expressed by British in that time.
Robert Morrison;the Amherst Embassy;official intercommunication;Sino-British rela⁃tions;equality
K 249
:A
:1007-6883(2015)05-0078-07
责任编辑 黄部兵
2015-04-13
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伍玉西(1965-),男,湖南新化人,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