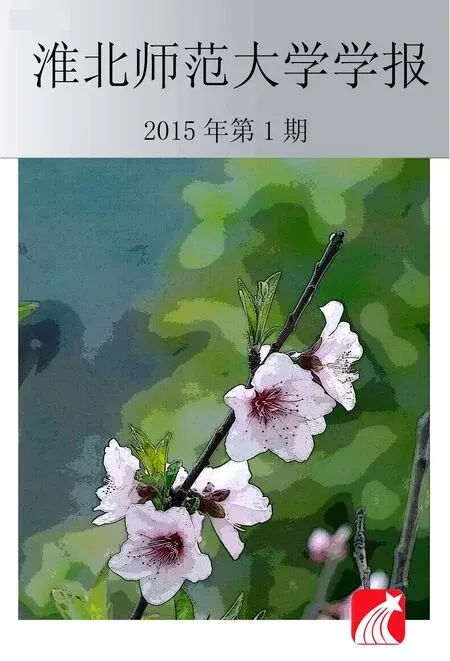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续补兼考
2015-03-27吴航
吴 航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谢国桢先生锐意于明末清初史学著述的研究,盛年即结撰《晚明史籍考》二十卷,1933年由北平图书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又增补至二十四卷,题为《增订晚明史籍考》,1964年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末附《补遗》一卷,补录《擒妖始末》等九种[1]1086-1092。“文革”之后,谢先生重新修订此书,其《补遗》之部,再次增入《见闻记录残存》等二十种[2]1086-1097。对于此书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早有学者衡定为“使人执此《考》以求其书,有事半功倍之乐”[3];“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4]358。谢先生搜辑之勤,用力之深,令人敬仰,然文献浩繁,不免遗漏。
笔者曾撰《〈增订晚明史籍考〉补遗》(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8期),补著此书所遗私史六种。今爰就读书所及,更事搜辑,在原书体例之基础上,略作变更,按照总纪南明史乘、南明三朝、人物传记三类分置;其有书现存者先列,有目无书者次之。需要指出的是,今所辑考之明末清初私史重要材料,主要来源于明末清初学者文集。明末清初学者文集关于明末清初历史之撰述与私史著述之记载,数量繁富,内容广泛,足资采摭,希望有益于明末清初史学的研究。
一、朱书《癸壬录》未见之书
朱书《杜溪文稿》卷二《癸壬录自序》云:
起万历元年癸酉,历九十年,讫于壬寅,合诸野史稗官之说,删其芜复,正其同异,为《癸壬录》若干卷。先癸于壬者,循两端之序也。上而朝廷之爵赏予夺、巡幸播迁,下而朋党之角争盛衰、往来报复,内而宫闱宦竖之显晦,外而督抚勋镇之战守,以至忠臣之捐躯湛族,义士之穷饿远遁,莫不见于是编。
於乎!渐有由滋,势有由极,乱有由兆,祸有由致,岂偶然也哉!是故明祀绝于壬寅,而其端伏于癸酉,何也?神宗即位之初,张居正秉政十年,帝一以委之,内安外攘,扩地奏功,无虚日,虽数百年长治可也,何为不旋踵而溃乱相继,以至于亡哉?然惟其委政于居正,而居正之祸已伏,居正之祸伏,而国家之亡,即与之俱伏矣。盖居正既得重祸,自是百官以能与阁臣异同为风节,而阁臣渐且无权,言路渐且日横,党祸作,而争门户者,不急国家之急,止急其党。是其党者,虽跖、蹻奉之登天,死犹有余美焉;非其党者,虽管、葛挤之入渊,死犹有余疾焉。收罗党人,智于朝廷之求策,力防异党之攻己而思去之,勇于将帅之除盗寇,卒至卑者泥首事仇,高者殒身膏斧,国与家俱尽,而向所争为党者,亦已烟消影灭,而不知何有,徒委君父于草莽而不能顾。夫孰非内外相抗以为风节者之实始基之也?岂不哀哉!
北都沦丧之后,一建南都,再建闽海,三建肇庆,由是迁武冈,迁南宁,迁安隆,迁云南,寄命缅甸,以终焉。方其始也,地大于昭烈、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刘崇,而所仗以立国者,则昏贪之马士英,海贼之郑芝龙,叛降之刘承胤、陈邦傅,流贼之孙可望,人主既无股肱心膂之托,而清流又或从而激之,夫安得而不败?
於乎!国家养士三百年矣,而崎岖蛮乡裨海、蛇虺蛟鼍之域,死而后已,传数世不变,不出于剧盗之身,即出于剧盗之子若孙。今而后,读书讲学之人,其无轻斥盗贼哉?要其祸自万历初基之,而万历末即受之,所以基祸者不一端,而党为大。故曰明祀绝于壬寅,而其端伏于癸酉。
呜呼!癸于水涓流也,壬则江海也,涓流之不塞,遂至稽天浴日而莫知其所底,则惟有载胥及溺而已耳。虽有舵工篙师,长年三老,其何能救?况以素未操舟者,徒手与共惊涛骇浪中,欲无亡得乎?日入于酉而昼于昏,日生于寅而夜以旦,乃竟为虞渊之沉,而不复见柎桑之出也。哀哉其为癸壬也!阴加于阳,夜不复昼,所为北罗酆者也,天殆颠倒而不能自主也夫!
书家世力农,三百年无一人通籍于朝,未睹金匮石室之藏,徒以中年好游,因合闻见为此书,挂漏诚所不免;至是非得失,或因仍旧说,或考证情事。友人梅文鼎尝言:“一家之人,一日之内,彼此犹不能知,况天下至大?”数十年至远,安能尽谓有当其实?论而定之,以俟君子焉。[5]24-27
按:朱书(1654-1707),字字绿,江南宿松(今安徽宿松县)人。家居杜溪,因以为号,学者称杜溪先生。康熙二十五年(1686)举人。后弃去科举,遍游天下。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复出,再次中举。次年,考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奉诏纂修《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书。康熙四十六年(1707),因积劳成疾而卒于京邸,享年五十四岁[6]345-346。朱书著述等身,有《杜溪文集》《杜溪诗集》《松鳞堂偶钞》《游历记》《恬斋日记》《恬斋记闻》《恬斋漫记》《寒潭琐录》《谋野录》《评点东莱博议》等十余种[7]2,卷二五。此外,他还著有《癸壬录》《皖砦纪事》《古南岳考》等,编辑《仙田诗在》康熙《宿松县志》等地方文献。
朱书所著《癸壬录》,不载《增订晚明史籍考》。考朱书编纂《癸壬录》,曾商之好友张符骧、李嶟瑞等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朱书游历闽中,与当地藏书家张岩(字明詹)多有过从,自言:“予方编《癸壬录》,常常往其家借书。”[5]卷四《怡山擘荔枝记》次年,他寓居南京,致书张符骧,商讨《癸壬录》编纂事宜。康熙四十年(1701)夏,李嶟瑞寄之以诗,有云:“笔搜后死此心苦,书就孤臣生面开。(原注:字绿著《癸壬录》,渐次脱稿,予以先赠外大父蒙修王公事迹寄之,顷诗言及,故有此答。)”[8]491据此,戴廷杰认为朱书《壬癸录》当编于康熙三十八、三十九年之间。[8]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九年德聚四徳堂刻九卷本《杜溪文稿》,除卷二载录《癸壬录自序》之外,卷六又载录《龙眠愚者方公家传》《金中丞传》,原注俱云:“入《癸壬录》。”故此书很可能是传记体史书,或至少存在为数不少的传记。
经过康熙年间影响深刻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和乾隆年间“寓禁于修”的官方《四库全书》修纂,朱书著作多散佚湮没。民国《宿松县志》称,朱书“著述等身,以友人桐城戴南山获罪,故文字牵连,致多湮灭”[9]46。尤其是官修《四库全书》之时,其孙朱效祖“性过兢慎,值乾隆朝有禁书之令,藏书数万卷,举而煨烬之,杜溪遗稿半没于此,学者至今深惜焉”[9]182;“杜溪之书,湮没于乾隆禁书之令下者,为不少已”[9]71。幸存下来者,不过《诗文集》《游历记存(燕秦之道)》《评点东莱博议》《皖砦纪事》数种而已。可以推断,《癸壬录》很可能在这两次浩劫中被毁。乾隆四十七年(1782),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缴应毁书籍,将《杜溪文稿》列入应禁书籍清单:“《杜溪文稿》一部,刊本。是书朱书著,共四卷,系序记杂文。前有戴名世《序》。其稿内《癸壬录自序》一篇,语意更为狂谬。”[10]1527可见《癸壬录》一书尤中清廷历史忌讳,即使行世,亦难逃禁毁之厄运。
《癸壬录》记事,上起明万历元年癸酉(1573),下迄清康熙元年壬寅(1662),取“癸酉”“壬寅”之首字,故名《癸壬录》。其书前后跨度九十年,卷帙虽不可知,记载亦当繁复。至其内容,关涉实多,“上而朝廷之爵赏予夺、巡幸播迁,下而朋党之角争盛衰、往来报复,内而宫闱宦竖之显晦,外而督抚勋镇之战守,以至忠臣之捐躯湛族,义士之穷饿远遁,莫不见于是编”。重在总结明亡清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明亡渐进的历史过程,“其祸自万历初基之,而万历末即受之”。因此,张符骧推奖此书云:“自有明中叶以来,一切阨塞战屯、兴革刑赏之大,与夫稗官野叟之信而有征,皆非亲历不能悉。字绿既博通掌故,又继之以周游,故其为《癸壬录》,俱见朱氏治忽之迹。”[8]492
朱书力主明亡于永历朝之说,向不为学者所注意。事实上,戴名世与朱书互为畏友,相互推重,在清初学界,皆欲以一己之力而私撰明史。至于他们同持明亡于永历朝之说,或当日互通声气,有所讲求。康熙二十二年(1683),戴名世《与余生书》感叹:“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11]2又,《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首章云:“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而其亡也忽焉。其时……而不遽亡者,无党祸以趣之亡也。”[11]363朱书《癸壬录》一书晚成,力主此说,很可能受到了好友戴名世的影响。再看《自序》,有云:“北都沦丧之后,一建南都,再建闽海,三建肇庆,由是迁武冈,迁南宁,迁安隆,迁云南,寄命缅甸,以终焉。方其始也,地大于昭烈、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刘崇。……所以基祸者不一端,而党为大。”两者相较,殊多相似之处。但朱书尤不顾及清廷历史忌讳,明言“明祀绝于壬寅,而其端伏于癸酉”。由此来看,戴、朱之说,可谓同源共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戴氏大略只引史例而不敢明决,无若朱书之直言,敢以“明祀终于壬寅”告世。
二、易学实《赣州乙丙纪略》一卷 《犀厓文集》本
易学实《赣州乙丙纪略》卷末史论云:
明高皇以淮右布衣,奋三尺剑,扫清宇内。一传而文皇,天纵雄略,威摄遐荒。仁、宣孝敬,以及肃皇,列圣相承,仁恩浸渍,显皇涵宥四极,风化熙然。虽中间裕陵遭土木之侵轶,武宗有□藩之窥觊,而宗社奠安,复于盘石。历九叶而烈皇励精,海内望治,不谓流寇内讧,齐鲁秦晋楚豫,所在□裂。甲申三月十九之变,寇薄都城,三日而陷,烈皇身殉社稷,皇后从之,太子二王并为贼害。
呜呼!虽天不祚明,揆之人事,屹屹都城,明天子在上,公卿百执,岂尽匪人?胡不能効数月之守,以待天下勤王之师?乃奸党内应,顷刻沦亡,岂流寇之势果大于安史、女真?而烈皇之君天下也,固不敢望唐之明皇、宋之高宗乎?此何异巨室大家,强寇毁庐,既杀主人及其诸子,邻之有力者奋勇杀贼,贼去而室空,室空而人亡,邻人安得不从而有之乎?乃主人之臣仆,且徐向邻人而问旧物,试诘其主人安在,主人之子焉往,当亦哑然无词以对矣。是以新朝一传檄,而齐鲁秦晋楚豫之区,不三月而底定。
当是时,福藩继立于金陵,大江以南,尚有吴越、南楚、西江、八闽、两粤、滇黔,幅员半天下。乃君臣荒淫,置君父之雠于度外,虽出史可法于淮上,以为江南屏蔽,而惟事调停于反复跋扈之间。及大兵渡河,四镇之将叛降者三,可法即知勇过人,忠义滔天,安能以一□□□足江北□□□,况内有□□□□庸好,不畏北兵□侵,而俱惧左师东下,故□□□防之军,一撤淮阳耳,掷而弃之矣。淮阳既掷,□□已坏,长江虽□可扬帆,而渡金陵,尚能为□□□,故京口防江之水师,未见敌而溃,马士英□死钱塘,赵之圻即日献城矣。呜呼!天不祚明,丧亡之易易如此也。
由是,金声桓入据南昌,袁临吉一时陷没,区区赣州,孤悬上游,兵力既寡,外援又绝,徒以全城百姓,墨守七阅月,至八闽沦陷,犹誓死不降。呜呼!何其烈也。若使海内名城,大都皆若是乘坚抗守,北都必不至三日而陷,南都必不至望风而降,岂至丧亡之易且速如是哉!
予尝读明史,常开平之取赣州,填兵三月,高皇数使诏谕,城下之日,不许血刃。圣祖保全赣人,可谓至矣!三百年后,赣州百万生灵,损躯报之,岂不宜乎!呜呼!由是观之,取天下者,固不可不以明祖为法也。[12]727-732
按:易学实,字去浮,晚号犀厓,江西雩都(今江西于都)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人。甲申乙酉之际,亲见大河南北,兵寇交讧,土崩瓦解,乃归里奉母入山,忧思感慨,多见诸诗文。后累赴清朝科考,铨授分宜县教谕,终辞不赴。杜门三十年,坚卧梓里,著书永日。年八十二卒。康熙二十六年(1687),崇祀乡贤。著有《犀厓文集》《云湖诗集》《椒斋制艺》行世[13]990-991。
考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二十一年(1682)前后,易学实先后参与《雩都县志》《赣州府志》的实际修纂工作[14]827。当时受聘于地方政府主修地方史志之学者,每涉明清鼎革之际历史,有感于清廷忌讳问题,往往迟回瞻顾,不能实录直书。王士祯、钱澄之、方文等皆有感触。或易氏亲见此状,故而别著《赣州乙丙纪略》,以存其真。此书在纪年上,开篇采用“大清(顺治)二年乙酉”,正文则更以南明“隆武二年”,前后乖舛;在内容上,记载了南明隆武元、二年间赣州地区抗清斗争形势以及隆武朝政治,较得其实。作者善于总结明亡历史经验与教训,但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大放厥词,为清朝定鼎中原寻找“合理”的政治借口。
温睿临纂辑《南疆逸史》时,将此书归入“专纪一人一事者”之列,不著作者氏里[15]卷首。及杨凤苞撰《南疆逸史跋》,始补注其作者为“雩水易学实”[16]17。乾隆间官修《四库全书》,易学实《犀厓文集》因有“弘光元年杨廷麟举义于虔”[17]104等字句,语涉忌讳,被确定为违碍之书而禁毁。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奏准江苏巡抚闵鹗元奏缴禁毁图书六十一种,易氏《赣州乙丙纪略》抄本一册,赫然在列[17]187;后又被列入“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18]451,以期彻底禁毁。足见当时遭禁之严重,其书不得行于世,有以焉耳。而此书早年实以抄本单行于世,庶几可以考定。
《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一因袭温、杨之书著录,置于“记隆武朝、绍武朝未见诸书”一类。然此书幸存于清康熙间刻本《犀厓文集》之末卷,笔者校读易氏《文集》,始得见之。
三、陈士京《海年录》 未见之书
黄宗羲《陈齐莫传》末章“旧史氏曰”云:
君自端州返于鼓浪,迭石种花,作鹿石山房,与闇公(徐孚远)、愧两(王忠孝)吟风弄月,好为鹏鶱海怒之句,以发泄胸中之芒角。虽参帷幄,盖未尝受一事也。故张苍水《过访诗》云:“君因久客翻为主,我亦同仇况比邻。”则君之在岛上,犹管宁之避居辽海也。宁在辽东积三十年乃归,君在鼓浪屿十有四年,卒不返故乡而死。向使青州有微管之祸,宁亦必不归也。此君以宁始而不以宁终者,其所处为更穷矣!余读君《海年录》而悲之,赐姓经略本末略具,不为删去,使知海外别有天地也。[19]82-83
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二十七《陈光禄传》略云:
久之,见海师无功,粤事亦日坏,乃筑鹿石山房于鼓浪屿中,引泉种花,感物赋诗,以自消遣,别署“海年渔长”。又筑生圹于其旁,题曰“逋庵之墓”。……及在岛上,徐公孚远有海外几社之集,公豫焉。虽心情蕉萃,而时作鹏鶱海怒之句,以抒其方寸之芒角。徐公尝曰:“此真反商变征之音也。”所著有《束书后诗》一卷,《喟寓》七卷,《巵言》一卷,《海年集》一卷,《海年诗内集》一卷,《海年谱》一卷。[20]498
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五《从亡诸公之二·陈光禄士京》补注一章云:
予求公之集二十余年,诸陈耆老凋谢,莫能言公事者,最后得其《喟寓》一集于老友董颛愚,不胜狂喜,尚属公之手笔也。然苕人温睿临言,尝得见公《濒海年谱》,则天地间或尚有足本,予日望之。公羁栖海外一十四年,投骨不返,志节可感天地。而吾鄞前辈如林,无道之者,亦咄咄怪事。惟万季野修《府志》,曾为公立《传》,而今又略之,文献之佚,良可耻矣。[21]398
按:据以上三传,陈士京字齐莫,一字佛庄,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晚年流寓鼓浪屿,自署“海年渔长”。他原是南明鲁王监国的兵部职方司主事。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夏,他奉鲁监国之命出使隆武政权。当时,唐、鲁争名分事发,他遁之海上,与郑成功游,并得器重。十二月,郑成功烈屿“会文武群臣”,定盟恢复;次年移兵南澳,陈士京均参与其事。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开始,他定居鼓浪屿,并参加筹划军国大事;有些事情,郑成功还请他出马。如永历二年十二月,派他到广东肇庆朝见永历帝;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准备派他去日本借兵而未果;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郑成功以他和徐孚远为师,教授子嗣。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三月,陈士京病卒,享年六十五岁。
陈士京《海年录》,或即全祖望所称《海年谱》。而全氏又有《濒海年谱》之称,疑“濒”为衍字。陈士京亲历其事,据其见闻而成是书,所记多涉郑成功闽台抗清事迹,颇具史料价值。故黄宗羲称《海年录》“赐姓经略本末略具,不为删去,使知海外别有天地也”,并删定为《赐姓始末》一册,置诸《行朝录》之中。其史源可考者,斑斑如是。徐秉义与黄宗羲等明遗民学者素有交往,纂辑《明末忠烈纪实》之时,或曾引证是书。温睿临撰著《南疆逸史》,自言实多袭取“万子季野明末诸传及徐阁学《明季忠烈纪实》诸传”[15]卷首。以《路振飞传》为例,徐书末尾双行小注云:“此鄞人陈士京所记,当不讹。”[22]239温书不仅照录徐氏原文,更直接引述徐氏原注[15]112-113。所以,全祖望称温睿临曾得见陈氏此书,恐怕即由此而来。当然,温氏高明之处,在于他多闻阙疑,并注他说,以备存疑。
四、李清《诸忠纪略》 未见之书
陈瑚《确庵文稿》卷十二《诸忠纪略序》云:
昔元主诏修三史,集儒臣议义例,前代忠臣义士,皆得直书而无讳。然读文、谢二公《传》,论者犹疑其未备焉。盖当变革之际,一时忠义之事,往往详于野史而略于国史,固其势也。吾明方正学之惨夷,妇人孺子能言之,而尚以叩头乞哀见诬,况其下者乎?然则国史何可尽信,而野史之作岂可无其人哉?
昭阳李映碧先生,今之陈尚书、范太宰也。当其筮仕,由司李入为谏官,昌言正色,天下畏爱其风采。自遭国变,蕴藉义愤,日取其立朝时所上《请谥建文诸忠疏》,置几案间,以自磨切。已而,举甲申以来死忠诸臣,撮其大节之卓荦可观者,勒为一书。瑚受而读之,为之瞿然起,曰:噫!九原可作,其将以先生为知己乎?非先生不能志诸公之实,非诸公不足以当先生之笔也。盖诸公之为烈妇也,先生之为贞妇也,贞妇而述烈妇之事,必刺刺乎不休,亹亹乎有味焉。非然者,舌挢而不得下矣。
先生尝与友人书,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士君子所守者,止此一关耳。此关一失,可越而二,则由此而三,之十百之,皆所弗论,岂非一守而二流,流斯靡底乎?妇人守此则贞,而流则夏姬,王后三而夫人七。丈夫守此则忠,而流则冯道,历朝六而历君十三。”此岂先生之好为危言激论也哉?悯夫世士以达权通变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当前后两朝之变,先生皆以奉使出都,故免于难。其不濒于死者几希耳!然则食人之禄,而徒以一死报国,诸公之不幸;既死之后,有人焉捃摭其遗事而排缵之,以耀后世而垂无穷,则诸公之不幸而幸也。不与于两都之变,而留其身以有待者,先生之幸。不获从诸公之后,含笑入地,而仅载之空言,祈以发抒志士仁人之气,而寒奸臣乱贼之胆,此又先生之幸而不幸也。百年遗藁,空山之泪,徒殷一恸西台,朱鸟之味安在?兴言及此,不亦悲乎!
先生又尝谓瑚,言:“诸公之中,某也吾师,某也吾友,某也从容而赴,某也慷慨而殉,某也砥砺于平日,某也引决于一朝。”盖以贞妇而论烈妇,故其言之不爽如此。嗟乎!无先生之贞妇,则诸公之烈妇不传。今日传诸公者,先生矣。他日之传先生者,谁欤?此愚小子所以投笔而长叹者也。[23]348
按:《增订晚明史籍考》卷十八著录李清《诸忠纪略》,并归入“未见诸书”一类。前此,王重民撰《李清著述考》,依据徐乾学撰《李映碧先生墓表》、汪琬撰《前明大理寺左寺丞李公行状》,考定李清确有此书[33]198-210。今人张晓芝撰《李清著述补考》,亦沿袭前说[25]。然皆未见及陈确此《序》,更不知此书之内容。故陈《序》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李清(1602-1683),字映碧,号心水,扬州兴化(今泰州兴化市)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李清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兵科给事中。南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升任大理寺丞。所记当日时事,朝章典故,皆其亲见亲闻。如《三垣笔记》、《南渡录》(一名《甲乙编年录》)诸书,颇具史料价值。《南渡录》作为编年体南明史撰述,专记弘光一朝史事,最为详允。据陈《序》知,《诸忠纪略》“举甲申以来死忠诸臣,撮其大节之卓荦可观者,勒为一书”,是为传记体南明史撰述。此书之作,“祈以发抒志士仁人之气,而寒奸臣乱贼之胆”,旨在表彰明清易代之际抗清忠节人物,发挥史学彰善瘅恶之功用。然此书所载人物为谁,规模若何,因其散佚而难究其详。考全祖望曾讥刺《三垣笔记》,云:“其中记甲申死难诸臣有李国桢,乙酉死难诸臣有张捷、杨维垣,则失考也。”[20]1340疑《诸忠纪略》一书抑或载入李、张、杨三人,取其末后一节焉。
[1]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孟森.晚明史籍考序[M]∥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铅印本,1933.
[4]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朱书.杜溪文稿[M].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德聚四徳堂刻本.
[6]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清]邬正阶,郑敦亮.道光宿松县志[M].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
[8][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俞庆澜、刘昂.民国宿松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戴名世.南山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易学实.犀厓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卢振先,管奏韺.康熙雩都县志[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3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4]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5]温睿临.南疆逸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杨凤苞.秋室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18]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M]∥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黄宗羲.黄宗羲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1]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3.
[22]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23]陈瑚.确庵文稿[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4]王重民.冷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5]张晓芝.李清著述补考[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4):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