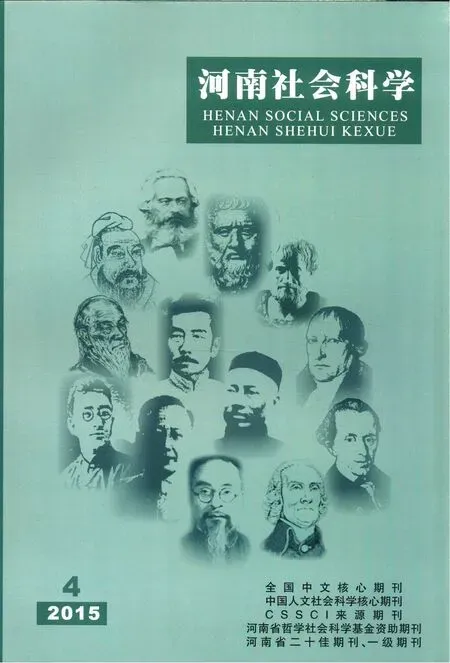马克思对资本文明价值的多重审视及其当代启示
2015-03-27张宇
张 宇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对市场作用认识的又一次飞跃,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构成中最为核心的一项战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中的一座里程碑。当然,如果我们把眼光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有机体之中,那么我们对于市场、资本、商品、货币(四者的核心是资本)等现代经济范畴之文明意义的认识和对于《资本论》等丰富思想资源的汲取仍有待深入展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资本论》文明观的解读模式,我们会发现两种片面化的倾向:一是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对《资本论》文明观的单纯否定论解读。其典型表现是,单纯以马克思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命题来评判资本。二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或者说广义上的市场经济时期,对《资本论》文明观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进步、社会形态更迭)的片面性解读。其片面性在于,只是从“社会”层面认识资本的物质作用,而没有进一步地从“人”的层面认识资本丰富的文明价值。因此,我们的分析就将以对《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解读为基础,从反思“三个有利于”式概括的局限性开始。
一、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之一的审视:交换的普遍化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被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三个有利于”作用,其在马克思原典中的语境是这样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当我们慎思明辨之后会发现,马克思所要强调的重点,并不是作为资本作用结果的“三个有利于”,而是作为资本作用原因的“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那么这一“方式和条件”具体是什么呢?马克思揭示道:“(古代)埃及、厄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2]
一言以蔽之,交换,就是资本得以超越以往生产形式的根本方法;而一切交换之中最大的交换,乃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交换的普遍化特别是劳动力交换的普遍化,是整个现代社会得以形成的根本立足点。其一,通过等价交换商品的形式来流通财富,就取消了暴力掠夺的生存基础,从而营造了日常生活中的和平氛围与平等心理,“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他们在社会职能上是平等的”[3]。其二,劳动力的商品化,第一次使得劳动者摆脱了暴力的胁迫(在原始积累后的资本主义常规时期里),生产动机由外驱转向内驱——致富欲,从而创造了普遍的勤劳。“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3],“普遍勤劳才是可能的”[3]。其三,不仅内在欲望刺激着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外在压力也把人们置于逆水行舟的活动状态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4]。交换普遍化的总结果,在人的层面表现为个人主体性的历史形成,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历史形成。
马克思关于资本这一文明面的深刻阐发,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具有重大的思想启示。首先,有必要升华一下对经济改革得以成功的微观基础的认识。从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5],都是建立在个体自主进行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交换基础之上的;交换,乃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的杠杆。这一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却被完全忽视;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仅被当作资本主义的罪恶面予以批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科书中则不予深入剖析。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就使得这一原理徘徊在自发作用层面,无法成为群众自己决策与实践的自觉理念[6]。
其次,从上述症候出发,我们就能够把脉到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迟缓的一个病灶,即人才自主性、创造性、流动性的缺乏。经济领域评判人才的标准是能力——效益本位,这种内在规定刺激人才的流动;政治领域则复杂得多,官僚主义的遗毒、战时模式的遗留、政府决策的非竞争性从而其效果评价标准的缺失、本位主义的人才壁垒、僵化的科层体制、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等弊端,严重地阻碍着人才的流动性,遏制着人才创造性的发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要“完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5]。对于这一决策,我们应当提升到劳动力自由交换这个现代社会立足点的高度进行理解。
再次,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存在着与市场经济最不能相容的保守意识。表现之一是,始终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视为各自独立的两手,而不能历史性地融合。邓小平同志启动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初衷,是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他的视野中市场化改革并不包含国民理性现代化的意义,因此他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当作两手(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是契合过渡阶段的实际需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文明意义日益凸显的新形势下,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却严重滞后于实践,滞后于个体主体性的发育要求。这种精神文明建设模式的意向是:承诺战时共产主义情感已经达到了道德顶峰,要始终保持不变,只待利用市场经济这只船把我们摆渡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彼岸,再手捧着战时——计划经济年代的意识形态,就实现了最高纲领。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表现之二,用原恩论政治哲学压制契约论政治哲学,表面上承认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源泉,而宣传教育中却往往暴露出救世主与大家长的霸权姿态,这就违背了党从群众出发、为群众谋利、受群众监督、向群众负责的政治本质。
综上可见,交换——这个看似最庸常的行为,却具有现代文明酵母的伟大意义。交换培育了个人主体性,从而使人格从依附性质向独立性质跃迁;现代社会不仅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也建立在现代理性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应当反思的一点就是在关注前者的同时,忽视了后者。所以,我们应当在经济认识、政治认识和文化认识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进对于交换这一现代文明密码的深入理解。
二、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之二的审视:生产的组织化与人化自然的形成
在前一问题中,马克思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这意味着他对于资本文明还有着其他多个方面的理解。综观《资本论》及其手稿,提到“资本文明”的地方有很多,但并未进行专门的、严密的逻辑分列。不过,通过马克思关于资本意义的宏观历史定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资本文明价值概括为现代社会的基石、人化自然的基石和世界历史的基石——这三个内在统一、本质相关的方面。上文探讨的是第一个方面,下面分别研究第二和第三个方面。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资本才……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3]。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施密特的术语来概括,资本具有创造“人化自然”的文明意义。资本主义大工业彻底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自然的依附性,使得自然对人的单向支配关系发生了一个逆转,使得人们早先对自然的小规模改造变成了大规模征服。站在今天生态保护主义的视角上,你可以批评资本主义大工业这种控制自然的狂妄心态,但你无法否认资本确实实现了有史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最高把握。这种把握的主要实现方式,一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刺激之下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进而利用)达到了外星系和微观粒子的层面;二是生产力在资本的高效组织之下获得了核爆炸式的大增长,“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4],从而使得人类获得了超越自然限制(肉体生存的物质资料稀缺桎梏)进入自由发展王国的历史阶段。下面我们就第二个方面,即资本组织大规模生产的文明价值,来剖析马克思这一资本文明思想的现实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作用的逐步凸显和西方经济学的东渐,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资本的生产性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21世纪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资本的生产性问题,即资本是否也创造价值的问题,其现实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资本性质的理论创新、从而政治定位的吁求[7]。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劳动价值论与资本的生产性绝然对立起来,机械地强调马克思关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来源的观点。这种理解模式,与其说是对《资本论》的科学解读,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使然。当我们回到原典,细致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生产性的阐述,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理解模式。马克思诚然强调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但从未把来源与生产条件混为一谈;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是生产的必要条件,“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8]。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客观地指出,“资本不是同单个的劳动,而是同结合的劳动打交道,正如资本本身已经是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一样……资本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2],“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2]。资本在生产组织中具有有机整合的系统作用,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作用;它不仅具有生产性,而且具有超越以往一切生产形式的高效性。
资本具有生产性的经济学结论,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政策的理论基础。首先,强大的组织生产职能,使得资本成为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第一前提。马克思指出:“关于资本是不是生产的这个问题,是很荒谬的……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3]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国有经济抑或其他经济成分,离开资本对劳动和客观生产要素的吸收、组织作用,就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5]。其次,是由资本的组织性进一步细化而来的管理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9]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双重性质:管理性质与剥削性质。管理作为一种复杂劳动,需要远高于工人普通劳动的成本,同时也创造远高于工人普通剩余劳动成果的利润,因此具有生产倍增器的重要功能。这一经典论述为我们超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束缚,解放思想从而充分肯定、发挥资本的管理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5]。这一政策规定只有取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性支持,才能名正言顺,也才能达到现实需求与伦理根据的统一。
三、马克思对资本文明面之三的审视:传播的扩大化与世界历史的形成
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自觉地用“世界历史”范畴来概括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发展态势。《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进一步阐发了资本主义发展终结了局域性历史、开辟出世界性历史的趋势。不过,上述两部著作还主要是以历史发展一般规律推演的方式来进行论证,而在《资本论》文献群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得到了最为深入细致的经济学阐释——“资本传播文明”的阐释。
资本对文明的传播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像十字军东征、郑和下西洋等或战争或和平的古代文明传播形式,其广度深度都是无法与资本同日而语的。不仅如此,传统的文明传播模式总是外在于生产方式本身的(如鉴真东渡或郑和下西洋都不是农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使然),而资本的文明传播模式则不然,“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2],“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所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2]。这是因为,“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3]。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文明交往则是派生性的实践活动;而在资本主导社会生产的历史阶段,二者合二为一,因此使得文明传导变成了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本身。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资本主义早期的殖民战争与奴隶贸易,其血淋淋的暴力活动总还是临时性的,资本扩张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和平交换的方式来出售商品,获取商业利润。在此过程中,流通时间越长、资金周转越慢,剩余价值获得就越少,因此资本的利益驱使资本家努力发展交通和运输。不仅如此,为了加快交换、缩短流通时间,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信贷、通信、网络也迅速发展起来。现代商业、现代信用、现代通信、现代传媒等作为文明传播的主要渠道,都是资本增值冲动的产物。
马克思概括道:“创造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就其对我们的现实意义而言,资本开拓市场、传播文明的趋向本是资本出于自利目的的活动(尤其是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实力优势所进行的剥削活动),但同时却为落后国家打开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其一,资本主义大工业彻底战胜了封建生产形式,从而使得任何民族要想继续维持自然经济都变得不可能。这就为野蛮的、培养依附性人格的、因循守旧的社会形态冲破既有牢笼打开了历史缺口。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是被迫卷入世界历史,那么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则是主动融入世界历史。这里需要厘清的一点就是,如何以历史形态的宏观视野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的计划经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即不能以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也不能以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发展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的计划经济,在“一穷二白”、外敌封锁的困境下集中力量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体系,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至关重要的战略抉择。同时,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延伸了的自然经济,即将传统家庭生产的自给自足扩展到一个国家,所以从长远来看,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生产效率方面、公民主体性培育与创造性发挥方面、普遍交往与文明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制度性桎梏。从改革开放前30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转向改革开放后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前者从历史合理性向历史片面性转变的趋势使然,也就是资本文明价值日益凸显的时代特点使然。
其二,资本在世界历史舞台所创造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为后发国家直接站在文明的前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制度资源与文化资源[10]。资本传播的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其中既包含适合各个落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包含西方国家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立场。如何趋利避害、去伪存真,是考验发展中国家智慧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我国来说,首要的是汲取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5]在此基础上,要辩证地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资本文明之间的张力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文明之间的张力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不应是计划模式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技术手段的外在相加,而应当是在各个方面都能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作用,在高度现代化的历史阶梯之上再来建设高于资本文明的新型文明。总之,对资本文明的深刻认识和自觉发挥,乃是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进而超越现代化的逻辑基点。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6]贾丽民.反思达致真理:马克思《资本论》的思维方式意涵[J].学习与实践,2013,(4):120—126.
[7]孔扬,姜大云《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的枢纽地位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3):37—42.
[8]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孔扬,姜大云.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的真实关系——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三次运用来看[J].长白学刊,2013,(1):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