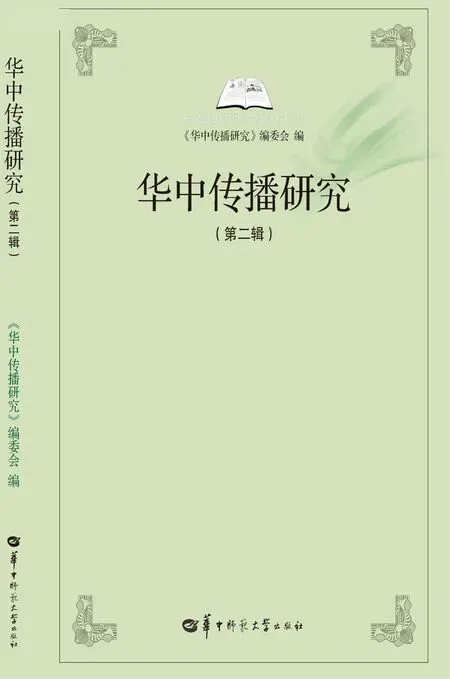经营伦理在媒介责任意识中的地位厘定
—— 由我国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缘起
2015-03-27江作苏刘文军
江作苏 刘文军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媒介伦理】
经营伦理在媒介责任意识中的地位厘定
—— 由我国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缘起
江作苏 刘文军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分析全国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可以发现媒体有讳谈经营责任的倾向。梳理文本内容可见,媒体讳谈经营责任的表层原因在于媒体的“道德神话”,而深层原因在于,当前的媒介属性规制环境下,媒体存在对经营功能的某种歧见及由此产生的不完整的媒体社会责任观。改变媒体讳谈经营责任现象的出路在于承认经营和责任形成同心圆结构,前者是后者的内核,同时增加媒体社会责任中的多元选项,重置媒体经营功能和经营责任的地位。但要避免矫枉过正而走向媒体的“非道德神话”,要实现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两者的融合。
经营责任 社会责任报告 道德神话 媒体功能
实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是我国对媒体实施现代化管理的新措施,也是我国普遍要求大型经济组织实施社会责任报告制的合乎逻辑的全覆盖。继2014年首次11家试点实施之后,2015年5月12日第二批试点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对外发布。经中国记者协会、地方新闻道德委员会以及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组织评议,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社等28家媒体对自身在2014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了报告并予以公开披露[1]。与上年首批试点的11家媒体相比,第二批试点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在“社会责任”总体框架下,各自报告了若干子项目:履行正确引导责任、提供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繁荣发展文化责任、遵守职业规范责任、安全刊播责任、合法经营责任、保障新闻从业人员权益责任等情况。
梳理这两批试点媒体所提交的38份报告,可明显发现:在报告所呈现的因子中,自我彰显成就因子多、自显社会优越地位因子多,而作为国有经济实体的媒介,本该报告的充要因子之一——经营责任的比例少之又少。从社会角度考量,这种仅仅强调媒体作为“道德人”的“道德神话”,并不能作为媒体忽视经营责任的理由以及对经营作为社会责任充要条件的冲销。
一、讳谈经营责任:由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得出的分析
关于2013年和2014年两批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分析首先对38份报告中出现“经营”一词的次数进行了统计,形成“经营”词频统计表,具体情况见表1:
续表
由表1可知,在2013年的11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中,《经济日报》发布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出现“经营”的频率最高,为1.273 07‰;而新华网发布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出现“经营”的频率最低,为0.071 94‰。在2014年的27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中,《贵州日报》发布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出现“经营”的频率最高,为2.018 3‰;而《陕西日报》和《河南日报》发布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出现“经营”的频率为0。由频率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来看,“经营”在两批试点媒体中占据最高值的《贵州日报》的报告中出现的频率也不到3‰;而《陕西日报》和《河南日报》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更是闭口不提“经营”。
同时纵向对比两个年份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可以发现:首先从两次发布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的媒体来说,《中国青年报》、人民网、新华网、《齐鲁晚报》、《河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以及《解放日报》7家媒体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经营”出现的频率相较上一年有所增长;但《经济日报》、浙江卫视、中央电视台以及湖北日报传媒集团4家媒体相应的指数则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所有社会责任报告中“经营”出现频率的最高值为2.0183‰(《贵州日报》媒体社会责任报告)高于2013年所有社会责任报告中“经营”出现频率的最高值1.273 07‰(《经济日报》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但2013年未出现频率为0的状况却在2014年两次出现(《陕西日报》和《河南日报》)。
仅仅凭借对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统计“经营”出现的频率并进行对比分析,从逻辑的角度来讲不足以充分说明各家媒体在媒体社会责任总体格局中对待经营责任的态度,但从统计学与关注度的关联角度来看,却可以部分反映各家媒体潜意识里对待经营责任的态度:各家媒体在撰写社会责任报告的过程中,媒体的集体无意识会影响执笔者的个人意识,执笔者在媒体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进行遣词造句,媒体以及执笔者认为重要内容的书写篇幅自然要长于非重要内容的书写篇幅。因此根据对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的考察,相比较其他关键词,“经营”出现的频率过低,有被媒体回避之嫌。并且,这些社会责任报告中出现的“经营”字眼多与“合法”等字眼结合在一起使用,主要用来强调“合法”,以此来凸显社会责任意识;而这些出现的“经营”字眼也主要涉及“管理”层面,而无意指向盈利。因此,媒体在有意或无意回避经营责任,这一回避是从侧面强化媒体“道德神话”的基因。
二、媒体“道德神话”:媒体讳谈经营责任的表层病因
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普遍淡化经营责任,这与媒体“道德神话”本位息息相关。媒体“道德神话”同理于“企业的道德性神话”,后者是指企业不把利润作为组织的首要目标,而遵从道德伦理去从事组织经营活动。“企业的道德性神话”是“企业的非道德性神话”的反面,后者认为企业的唯一主旨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经济利益,其所有行为完全是经济的,与伦理道德无关。同理,媒体“道德神话”将媒体社会责任当作媒体的主要存在价值,而所指的社会责任却不包括经营责任或经济责任,因此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讳谈经营责任实则是不自觉地将媒体置于“道德神话”的境地。
1992年,我国新闻传媒领域由上而下推动的改革确立了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新闻事业既属于上层建筑,又属于信息产业。并据此确立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经营管理思路,部分新闻媒体,特别是出版系统的媒体自此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造。改造之后的新闻传媒业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发挥宣传功效的同时,努力通过经营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直到当下,新闻传媒业迅猛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喻国明主编的《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4)》统计分析指出:“2012年全国传媒业总收入为5 793.7亿元,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40.33%,创下2006年以来最大增幅。”[2]相关数据显示,新闻传媒业经济体量大,并且增长迅速,在信息社会、大数据时代以及“互联网+”背景下尤盛,成为第三产业中具有支撑性的行业。
新闻传媒业获得了“企业管理”的通行证,并且持着这张通行证一路高歌猛进,“2014年全年传媒产业总值达11 361.8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万亿大关,较上年同比增长15.8%”[3],“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已然成为新闻传媒业的一体两面,那么作为“企业”的新闻传媒业就要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并遵守企业伦理规范。企业伦理产生于20世纪中叶前期西方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工商业出现一系列经营丑闻的背景下,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形成企业伦理的三个主要派别:“一是以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利润学派,他们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像自然界中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适者’们的正常行为;二是以弗兰奇为代表的伦理学派,主张伦理先于利润,企业在具有法人地位的同时,也具有道德人格;三是以S.P.塞西为代表的调和派,主张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范畴中同时包含着利润目标和伦理目标。”[4]
塞西所代表的调和派更为理性地面对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努力追求利润和伦理的平衡,强调企业同时具备“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双重身份。新闻传媒业所具备的双重属性同样驱使着自身走向利润和伦理两难选择的交叉路口,“责任”作为伦理的关键范畴,被新闻传媒业所重视并发布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在我们看来正当其时并乐见其成,但通过以上对38份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笔者又忧心忡忡:社会责任报告讳谈经营责任是对新闻传媒业“经济人”身份的否定,而着力凸显自身的“道德人”身份则会陷入媒体“道德神话”的陷阱。反之亦然,媒体“道德神话”亲近“道德人”而疏远“经济人”,从而导致新闻传媒业失去均衡的自我认知,进而回避在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中谈论经营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媒体“道德神话”是新闻传媒业讳谈经营责任的动因,而新闻传媒业讳谈经营责任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媒体社会功能:媒体讳谈经营责任的深层病理
新闻传播学者在谈论媒体社会功能的过程中,大多回避了媒体的经济功能,虽然经济功能是当下媒体不容忽视的功能之一,学界、业界对此心知肚明。但我国学界、业界在谈论媒体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更多地关注媒体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因此媒体经济功能被忽视的同时,媒体被更多地要求承担起政治组织和宣传以及文化培养和传播等方面的功能。在此背景下,当谈论媒体社会责任的时候,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自然压倒甚至是淹没经济功能。而这种对媒体经济功能的忽视,直接影响学界、业界对新闻传媒业社会责任的认定,两者共同导致媒体讳谈经营责任的病症。
(一)媒体社会功能缺乏对经济功能的重视
1948年,H.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最早概括了传播的社会功能。他认为,传播主要具备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以及社会遗产传承功能。1959年,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中继承了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提出“四功能说”,即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以及提供娱乐。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则更为强调大众传播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社会规范强制功能以及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三项功能。以上三种传播社会功能的概括和分类,均着眼于传播的政治和文化功能,甚至是更大层面上的社会功能,却鲜见媒体的经济功能被重点关注。鲜有的例外是1982年W.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一书中,将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以及一般社会功能一起归为大众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他认为:“采用机械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参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宏大的知识产业。”[5]施拉姆所谓的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包括经济信息的收集整理、报道和解释、制定经济政策以及活跃和管理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开创了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使得新闻传媒业本身成为知识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施拉姆提出大众传播具有经济功能的这一远见卓识早已为新闻传媒业的迅猛发展所证实。
虽然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早有洞察,但当学界、业界在谈到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的时候,传播的经济功能仍然鲜被提及,从笔者根据关键词检索获得的相关论文可以佐证这一点。思考这种现象,我们不妨认为,拉斯韦尔、赖特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早期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探讨已经形成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对后来者的研究和表述形成压力,导致后来者的表述跳不出前人的“窠臼”;或者说前人早期的探讨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左右了后来者的无意识,虽然后来者否认这种影响的功效,但这种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例如在我国,由于苏联媒体计划模式的影响,媒体经济功能和经营责任更是长期被弱化到几乎为零的地步。
因此,从传播的社会功能探讨之初,直到当下信息社会背景下学者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深化和发展,新闻传媒业的经济功能始终只是自己“鞋底上的洞”:自身明知,却不愿道与他人。学界、业界忽视或者讳谈新闻传媒业的经济功能,那么讳谈经营责任则在情理之中。虽然因果关系明确,但还是应更为明晰地理清忽视新闻传媒业的经济功能、讳谈其经营责任以及媒体社会责任之间的逻辑。
(二)媒体社会功能决定了媒体社会责任观
能力往往和责任相对应:具备何种能力,则被要求承担何种责任。媒体自身所具备的社会功能要求媒体承担对应的责任,学界、业界对传播经济功能的忽视导致新闻传媒业被“免除”了经营责任。中西媒体社会责任论的发展演变足以佐证这一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奉行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背景下,美国各个行业纷纷步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闻传媒业概莫能外。随着媒体垄断在20世纪前40年里加剧,时代公司的亨利·R.卢斯在1942年12月建议罗伯特·M.哈钦斯对新闻自由的现状和前景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在1947年发布,即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报告根据一个自由社会的要求,对满足这一要求的新闻传播业责任进行了梳理: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平台、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以及充分接触当日消息[6]。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对新闻传媒业的责任要求只字未提“经营”,或可能是因为该报告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新闻传媒业过度经营而造成垄断的局面,或可能是该报告的发布早于学界对传播的社会功能的探讨,更不用说施拉姆对传播的经济功能的发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的奠基之作,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新闻传播业的经营责任,为此后媒体社会责任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基调,但正如上文所述,这一基调是基础也是囚笼。
反观国内,晚清以来中国媒体社会责任观的演变历程显示,新闻传媒业经营责任同样在中国的语境中被忽视[7]。从1839年林则徐创办《澳门新闻纸》并认识到“报纸有利于国事”,到社会启蒙者寄希望于报纸能够开启民智进而实现自身的抱负,到民国时期报纸成为思想启蒙的阵地以及舆论监督的利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肩负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宣传的重任,再到“文革”时期媒体的社会责任观发生重大转变,晚清以来的媒体社会责任观强调媒体的政治和文化作用,鲜有提及报纸的经济作用,改革开放之后媒体社会责任观才获得多元化发展。
通过考察媒体的社会功能以及中外媒体社会责任观,笔者发现,中外媒体的社会责任观都由其社会功能所决定,因为缺乏对新闻传媒业经济功能的认知,或者有意回避谈论媒体的经济功能,导致学界、业界忽视或者讳谈媒体的经营责任。对媒体社会功能的认知决定对媒体社会责任观的认知,两者合谋完成了对经营责任的“绞杀”。
四、同心圆结构:媒体经营和社会责任两者关系的建立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传播学界从伦理角度对媒介的经济功能重新进行了思考。美国媒介伦理学家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在《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一书中,将媒介的功能重新定义为四个功能,即新闻、广告说服力、公共关系与劝服、娱乐。中国学者陈昌凤将之解读如下:劝服即广告,呈现即公关,并认为克里斯琴斯在该书中“对报道(新闻)、劝服(广告)、呈现(公共关系)和娱乐四大功能中的代表性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8]。广告及公关都具有经济功能的特性,在实践中都需要遵从媒介伦理。
经济与责任两者孰轻孰重,自古就是中外伦理学家思考的永恒话题。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专著《国富论》中阐述了“经济人”的利己性,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强调了“道德人”行为的利他性。两者的矛盾性构成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这一问题困扰了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但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需要通过投资和生产才能获得利润,“经济人”的投资和生产行为却又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因此,伦理学家宋希仁在分析亚当·斯密的观点之后认为,“在斯密看来,利己和同情是人性的两个方面;‘经济人’受自私利己本性驱动,‘道德人’受同情仁爱本性驱动;利己心既是人性中的主要倾向,也是道德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没有人的自私性,就无所谓人的道德性;没有人的同情性,就不可能有道德”[9]。按照斯密的观点,“经济人”和“道德人”不存在冲突,反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斯宾塞,他认为,利己和利他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消耗生命力,但利他的行为必须以个体本身具有足够的生命力量为前提,否则就谈不上利他。因此,“斯宾塞的结论是:绝对利他主义是自欺欺人。只为自己活着是错误的,只为别人活着也是错误的。和解是唯一的可能性,即为自己和别人活着”[10]。
根据斯密和斯宾塞的观点,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仅仅是强调社会责任,而回避经济责任,这是不公正的行为。因为行为的公正既包括利己,也包括利他。并且在斯宾塞看来,媒体唯独强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不顾及自身的经济利益,媒体这种绝对的利他主义是自欺欺人。斯密和斯宾塞致力于协调好“经济人”和“道德人”以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关系,辩证地看待两者从而消除二元对立。中国学者程恩富则提出“新经济人”的概念,对斯密的“经济人”概念进行了深化和更新。“新经济人”概念意指“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11]。“新经济人”概念强调了利他对于利己的益处,从而丰富了“经济人”和“道德人”两者的关系。
媒体经营是一种利己行为,只有通过良好的经营管理,媒体才能够在市场经济中存活下来,凸显自己强的一面;媒体社会责任是一种利他行为,因此,媒体又需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展现自身善的一面。利己和利他、经济和责任、“经济人”和“道德人”以及强和善,这些二元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冲突,但它们实则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形成一个同心圆结构:利己、经济、“经济人”以及强作为内圆是这一同心圆结构的核心部分;而利他、责任、“道德人”以及善是这一同心圆结构的外围部分。同心圆结构必须以内核为基础,去支撑外围,同时内核是外围的应有之义,是形成外围的充要条件。科斯洛夫斯基用“经济伦理学”的概念来阐释最强与最好的差异性与同一整体性[12],认为经营与责任是有区别的,但两者是一个整体。因此,媒体必须认清自身经营和责任组成的同心圆结构,以经营为核心,在强调经营责任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去谈论社会责任。
五、回归多元社会责任:改变媒体讳谈经营的社会责任意识
媒体只谈政治、文化等责任,而讳谈经营责任,同理于只谈“责任”不谈“盈利”的企业,是犯了“道德神话”的病。媒体“道德神话”的后果是片面注重媒体的政治和文化责任,而不利于媒体在自由的市场中竞争。虽然中外媒体生态中不乏媒体间竞争,但媒体的正当盈利是媒体作为经济体的正当追求,没有理由回避和遮掩。
由上述分析可知,媒体“道德神话”的病灶在于忽视媒体的经济功能,因而必须重提施拉姆提出的媒体的经济功能,虽然这一前提已经在当下社会不言而喻。作为具备经济功能的经济体媒体可以借鉴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论,来医治自身的“道德神话”。媒体具有事业和企业的双重属性,讳谈经营责任是强调其事业属性而忽视其企业属性,而医治媒体“道德神话”的“药”则是回归多元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时间早于媒体社会责任。1916年,芝加哥大学的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在《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媒体社会责任一样,因研究者的视角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模糊且多样。经过分析归类,存在着两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独立责任说和综合责任说。前者是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认为企业除了履行传统的经济责任,还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对立;而后者则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综合责任,也可以看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责任观,而这种多元责任观正是犯了“道德神话”之病的媒体所需要寻求的药方。
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社会责任观以美国著名管理学者阿基·B.卡罗尔为代表。克拉克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但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两者孰轻孰重又成为困扰管理学者的难题。卡罗尔把两者进行协调,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在经济、法律、伦理和自行裁量(慈善)上的期望”[13],并据此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他认为,“企业的慈善责任构成金字塔形结构,经济责任是基础并且比例最大,法律的、伦理的以及自行裁量的责任依此递减”[14]。由此可见,卡罗尔最为重视企业的经济责任,因为企业最本初的目的就是盈利,而“经济责任也是社会对企业的期望所在”[15]。
虽然媒体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但媒体具备企业属性,那么媒体就可以借鉴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社会责任观,将经济责任或者经营责任纳入自身应该遵守的责任范畴,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应该将经营责任看作自身社会责任的核心和基础。讳谈经营,伤害媒体的竞争力和自身利益;而讳谈经营责任,则有损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在强调媒体凸显经营责任的同时,也要警惕媒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过度强调经营、经济功能以及经济责任,而冷落媒体的社会责任,否则治好了媒体的“道德神话”之病,却患上了媒体的“非道德神话”之病。只有平衡好经营责任和社会责任,才能走上康德所谓的通往善的中庸之道。
人民日报社旗下的人民网具有强制性责任,因此与《人民日报》一样,同属党媒性质,但人民网的经营意识和经营责任意识强烈。例如,《人民网社会责任报告(2014年)》披露了其收入和增长情况:“2014年前三季度人民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0.0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2.52%;净利润2.4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3.30%。”[16]仔细考量人民网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笔者梳理了报告整体框架及部分内容,详见表2:
由表2可知,人民网的社会责任报告将履行遵守职业规范责任和履行安全刊播责任放在一起,但其增加了在规定之外的“履行上市公司责任”的内容,并就此具体做出详尽的报告。人民网此举凸显了自身的“经济人”身份,在谈论社会责任的同时,努力实现自身“道德人”与“经济人”双重身份的和谐共处。
结 语
综观38份媒体社会责任报告,笔者认为,媒体社会责任报告要减少无益的自由裁量性,需要完善媒体社会责任,其中包括经济责任;而讳谈经营责任广泛存在于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中,这种系统性缺失说明媒体要进行系统性改革,使得媒体真正遵照市场规律及股份制度合理运行。媒体讳谈经营责任源于对媒体经营功能的回避,但当下股市巨震和IPO暂停影响媒体融资,传统主业经营趋紧,媒体普遍资金饥渴。《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指出:“46家报刊出版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与盈利总额分别降低1.0% 与16.0%,报业集团中有17家营业利润出现亏损,较2013年增加2家。表明传统报刊出版面临严峻挑战。”[17]在这种态势下,媒体经营的重要性更为凸显,更应重拾对媒体经济功能和经营责任的认知。特别是在媒体转型时期,改变讳谈经营责任的态度,强化经营意识,是媒体转型成功的必备条件。
注释:
[1]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zgjx/zt/2014mtzrbg/ index.htm.
[2]喻国明主编:《中国传媒发展指数报告(20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3]崔保国、何丹媚:《互联网驱动传媒产业增长——2014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中国报业》2015年第6期(上)。
[4]叶陈刚主编:《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5][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55页。
[6][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展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15页。
[7]查英:《晚清以来中国传媒社会责任观演变历程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8]陈昌凤:《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伦理:从专业伦理向公民道德拓展》,引自[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等著:《媒介伦理:案例与道德推理(第九版)》,孙有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代译序第2页。
[9]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4页。
[10]宋希仁主编:《西方伦理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7页。
[11]高建国:《人性经济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页。
[12][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13]叶陈刚主编:《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14]叶陈刚主编:《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15]周祖成编著:《企业伦理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16]《人民网社会责任报告(2014年)》。(2015年5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 zgjx/2015-05/12/c_134218608.htm.
[17]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节选),《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9期。
The Status Definition of Management Ethics in the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Medias —Originated from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of 38 Domestic Med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