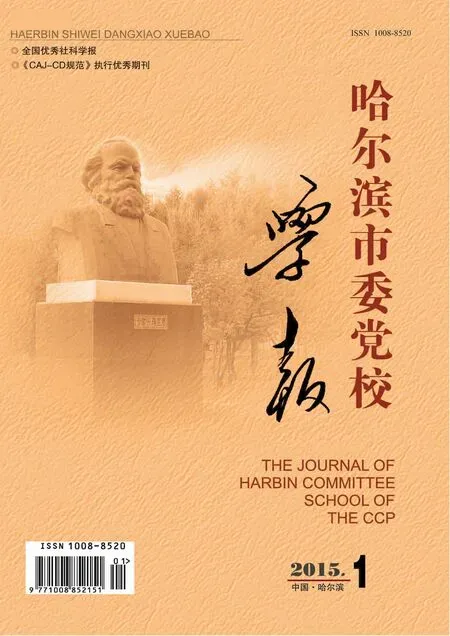交往视域中的公民与中国大学公民教育
2015-03-27宋晶
宋 晶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院,河南商丘476100)
“公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文明。随着城邦的没落,公民这一公共身份也屈从于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之下,成为“教民”或“臣民”。近代启蒙思想点燃了“自由之火”,将“为权利而战”的呼声付诸行动,由此掀开了公民的新篇章,公民身份由国家法律予以确认。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是指由法律确认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籍,公民享有该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与承担相应的义务。公民归属于特定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致力于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公民社会生活,然而对私人生活的关注使得公民的政治热情日渐低迷。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对私人领域的侵蚀唤醒了人们的公共意识,“公民的回归”成为当代最主要的政治话语。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学家马歇尔在剑桥大学所作的关于“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的著名演讲以及随后出版的同名经典著作,激发了人们对公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欧盟的扩张、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也使传统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单一公民身份模式遭受严峻的挑战,形形色色的公民身份(如性别公民、生态公民、移民公民、差异公民、多文化公民、世界公民等)纷纷涌现,“公民”这一概念已经在全球拓展开来。随着“公民”概念的全面拓展,公民教育成为当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培养“好公民”成为教育的旨归。
一、交往视域中的公民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试图以主体间的交往在传统的社会二分法(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中建构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为当代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观念和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虽然并没有关于“公民”概念的直接的、系统的论述,但“公民”一词频繁出现于其著作中,成为其话语民主理论的关键概念。从交往行动理论中匿名的言说者和听者以及主体间关系的建构,到话语民主理论中频繁出现的双重角色集于一身的公民这种特殊身份,主体间性转换为以公民身份建构的特殊的主体性。依据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交往视域中的公民具有以下特质:
1.理想交往共同体中的公民。哈贝马斯认为,启蒙理性彰显个体自由使公民社会日益远离政治国家,也使公民逐渐淡出传统的公共领域——政治国家。公民作为共同体成员身份由政治国家予以确认,但并不把政治共同体作为生活的中心,而是在公民社会中确定存在的意义。作为“信念的储备库”,生活世界是非主体性、隐含的、潜在的、前反思的,是哈贝马斯为重建公民的公共性寻获的另一公共空间。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与公民社会、政治国家同时并存的、非政治非经济的公共生活空间,现代社会公民缺失的公共性可以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重新寻获。“交往行为者不可能走出其生活世界境域,他们本身作为阐释者凭借言语行为属于生活世界。”[1]
2.作为能动的交往行动者的公民。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连通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个人与国家,其动力源于以主体间性为特质的交往理性,交往视域并不否定主体而是要以这种间性重构主体身份。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性是一种动态的“你—我”关系,从我出发,致力于你我的同一性。公民是带着私利诉求进入公共交往中的,公民身份确证的意义在于通过交往实践将私利统合于公益中,并通过政治这道阀门予以建制来确证其有效性。区别于关注个体权利的消极公民与以权力建构实现“共同善”的积极公民,交往视域中的公民是能动的交往行动者。哈贝马斯将重心从传统的国家移至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公共领域,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行动和商谈行为实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互动与融合,其中公民则担当了统合人权与人民主权、权利与权力、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重任。
3.具有交往资质的公民。哈贝马斯将交往资质引入公民品质,认为交往资质是掌握一般交往规则的能力,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前提条件,它要求交往主体必须是自主的、独立的、自由的、有语言和行动能力的自律主体。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资质是学得的。一方面,这种学习机制以交往建构的主体间性实现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即由自我经由他我(主体间)回归自我(共在的他我),主体意识得以提升。另一方面,这种学习机制使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融合程度在交往视域中不断加深,社会逐渐趋向合理化。“恰恰是个体系统,才是个体发生学意义上的学习过程的承担者。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只有社会性主体才能从事学习。但是,社会系统借助于社会性主体的学习能力,能够形成新的结构,以解决威胁自己继续存在的问题。在这个程度内,社会进化意义上的学习过程依赖于自己所属的个体的资质。反过来,个体又要求他们的资质不是作为孤立的单位,而要成长并进入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系统。”[2]
二、交往实践是中国大学公民教育的新形式
哈贝马斯为中国大学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公共交往为公民品质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平台。中国大学公民教育从以下方面在交往实践中展开:
1.拓展公民的公共生活空间。现代西方社会的公民主要关注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利益得失,而政治国家却主要着眼于公共生活的体制化和政治权威的确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对立使得公共生活的意义无法凸显。哈贝马斯主张重回生活世界寻获公共生活的意义并与当代公民社会的发展形成对接,认为当代公民教育的领域应拓展到政治与经济的建制之外的日常公共交往中。区别于以血缘、地域为纽带的封闭的私人交往,公共交往以其开放性渐渐成为现代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交往“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人们作为私人来到一起形成公众。……他们可以自由地集会和组合,并在自由地表达和公布他们的意见的状态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他们是作为一个公众来行动的”[3]。日常的公共交往作为公民教育的领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对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权益诉求,日常的公共交往空间确保关注此事项的人的参与,在平等的交往关系中通过论辩达成共识,以共识的公共意义吸纳更多人的关注与参与,在开放、平等、自由的氛围中将公共交往拓展开来,公民品质也会随着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得以提升。
2.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传统公民教育是建立在主体—客体关系上的单向的受动教育。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的公民不仅是公民教育的对象,更是公民教育的主体。当代公民教育不仅建构主客体关系、呈现主体间性,而且以间性结构培育主体意识。公民作为能动的交往行动者以具备主体意识为前提,公民品格是一种实践品格,“公民必须能够去做,而不是仅仅能够成为公民”[4]。公民教育应该是一种以公共交往为基础的实践教育,是以主体间在公共交往中实现的,并非单一主体掌控的政治权力。当代公民教育应改变以往单向的说教模式,通过公共生活实践提升公民的主体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就开始提倡“服务学习”的公共参与理念,主张公民教育应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服务;1998年英国教育部门颁布的《科瑞克报告》也认为公共参与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基础,学校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社区的公共生活,锻炼公民品质。
3.提升公民的交往资质。公民教育应在公共交往中培育公民的公共性、主体性,公共交往以提升公民的交往资质为前提,当代公民教育应将智育、德育与心育结合起来提升公民的交往资质。智育应强调两方面的内容:一为语言知识。当代公民教育应加强语言规则和语言技巧的学习。二为背景知识。背景知识的内化程度影响着交往的顺利进行,公民教育应努力促成这种内化并强调通识教育的意义。从德育的层面看,公民教育历来重视对公民的道德教育,但单向、被动的道德教育模式充其量只能让公民掌握道德知识,而不能内化为公民的道德素质。当代公民教育应实现德育由知识教育转向实践教育的转型。心育应注重三个环节:一是健全的心理,心理的健全与否直接关联着交往的进行。真诚性作为交往行动的一个有效条件连通交往与人的主观世界,要求所有交往行动者动机纯正,除了本着追求理解共识的目的而不能有其他目的。二是反思意识。交往的实质是以论辩方式实现的主体间性反思,自觉的反思意识是交往的前提。三是耐挫能力。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会面对异议的风险,公民教育应包含增强主体耐挫能力。
三、交往视域中的中国大学公民教育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的生活世界应是以公民权利平等为基础而建立的多元社会。然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传统社会描绘成“差序格局”的“礼俗社会”。“差序格局”是指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为动力、逐渐向外推移的人际关系格局。“礼俗社会”是指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较少、以家庭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的导控力量在于“礼俗”(传统习俗)的内化,传统习俗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社会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公共生活与私生活两无的独特格局[5]。在这种“差序格局”和“礼俗社会”中,人的存在形态只有子民、臣民而无公民。教育侧重于以义务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强调礼俗的内化。义务本位的传统伦理强调培育社会成员的臣民意识,以利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社会控制。新中国将民众从传统的等级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法律确定了公民身份,并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但“重德轻刑”的传统思想阻碍了人们对这种法律身份的认识,公民教育没有被提上日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教育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又被视为生产力,成为开发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本的工具,公民教育强调社会成员以增产创收为目标积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这两类公民教育都是工具型教育,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实效,公民的公共意识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以契约精神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市场经济孕育了能动的市场主体,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但市场经济催生的能动主体也带来了公共道德冷漠、责任感缺失等新问题(如“三鹿奶粉事件”、“瘦肉精”、“地沟油”以及“小悦悦事件”)。人成为只顾自己的“私”民,而非社会的“公”民。
大学是公民教育的主阵地,年龄的特征使大学生真正获得公民的身份(选举权),因此,培养大学生的公民品格应成为大学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大学公民教育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品德教育,以思想道德修养课中的爱国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二是政治教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三是法治教育,以法律基础课中的法律常识为主要内容。虽然教育内容比较完备,但建立在主—客关系上的单向的课堂教学模式却使教育内容只停留在书本和课堂中,无法进入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公共交往应成为中国大学公民教育的关键。具体包括以下途径:
1.多渠道营造大学生的公共交往氛围。大学的公共交往主要包括校内与校外两个部分。中国大学公民教育的实施,一方面要充分运用校内的公共交往,主要包括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学生社团。学生社团是学生基于共同兴趣或目标组成的社团,采取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方式来追求公共目标。据调查,90%以上的学生都参与了社团活动,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多。但当前的学生社团并没有形成理想的公共交往氛围。学生加入社团的目的主要是结交朋友、锻炼能力,对社团的公共目的并不明确。中国大学公民教育应努力营造社团的公共交往氛围,明晰社团的公共目标并形成认同,在社团活动中加入更多的公共话题,形成交流的氛围,通过对学校公益的关注将教师与学校管理者纳入社团中。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校外的公共交往,主要包括社区和社会两个渠道。通过服务型学生社团或学校将公共交往领域拓展到离学校最近的社会公共交往空间——社区中;通过网络、媒体等将大学生与其他关注公共问题的社会成员连通起来,拓展校外的公共交往。
2.在公共参与中培育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中国大学公民教育应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公共交往,主要包括:一是论辩式参与。当前中国大学教育非常重视论辩,如课堂上的讨论、课下的各类辩论赛,但论辩的主题更多是知识性的,缺少蕴含民主精神和公共精神的公共性话题,不利于公民教育的开展。论辩是主体反思在交往的主体间性结构中的呈现,有利于交往行动者主体意识和公共理性的养成。学校应组织或允许学生自发地组织更多自由、民主的公共辩论式交往活动,如对学校的公共环境、设施、学习乃至餐饮等公共问题进行公开的民主辩论和交流。在辩论过程中,学生可以就学校亟须改善的公共问题进行申诉,争取自身的权利,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权利救济,对不合理的制度展开抗辩或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学校对学生的申诉、抗辩和建议给予公开回应。二是社团式参与。社团式参与并不仅仅指加入社团,而且要求大学生通过积极参与社团以公共目标为目的的活动提升主体意识和公共理性。三是服务式参与。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的卫生、交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公共活动或作为志愿者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服务社会。大学生以服务社区、服务社会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交往活动中,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3.充分利用各种教育手段提升大学生的交往资质。交往资质不仅是公民的交往能力,更是一种综合性的公民品格。中国大学公民教育应重视智育、德育、心育三种教育手段在提升大学生的交往资质方面的作用。智育方面应加强大学通识课程的体系构建,以博学与精专相统一为目标,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整合起来。具体而言,将通识课按性质设置为必修课或选修课,既满足大学生的需要又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对不同专业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按类设置通识课程,如文科专业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理科则适当增加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德育方面应将课程设置与德育实践结合起来,适当增加实践学时,鼓励学生关注社会公德、法律问题,并作为实践材料纳入课程教学中。心育方面应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是通过开设心理常识课程或将心理常识纳入其他相关课程中为心育做知识铺垫;二是通过心理调查让大学生对自身的心理问题进行自查,防患于未然;三是通过心理热线、心理咨询使大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得到及时诊治。
公民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观念,将其升华为现代社会公民的责任意识,实现公民的权责统一是当代中国大学公民教育的关键。
[1][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91.
[2][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59.
[3]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25-126.
[4][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M].郭忠华,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183.
[5]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整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6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