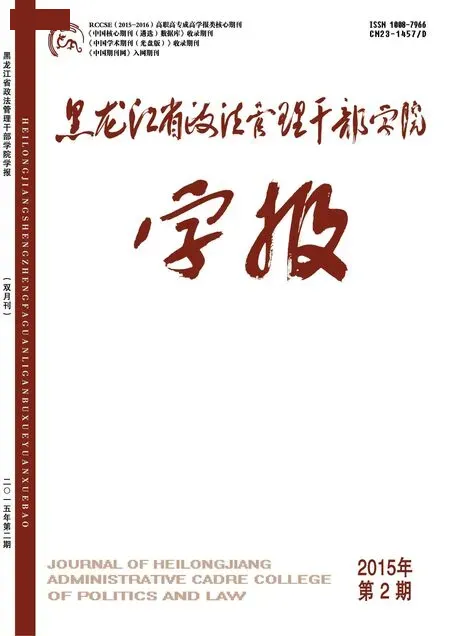司法行政权对司法独立的保障与干涉
——第三轮司法改革的展望与隐忧
2015-03-27宋振策
宋振策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司法行政权对司法独立的保障与干涉
——第三轮司法改革的展望与隐忧
宋振策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司法行政权内在隐含着对司法独立保障与干涉的双重倾向。司法行政权的配置与行使关系着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它们都不是中立的,不能做到利益无涉。因此,能否实现司法行政权的合理配置决定着第三轮司法改革的成败。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针对的仅仅是司法行政权在司法系统内部的调整与重置,这是有局限性的。我国要想彻底革除司法不独立的痼疾,应当对司法委员会模式予以借鉴。
司法行政权;司法独立;裁判权;分离
一、一个隐藏的“两难命题”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这确立了深化司法改革的目标,公布了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开启了第三轮司法改革的序幕。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本轮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路线,通过改革司法体制着力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与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前两轮司法改革不同的是,第三轮司法改革是在中共中央的推动和协调下开展的,伴随着强大的决心和动力,主要解决的是损害司法独立的两大“痼疾”: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透过现象看本质,祛除两大“痼疾”的核心在于合理配置人财物管理等司法行政权,而司法行政权内在隐含着对司法独立保障与干涉的双重倾向。如果将司法行政权完全剥离出司法系统由行政机关掌握,就无法切实、及时地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运行,甚至强化行政机关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如果将司法行政权完全纳入司法系统,又可能造成掌握司法行政权的上级司法机关或者行政管理人员权力过大,恃权专横、干预司法,也会降低司法权的运作效率;因此,就产生了一个司法行政权归谁所有的“两难命题”。如何合理划分司法行政权与裁判权的界限,能否绕开行政模式和司法模式开辟第三条道路,值得深入研究。可以说,能否实现司法行政权的合理配置、有效发挥其对司法独立的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司法独立的干涉,决定着第三轮司法改革的成败。
二、司法行政权的配置及其对司法独立的制约
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1]。要研究司法行政权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必须先从司法行政权的概念入手。司法行政权,是指以辅助和保障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为目的的行政事务权。它包括司法机关设置,司法工作人员的任免、调配、培训、管理,法律宣传,律师公证工作,司法机关及其附属机构的经费的预算和使用等方面[2]。司法行政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权,但由于司法行政权针对的是司法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的安排与管理,与司法裁判权的有效运行息息相关,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划分出明确的界限。可以明确的是,司法行政权不能参与司法裁判权在具体案件中的运作,不能干涉法官根据自己的心证依法独立地作出裁判,它的行使过程有别于司法机关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域外各国对司法行政权的配置有3种模式。一是行政模式,这种模式以法国为代表,是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模式。司法部是法国政府下设的一个负责司法人事管理的行政部门,其掌握着法官的任命、委派、临时调动、日常管理等权力,还负责司法辅助人员的招聘、任用和管理,当然也负责法院内部行政性事务的处理,例如司法经费的分配、司法人员的培训、考核等。二是司法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由大法官掌管司法行政权,其主要职责包括向英国女王提出拟任的法官名单,任命各巡回区的司法行政长官,并定期召集司法行政长官会议,决定法官的工作调动和员额增补等事项。三是多元模式,这种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由内阁和高等法院共同行使下级法院法官的人事任免权。另外,从司法经费的保障来看,世界通行的做法是单独编制司法预算,由议会讨论和批准,必要时可以再次追加经费,司法经费必须专款专用,不能被随意截留或处置,议会对司法经费的使用有监督权限。
我国司法行政权的配置最早采取的是行政模式。1954年9月2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现行的配置模式是由各级司法机关、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享司法行政权。从横向上看是由多机关分权共享的模式,从纵向上看是行政区划各级分享的模式,权力未集中于中央机关。由于我国各级权力机关的相对弱势地位,这种分散于各级政府、受制于行政命令的司法行政权配置模式实际上成为我国司法不独立的根源之一,在这种模式下司法机关承担了更多的行政性事务,裁判权中混杂了行政权,司法权很难强力排除行政干扰,封闭地独立运作。孟德斯鸠最早明确论述:“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3]这种职能分离的思想也应当贯彻到司法行政权与司法裁判权的关系上,所以司法行政权与司法裁判权的分离是基本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至于是外部分离还是内部分离则是需要另行探讨的问题。
三、司法独立的内涵解析与中国问题
司法独立是一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已经为许多国际人权文件所确认,对于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款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对司法独立的论述是:“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间接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何种理由。”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成员国司法和行政部门的功能和权力没有清楚的划分,或者行政部门能够控制和指挥司法的状况是与公约第14条第一款所要求的独立和公正的规定不相符合的;法官的任期可能对司法独立产生影响[4]。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内含着司法行政权与裁判权分离的思想。
“司法独立”一词源自西方的宪政制度,要界定西方的司法独立,必须先界定“司法”一词,西方国家的“司法”专指审判活动,而检察官隶属于行政系统,所以司法独立特指法院独立,司法权专属于法院。西方国家更加强调法官个人的独立,可以说,西方的司法独立本质上是法官独立。各个法院内部的法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法官之间没有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独立审理分配给自己的案件,不能干涉他人所审理案件的裁判结果。
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同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因为我国的司法不同于西方。将司法界定为诉讼,即国家解决纠纷、惩罚犯罪的诉讼活动,不仅在理论上有根据,而且更契合中国实际[5]。我国的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注意的是:其一,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主要强调外部独立,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其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相对意义上的,不是绝对的,不独立于党的领导(党委、政法委)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实践中,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并没有贯彻到实处,仍然停留在纸面上,司法不独立一直是我国司法体制的软肋与“肿瘤”。为了简便起见,本文着重从审判独立的角度进行论述。
(一)外部不独立——司法地方化
地方政府掌握着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分配权,导致行政干涉司法。第一,行政权过大,不受制约,且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政府财政保障,统一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院成为“地方法院”,维护的是地方利益。第二,参照公务员编制管理,法官具备行政级别,如正处级审判员、正厅级审判员等称谓。第三,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导致一些地方人大代表插手具体案件的审理。第四,地方党委、政法委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使其可能插手个案的裁判。
(二)内部不独立——司法行政化
第一,法院内部存在科层制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审判庭法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审委会专职委员)——院长,各有行政级别,院长实际上是法院的行政首长。第二,法院的人事权掌握在院长手中,存在行政化的法官任免制度。院长有审判员的提名权、助理审判员的任免权,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院长担任党组书记,实际上控制着整个法院。第三,个案裁判中存在请示汇报制度,下级法院在个案裁判作出前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并按照上级法院意见作出裁判,导致上级提前介入个案裁判,破坏了审级制度。第四,存在行政化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损害了审判组织的独立性。审判人员很难在重大案件中独立作出裁决,合议庭的裁决权仍会受到审判委员会甚至法院行政首长的制约。第五,存在行政化的案件审批制度: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分管副庭长、庭长、分管副院长和审判委员会(院长)都有一定的案件审批权限,形成了层级化的行政审批模式,导致审判组织的独立性被削弱。
四、司法行政权与裁判权分离的改革实践
(一)官方思路——“相对合理”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以下简称《框架意见》)明确了第三轮司法改革的具体思路,并在相关省份开展试点。《框架意见》确定的四大改革事项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随之而出的七个政策导向是: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等。这些改革措施直接指向长期以来广受诟病、严重戕害司法公正及司法能力的“司法行政化”和“司法地方化”两大“毒瘤”。可以说,通过对司法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管理来实现司法的“去行政化”,通过对司法机构的省以下垂直统一管理来实现司法的“去地方化”,是《框架意见》为第三轮司法改革所做的“顶层设计”。这一改革在纵向上将县、市两级的司法行政权向省级集中,这种纵向集权思路值得肯定。
但是,“顶层设计”针对的仅仅是司法行政权在司法系统内部的调整与重置,这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司法机关原来享有的司法行政权没有被剥离,原有的多机关分享司法行政权的模式总体上没有改变,仍然是一种“小修小补”。问题在于:司法机关仍然不享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限,只不过这一权限集中到了省级人民政府手中,而省级人民政府可能由此控制省级司法机关,进而控制整个行政区域的司法机关;由省级司法机关垂直统一管理人财物可能导致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加强,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被架空,省级司法机关权力过大可能造成司法擅断、司法专横,造成省级的司法割据;最高司法机关的统率作用没有凸显出来,省级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管理权限没有被明确纳入最高司法机关,司法在省级的地方化仍然存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仅使法官、检察官从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但是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司法行政权还是掌握在院长手中,负责司法行政的司法人员可能通过手中的权限干预裁判权的独立行使。另一方面,如果将司法行政权完全剥离出司法系统由司法部以及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掌握,无疑是强化了本来已经庞大臃肿、恣意妄为的行政权,使本来已经处于弱势地位的司法机关变得更为弱小,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粗糙、违宪审查机制缺乏的现状下,司法独立更加难以实现。这种左右摇摆、拖泥带水的改革思路仅仅是一种“相对合理主义”[6],而这种“相对合理主义”可能使第三轮司法改革陷入两难境地。
(二)第三条道路——司法委员会
不论司法行政权由司法机关掌握还是由行政机关掌握,都难以真正保障司法独立,却可能干涉司法独立。究其根源,司法行政权的配置与行使关系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切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它们都不是中立的,不能做到利益无涉。根据“任何人都不得担任自己案件法官”的朴素思想,必须由一个中立的中央机构或组织统一行使司法行政权,才能真正实现对司法独立的保障。事实上,第三条道路是存在的,也是被域外各国践行的,那就是由司法委员会这一中立组织掌管司法行政权。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开始设立司法委员会,执掌司法政策、司法人事、司法预算、经费保障等司法行政事务,这些尝试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推动这项改革的动因在于:若把司法行政权移交司法部等行政机关,审判独立更难保障;若将司法行政权完全交给议会,又恐司法卷入政党纷争,因此,设立一个相对独立、多方参与的委员会是合理的。之所以说是“相对独立”,是因为有些委员会虽然依托于某一机关设立,但委员来源多元、决议实行票决,可以避免受长官意志影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新一波司法改革浪潮的推动下,域外各国相继设立司法委员会执掌司法行政权,如波兰、匈牙利、葡萄牙、丹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
现实挑战和应对使我国的司法转型不得不肩负着历史补课和未来建构的双重任务[7]。我国要想彻底革除司法不独立的痼疾,应当对司法委员会模式予以借鉴。其实,本轮司法改革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就是引进司法委员会模式的良好开端,中央司改办负责人的解读是:“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代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遴选委员会由于具有广泛代表性,而自然具备了一定的中立性。以遴选委员会负责法官、检察官人事提名工作为切入点,逐步设立一个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委员会,由其掌握司法人事权、司法预算权、司法政策权等司法行政权力,该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只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平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这样做既可以将司法行政权集于中央、削弱地方干预和行政科层制,又可以强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权,贯彻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笔者真心希望遴选委员会制度能够贯彻到实处,真正实现多元性、中立性和权威性,为我国进一步引入司法委员会模式做好制度铺垫。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86.
[2]张光博.简明法学大辞典[K].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502.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6.
[4]杨宇冠.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54-255.
[5]陈光中,崔洁.司法、司法机关的中国式解读[J].中国法学,2008,(02):78.
[6]龙宗智.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1999,(02):130.
[7]胡云腾,袁春湘.转型中的司法改革与改革中的司法转型[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03):49.
[责任编辑:李 莹]
DF916.1
A
1008-7966(2015)02-0111-03
2014-10-25
宋振策(1991-),男,山东青岛人,2013级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