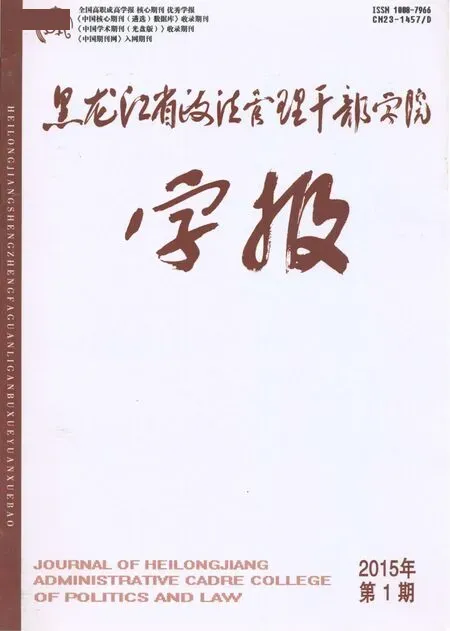论我国国际私法中权利质权设立地的认定
2015-03-26丁汉韬
丁汉韬
(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430072)
论我国国际私法中权利质权设立地的认定
丁汉韬
(武汉大学法学院,武汉430072)
权利质权,适用权利质权设立地法,是《法律适用法》中的最新规定,但是学界对权利质权设立地现有的解释仍存在着一定争议。目前质权设立地认定的最大障碍在于:识别权利质权时严格的按法院地法识别导致的适用法律的偏差,以及忽视了权利质权设立这一概念在冲突法与实体法上的区别导致的可能的逻辑循环。为了准确认定权利质权设立地这一概念,必须从比较法的层面对法院地法作广义理解,并且准确区分权利质权的设立在冲突法中的特殊含义。
权利质权;质权的设立;识别;冲突法概念
一、问题的提出
权利质权是指以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如依法可转让的各类债权或者其他权利)为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权[1]。现代社会以证券设质融资的方式甚为普遍,尤以国际贸易中商业票据的设质为最。而这种权利质权的兴起,必然带来的是相关涉外案件数量的增加,因此相关国际私法的立法也必须符合这种商业实践的要求。
我国《物权法》第223条明确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根据一般原则,一般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必须从属于它所担保的债权。但是在国际私法上,担保物权的准据法并非附属于债权的准据法。对于有形物,其担保物权也应适用担保物之所在地法。但对于权利质押担保,由于不存在一个有形的物,因而也没有对应的物之所在地,因而必须对其连结点做出特殊规定。事实上,部分国家并未将权利质权从无形财产中分离出来单独规定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而专门规定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的各国间,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尚未对权利质权形成普遍的法律适用规则[2]220。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并未对涉外的权利质权进行规定。《适用法》第一次对权利质权的冲突规则做出规定:权利质权,适用质权设立地法律。该条的适用,其关键在于确定质权设立地。但在如何界定质权设立地这一连结点存在着对立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这一规定很不明确。首先,权利质押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哪些权利可以设立质权,此时质押权是否设立尚不得而知,而且权利又是虚无缥缈的,如何判断设立地?其次,如果权利质押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质押权是否有效设立,此时如果依据第40条的规定,就是权利质权的设立适用设立地法律,这岂不是同义反复吗?质权是否有效设立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问题,本身就需要一个冲突规范来指引其准据法。”[3]也有学者认为质权设立地这一连结点具有明确性和可预见性,并将质权设立地做了如下解释:“权利质权引发的法律冲突,适用质权设立地法律,具体而言,需要登记的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指的是适用权利登记地法律;不需要登记的,指的是适用权利成立地法律。”[2]219这种解释与我国《物权法》关于权利质权的设立是相互协调的。《物权法》第224-228条明确规定了,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基金份额、股权、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应收账款等出质的,所应当采取的设立方式。因此根据条文,很容易就能确定相应的权利质权于何时、何地设立。但是,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严格按照法院地法来对权利质权的相关概念进行定性。除非将所有的涉外权利质权按照我国物权法中的权利质权的种类进行分类,才可能明确哪些是需要登记设立的,哪些是不需要的。否则,各国对于权利质权的规定各不相同,必然会出现法院地法与质权设立地法在某一权利质权是否需要登记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综合两方观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权利质权设立地是可以进行认定并指向相关准据法的。但在认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两点。第一,权利质权的设立及相关问题的定性必须结合涉外民事法律适用的特点来加以解释,而不应完全依照法院地法对所有概念进行定性;第二,应当明确冲突规则中权利质权的“设立”与实体法中权利质权的“设立”存在着差异,而不应简单的将冲突规则与实体法中的概念加以等同。
二、对权利质权设立的定性冲突
目前对于质权设立地的通常解释是,需要登记的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指的是适用权利登记地法律;不需要登记的,指的是适用权利成立地法律。但在实践中,这一概念必需要以《物权法》中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定性,才能够准确的将不同的权利质权进行归类。因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定性上的冲突。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种情形:
(一)当外国与我国就同一权利质权的设立方式规定不一致时,如何对质权设立地进行定性?例如,在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的质押上,各国立法规定的设定要件就有所不同。我国《物权法》第226条规定:以其他股权出质的,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此,质权设立地应该是登记地。但根据日本《有限公司法》,只要有当事人之间的设质合意,并转移出质权利凭证,质权就已经设立。假设,某中国公司在日本同某日本公司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质权关系。那么根据对质权设立地的不同识别标准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如果完全按照《物权法》对质权设立地进行定性,认为该股权是需要登记的权利,但实际上该权利质权却是通过交付设立的,此时质权设立地应该是登记地呢,还是交付地呢?
(二)当外国对于特定权利质权的存在第三种设立方式时,如何认定质权设立地?例如,有的国家规定对于某些权利,只要当事人达成合意即能设立质权。关于一般债权的设质《德国民法典》第1280条规定:“出质有转让合同即可移转的债权的,仅在债权人将质权的设定通知债务人时,视为有效。”该法典显然认为通知第三人是债权质权设定的成立要件之一,因而,在德国法上债权之设质不需交付债权证书[4]。这会导致该权利质权的设立可能既无交付地又无登记地。完全按照中国法对设立地进行定性,则该质权是需要登记的,但是该权利质权却是通过双方合意设立的,既不存在登记地又不存在交付地,此时如何确定设立地呢?
(三)当存在涉外权利质权的权利标的不属于《物权法》所规定的范围时,如何认定质权设立地?例如,美国可以以保险金设质,而此种设质方式,在《物权法》中并未规定。如果完全按照《物权法》对质权设立地进行定性,无法确定其是需要登记的还是需要交付的权利质权。
笔者认为:权利质权设立地的认定难题根源于,在权利质权的设立中,存在着标的、设立、效力等诸多需要考量的因素,而在这些问题的立法上,世界各国均有着较大差异,因而会产生多于其他法律关系的识别冲突。因为不仅仅是要识别哪些权利可以设质,还要判断存在着哪些设立方式、哪些权利需要以哪些方式设立方为有效。上述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严格按中国法进行定性,这一做法尽管有《法律适用法》第8条作为依据的,但在涉外民事案件,特别是权利质权中完全以《物权法》中的概念进行判断进行定性是否一定合理?二,将权利质权设立地定性为:需要登记的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指的是适用权利登记地法律;不需要登记的,指的是适用权利成立地法律。这是将一个需要进行识别的概念定义为了另一个需要进行识别的概念,因此不仅不能够对设立地进行界定,反而产生了更多需要界定的问题。
针对上述原因,笔者认为要解决质权设立中的若干定性困难,对质权设立地进行准确认定,应当做到两点。
首先,应当将权利质权设立中的若干概念根据国际社会的一般立法和实践,进行定性,而不能仅以我国法律的相关概念进行定性。因为尽管根据《法律适用法》第8条,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但作为定性依据的法院地法并非一成不变。许多学者认为对于“法院地法”应采广义的理解,应对作为定性依据的法院地法作扩张解释。仅依实体法定性存在缺陷,应依法院地的国际私法进行[5]。具体到权利质权的设立,单一地采用《物权法》作为定性依据,并没有照顾到涉外权利质权设立过程中定性问题的特殊性,容易导致实践中法官将涉外权利质权的定性与国内权利质权的定性混同。为适应国际私法关系之发达与复杂性,法院地法说必然无法避免自我膨胀,运用时应摄吸外国法,必要时,尤应改变及扩大法院地法本身之概念[6]。
其次,在解释中应当注意用语,避免需要进行二次定性的问题。质权设立地之所以会导致认定的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是一个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法律概念。因此不仅需要对范围定性,更要对连结点定性。从法学方法论上看,定性被认为是一种司法归类活动(act of juridical subsumption),亦即法学上通常所说的涵摄或归摄(Subsumption),也有学者称之为法律事实的解释[7]。德国学者拉伦茨对涵摄的界定是,将案件事实归属于一法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8]。法官将法律事实涵摄于特定法律概念的过程:一是该概念的定义为其大前提;二是经由观察所认定的结果亦即认定该特定的客体具有该定义所称之全部特征则为小前提;三是以经由涵摄所获得该客体为该概念所指称之客体之一的认识作为其推论的结果[9]。换言之,定性就是对已确认的案件事实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评价,舍弃其中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特征,对其中具有法律意义的特征加以抽象和概括,并使之类型化,从而使其与法律规范中被假定的法律构成要件具有可比性,最后将已确认的该案件事实归属到某一特定的法律构成要件中去,实则以相关的法律概念的内涵为依据,使其归属于构成某个法律规范中心概念的适用范围[5]。因此如果将权利质权设立地定义为需要登记的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指的是适用权利登记地法律;不需要登记的,指的是适用权利成立地法律。这一定义还不能满足将已确认的该案件事实归属到某一特定的法律构成要件中去的要求。根据此结论,质权设立地应当解释为:质权设立地法是指,权利质权以登记设立的适用登记机关所在地的法律,以交付设立的适用交付所在地的法律,以双方合意设立的适用合意缔结地法律。
三、权利质权设立地与权利质权的设立
不论是目前通行的关于权利质权设立地的解释,还是前文所建议的解释,面临的另外一个质疑是,如果权利质押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质押权是否有效设立,此时不得不依据第40条的规定,就是在权利质权的设立地去寻找准据法,将会出现一种逻辑循环。产生这种循环的原因在于,其认为质权设立地本身是一个实体法概念,想要确定质权设立地,则必须考虑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作为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应是,民事实体法乃是冲突法的母法,冲突法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若非特有应与实体法一致。有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实体法即没有冲突法存在的必要,冲突法的概念应与民法实体法一致[10]。因此具体权利质权的设立上,作为连结点中的“设立”应当同实体法中的“设立”具有相同含义。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包括冲突法也包括实体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除有特殊规定或有理由作不同的解释以外,均应作相同的解释。但是,同样有学者对此观点持保留态度,并提出了国际私法自体理论,认为识别不应依特定的国家的实体法,而应站在国际私法自己的立场上独自进行。法律关系的识别问题实际就是国际私法法律概念的解释问题。国际私法是上位法,国际私法上的法律概念与特定国家实体法上的概念是不同层次的、彼此独立的[11]。显然后一种说法更为合理,冲突法上的概念不完全等同与实体法上的概念,例如我国《婚姻法》中对扶养与抚养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法律适用法》中,扶养关系显然是不限于实体法中扶养的含义;又如,《法律适用法》中所指的婚姻手续,根本无法在实体法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因此,从实际情况上看,民事实体法与冲突法的关系很难说是一种直线关系[12]。德国学者拉贝尔就认为,冲突规范的概念应在比较法的基础上提出,诸如,婚姻、合同和侵权等法律关系和范畴应独立于法院地的实体法,而完全建立在比较法的基础上[13]。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逻辑上的循环,更好的解释《法律适用法》第40条中的权利质权设立地,就不能将其与实体法中的设立对等。而应当结合各国立法的实际和冲突规则的需要来对其进行解释。
与实体法中质权设立的“设立”相比,笔者认为冲突规则中的“设立”至少有两点不同。
首先,《法律适用法》中质权设立地中的设立不等于有效设立。因为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效力如何是实体法的重要内容,也是冲突规范寻找准据法的重要目的。因此在冲突法中,“设立”不需要满足实体法上的要件。例如,冲突法中规定的“婚姻”并不必然符合我国婚姻法中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因此涉外案件中,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同性婚姻,无疑在冲突法中都应被视作婚姻,而其在特定案件中是不是有效,则应通过准据法来判断。
其次,《法律适用法》中的设立方式并不局限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根据我国《物权法》设立方式,及其相对应的权利质权种类是固定的,但在比较法视野之下,这种设立方式并不能完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一致。事实上在各国立法中,以登记、交付、背书、合意、通知等方式设立权利质权的立法例普遍存在,并且各国之间对特定的权利质权采纳的设立方式不尽相同。很难以某一国家的立法为基础来处理各国间的权利质权问题。于此同时,由于冲突规则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找到相关的准据法而非直接解决实体问题,因此在冲突规范上可以作更广义的理解,即只要是当事人之间认为其存在一个权利质权的法律关系,那么都应当被视作设立了权利质权。否则相关的涉外权利质权将无法由我国冲突法调整。
综上,权利质权设立地中的“设立”指的是设立权利质权的这一行为,而非实体法意义上的“设立”。那么权利质权设立地的认定根本不需要借助实体法来判断该权利质权是否设立、何时设立。而只需以设立行为的行为发生地来进行判断。适用法律时潜在的逻辑循环的危险也不再存在。
四、结论
对质权设立地的理解存在着的理论分歧,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国际私法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冲突法中识别的范围、方法,实体法与冲突法二者的关系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而这些已存在的争议在权利质权设立地理解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是由于各国在权利质权设立上的差异较其他法律关系更为突出,同时权利的无形性又致使各国对权利质押的设立的要件也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要想更好的解释质权设立地,为日后可能的法律适用排除障碍,笔者认为将权利质权设立地作如下解释比较合适。质权设立地是指:当事人之间,以登记、交付、合同等行为设立权利质权的行为发生地。
[1]王利明.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27.
[2]黄进,姜娇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20.
[3]杜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评[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263.
[4]钟青.权利质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43.
[5]翁杰.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定性——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J].法学家,2012,(2).
[6]柯泽东.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79.
[7]陈金钊.论法律事实[J].法学家,2000,(2).
[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
[9]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3.
[10]谢新胜.“委托代理法律适用”的立法设计及论证[C]//2004年中国国际私法年会论文集(下卷).2004:303.
[11]李旺.冲突法上的实体法导论[J].法商研究,2003,(2).
[12]徐青森,杜焕芳.国际私法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1.
[13]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325.
[责任编辑:郑 男]
DF90
:A
:1008-7966(2015)01-0134-03
2014-10-12
丁汉韬(1988-),男,湖北武汉人,2012级国际私法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