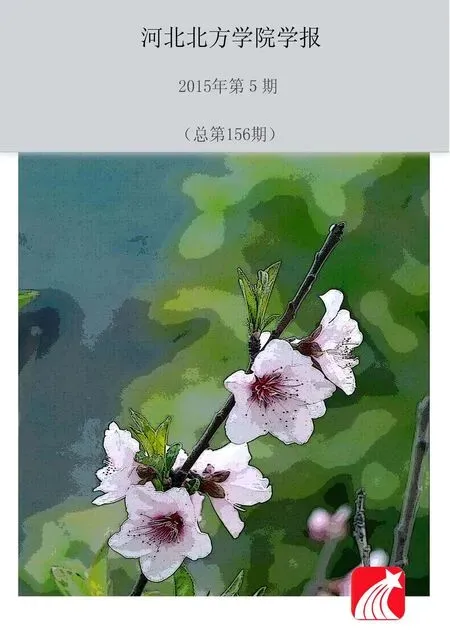安·苏·拜厄特《占有》的身份研究
2015-03-26李瑶
李 瑶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安·苏·拜厄特《占有》的身份研究
李 瑶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需要得到社会认同以及自我认同。从信仰的失落与追寻、性别的焦虑与重构两个方面,对《占有》的主要角色进行分析。达尔文主义对上帝的冲击和现代社会的精神匮乏使两对主人公艾什与拉莫特、罗兰与毛德陷入信仰的迷茫状态,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也让主人公陷入身份危机,但他们努力重构男女性别身份的等同地位。罗兰和毛德的结合标志了性别身份危机的解除,性别身份得到认同,两性关系走向和谐。
《占有》;身份认同;信仰;性别
网络出版时间:2015-10-09 10:06
安·苏·拜厄特的《占有》于1990年获布克奖,纷乱杂陈的文本碎片,应有尽有的体裁形式和错综复杂的叙述层次,使其有“魔书”之称[1]。它以侦探小说的叙事形式讲述了一场拨人心弦的学术探险:郁郁不得志的青年学者罗兰在伦敦图书馆偶然发现维多利亚时期著名诗人艾什写给拉莫特的情书,这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激起了罗兰久违的激情,于是他找到女性研究中心的学者毛德并与之为伴,细细温读了两位诗人曾经的爱情信笺,重走了他们的秘密爱情之旅,随着艾什和拉莫特爱情真相的慢慢揭开,罗兰和毛德也暗生情愫,在情感匮乏的现代社会萌生了一缕真情。
自获奖以来评论界掀起了对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热潮,国外的研究已经趋向成熟,国内虽对拜厄特的总体研究较英美国家相形见绌,但针对《占有》一书的研究却同样热火朝天势头不减,研究主题多集中在小说的主题涵义、叙事技巧、艺术形式、女性人物、小说互文性、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神话的意义、幽闭意象、颜色象征、不确定性和视觉意象等。该文旨在从身份研究的角度,对小说的主要角色进行分析。
一、身份认同
英文中“identity”一词,在汉语环境中有着身份/认同的双重含义。“身份”和“认同”不太一样,身份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组织规则建构起来的社会位置,个人的角色与社会定位产生于个体与其身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协商安排之中;而认同则是个体主动进行的意义建构,它要确定自身的意义来源,只有在将自身的社会角色作为自身的意义来源主动内在化并加以接受的时候才能算作“认同”。二者紧密相关,一定语境下的身份塑造着相应的认同归属感,主体的认同归属又强化着自身独特的身份意识[2]。
身份认同包括: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占有》从整体布局来看跨越了3个历史时空:远古的神话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及当代。贯穿整部小说的归根结底正是“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由古至今,从人类整体到故事中的拉莫特、艾什、毛德和罗兰,身份认同始终缠绕着人们的心灵难以松解,每一个人在心理上都需要得到社会认同以及自我认同,在确认身份和追求认同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并带来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3]。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个人身份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归属性的,例如年龄、性别、祖先、血缘家族、血统民族属性;二,文化性的,如民族、部落、语言、国籍、宗教、文明;三,疆域性的,如所在村庄、省份、国别、半球;四,政治性的,如集团、派别、领导地位、利益集团、党派、意识形态、国家;五,经济性的,如职务、职业、工作单位、经济部门、公会、阶级;六,社会性的,如友人、俱乐部、同事、休闲团体、社会地位。”[2]该文着重从信仰和性别两方面探讨小说角色的身份问题。
二、信仰的失落与追寻
在传统叙述或利奥塔所谓的“宏大叙事”中,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宗教观大行其道的社会,保守、压抑、勤勉、节制、严肃而又狭隘。拜厄特笔下的维多利亚社会并非一个稳定、和谐和具有统一价值观的世界,其原因并不在于它的秩序和相对完整的自我观念或是统一的时代精神,而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于变化取代了稳定[4]37。
早在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就提出了经验式理性主义,否定了先天观念的存在,即否定了上帝的存在。18世纪的思想家大卫·休谟提出怀疑主义,否定宗教赖以生存的根基——灵魂的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更给了上帝致命一击。达尔文主义者一般认为,所有现存的生物是由一个自然的和逐渐改变的过程进化而来的,强调偶然和无目的性;而与之相对的基督教则相信万事万物都是由神创造出来的,并按照一定的计划和目的控制这一创造过程[5]。当达尔文主义像暴风雨一般席卷过境,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信仰在黑暗中飘摇。拉莫特在给艾什的信中写到:“你的大作《北欧众神之浴火重生》曾为我一直很单纯的宗教生涯带来前所未有、最难以想象的危机。”[2]神圣高洁无可撼动的上帝,在拉莫特对艾什诗歌的思索中被深深质疑,她接着说:“这个创造了普莱厄波、创造了拿撒勒、创造了满口异端邪教的贝拉吉斯的人,倒是和蛇一样的精明。你知道批判哲学中所谓的‘迂回’和‘曲折’,那就像是奥古斯丁说道你那个贝拉吉斯时的看法——这个人物我非常喜欢,因为他不正如我一般,身上流着布列塔尼的血,难道他就不是希望罪恶的男男女女都能超越本我、让自己更加高洁更加自在吗……”[2]在这场信仰危机当中,艾什也没有幸免于难,“对宗教的热望,或许是一种对安全感的需求——也可能是一种理解异象的能力——而我自身对于宗教的感情,一直都是依凭着后者这样的动力。没有了造物主,我发觉,变异并不容易——我们所见所了解的愈多,万事万物那莫名交错如山的堆积就呈现出愈加复杂的不可思议——这一切都尚待整理就绪”[6]154。旧的宗教和新兴的科学之间冲突激烈,在时代的激流中拉莫特和艾什两人心中的信仰被左冲右撞,其文化身份始终不能找到归宿。艾什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对基督教和异教传统异同的比较,以及拉莫特对宗教的热忱和对降灵术的迷恋,无一不是在试图解释自我和阐释世界,虽然艰难,但他们仍然勇于承担起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通过罗兰和毛德发现的信件和日记,拉莫特和艾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被建构起来,历史和现实构成互相“凝视”的镜像关系,两条线索平行并置。拉莫特和艾什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代表,他们风雨飘摇的信仰也同样映照在当代社会上:“我们了如指掌,就像你说的,我们懂得非常多的知识。好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何以自我不会单一地存在——知道自己是怎么由各种矛盾的、互相影响的体系构成的——然后我就想,我们当真相信这一切吗?我们知道欲望是我们的动力,可是当真发生的时候,我们却又不明所以,不是吗?我们从不谈爱这个字,对吧——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尚待查证的意识形态下的产品——特别是那种有浪漫色彩的爱……”[6]262拜厄特本人也曾说:“我们没有一个有机的,可发现的,独立的自我。我们也许只不过是一系列分裂的印象,回想起的时间,以及不断变换的零碎的知识,观念,意识形态和陈腐的反应。”[7]31当代社会物质丰富,知识爆炸,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却价值堕落,精神匮乏。在思想和信仰上,毛德和罗兰与拉莫特和艾什一样,如水中浮萍一般找不到依靠。但拉莫特和艾什在对待爱情上的态度却诚挚勇敢,而当代的罗兰和毛德却身陷在感情的荒原里,不敢谈爱。为了寻找完整的自我,赋予生命存在的意义,他们回首历史,在拉莫特和艾什的故事当中找寻答案。在小说的最后,两个人终于在身体和心灵的契合之中走向认同。虽然他们对当代社会精神匮乏的内在根源缺乏深刻认识,但这追寻并不是毫无价值的,正是这些努力赋予了生命意义和价值。
三、性别的焦虑与重构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视作“家庭的天使”,她们绝不属于社会,约翰·拉斯金曾写过:“妇女在她的家门口以内是秩序的核心、痛苦的安慰和美的镜子。”[8]84乍看之下,女性被保护在家庭当中是何其幸福,但实际上这位“家庭的天使”每天要做繁杂的家务和侍候其他家庭成员,是男人被禁锢被驯服的仆人,女人不得自由,远离外部世界[9]。如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传达的,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则是他者。但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并非是大一统的,在看似单一的时代精神下暗藏着喧哗的众声,在男权社会中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试图颠覆男性霸权的话语,维多利亚时代实则蕴含着现代意识的根[4]32。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女性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女性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尽管女性的第二性地位普遍而持久,它跨历史跨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甚至是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男女都处在不平等地位,社会意识变革举步维艰,进展异常缓慢。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男女平等意识已经开始逐步渗透到各个方面,女性权力扩大,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拜厄特通过一系列男女角色的描绘,在书中展现了在特定时代性别意识的操控下,人们陷入性别身份焦虑,又不断努力重构并希望达到认同的过程。
艾什之妻爱伦基本上呈现了经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贤妻形象,她在婚姻中是仆人,“她成了他的女奴”,“每说一个字就不住地发抖”[6]433。她没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我以前很想成为一名诗人,成为一首诗,而现在我既非诗人也不成诗,就只是一个小小家庭里的女主人而已……”[6]114在和艾什的关系中,她失去了自我,“这个屋子少了我亲爱的鲁道夫之后就只剩下回音和寂寞。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我有好多事要处理,我要让他平常用到的东西更好更方便……”[6]217表面上看爱伦似乎匍匐在男权的统治之下,但是她并非对艾什百依百顺,她渴望女性的自由天地和独立权利,“在棋盘的世界里,女人的空间是那么大,行动是那么自由无阻,而到了现实人生,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6]223。爱伦自始至终拒绝奉献自己的身体,男性在肉体上占有女性是历史上最基本的压迫形式,爱伦通过保守贞洁的方式对艾什宣布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主体权利和自我存在感。
拉莫特则比爱伦走得更远,同性恋的爱情取向,反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坚持经济独立,写作诗歌颠覆男性主导文学的现状,与艾什灵与肉的结合并诞下私生女,这些在维多利亚时代都可说是女性反叛的极端案例。但是拉莫特也并非毫无惧色,她竭尽全力为女儿梅的将来精心打算,既不愿让艾什抚养孩子而向男性低头,也不愿让梅因为自己私生女的身份而受人鄙夷,最终只能向社会道德妥协,将梅送到妹妹家抚养长大。但总体上拉莫特凭借自己的力量维护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实现了自我的理想和价值,重构了女性的独立主体地位。
小说中,拜厄特通过女神梅卢西娜在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拉莫特和当代女学者毛德身上的两次转世轮回,展现了男女两性的地位演变,在女性形象呈上升趋势的同时男性形象发生了下坠式变化[10]。梅卢西娜是长着蛇尾的女神,她被母亲下了咒语,每周六蛇尾现出时如果被丈夫雷蒙偷窥就将被永生驱逐,梅卢西娜最终没能逃脱被驱逐的宿命,只能偷偷飞回喂养自己的孩子;拉莫特是梅卢西娜的化身,她被情人艾什偷窥,也获得了同样的命运,住在妹妹家的阁楼上,成为女儿梅成长的旁观者。毛德则是当代梅卢西娜的化身,罗兰通过浴室锁眼偷窥她沐浴但未成功,因而她一改梅卢西娜被偷窥的命运,在与罗兰的关系当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与此相对应,3个男主人公中,雷蒙是贵族骑士,艾什是大诗人,而罗兰却是一个穷困潦倒处于兼职状态的学者。在3条故事线索中,雷蒙拯救了被诅咒的女神,艾什与拉莫特灵与肉相结合,是互相拯救,而罗兰则是想要寻求毛德的帮助来实现自我抱负并获得社会身份的认同,也就是说在罗兰与毛德的关系当中,是毛德拯救了罗兰。故事落幕时,罗兰收获了3份职位邀请,他不再是经济上的寄生虫,职业上的兼职者和交际中的边缘人,而最终获得了自我以及社会认同,感受到了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罗兰和毛德的结合没有权势的差别,只有身份的等同,男性和女性之间扭曲的关系终于走向和谐,表达了男女两性在当代都能得到身份认同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美好理想。
综上所述,不管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是现代社会,两对主人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在信仰问题上,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给了上帝致命的一击,艾什和拉莫特在上帝与科学之间艰难求索;现代精神的极端匮乏让罗兰和毛德在爱情面前犹疑不决,无所适从。但他们选择直面惶惑,找寻生命的本源和存在的意义,尽管最终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作者肯定了他们勇于求索的精神,罗兰与毛德也在爱情的感召下结合。在性别认同中,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普遍而持久,在性别意识的操控之下,两性关系出现危机,所幸,他们并未匍匐于主流意识之下,而是主动宣示并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努力构建男女性别的等同地位,最终获得自我及社会认同,从而使两性关系走向和谐。
[1] 程倩.历史的回声——拜厄特《占有》之多重对话关系[J].当代外国文学,2006,(1):20-28.
[2] 罗如春.身份认同问题三论[J].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刊,2009,280-293.
[3]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37-44.
[4] 金冰.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历史想象——拜厄特“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彭新武,孙爱军.进化论与宗教[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1):80-82.
[6] 拜厄特.A.S.隐之书[M].于冬梅,宋瑛堂,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7] Byatt A S.On Histories and Stories[M].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0.
[8] 约翰·拉斯金.拉斯金读书随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9] 郭俊,梅雪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中产阶级中上层的家庭意识探究[J].世界历史,2003,(1):23-30.
[10] 陈菊.论A.S.拜厄特小说《占有》中梅卢西娜原型的改写[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2,(1):92-95.
(责任编辑 白 晨)
An Identity Study ofPossessionby A.S.Byatt
LI Y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Everyone needs self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psychologically.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protagonists inPossess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ss and pursuit of faith,and the anxie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nder.The impact of Darwinism on God and the spiritual deficiency in the modern society causes the two pairs of protagonists,Ash and Larmont,Roland and Maud,to be caught in the confusion of faith.The gender inequality makes them be stuck in identity crisis.But they strive to re-construct the sexual equality.The mutual possession of Roland and Maud marks the relief of their identity crisis,their sexual identity is acknowledged,and the sexual relations become harmonious.
Possession;identity;faith;gender
2015-05-29
李瑶(1990-),女,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I 106.4
A
2095-462X(2015)05-0059-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009.1006.0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