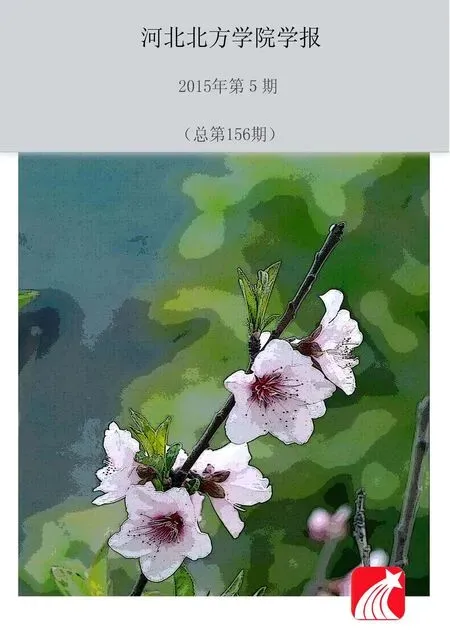汉武帝时期教育与考选对《春秋》公羊学的影响
2015-03-26刘红妹
刘 红 妹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汉武帝时期教育与考选对《春秋》公羊学的影响
刘 红 妹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汉武帝时期的教育与考选制度对此期《春秋》公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公羊学的大兴,而且改造了《公羊春秋》的释解思想和体式,形成了《公羊春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原则。释解方式则由字句走向比类事例。
汉武帝;教育;考选;《春秋》;公羊学
网络出版时间:2015-10-09 9:51
汉承秦制,但汉朝教育选拔制度多异于秦,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儒家经学成为有汉一代教育考选的重心。而经学教育中的《春秋》学一门更为特殊。《春秋》学以其相较其他经学类型更为鲜明的“经世致用”功能在汉代政治社会中大展拳脚,曾被广泛运用于立嗣、决狱和处理民族关系等领域,汉代士子常通过研习《春秋》而步入仕途。就现有史料来看,西汉言《春秋》又多为公羊派学者,《春秋》公羊学天人感应及大一统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西汉统治的需要,统治者的偏爱又成就了其较其他经学更为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的教育培养及考选制度更加丰富了其内容,影响了《春秋》公羊学的解经方式。前贤对此谈论较少,笔者不惮鄙陋,拟对此问题做一较为全面的讨论,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汉武帝时期教育、考选与《春秋》公羊学的兴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策略的实施,使汉武帝时代迅速掀起了“行仁义,法先圣”的潮流,统治者也随之开始制定并逐渐推行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系列治世措施,其中对人才的教育培养以及对官吏的选拔任用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宝。在这一制度设计中,儒家经学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当仁不让地成为教育考选的标准和尺度。在经学的众多领域中,经世致用色彩最为浓厚的《春秋》公羊学脱颖而出,为更多求官寻禄的士子搭建了阶梯,如这一时期两位著名人物公孙弘与董仲舒都是以治公羊《春秋》声名鹊起。《汉书·武帝本纪》载汉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其中《春秋》一门即为公羊《春秋》,公羊《春秋》成为汉朝官方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统治者通过培养经学人才,以经取士,发挥其作用,促成了汉代教育的经学化。
与之前相比,汉代教育制度系统完整,特别是武帝时期官学全面发展。此期官学主要为太学和地方上的郡国学校,而私学也步官学之后逐渐走向繁盛。《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的对策中阐述求贤必先养士,不应该盲目或者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俊才,而应通过“兴太学,置明师”[1]2 512,积极主动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以考试策问发挥其才能,为国家效力。元朔五年,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开始了兴办太学的进程,诏曰:“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与博士子弟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焉。”[2]75“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1]172
汉代选举以察举应用最广,与经学关系最为密切。汉代察举有孝廉、茂才(秀才)、贤良方正与文学以及明经、明法和治剧等科目。上述已提到元朔五年,汉武帝诏令公孙弘拟设兴办太学计划。公孙弘即提出,太学生一年后进行考试,按成绩等级高低录用和授予官职。“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2]742武帝时,秀才一科最初是为太学学生开设的考试进官通道,后因为要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才扩大了范围。此外,还有专门以文学经学取士的察举科目——文学和明经。汉代所指文学即为经学,汉武帝时,文学一科成为正式的察举科目。
从汉武帝时期学校教育及选官制度可以看出,武帝处处把治经学好坏作为人才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经学在汉世被奉为圭臬。公孙弘与董仲舒都因《春秋》公羊学而名噪一时,《春秋》公羊学一门成为武帝一朝经学中的显学。从文本来看,《春秋公羊传》较其他经典更接近政治。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需要明经法典来指导政治与社会的运行,《春秋》公羊学多论及军国大事,更具有现实参照意义。再加上汉初的《春秋》公羊学者如董仲舒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越发适合汉武帝统治的需要。所以,《春秋》公羊学的社会政治功能被强化,出现以《春秋》说灾异、法则、议礼和决狱的现象,这些均从官方确定了《春秋》公羊学至高的地位。明经博士的确立,明一经即可入仕的诱惑,统治者的偏向,公孙弘与董仲舒明《春秋》而官获高位的现实例证,都在煽动天下士人的入仕之心。《春秋》公羊学相比《易》《尚书》等经书更易理解,在对策试问中更易举一反三,提出解决方案;且公孙弘为丞相,也容易影响士子的学习倾向,不仅在于其以治《春秋》而位居显要,同时因为受其自身学术背景的影响,必然会在选拔上产生一定的偏向。武帝时,治《榖梁春秋》的瑕丘江公在为学方面与董仲舒不分上下。《汉书·儒林传》记载:“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1]3 617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董仲舒被任用与其治公羊学及公孙弘的选择偏向是有关系的。士人明经权衡利弊,治《公羊春秋》入仕成功几率更大。这些因素促进了此时期社会士人对《春秋》公羊学的崇尚。汉武帝时期,学《公羊春秋》的情况蔚为大观,如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2]745。弟子中后来为官的也大有人在,“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2]746,如吾丘寿王、褚大、殷忠、吕步舒和嬴公等。
二、教育与考选标准对《公羊春秋》性质形成的影响
汉武帝兴办学校和选拔官吏以经为本,学校博士的释经方式必以武帝统治需要即经世致用为准。这一思想原则深刻影响了《公羊春秋》性质的形成。
汉武帝时期,治讲《春秋》要遵循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其指导思想则是追捧和维护封建大一统思想和封建等级制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自汉初至武帝时,真正通晓《公羊春秋》的只有董仲舒一人。刘歆认为:“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1]2 526这些评价都说明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在汉代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其学术思想在同时代及稍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2 523,“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1]2 510。在《春秋繁露》中,他从“尊王”的角度对《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精神和封建等级制度加以发挥,“《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3]75。只有像董仲舒这样研读《春秋》,比附政治,才会被武帝选中,进入仕途飞黄腾达。这也使得《春秋》公羊学成为一门功利性极强的学问。
在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原则指引下,教学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使学者经世致用。研读《春秋》时也要把《春秋》当作实践的理论指导。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武、宣之间,经学大昌……以《春秋》决狱。”朝廷考核官吏有考课一项,察其治绩功状。中央考课郡国中即有治狱一项,优秀者能凭此升迁。《汉书·酷吏传》载:义纵“补上党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举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1]3 653。汉代以《春秋》义决狱盛行,断案离不开《春秋》大义,《后汉书·应劭传》载:“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4]1 612董仲舒把以《春秋》决狱的方法和案例诉诸笔墨,上至朝廷下至诸侯百官,遇到难断案件,以《春秋》解之已成为一个重要方法。《春秋》的经世致用功能在选擢官吏上得到优化。
三、教育与考选标准对《公羊春秋》阐释方式的影响
关于汉代及以前《春秋》的诠释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榖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公羊外传》五十篇、《榖梁外传》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榖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杂记》八十三篇、《公羊颜氏记》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5]11-12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春秋书目来看,西汉时对《春秋》的诠释主要可分为传、微、章句和记几种体式;而对汉武帝及以前时期的《公羊春秋》进行诠释的,则有外传、章句及杂记。外传是相对内传而言的,专主解释经义的书为内传;外传则是附经作传,广引事例推演本义而不完全以解释经义为主,是对作者之前著作的主要内容作进一步解释或者补充。杂记是记载杂项的笔记,是混杂的记录。如《礼记·杂记》陆德明释文引汉郑玄曰:“杂记者,以其杂记诸侯及士之丧事。”孙希旦集解云:“此篇所记,有与《小记》相似者,有与《大记》相似者,又有非丧事而亦记之者,以其所记者杂,故曰《杂记》。”章句依附经传而行,把经义放在首位,分章析句释义,就是在分章断句的基础上,对经籍逐次解释字词句和段意,进而阐发经师的思想。
无论外传、杂记和章句都有可能成为汉代学校教授生徒的课程教材。章句从基础词汇、断句与词义层面逐渐上升为篇义,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而外传更像是对篇旨大义的一个补充,杂记相当于一种课外拓展的材料。学校教学以章句为主,其他释经方式为辅,充分照顾了学生的学习规律,由基础阶段的具体深入学习到适应汉武帝时期政治和社会需要的应用,是针对官方培养选拔人才要求而实行的最佳教育模式。此外,章句也适时地成为武帝时期《春秋》公羊学学校教学的重要形式。
经世致用的《公羊春秋》要求把《春秋》运用到具体的现实社会中,这也是汉武帝倡导经学的原因。据戴维《春秋学史》云:“董仲舒对策可能就在建元五年或随后的元光元年。”[6]66建元五年之前的几年里灾异不断,建元二年春日蚀、三年春河溢、秋星字日蚀、四年秋星孛谙事[2]66-67。面对连年灾异,汉武帝思绪踌躇,难觅缘由,苦思方策,对策试问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董仲舒在3次对策中都以《春秋》比类事情,探讨问题的源头,提出解决问题的方略。武帝第一次诏问灾异之缘起,膏露何以降,董仲舒多次结合《春秋》重点谈了天人关系与性命之理,对《公羊春秋》进行了天人感应说的改造;第二次对策中,董仲舒又多次结合《春秋》重点阐述了如何使用和培养贤才,兴太学、置明师与教化百姓,从国家教育与教化方面对《公羊春秋》进行改造;第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劝告武帝效法先儒古道,大量运用《公羊春秋》说事,然后对《公羊春秋》中的大一统思想进行全面升华,吹起了儒家独尊的号角,兹此以引文为证:
孔子作《春秋》……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317-323。
3次对策后,董仲舒及其推崇的对策得到了武帝的重视,这种形式的经解才是统治者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对策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明师及官吏教化百姓等政策,武帝最终同意,部分原因应是希望这些政策能够培养出像董仲舒这样通经致用的人才,而不是死守经典的腐儒。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涵盖了董仲舒及汉武帝时期的《春秋》公羊学思想,神秘主义笼罩下的天人感应说、命理说和灾异说适应了汉武帝大一统及等级制度等思想。而章句形式的教学,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政治生活中熟练运用《公羊春秋》解决问题的现实需求,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达到了武帝选拔人才的要求。这种熟练运用《公羊春秋》的能力是离不开好的章句、外传和杂记的学习与训练的。董仲舒对教学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便于得到武帝赏识的经解《公羊春秋》的体式。
自汉武帝兴办太学以后,博士立为正式的学官,也就是最高学府太学的教师。太学中的《春秋》教学则多依《春秋》博士选定的《春秋》章句教学。武帝时期兴办太学后的《春秋》博士,明确可考的只有褚大,《汉书》载:武帝元狩六年“六月,诏曰:‘今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1]180元朔五年武帝下诏兴办太学时,公孙弘已经为丞相,但其《公羊春秋》学的影响力不及董仲舒,武帝时的经学是以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为主体的。董仲舒虽然不是武帝时期的博士,但其弟子褚大却在博士学官中占有席之地。《史记》载:“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2]746董仲舒教授经学的盛况在史书中也有记载。西汉重师法家学,褚大承袭董仲舒之《春秋》公羊学,自不待言。所以,武帝时《春秋》学尤其是太学中《春秋》学,董仲舒的春秋学思想占统治地位。史书记载董仲舒的《春秋》著作有《春秋繁露》数十篇、《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及《春秋灾异传》一卷。从《春秋繁露》看,董解春秋的体式符合学校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由浅入深培养学生的要求。周光庆《董仲舒〈春秋〉解释方法论》一文指出,《春秋繁露》对春秋的解释,分为“名号论”,即深察名号;“辞指论”即剖析辞指;“事例论”即通释事例3个层次。“深察名号”是基础层,需要运用传统训诂学的“形训”、“声训”和“义训”;“剖析辞指”是关键层,需要运用语法分析、修辞分析和逻辑分析;“通释事例”是最高层,需要运用“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这与《毛诗故训传》的“诂——训——传”体式殊途同归[7]。这种体式一方面使得经书更易被理解接受,促进其繁荣;另一方面在通释经书的基础上比附政治,正符合汉武帝时期教育考选制度对人才培养的标准。而《公羊董仲舒治狱》与《春秋灾异传》更像是官吏履职之必修书目。武帝时期的官员选拔,十分重视治狱和说灾异,能够作出恰当的解释和应对这类政务,是官吏业绩能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董仲舒作此二书,无疑是为官吏提供了为政的36计,是武帝对人才官吏选拔要求的产物。此后,董仲舒著作中的《春秋》思想及解《春秋》方式经过了学者、博士弟子和学校生徒的进一步发挥,与政治联系更加密切。这些思想与形式的衍生原因之一就是汉代选拔官吏的趋向导引。
综上所述,汉武帝时期对人才的培养和对官吏的选拔要求,首先促进了《公羊春秋》学的兴盛;而《公羊春秋》学者也不负重望,极力改造和适应该时期武帝对士子的期望,培养人才注重遵循学习规律进而熟练运用《春秋》公羊学于政治生活。
[1]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汉)司马迁.全本史记大全集·儒林列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3]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三策[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1997.
[4] (南朝)范晔.后汉书·应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6] 戴维.春秋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7] 周光庆.董仲舒《春秋》解释方法论[J].孔子研究,2001,(1):116.
(责任编辑 张盛男)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onGongyang’sCommentaryonSpringandAutumnAnnals
LIU Hong-m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The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emerging ofGongyang’sCommentaryonSpringandAutumnAnnals.They not only promote the study of this book,but also remold the ideas and forms of explanation, in which the ideological principle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in the book came into being. The explanatory way shifted from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 analogical examples.
Emperor Wu of Han Dynasty;education;examination;Gongyang’sCommentaryonSpringandAutumnAnnals
2015-05-18
刘红妹(1989-),女,河北肃宁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K 02
A
2095-462X(2015)05-0005-04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51009.0951.0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