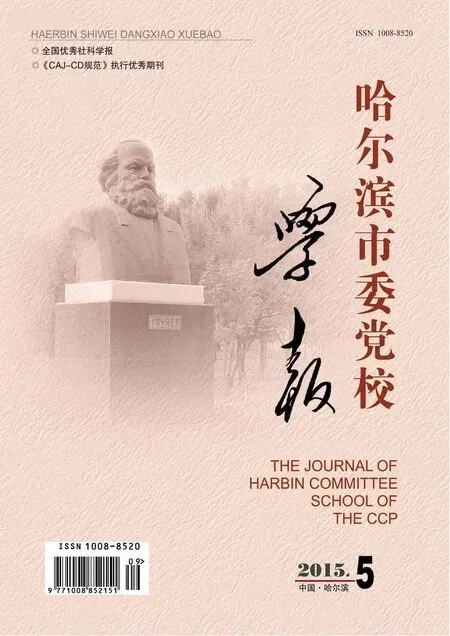身教传统及其当代创新
2015-03-26马庆玲
马庆玲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身教传统及其当代创新
马庆玲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哈尔滨 150080)
注重身教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曾经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积极的作用。传统文化对身教的必然性、可行性及身教的实践路径都有深刻认识。今天,在典型塑造、宣传渠道、社会道德氛围营造等方面对身教传统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必将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身教;传统文化;道德;当代价值
注重身教是中国古代教化思想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曾经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积极的作用。今天,认识并对身教传统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必将对当代社会道德建设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一、传统身教理论及实践
中国传统教化思想强调身教原则,认为身教,即在道德教育和实践中,掌教化之权者和负教化之责者以自身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实践对受教化者进行道德示范,是使教化工作收到良好效果的关键之一。身教因何必行?如何可行?又是如何施行的?传统文化对这些问题有着深刻认识。
(一)传统文化对身教必要性的论证
传统文化认为,身教之重要与必须是由教化自身的特点决定的。道德教化有别于一般的知识、技能教育,它的目的是导人为善,令人们实践道德,这就要求必须“以德服人”,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必须高度统一。因此,道德教育者自身的示范、表率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
首先,教化者只有在道德上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具备教化的合法性。《吕氏春秋》曾言,“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孟春纪》),离开自身的躬亲践履,难以教化民众。孔子早就说过:“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欲正人,先正己,如若自己不能做到“身正”,又如何去教导他人何为正呢?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孟子·万章上》)。自己不正,是没有资格和能力去正人的。朱熹指出,道德教化要求教化者首先必须对道德躬行践履,为民先导,为民表率。“如必自尽其孝,而后可以教民孝;自尽其弟,而后可以教民弟。”(《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自己首先做到孝悌忠信,才有资格教人孝悌忠信。“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只有教化者自身有善行,才有资格要求他人立善行;只有自身无恶行,才有资格纠正他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这些论述都表明,教化者只有自身成为道德楷模,才有资格对他人施行教化。
其次,教化的目的在于道德践履,而身教正是知行合一,恰能沟通知行。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孰先孰后有争论,至于二者孰轻孰重的态度则基本一致,那便是道德实践更重要。教化的目的不仅在于告诉民众什么是善,更要引导民众躬行践履,将道德认识付诸于道德实践。古人早就认识到,道德生活中存在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的情况,或者明知何为善、何为善行却不愿、不为善的情况。教化者必须身体力行、为民表率,唯其如此,才能令受教化者确信道德知识是真实不虚的,进而在行动中实践这些道德,教化工作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传统文化认为,教化的实际效果更多取决于身教。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孔子世家》)身体力行的教育效果优于口头说教,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一个人如果做到了言行一致,不用要求,他人也会主动仿效;如果自己没有做到言行一致,即便是采取强迫手段,他人也不会服从。教化者自身的行动示范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作用,如果教化者自己言行脱节、表里不一,自身无德,即便他说得再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也无法取信于人,道德教化不可能有什么实际效果。身教是沟通知行、教人实践道德的重要方法和原则。
(二)传统文化对身教可行性的论证
传统文化认为,广大民众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以至社会的道德精神风尚,完全取决于教化者、统治者(特别是君主)。
孔子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教化者、君主)之德好比风,小人(受教化者、普通民众)之德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荀子·君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这些论述表明,在古人看来,上对下、君对民具有强大的道德示范作用,掌教化之权、负教化之责的统治者、君主、君子、师长等人的德行,他们的爱憎好恶,对于民众具有强大的价值导向作用,少数精英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决定者,而广大民众只是被动的趋附者。上位者对下的示范、下位者对上的效仿正是“上行下效”,正如朱熹所言:“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上对下的影响、下对上的仿效,比影之随形、响之随声还要迅速[1]。因此,上位者、统治者、教化者的身教、表率至关重要。这种上行下效不仅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影响,若统治者、教化者其身不正、其行不德,其对下的反面示范作用亦是巨大的。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楚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是而后欺……上好曲私,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偏……上好倾复,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险……上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乘是而后丰取刻与,以无度取于民(《荀子·君道》)。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传统文化始终要求统治者、教化者自身必须德性卓绝,善于自律,躬行实践,为民表率。这种认为少数社会精英能够左右、引导社会道德风尚的认识无疑具有英雄史观色彩,期待有位者必然有德,这也带有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但“上行下效”的效应则是道德教化中客观存在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三)传统文化的身教实践
在古代中国,使身教原则落到实处,使其真正起到导民为善的作用,大概有两条途径。一是始终要求教化者自身要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并且能够将道德知识付诸于道德实践,为民表率。二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有意识地、持续地表彰道德楷模,为道德教化树立典范和榜样,并注重为道德行为提供制度保障,从而扬善、彰善,在全社会营造崇德贵德的道德氛围。为此,传统社会树立了多层次的、能够明确反映当时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道德楷模,如圣人、圣王、贤师、清官廉吏、忠臣孝子、贞女节妇等等,并大力对道德楷模加以宣传、提倡和旌表。
1.对重点道德示范群体的塑造。为引导教化者、统治者以身作则,成为道德楷模,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君主、教师这两个群体的道德建设,并为之量身打造了圣王、贤师这两种道德典范。尧舜禹是圣王的代表。尧“克明俊德”、简朴任贤;舜孝行卓著、至公任贤;禹辛劳为民、谦虚乐善。他们不仅自己是道德表率,而且能够以自身行动影响、感召民众,引导社会风尚。《史记》对禹的评价可以看成是圣王的道德标准: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史记·夏本纪》)。不违道德,可亲可信,言行举止以身作则,可以为人法度,为民纲纪,这是圣王理应具备的德行。孔子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是师德的代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见贤思齐、因材施教,时时处处以高尚的品格对学生进行道德示范,以德服人,循循善诱,其人格力量令弟子及后来之人感叹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王夫之曾指出,教师必须率先垂范、为人师表,与弟子的交往“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四书训义》卷三十二)。统治者是万民表率,教师则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良好的君德与师德,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引领、示范作用至关重要。
2.官方的道德示范方法。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届政府无不重视对道德楷模的提倡、表彰。
首先,政府对道德典型加以奖励、旌表。汉代以降,表彰奖励忠臣、孝子、贞女、节妇、廉吏的诏书朝朝皆有,数不胜数。政府还常常赏赐酒帛财物以为奖励,唐时孝子还可以获得政府减免赋税的优惠,等等。除物质奖励外,精神激励也不可少。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时曾有一个名为清的巴郡寡妇,因丈夫死后能够“用财自卫,不见侵犯”而被秦始皇赞为贞妇,并特命筑“怀清台”以使其“名显天下”。为表彰贞节,历代朝廷多有为节妇赐祠祀、树坊表的规定;为弘扬孝道,历朝对孝子、义门的礼敬旌表从未间断;为倡导忠义,历朝不仅为本朝忠臣义士树碑立传,且高度礼敬忠于前朝的不降之臣,如赵匡胤对韩通、卫融,朱元璋对余阙等人就大力褒扬提倡。历朝一方面为忠臣义士建立“忠臣祠”、“昭忠祠”供世人纪念瞻仰,一方面对不忠之人,哪怕是投降己方的人,亦在史书中多予严厉谴责,例如清史便将曾经帮助自己夺得江山的明朝降臣列入《贰臣传》,予以道德上的批判。
其次,由中央政府编纂的正史为各种道德典范立传,表彰其德行义举。自汉《列女传》以来,为那些能够助国君之政、隆家人之道、弘清淳之风、亮明白之节的贤妃、哲妇、贞女等优秀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女性立传既成常态。这其中有尊重理解丈夫志向的鲍宣之妻桓少君,有与丈夫共安贫苦、相敬如宾的庾兖之妻荀氏、乐氏,有才华出众的班昭,有恪守妇德、温良贤淑的韩觊妻。当然,更多的则是誓不改节的贞女节妇。到清前期,几乎所有方志中都辟有《列女传》。历代正史记述、表彰孝行突出者的传统早已有之,而自《晋书·孝友传》始,除少数史书外,历代正史均为以孝悌闻名者立传,名之曰“孝友传”、“孝行传”、“孝义传”、“孝感传”[2]等等。而后来由元人辑录的“二十四孝”,更成为古代中国宣传孝道的典型。此外,为公忠体国、廉洁奉公的忠臣义士、清官廉吏所著的《忠义传》、《良臣传》、《循吏传》以及各种专门传记亦成定例。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犯言直谏的魏征、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浩然正气的文天祥、清廉刚正的海瑞……这些忠臣义士的名字彪炳史册,令千秋敬仰。正史对众多忠孝节义、友悌坚贞的德行卓绝之士、各种堪称表率的道德事例标榜记述,不绝于书,这既树立了道德楷模,更向全社会申明了什么是人们应该效仿、实践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这对社会道德风尚的引导、塑造无疑作用巨大。
再次,中国古代历朝历代还注重为道德典范提供制度保障。朝廷将人才选拔与德行相结合,为道德突出之士提供政治激励,从而导民为善,学习道德楷模。据《汉书》记载,汉高祖曾下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置以为三老。”(《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有修行”且能够带领民众为善的道德楷模可以担任掌教化的官员“三老”,他的职责是对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为民典范者予以表彰宣传(扁表其门),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察举是自汉代起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途径,尤重被选拔者的德行,其中“孝廉”,即选拔孝子、廉吏为官,是察举的重要一科。魏晋承汉制,仅曹魏时期,“如以建安元年曹操都许控制朝权时起算,魏计有18人以孝廉出身为官,其中魏国建立后所举孝廉占一半”[3]。唐代在科举取士的同时,实行“孝廉与旧举兼行”的选官制度,通过选士、拜官方式表彰擢升孝悌力田之士。而自隋唐以降的科举取士,尤其是以儒家经义为考核内容的进士科,更以封建道德规范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强调“任官以德”,重视人才的道德素养及其对封建纲常名教的认同,这些被选拔之士是力行当时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佼佼者,他们自身就是人们学习的道德榜样,是社会道德风气的引领者,而任用德行优异者为官这种制度化激励,比之物质激励和一般表彰无疑对鼓励、感召民众践履道德、归附教化效果更大。
古人深知身教在教化中巨大的示范、导向作用,因而重视教化者的以身作则,重视对道德典范的提倡、表彰、奖励,尤其是后者,通过生动的典型及其活生生的道德事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感召民众,这在历史上对于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曾起到重大作用。重视身教示范、重视扬善彰善对道德教化作用的传统以及一些具体方法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身教传统的当代创新
中国共产党很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身教原则。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视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发挥对民众的道德示范作用;而通过榜样、典型进行道德教育,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党的宣传部门针对不同需要,塑造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道德典型,并通过发挥典型的榜样示范效应,有效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塑造了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今天,我们应继承并创新身教传统,灵活运用道德示范的方法,使之在弘扬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一)继续发扬身教传统的现实意义
当前,继续发扬身教传统具有现实意义。古人指出的道德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上行下效的德育效果在今天仍然成立。教化者的以身作则以及将道德规范融入到生动形象的道德典型身上的道德示范做法对社会成员的心理感召与社会道德风气的引导作用仍然巨大。而当前社会环境的一些新变化则进一步提升了身教在德育教化工作中的价值,也对传统的身教示范方法提出了创新要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再加之信息化传播媒介的发展。这些变化无疑对德育教育、对价值观培育、对身教传统产生巨大影响。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开放意味着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意味着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意味着人们的道德取向有了更大自主性和更多选择。在这个足不出户便能知天下事的时代,通过观察学习公众人物、社会事件而逐渐形成个人价值判断,业已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养成的最突出因素之一,身教在道德培育中的示范效应自然相较从前更为突出。而高速发展的社会必然导致价值、道德判断标准有较之从前变化更快,更具相对性,开放多样的价值、道德观念令人们往往陷入无所适从、难以分辨是非的道德选择困境。此时更需要树立能够充分代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道德典范,以身教示范的方式告诉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学习什么、选择什么、实践什么,以避免在纷扰复杂的道德选择中迷失方向。
(二)对身教传统的创新发展
当前继续发扬身教示范的优良传统,发挥道德典型更大的表率作用,必须不断创新身教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要转变典型塑造和宣传的惯性思路,打造更具广泛代表性的道德典范群体。无论是古代社会忠孝节义的道德楷模,还是建党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直至20世纪末的道德模范,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典型、榜样无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对于这样的榜样,我们应该继续宣传,发挥他们的作用,针对当前对传统道德典范的质疑、歪曲、恶搞等行为,要坚决抵制。但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这些传统道德典范的影响力在当代弱化了?这是因为,传统道德典范普遍具有“高大上”的精英色彩,且以往的宣传往往片面强调道德典范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感人肺腑的道德事迹,忽略其个性或道德之外的其他诉求。这种片面突出责任义务的、几无瑕疵的榜样,在个人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生活、政治生活高度统一的社会环境中,依靠自上而下的宣传灌输,能够起到巨大示范效应。但随着如前所述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大众对近乎完人的榜样的心理认同度有所削弱。仅靠传统道德典范已经不能满足今天人们道德选择的需要,当今社会还需要贴近生活、平易近人、易于模仿、有血有肉的道德典型,这样的典型与普通民众距离更近,更易令人感到可亲、可信、可学,示范效果更好。近年来,各种“最美”人物的评选已经体现出这种典型塑造思路的转变,“最美乡村教师”、“最美乡村医生”、“最美孝心少年”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社会基层的普通人形象,感召力极强。而一些地方更在街道、社区宣传本地的“身边好人”,这些榜样无疑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更能激发普通民众的情感共鸣,可接受性更强。
与道德典型群体的渐趋丰富相适应,以往那种道德精英主义的习惯宣传方式也必须被打破。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应该就事论事,仅就道德榜样的道德行为所展现的道德境界(如大公无私、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等等)加以宣传塑造,不宜将其拔高为千人一面、完美无瑕的圣人,尤其要避免那种只强调责任义务,贬低道德榜样正常物质需求的做法,这既是对道德典型利益的尊重,也有利于提高榜样的可接受性、可模仿性;二是要创新宣传渠道,除了重视以党报、国家电视台、学校为代表的传统渠道外, 必须重视发挥依托于互联网的,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榜样宣传、社会道德风气塑造中的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5年7月23日发布的第36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统计,截至2015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网民总数已达6.68亿人,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人。随着人们更多地从互联网获取信息,交流意见,网络参与宣传或首倡道德典型人物、事件也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网选正能量人物、为善行义举点赞已经成为传播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渠道。这种信息传播、道德示范途径是史无前例的,强大的,是今天进行道德教化绝对无法忽视、必须牢牢掌握和积极利用的。可喜的是,许多传统媒体和政府机构正通过纷纷开通官微等方式更多地利用这个渠道宣传主流价值观,这对于正确引导舆论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起到积极作用。
其次,要为提升道德典型的示范效果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当前身教示范、道德表率作用有所弱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道德典型的示范导向与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氛围导向的偏离。因此,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非常重要。
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必须提出明确的价值纲领。中国古代的道德教化、道德典型的塑造,始终围绕“三纲五常”这一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始终体现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官方在道德教化中始终以此为宗旨,自宋代以来在道德教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戏曲、说唱、小说等艺术形式在道德典型塑造中也自觉以宣传忠孝节义,表彰歌颂忠臣孝子、贞女节妇为圭臬。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精神的宣传提倡,对白求恩、张思德、黄继光、邱少云、王进喜、雷锋等道德榜样的树立,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当前社会环境复杂多变、信息传播空前快速、社会生活丰富多元、人们的道德选择愈发自由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尤为重要,它在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中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明确了规矩、绳墨,为社会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
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必须突出强调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党员干部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形象,理应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普通民众的道德示范作用、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巨大,而个别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要营造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好的社会风气,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道德建设,要严于修身、严于律己、严于用权,这既是树立党的光辉形象、转变党风和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建设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是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要求。
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必须加强舆论引导、监督。媒体要自觉负起宣传社会正能量的责任,多宣传真善美,要积极监督社会风气,旗帜鲜明地谴责假恶丑,在道德典型宣传中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整合多元社会价值思潮。
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还必须加强保障道德典型权益的相关制度、法律建设。近年来社会上发生的诸如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争论,与道德人性有关,也与制度有关,既是道德水平问题,更是制度、法律问题。切不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泾渭分明之两事,制度、法律体现了社会道德取向与价值观念。就像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有具体制度对道德楷模进行物质与精神激励一样,当前也要制定能够保障道德典范正当权益的制度或法律,令其在赢得社会尊重、获得精神上认可的同时,也能够理直气壮地因其出色的德行而获得相应物质奖励,更要保障他们不会因善行义举而受到误解甚至利益受损。道德典型的权益得到保障,这必将给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强大的效仿动力,必将起到事实胜于雄辩的强大示范效应。
明代吕坤曾经说过:“化民成俗之道,除却身教,再无巧术;除却久道,再无顿法。”(《呻吟语·治道》)陶行知指出:“身教最为贵,知行不可分。”赵一曼烈士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道德教育、化民成俗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身教则是我国道德教化思想和实践中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持之以恒地长期坚持身教示范,坚持知行合一,并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对其进行创新发展,道德教化方能取得实际效果。
[1]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285.
[2]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76.
[3]刘伟航.三国伦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69.
[责任编辑:孙 霁]
2015-07-15
马庆玲(1974-),女,黑龙江大庆人,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
G641
A
1008-8520(2015)05-0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