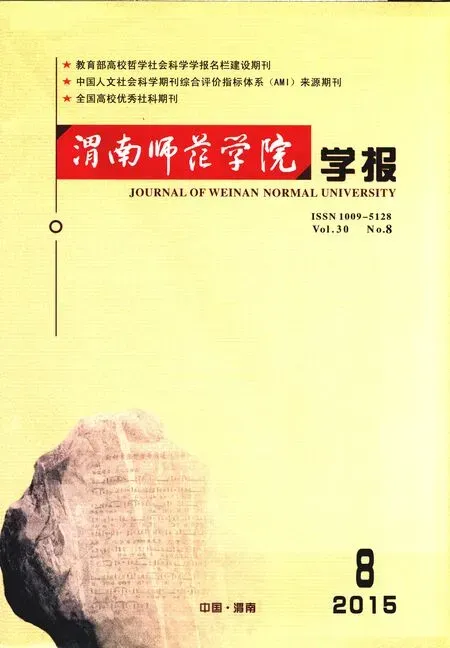郑振铎的翻译精神及其理论
2015-03-20周心怡
周 心 怡
(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州 350108)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
郑振铎的翻译精神及其理论
周 心 怡
(闽江学院 外语系,福州 350108)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学者、作家、文学评论家。然而,他在翻译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却鲜少被提及,相关的系统研究也屈指可数。以郑振铎的翻译实践及论著为基础,从翻译的初衷、地位以及具体的翻译方法,对其相关的翻译思想与理论作出归纳与评价。
郑振铎;翻译理论;文学书译法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祖籍福建长乐。他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扮演过许多意义非同寻常的角色。20世纪早期,在国内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合编创刊《新社会》,以期寻求中国社会改造的复兴之道。五四运动之后,与周作人、沈雁冰等人联合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使该会成为新文学运动中贡献和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五卅运动时期,郑振铎积极奔走,多番支持社会团体运动。即使因政治原因被迫离乡,前往法国避难留学期间,他仍心系祖国安危,并在回国后的第一时间投入文化运动,成为以鲁迅和茅盾为首的文化运动的“台柱”之一。1949年后,郑振铎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重要职务。
纵观郑振铎的一生,虽经历丰富,涉猎广泛,但其与文学、文字的渊源却贯彻始终,从未间断。尤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以文学评论家显身文坛,创作的杂文、小说和诗歌广为人知。但遗憾的是,他的翻译家身份却鲜为人知。根据穆雷对两岸四地共计686篇翻译类博士论文进行的计量分析,在62篇涉及中国翻译家/者的研究论文中,仅有一篇《近现代闽籍翻译家研究》对其翻译家身份略有提及,但也未作详实的介绍与分析。[1]纵观国内翻译研究领域,郑振铎的翻译成就与思想理论并未引起重视。那么,他的翻译实践以及理论是否有研究的价值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一、翻译的初衷
郑振铎出生于浙江永嘉县(即温州),该地曾被帝国列强辟为通商口岸,这为他从小接触外国传教士和商人提供了种种机会,进而接触了欧美文化。他的翻译事业起步于“五四”时期前后,在其北上求学期间,结识了当时国内众多进步人士,他们常常就政治、文学与人生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这段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翻译目标文本的选择。例如,在北京读书期间,郑振铎常常会去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并在此认识了俄国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据他回忆,“在那里面,有契诃夫的戏剧集和短篇小说集,有安特列夫的戏曲集,托尔斯泰的许多小说等。我对之发生了很大的兴趣。”[2]215并且“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2]243由于当时国内时局动荡,郑最初的翻译目标多集中于社会与政治方面的文章,文学仅列其次。19世纪20年代初,他逐渐把精力投入新文学运动,翻译也随之集中于文学作品。[3]421他倡导现实主义文学观,主张“为人生”的文学思想,用他的话说:“文学必须具有社会问题的色彩和革命的精神”[2]245。这一思想与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大家不谋而合,正如鲁迅晚年也曾说过:“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4]165由于当时国内社会正处于政治文化的巨大转型变革时期,在郑振铎的眼里,“血与泪的文学”比起鸳鸯蝴蝶式的情诗情文更能激励爱国青年及革命家的情绪,刺激冷漠大众的内心。陈福康认为郑振铎的这一文学思想是受俄国进步文学运动的影响:相比于西方各国的现实主义,19世纪后期俄国的现实主义在社会责任感、倾向性、功利性和战斗性等方面更贴近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3]106正是基于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郑振铎积极投入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同时,郑振铎捕捉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诗歌中对自然与人世美好的歌颂,对暴力的憎恶和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因此,他还较为系统地选译了泰戈尔的诗集。此外,郑振铎还译述了部分希腊、罗马的神话寓言,也是出于希腊神话中充满着对立面的斗争和被压迫者“反抗的调子”[3]442。但当时的中国,大多数民众仍囿于封建主义思想,对本国文化自视甚高而贬低外来文化,对翻译作品嗤之以鼻;或是一味沉溺于言情侦探等脱离社会现实的翻译小说,这也使得许多翻译者为了迎合读者口味而迷失了方向。不同的是,郑振铎从一开始便明确了“为人生”“为现实”的翻译初衷与目标,他总是谨慎地选择翻译作品,力求在思想及艺术方面给予中国读者以激励与启示,这种坚定的精神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不断加强,未曾偏移。
二、翻译的地位
19世纪末,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迷茫困顿的中国人民亟待精神的宽慰与救赎,林纾所译的西洋小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乘势而出,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尤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受到“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感召,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为中国翻译家翻译西方著作提供了便利。然而,翻译事业的盛行却受到了一些文人的抨击,例如郭沫若在写给《时事新报·学灯》主编李石岑的一封信中,便提出了著名的“处女媒婆论”:“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女;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生产。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 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郭沫若的此番言论立即遭到了茅盾、郑振铎等人的批驳。茅盾曾撰文写道 “翻译之难绝不下于创作”[5]421,不应受到贬责;郑振铎也针对性地发表了文章《处女与媒婆》,对于翻译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肯定:“我们看文学,不应当只介绍世界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创造,自然也很有益处。就文学的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有多一个慰藉与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6]487可见,在郑振铎看来,翻译不但与创作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更在文化思想层面、文体形式层面,为国内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流,使之焕发新的生命。“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造丰富而有力,绝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家散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如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的所有努力做去的。”[7]193
正如郑振铎所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凭借其简短的形式、清雅的文风、自由的意境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掀起了小诗的创作风潮,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郭沫若、冰心等人的早期诗歌创作便受其影响。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具有深远的影响与意义。
三、翻译的方法
郑振铎的翻译理论虽未成专著,多散见于各类文学报刊中,然而,他对翻译理论也做过较为系统客观的分析评述,值得后人借鉴。
(一)文学可译性
文学是否可译,是翻译研究领域争论最为激烈的阵地之一。19世纪20年代初期,郑振铎与沈雁冰、沈泽民两兄弟就曾对此问题展开过辩论。沈泽民持有文学不可译的观点,他认为原作的生命在于作者的“情绪”,而情绪受作者的生活感悟、激情与灵感左右,译者仅能隔着文字的体悟,在这过程中“文中的情绪要损失不少”。再者,随着翻译,作品所处的特定环境在语言与时空的多重转变下,精神气质也随之改变。[8]然而,郑振铎坚持“文学绝对可译”。其一,文章的“风格”(style)是作者思想的“表白”(expression)或文字化,人类的思想是共通的,因此,风格也是可以转移的,并非“乡土的”(native)或“固定的”(original)。其二,译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译”,思想必然无法与原文“一样的充分而且好看”,“但一个艺术极好的翻译家,确能把译文的思想弄得与原文一样的美”。其三,在诗歌可译性的问题上,虽然诗歌的韵律在不同文字间无法转嫁,但是诗歌的情绪与韵律是分离的,由其对于散文诗而言,完全不受韵律的羁绊。可见,就郑的观点来看,“文学中最主要的元素是情绪”[7]49,作品的情绪与文字相互依赖却又能够独立分割,因此情绪能借由不同的文字得以转达。
(二)文学书的译法
郑振铎在A.F.Tytler的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过三大翻译法则。
法则一,译文必须能传达出原作的意思。译者除了在语言文字方面应具有较高造诣以外,还需对原文的背景等有充分了解。再者,译者有相对的自由,即在不影响原意,且能赋予原文“更伟大的力量的意思”的前提下,译者有增减原文的自由。[7]60这不失为一个大胆的提议,一方面能够纠正原文中的部分错误,更重要的是赋予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下更顽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诗歌翻译中,避免了为保持原诗的结构和韵律等而束手束脚,造成译文晦涩拗口。但此种译法也容易置译文于危险的境地,毕竟是否增减,增减的程度多是依靠译者的主观判断,稍有差池,就会造成误译。
法则二,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7]64这要求译者在忠实原意的基础上,要能够准确把握原作的风格。倘若说作品的文字内容好比骨骼或皮囊,那么风格便是灵魂和神韵。它可以是清新寡淡、严肃庄重的,也可是鲜艳华丽、浓烈激昂的。翻译就像在临摹一幅人物肖像,如果仅仅追求表象的相似,而混淆甚至曲解了神韵,那注定是一幅败笔。能否实现这一法则,郑认为“与译者的天才有关系,与他的趣味也有关系”[7]66。另外,郑振铎考虑到:在“有移植不可能的地方”的情况下,“则宜牺牲这个风格与态度的摹拟,而保存原文的意思。……或以意译为高。”[7]67
法则三,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由于翻译是跨越地域、语言、历史、文化的语言行为,原作中的意识形态,尤其涉及到道德、情感等抽象概念是很难在译文中得到完全切合的再现。例如原文中某个场景的意境,某段历史之于国家民族的深远意义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是非常困难的,正因如此,流利成为郑振铎认为难度最高的一项法则。真正的流利就是“他(译者)必须采取原著者的精神,由他自己的官能里说出来。”[7]68也就是在不背叛原作内容和风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做出适当改变,使译文成为读者熟知或易于理解的内容。
(三)其他问题
郑振铎还就翻译若干问题公开发表过见解。
重译的问题。当年,国内小语种文学书大多经由“二手”的译本,重译必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前文提到的文章的“风格”“流利”等要素,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辗转,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文的风貌。为何重译问题突出却在当时如此盛行?郑振铎归因于“中国现在从事文学的人之稀少……从事文学翻译的只有那一部分通英语的人。……其余通外国文的大多数的人对于文学的兴趣,是如何的薄弱。”[7]73为此,郑振铎更是哀叹“中国人之迟钝麻木”。然而,在缺乏翻译人才,外国文化思想又急为国人之所需的客观事实面前,重译确是无奈之举。因此,郑振铎对重译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择译本里最可信的译本来做根据”“如译本有两本以上时,应该都搜罗来,细细的对照一过”“译完后,应该叫通原本的文字的人校对一下”“若各本间有大不同的地方,在重译本也应特别的注出”。[7]76
在翻译的选材上,郑振铎认为,翻译英美杂志上的新创作实为无意之举,因为“自文学在英美职业化以后,许多作家都以维持生活的目的来作他们的作品,未免带有铜臭,且也免不了有迎合读者心理的地方”,因此“不宜乱译”。再者,并非所有的名家名著都适合在这个特殊时期拿来翻译,郑振铎就曾疾呼“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吧”[6]491。此番言论恰恰呼应了他“为人生”的文学精神,也为当代译者敲响了警钟。面对当今的翻译市场乱象,译者在选择文本时,除了考虑自身的兴趣与需求之外,更应时刻牢记国家利益以及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语体欧化的问题上,郑振铎也提出异于他人的见解,较之众多贬责语体欧化、称其破坏国文体系的反对声而言,他认为“语体文的欧化是求文学艺术的精进的一种方法”[6]414。所谓的“翻译腔”并非一无是处,它或可为丰富本国文化,提供新的语言素材。
综上,郑振铎的翻译理论及其成就,助推了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传播,启蒙了一大批立志用笔唤醒国人的青年文学创作者,其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不容忽视。同时,更值得大家学习的是,相比于其他打着“为文艺”“为解放个性”旗帜的翻译者,郑振铎一生的翻译事业,无论从选材、立意到目的始终站在“人生”“现实”与“国家”的高度,这样的境界和勇气是值得后辈敬仰与学习的。
[1] 穆雷,邹兵.中国翻译学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分析(1992—2013)——对两岸四地近700篇博士论文的考察[J].中国翻译,2014,(2):14-20.
[2] 郑振铎.黄昏的观前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3] 陈福康.郑振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 鲁迅.鲁迅经典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2009.
[5] 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7] 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十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8] 任淑坤.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以五四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J].河北学刊,2010,(5):175-178.
【责任编辑 贺 晴】
Zheng Zhen-duo’s Translation Spirits and Theories
ZHOU Xin-y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Zheng Zhen-duo is a famous scholar, writer, literature critic in modern China. However, his great contribution in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is seldom mentioned.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systematic researches related. Based on Zheng’s practice and published opinions, this paper sums up and evaluates his spirits and theories on translatio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at is, translation aims, status and techniques.
Zheng Zhen-duo; translation theories; translation skills of literature
I046
A
1009-5128(2015)04-0057-03
2014-09-26
周心怡(1985—),女,福建福州人,闽江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