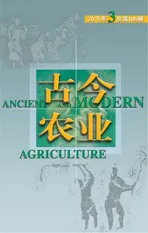由副食到主食:从马铃薯的本土化看其主粮化的前景
2015-03-20陈桂权
陈桂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190)
由副食到主食:从马铃薯的本土化看其主粮化的前景
陈桂权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190)
基于马铃薯本土化的经验可看出,技术的进步是马铃薯在中国种植范围全面扩展的关键。在我国以谷为主的饮食习惯中,马铃薯由副食到主粮地位的转变加工方式的进步是关键;产业的合理布局、政府的正确引导又是推动马铃薯种植业优化发展的重要保证;育种、栽培技术的进步则是提高产量、质量的基础。从世界经验及马铃薯自身的优势看,其主粮化的前景广阔且意义重大。
马铃薯;主粮化;本土化;饮食习惯
马铃薯这种原产美洲的旱地作物,自从18世纪中叶在中国传播后[1],便以“高产”、“易种”,“便食”的优势迅速地在我国西南、西北等高寒地区扎根下来。后来,随着品种的纯化与改良,其种植范围开始扩展;新中国后,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其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在我国作物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同其他原产美洲的高产旱地作物一样,马铃薯的引种与推广对我国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作物亩产,促进了山区的开发,为区域商品经济的流通打下基础,并为人口的增长提供支持。[2]但是,与玉米、甘薯相比,马铃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种植范围相对有限的。这主要是因其生物属性所限,后来在政策引导与技术改良的推动下,其在我国的种植范围才推广开来,并形成“北方一季作区、中原二季作区、南方秋冬季作区、西南单双季混作区”[3]四大种植区域。截止2010年我国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已达到“450-500万公顷,占农业播种面积的3.03%(蔬菜占农业总面积的10.53%),占世界马铃薯总面积的20%-25%,总产约占18%,占亚洲的70%,人均占有量45.8千克,人均实际消费量32.1千克左右”[3]。在世界范围,马铃薯是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大农作物,尤其是在欧洲跟北美地区,其充作主粮的历史悠久。据统计,欧洲人每人年平均食用马铃薯80-100千克,可见其在生活中之重要。[4]鉴于马铃薯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联合国将2008年定为“国际马铃薯年”,并确定马铃薯在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的马铃薯种植历史虽不算悠久,但近半个世纪的经验积累与技术进步使马铃薯种植业发展迅猛,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一大马铃薯生产国,年产量保持在7000万吨以上,且增产空间巨大。2015年1月7日,农业部召开“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研讨会”,开启马铃薯主粮化之路。[5]这一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强化马铃薯在我国作物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对农业经济结构及社会饮食习惯均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以马铃薯本土化经验为借鉴,来阐释其主粮化的前景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一、“洋芋”到“土豆”[6]:本土化的历程与特点
目前,学界对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年代、路线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7]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对外文化、技术交流的历史特征看,马铃薯进入中国或也经历了多途径,多次引种的过程。虽然,引入年代未可定论,但其在国内开始扩展的时间是可推至18世纪中叶以后的,[8]其分布的范围也主要集中于西南、西北等高寒、贫瘠之地。马铃薯因其生物学特性,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传播链短,传播容易中断,传播路线难以描绘”[9]的特点。马铃薯本土化的过程相当漫长,从18、19世纪的引种,自然栽培,到20世纪早期的品种改良与推广,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规模种植。期间经历了长期反复与蜕化的过程,最终在全国扩展开来则得宜于品种的改良与栽培技术的进步。下面分阶段概述马铃薯本土化的历程。[10]
(一)早期引入与局部种植(18、19世纪)
18世纪后各地方有关于马铃薯的记载频现于方志中,主要集中在云贵川、陕南、甘南、山西、湖北等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山区成为其主要的种植基地。据何炳棣的统计,19世纪的方志中,四川有15条,陕西有7条,湖北有12条与马铃薯相关的记载[11],这些地方多是山区。马铃薯种植的这一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其生物特性所决定,若在低海拔地区种植,其在无性繁殖过程中会出现严重退化现象,传播过程中绝种也时有发生,[12]故早期在南方亚热带低处引种失败,而当移民将其带入西部山区,[13]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其他作物不宜生存,反到为马铃薯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所谓“其深山苦寒之地,稻麦不生,即玉黍亦不殖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14],“高山冷处咸莳之”[15]。此阶段马铃薯的种植多为自然引种,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较强,“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而种植技术方面虽“不费耘耕,不烦粪壅”亦可结出累累硕果。[16]
(二)改良与推广:设种于田(20世纪初期-30年代)
20世纪后马铃薯的传播进一步扩展,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一,随着西方农学知识的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译介国外马铃薯栽培相关知识。罗振玉在这方面贡献颇多,先后翻译《论薯种》、《马铃薯栽培法》、《爪哇薯制酒精法》、《简易淀粉制造法》等文章传播马铃薯栽培与加工方面的技术知识[17];其二,国门洞开之后,大量外国人进入不但带来了新的品种,而他们以马铃薯为主食的习惯客观上也推动了马铃薯在中国的种植,如民国《辽阳县志》记:“近因日本人用为佐餐常品,种植宜多”[18]。齐如山在《华北农村》中也说:马铃薯“清末天津种者已很多,因天津外国人多,消此亦很多也”[19]。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沿海城市、西南、西北及华北已经形成比较集中的马铃薯产区。[20]1932年时,山西省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已达131.7万亩,总产量49690万公斤,位居全国之首[21]。1936年全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540万亩,亩产375公斤,总产量在20亿公斤以上[22]。
(三)品种与选育:本土化之关键(20世纪30-40年代)
20世纪30年代在农业改进的大背景之下,管家骥率先主持马铃薯的改良工作。1934—1936年间,他通过收集地方品种,引进英国、美国良种的方法,从数十个品种中选出4个优良品种,并在江苏、陕西、河北等地推广示范,亩产均在500公斤以上。之后,他又发表《我国马铃薯之改进》一文,详细总结了其在各地试验推广的经验,并介绍了我国马铃薯优势品种与改进方法,[23]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各地农业改进所也立足本省实际情况,展开马铃薯的改良工作:姜诚贯在贵阳进行马铃薯两季栽培试验,并根据当地气候特点总结出应选用休眠期短的品种、适时早播、防治病虫害等技术要领;[24]杨鸿祖从苏联引进16个马铃薯野生种,在成都将其与栽培种进行杂交育种试验,并在彭县高海拔地区成功选育以小乌洋芋为代表的37个天然种和峨嵋白洋芋等18个杂交种,从中进一步选育出24个产量较高的优势品种;[25]西北地区,王绶、宋玉墀在陕西试验推广良种,选出优良品种——七百万,亩产可达583公斤,在武功、西安、耀县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26]1943—1945年,川、黔、陕等传统种植区都在进行马铃薯杂交品种的选育工作,先后多次从英美等国引种,并选育出适合中国种植的优良品种:“七百万”、“胜利”、“西北果”、“火玛”、“红纹白”等一系列杂交种。杨鸿祖在此基础上于1947年育成“292-20”号良种,此种具有丰产性好、抗病毒性强、防晚疫病等优点,后来在黑龙江、内蒙古、山西等地区大范围种植。[27]这一时期,因马铃薯高产的特性,使其成为战时粮食供应的重要保障,无论是在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日占区,马铃薯均得到官方重视,种植面积也进一步扩展。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当时在马铃薯的品种选育、栽培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技术成就与积累的经验,为50年代以来我国马铃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全面发展:品种、产量、种植规模(1949年以来)
20世纪50年代为应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作为救荒作物的马铃薯再次被农学家号召“多种,抢救春荒”[28]。当年全国的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2300余万亩,但翌年因天气原因,诱发晚疫病使得东北、华北、西南马铃薯主产区减产严重。为此农业部于1952年组织“马铃薯疫病专题训练班”向各地技术人员传授防病、治病措施,并将所讲技术内容通报全国。在良种选育方面1950年,农业部便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良种,共采集567个地方品种,从中比较整理出36个优势种,其中以四川高抗晚疫病的“巫峡”、“丰收”、“多子白”,耐旱性强的“火玛”,品质优异的“乌洋芋”;吉林抗虫性好的“延边红”;广东耐高温,防退化的“兰花”;江苏抗退化的“上海红”等优势品种为代表,它们为后来的杂交育种提供了优良的亲本材料。[29]这一时期我们马铃薯种植事业迅速发展,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576万亩,总产量达到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90%和193%。[30]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马铃薯种植的面积大致经历了:第一,50-70年代的发展,由1950年的2339万亩到1970年的5200万亩;第二,1970至1985年的下降:面积由5200降至3716.3万亩,主要是因当时政策对农业生产布局的调整,由于单产的提高,种植面积的下降并未影响到总产量;第三,1986年至2000年面积逐渐回升,由1986年的3764.9万亩升至2000年的7085.1万亩。马铃薯的种植已经遍布全国,北方一作区和西南混作区为主产区,播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0%以上。[31]2000年以来,中国的马铃薯产业经历了又一轮的调整期,种植面积也有所起伏,2000年至2003年种植面积下降,2003至2005年,又有所回升,2006年则急剧减少,此后,便呈稳步上升的态势。
总之,经过400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在技术改进与政策鼓励的双重因素作用之下,截止2010年在我国粮食生产结构中马铃薯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稻、玉米、小麦的第四大粮食作物,[32]且其未来发展潜力依然巨大。
二、“菜”或“粮”:马铃薯在我国食物结构中的地位
就马铃薯而言,虽然今天的相关著作中多将其定义为“一种兼具粮、菜”的作物。但它这样的双重身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及不同的人群间,都会各有侧重。在我国食物谱系中马铃薯的主要功用,曾被吴其濬精当地概括为“疗饥救荒,贫民之储”[33],其亦基本如此:
(一)接济正粮之杂粮
杂粮是相对于主粮而言,在我国杂粮的范畴也是在不断的变化。最早“五谷”之外的粮食为杂粮,明清以来稻、麦以外皆称杂粮。“补种杂粮”往往多是在正粮歉收的情况下的一种接济措施。这类例子在官方救灾文件中是经常出现的,如雍正二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在向皇帝奏报地方“粮食收成事宜”的折子中这样说道:“湖北沔阳、天门、潜江、江陵四州县,沿江受水之乡,各令补种杂粮以资接济,事关地方收获。”[34]又乾隆元年,皇帝在指示江南、江西地方官员善后水灾事宜时,亦道:“被灾之家,俯仰无资,甚可怜悯,所当加意抚绥,毋令少有失所。其水势旋即消退之地,固可补种杂粮”[35]。马铃薯充作粮食时,也是杂粮,固其亦为正粮之接济,如同治湖北《施南府志》记:“郡在万山中。近城之膏腴沃野,多水宜稻。乡民居高者,恃包谷为正粮,居下者恃甘薯为救济正粮。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定丰歉。民食稻者十之三,食杂粮者十之七。”[36]由“定丰歉”三字不难看出马铃薯对于地方粮食生产之重要。如马铃薯、甘薯这般食根茎类的作物,虽是杂粮但在主粮缺乏之情况下也是人们主食的选择,如宣统《甘肃通志》称:“洋芋,生坡地,可作谷食”[37];民国《霞浦县志》记:“今民间食米十之二,食薯十之八,虽曰杂粮,其效用过之,因改列谷属”[38]。这两则材料透露给我们这样两条信息:其一,谷类作物为主食的观念是根深蒂固,薯类因其在当地食物结构中的重要性亦被划入榖属;其二,作物杂粮的薯类也可充当主食。
(二)山民、穷人之粮
马铃薯早期引种至我国南方亚热带平原地区,因对环境的不适应,种子退化现象严重,种植失败,其真正成功扎根下来,则是在进入西部高寒地区之后了。清代移民的活动成为了作物传播的重要载体,地区间的作物通过移民的流动发生了广泛的交流,尤其是美洲高产作物的扩展与移民的关系更是密切。清康乾以来,东南沿海过剩的人口西迁入内陆,在长江流域的开发由腹地向边缘扩展,进入川陕甘鄂交界的秦巴山区。美洲作物则成为移民开发山区的重要粮食来源,这些移民若暂居山中就被称为“棚民”,若定居下来数代之后则成为“山民”。马铃薯因其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便成为山中居民的主要粮食之一。如,道光陕西《宁陕厅志》卷一:记:“洋芋,此种不知所自来。山多种之,山民借以济饥者甚众。”同治湖北《宜昌府志》记:“山居者……所入甚微,岁丰以玉黍、洋芋代粱稻。”[39]《房山县志》:“洋芋产西南山中。……至深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40]。光绪时人童兆蓉在调查陕南山区的民生情况后,对当地居民多以洋芋为主食的习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耕,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41]。山区因气候的原因,使得农作物的分布也具有垂直地带性的特点。就玉米、甘薯、马铃薯三种高产作物的分布来看,马铃薯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更强,因此那些高山、高海拔地区当玉米、甘薯无法种植时,马铃薯发挥了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成为山民们果腹的无奈选择。光绪陕西《佛坪厅志》:记“低山种包谷,高处只宜洋芋、苦筱”;《凤县志》:“高山险僻宜洋芋”;《洋县志》也称:“山顶老林旁,包谷、麻豆清风不能成,则种苦荞、燕麦、洋芋”。地处秦巴山南麓的四川南江县“山坡地”种洋芋,“一亩尝挖芋十余石”;低地种红苕;“洋芋尤为山民食料所资”。[42]除山民之外,以马铃薯为主食的另一大群体便是贫民。同治时在四川北部的城口地区,洋芋是贫民的主食。[43]光绪湖北《大宁县志》中称:“洋芋……邑高山多种此,土人赖以为粮。邻县贫民来就食者甚众”[44]。民国时甘肃文县“虽颇产米,而大米不用为常食,麦亦珍贵而不普通。一般农民以洋芋、包谷为主要食品。”[45]贵州镇宁县城乡饮食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城中食粮以米为主,间有包谷磨粉和米蒸食者,但为数不多。至乡间民众食米者甚少。中等人家即多杂食苞谷;贫苦农民则多纯食苞榖、荞麦或甘薯、马铃薯等”。[46]1924年许珂在《可言》中总结了南北贫苦人群的日常主食是“南为薯芋,北为玉蜀黍;南之佐以豆,北之佐以黍、稷者则仅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铃薯作为粮或菜的角色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正如曹玲所总结:“清代,在土地贫瘠的山区,传统作物无法生长,它们以其强大适应性迅速成为山区人民的主粮,马铃薯在高寒山区意义更为重大,成为山农的重要食料。在平原地带,稻麦处于主粮地位,玉米、番薯作为辅助杂粮,马铃薯主要用作蔬菜。进入二十世纪后,玉米则成为北方农民主食,加之农民日益贫困化,以杂粮为主食的贫民比重增大,马铃薯这类粗粮成为贫民的主食。”[47]1936年王绶在《中国作物育种学》中这样描述马铃薯在当时的地位及未来价值,他说“马铃薯在我国食用作物中,尚属幼稚,除北部数省有大规模之栽培外,余则当为园艺作物。但马铃薯为极有价值之作物,不但产量丰富,可以避荒,并可制造他种工业产物,如淀粉、酒精等,故极应提倡改良,以应需求。”[48]可见,进入现代社会后马铃薯的经济价值也开始被人们所认知并提倡。
(三)“以谷为主”食物谱系下的蔬
中国的食物结构特点是“以谷为主,多元为辅”,长期以来“五谷”:稻、黍、稷、麦、菽等粒食作物是汉民族的主食来源,而食根茎类作物,如芋、藷芋等则是主粮之外的主要补充,如《史记货值列传》记:秦破赵后,迁卓氏于蜀,卓氏曰“吾闻岷山之下沃野,有蹲鸱,至死不饥”。其所言蹲鸱便是芋头。从人类最早对食物的利用看,根茎类的作物是主要来源之一,而后来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种植取代采集后,在人类的食物谱系中根茎类食物,则退居次要地位,仅成为灾荒年景的保障或穷苦人的无奈选择。这点在我国的食物谱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谷类作物长期以来是人们主食的首选,其座次虽经更迭,但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南方以米为主、北方以面为主的特色已成为一个刻板的文化烙印根植于大多数国人的印象中。虽然,齐如山曾纠正“中国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这一笼统的概括,他说:“南方人吃米,是不错的,可以说是绝对的吃米,虽然偶尔也有些面食,然不过是点缀品;北方人吃面则不然,大多数的人一年中难得吃一次白面(小麦面)。北方人吃的是杂粮。”[49]何谓杂粮,齐如山称“各种粮食也”。而从他列举的杂粮种类看,绝大多数仍是榖类作物。这也正是我国“以谷为主”的食物特点的写照。自宋元以后谷物中的水稻、小麦便占据了前两名的位置,大麦、黍、稷、粟、菽、麻居其后,也有一定份额。[50]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到19世纪中期,在美洲作物玉米开始在北方旱地与南方山地广泛种植后,才逐渐有所变化。另一种高产美洲作物甘薯,虽较早地进入农学家的视野,但其却未能跻身“榖”类,而是被认作蓏类[51]。所谓:“木实曰果,草食曰蓏”[52]。在中国古农书体系中最后一部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之“榖种门”中各榖类作物的顺序是:“稻、梁、稷、黍、粟、麦、豆、麻”,而甘薯则编入“农余门”之“蔬部”[53]。虽然,书中尚未见马铃薯的踪迹,但作为与甘薯同类的食根茎作物,且此时其种植规模远不如甘薯,若被著录,其地位亦不会出甘薯之右。在成书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另一部大型农书《三农纪》中玉米已被收录于“谷属”,而甘薯则列于“蓏属”之下。若按照张宗法这套分类标准,马铃薯也只能属蓏类食物。民国时甘肃天水地区的人民也是把马铃薯视为菜蔬,而且将其称为“蹲鸱”,[54]即芋头。将马铃薯类比芋头,可见当地人对马铃薯属性及功用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农学家金善宝曾就马铃薯在中国食物中的地位做了这样一段评价,他说:“马铃薯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作物,它在食用作物方面只占着次要的地位。西北诸省如山西、察哈尔、北满和南满在食用上比较重要,但亦不能与小麦、小米比拟。长江流域,马铃薯只有零星的种植,并没有大量生产,所以它的用途只是限于蔬菜方面”[55]。后来,马铃薯种植规模虽有大幅度提高,食用方式也更为多元化,但其在食物中的地位却并没得到太大改变。
所以说,从整体上看,在我国以谷为主的汉人饮食文化中,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及大部分地方马铃薯多被视为是菜蔬或主粮之补充而已。
三、从“菜”到“粮”:马铃薯的主粮化
2015年1月,农业部正式提出“马铃薯主粮化”的战略,称:“今后要通过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力争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使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单产水平、总产量和主粮化产品在马铃薯总消费量中的比重均有显著提升,让马铃薯逐渐成为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我国第四大主粮作物。预计到2020年,50%以上的马铃薯将作为主粮消费”[56]。之所以选择马铃薯作为第四大主粮,这与它本身的优势有很大关系。农作物能成为被广泛人群所接受的主粮,至少需满足如:产量保证、营养支持、种植面积、食用口感、易于储存等基本条件。以此比照马铃薯,不难看出其是合符要求的。而且,马铃薯适应多种耕作制度,栽培时间长,不与其他作物争地等特点都是其成为主粮作物的优势所在。当然,由蔬菜或杂粮变身为主粮并不是件易事,这个过程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大众的饮食习惯
在欧美地区马铃薯充当的是主食的角色,其高产的特点使在同等单位面积上种植马铃薯的收获量远高于其他作物,而其廉价的优势,又让它成为贫苦大众度日的首选。所以,在欧洲西北部高寒的天气,贫瘠的土地使小麦等其他作物无法生存,只有马铃薯才能适应当地恶劣的环境,成为人们维持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故有人曾说:“马铃薯改造了欧洲”,足见其作用之大。在我国马铃薯引入较晚,且因其生物属性所限,早期的种植区域也相当有限;加之,以谷为主的饮食习惯,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追求,使得米、面这般细粮成为广大民众所向往的,而玉米、红薯、马铃薯这些杂粮、粗粮也只是贫苦人餐桌上的常品而已。即便如此,在杂粮中马铃薯的地位也远远不及玉米、粟、高粱、大麦等榖类,其多数时候也就扮演着菜蔬或零食的角色而已。虽然,扩种面积、提高单产也是马铃薯主粮化的内容之一,但主粮化的核心是如何使它成为人们日常餐桌上选择的主食之一。因为,种植面积、单产等方面看,马铃薯早就成为仅次于水稻、小麦、玉米的第四大作物,[57]但这些只是它成为主粮作物的必要条件,其要以怎么的形式才能让人们接受才是关键所在。在食用方面,马铃薯“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烹饪方法也较多样,“羹矐煨灼,无不宜之”[33]。具体而言,“一,整个煮熟当饭食之,切成细条炒之又能作菜;二,搀以筱面蒸而食之,或烙之均可;三,磨烂后沥成粉面,少加白馨能制成面粉及粉条,面粉与藕粉相似”[58]。也就是说,传统方法中马铃薯充当主食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煮食或做成土豆饼;其深加工方式是做成土豆淀粉,再制成粉条,这一加工过程会使其丧失很多营养成分且成本较高,而粉条之类的成品也不宜作主食。显然,马铃薯这种充当主食的传统做法是不太符合大多数人饮食习惯的,偶尔一餐尚可。故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中强调将它“加工成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产品,实现其由副食消费向主食消费转变、由原料产品向产业化系列制成品转变、由温饱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变”[59]。将马铃薯加工成面食对于其主粮化是有益的,只是经过加工后的马铃薯面食能否既保持营养价值,又兼顾口感,便成为主要解决的问题。食物的口感好坏是其能否成为广泛主粮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小麦的本土化过程的早期便因不当的食用方式制约了其在食物中的地位,后来加工方式的转变才使得它变成人们乐于接受的主食之一。[60]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铃薯主粮化,并不等于以马铃薯为主粮,而是要在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之一,再寻马铃薯作为第四大主粮,其主要目的是着眼粮食安全,丰富主食选择。宏观层面的政策支持有助于产业的发展,但真正能否为大众接受,加工成符合饮食习惯的食品也十分重要。
(二)生物属性缺陷与技术应对:退化、疫病、储存、加工等
马铃薯的“退化现象”是指当在南方气温较高地区种植时其产量往往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老百姓形象地总结为“一年大,二年差,三年结个小疙瘩”或“一年好,二年小,三年不见了”。退化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制约马铃薯在我国种植范围扩展的首要因素。在农学界对于如何解释马铃薯的退化现象,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衰老说”,即生物不可避免的有机衰老;其二,“生态说”,高温环境导致退化;其三,“病毒说”,病毒感染有机体,并遗传给后代。我国科学家通过系统地研究认为病毒浸染是马铃薯退化的主因,高温环境则是病毒复活的助因,所以南方平原地区的马铃薯退化尤其严重。20世纪50、60年代,以杨鸿祖、林传光、林世成、程天庆为代表的农业专家,通过大量系统地研究正确地指出马铃薯退化问题的根源,通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与发展,如今马铃薯退化问题可通过二季栽培、培育实生种薯、种薯脱毒等方法得到较好的解决。但是,在我国马铃薯种植中脱毒种薯应用面积小,2011年时仅占总面积的20%左右,[61]进一步推广脱毒种薯是防病、防退化、提高产量的重要工作。
病害是马铃薯种植的最大威胁之一,影响马铃薯的病害很多,如早疫病、卷叶病、黄斑病、晚疫病、黑腿病等,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晚疫病,世界农业史上的灾难“爱尔兰大饥荒”的祸魁便是它。我国马铃薯病害最严重的是过滤病与晚疫病,过滤病毒之中又以卷叶病最为严重,其几乎出现于我国每个马铃薯产区;晚疫病则在西南云、贵、川等省份最为严重,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也较为多出现。[62]针对马铃薯抗病害的研究于1943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恰逢美国专家戴创兹受聘来华,在管家骥、杨鸿祖、姜贯诚等国内专家的陪同下,戴创兹先后考察四川、贵州、陕西、青海、甘肃等马铃薯主产区后,确定卷叶病是影响我国马铃薯的主要病毒,并制定了建立无病种薯繁殖区、实行供应种执照、开展杂交育种等防范措施,[63]如今在防治马铃薯病害方面,已经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技术,基本措施主要有三:一,选择无病种薯,可通过建立无病繁殖区或种薯脱毒的方式实现;二,从无病害的北方产区引入优良种;三,应用二季栽培种薯,即“翻秋制种”。
储存是马铃薯从生产到消费过程的重要环节,马铃薯含水较多、抗挤压性弱,且集中堆放下层马铃薯在缺状态下的呼吸极易引起腐坏。我国马铃薯每年大概有10%-15%在存储中腐败,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减少马铃薯在储藏中的损失,需满足低温、通风两个基本条件。低温可降低呼吸作用,通风则是为了提供充足的供氧以减少无氧呼吸产生的酒精。另外,化学技术(防腐药剂的运用)、生物技术(培育易储存的品种,杂交育种或利用转基因技术)均能减低马铃薯在储藏中因腐烂而引起的损失。即便如此,马铃薯的生物特性决定了其在储藏方面不如三大主粮便利,故这方面的研究仍需深入。
加工方式的转变是马铃薯主粮化的关键环节。传统的马铃薯食品加工技术主要有:简单加工,如马铃薯泥、马铃薯片;深加工的各类淀粉制品、灌装食品、膨化食品等。正如前文所分析,传统加工方式所制成的马铃薯食品均不宜作主粮。而欧美以马铃薯作主粮的国家,他们多数的是直接食用,既不损失营养、又方便食用。只是,直接食用马铃薯并不符合我国多数民众的饮食习惯。故改进加工技术将马铃薯制成面粉类食品是其在我国主粮化的必然选择。欧洲国家如英国,在这方面有技术可兹借鉴,我国农业科学院也正在研发这一技术。未来的马铃薯加工技术必会有大的革新以适应其主粮化。
另外,马铃薯的转基因问题,也是其主粮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农作物中,转基因马铃薯已经相对成熟,带来了如高产、抗病、防腐等优势。虽然,德国一家公司已于2011年11月向欧盟申请批准其种植世界上第一个以商业为用途的转基因土豆——Fortuna,主要为人食用,也可为动物食用。[64]但是我国明文规定,禁止主粮作物转基因商业化。马铃薯过去不是主粮,其在“转与反转”的争论中的地位并不显著,可如今其既要充作主粮,且在国内“谈转色变”的时代背景,及技术发展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如何处理马铃薯的转基因问题,仍需审慎。
总之,技术的发展使我们能够解决原来那些制约马铃薯种植的诸多问题,只是这些技术手段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因为技术发展是一个不断异化的过程,旧问题解决的同时,新问题又产生了;另一方面,有些问题因操作执行中的偏差,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尽量优化而已,如马铃薯储存的问题。因此,主粮化战略提出后,为实现马铃薯单产、总量、面积的全面提高,技术更新仍旧关键,培育优势品种尤为重要。
(三)产业布局及地方经济
2010年以来,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均稳定在8000万亩左,2013年全国马铃薯总产量达8892.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24.2%,中国已成为全球马铃薯第一大生产国。但是,因为缺乏引导、社会资金无序进入,种植户盲目扩种,生产质量不高,导致销售时价格起伏明显,滞销、低价的现象频发,形成“农业周期律陷阱”,严重制约了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如今,实施主粮化战略后,政策方面对于马铃薯的种植必有更多支持,也将会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马铃薯生产、加工领域,如何调节供需间的平衡、避免价格大幅度波动、防止薯贱伤农现象继续出现,都是主粮化后我国马铃薯产业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加工环节,缺少大型龙头专业加工企业,马铃薯转化利用率低。主粮化战略实施之后,不仅要提高传统加工转化率,也还要开发应用将马铃薯加工成面食的新技术,同时,专用薯类的加工也需加强。
从我国产区分布看,西南、西北、东北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是马铃薯生产的主要地区。主粮化的提出,对这些地区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各地更应注意结合自身的生产特点,发展特色的马铃薯种植业,而非仅扩种而已。2008年农业部发布的《马铃薯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已经为各产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发展方向。[65]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是西南山区的马铃薯产业问题。从本土化历程看,这一地区的马铃薯种植历史久,但因其多为山区、坡地,种植分散,技术相对原始,对于当地经济,马铃薯给农民带来的收入也不大,仅是维持生计而已。蓝勇曾指出,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进入,使“山区趋向以种植业为主体,而种植业的单一性又较明显,这些作物在平坝地区也能较好生长,山区经济作物多样性的优势难以体现,产业与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水平滞后,使山区经济形成结构性贫困”[66]。这种结构性贫困的根源在于马铃薯等作物生产粗放,同质性高,附加值低。以前“退耕还林”发展大林农业是这些地区摆脱结构性贫困的主要思路及办法。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地区能成为马铃薯优势产区,也正是因为其高寒的气候环境为马铃薯的种植提供了合适的条件。马铃薯的主粮化为这些地区摆脱结构性贫困提供了可能。只是,地方必须转变生产方式,走专薯生产及建立优势种薯培育基地等专业化生产之路,以提高马铃薯的附加值。
四、结语
马铃薯主粮化的战略,从宏观层面而言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从微观层面看亦有助于丰富人们主食的选择。基于马铃薯本土化的漫长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如今我国马铃薯种植的现状,及在技术方面所积累的优势,使其已经具备了成为主粮的基础条件。但是,传统的饮食习惯,马铃薯种植中的病害、退化问题、储藏问题以及整个马铃薯产业的合理布局,这些都是主粮化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将马铃薯加工成既符合国人饮食习惯的馒头、面食、粉条等食品,又不失其食用价值便成为马铃薯变身主粮的关键。当然,如今在提倡健康多元饮食的前提下,马铃薯的主粮化也只是为人们给健康多元饮食多提供一种选择而已。故那些认为主粮化就是要替代传统三大主粮,“顿顿吃土豆”的说法是对政策的误读与曲解。而且随着主粮化道路的打开,在政策的引导下,市场进一步扩大,更多的社会资金将进入马铃薯加工产业,也有助于马铃薯走出“农业周期律陷阱”摆脱“宿命论”的怪圈。
总之,综合考虑所有因素,我们可以很乐观地认为,在未来我国农业布局中马铃薯种植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其主粮化及所带动的相关产业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附记:感谢导师曾雄生先生对本文写作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
[1]关于马铃薯最早引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学界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主要有三种意见,有认为明末,有认为清初,虽然如此,但对于其在中国推广的时间应该是嘉庆朝时,故本文取18世纪中叶为其推广的时间,当无大误。
[2]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A].历史论丛[C].济南:齐鲁书社1985(05):175-223.
[3]侯振华.马铃薯栽培技术[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0:9.
[4]侯振华.马铃薯栽培技术[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0:7.
[5]李慧.我国将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N].光明日报,2015-1-8(08).
[6]马铃薯,在国内有诸多名称,土豆、山药蛋、洋芋、土芋等。此处取“洋芋”到“土豆”偏重于“洋”、“土”二字,重点是强调其在文化上本土化的意义,而非其名称原意,故作引号处理。
[7]以翟乾祥为代表的认为,马铃薯引入时间当为明万历年间,见:《马铃薯引种我国年代的初步探索》,《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第91-92, 22页。谷茂,马慧英,薛世明认为,马铃薯进入中国最早应为18世纪,见:《中国马铃薯栽培史考略》,《西北农业科技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77-81页。就路径而言,多路进入可能性较大,一、东南:由荷兰人带入台湾,再传入广东、福建,再进入江浙;二、西北由中亚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再入山西;三、南路由爪哇(印尼)传入广西,再进入西南云贵川地区。
[8]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A].历史论丛[C].济南:齐鲁书社1985(05):212-217.
[9]丁晓蕾.马铃薯在中国传播的技术及社会经济分析[J].中国农史,2005,(3):14.
[10]此处参考:佟屏亚、赵国磐.马铃薯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35-58中的相关内容。
[11]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A].历史论丛[C].济南:齐鲁书社1985(05):213-216.
[12]民国《南川县志》卷四:“山土产,前独产洋芋,今已绝种,下地亦多腐于地中”。
[13]光绪童兆蓉描述陕南山区马铃薯种植情况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参见《童温处公遗书》卷三。
[14]同治《宜都县志》卷一。
[15]光绪《定远厅志·风俗》。
[16]光绪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三。
[17]佟屏亚、赵国磐.马铃薯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43.
[18]民国《辽阳县志》卷二十八《物产志》。
[19]齐如山.华北的农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169.
[20]佟屏亚、赵国磐.马铃薯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45.
[21]李秉权.乡村生活见闻录[J].农业推广通讯,1944(8):29-33.
[22]唐启宇.战时粮食问题及我国战时粮食管理政策的探讨[J].中华农学报,1938:164.
[23]管家骥.我国马铃薯之改进[J].广西农业,1941(4):295-306.
[24]姜诚贯.贵州省栽种二季马铃薯之研究[J].农报,1944(25-30):297-305.
[25]杨鸿祖,四川薯类作物之改进[J].四川农业改进所简报,1945(9-12):20-40.
[26]王绶、宋玉墀.介绍马铃薯良种——七百万[J].西北农报,1946(2):11-13.
[27]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作物卷1[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45.
[28]金善宝.多种马铃薯渡春荒[N].新华日报,1950-1-14.
[29]佟屏亚、赵国磐.马铃薯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68.
[30]佟屏亚、赵国磐.马铃薯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71.
[31]张长生.中国优质专用薯类生产与加工[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4-5.
[32]胡志全、吴永常、郭晓燕.小土豆大产业:“中国马铃薯之都”产业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11:4.
[33]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六.蔬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144.
[34]《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
[35]乾隆《江南通志》卷首四之一《皇上诏谕》。
[36]同治《施南府志》卷十《风俗》。
[37]宣统《甘肃通志》卷十二《物产》。
[38]民国《霞浦县志》卷十一《物产志》。
[39]同治《宜昌府志》卷五《赋役》。
[40]同治《房山县志》卷十一。
[41]童兆蓉《童温处公遗书》卷三。
[42]民国《南江县志》卷二。
[43]同治《城口厅志》卷十八:“洋芋,厅境嘉庆十二三年始有之,贫民悉以为食,亦多饲猪。”
[44]光绪《大宁县志》卷一《方舆集之风俗》。
[45]李秉璋:《文县要览·社会·生活状况》1947年石印本,第14页。
[46]胡乔:《镇宁县志》卷三《民生志·衣食》1947年石印本,第2页。
[47]曹玲.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对我国人民饮食生活的影响[J]农业考古,2005(3):180 -181.
[48]王绶.中国作物育种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06.
[49]齐如山.华北的农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1-2.
[50]宋应星称:“今天下育民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参见:宋应星著,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乃粒[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11.
[5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之蓏部[M].北京:中华书局,1956:523.
[52]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53]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3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438.
[54]民国《天水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菜蔬》。
[55]金善宝.马铃薯栽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3.
[56]李慧.我国将启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N].光明日报,2015-1-8(08).
[57]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土豆种植面积和总产一直呈稳定上升趋势,种植面积从1982年的367.5万亩增加到2010年的7808万亩;产量从1982年的2382.5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8154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增加了95.3%和70.8%。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土豆生产第一大国。参见:我国土豆产业现状和发展前景[N].期货日报,2012-6-18.
[58]民国《张北县志》卷4《物产志之榖物》,第17页。
[59]土豆能否当主粮[N].中国环境报, 2015-1-29(08).
[60]曾雄生.小麦在中国的扩张[J]中国饮食文化,2005(1):99-133.
[61]杨红旗、王春萌.中国马铃薯产业制约因素及发展对策[J].种子,2011(5):100.
[62]金善宝.马铃薯栽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0:65.
[63]佟屏亚、赵国磐.马铃薯史略[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1:53.
[64]白云.第一颗转基因土豆即将登上餐桌[J].农产品加工,2011(11):46.
[65]农业部.马铃薯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年)[J].农业工程技术(农产品加工工艺),2009(11):4-7.
[66]蓝勇.明清美洲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J].中国农史:2001 (4):10.
From Non- staple Food to Staple:An Analysis of the Prospect of Potato as Food Staple Based on the Localization of Potato
Chen Guiqu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potato localization,it can be seen that technology advances is the key to overall extension of potato cultivation in China.Under the grain-based diet background in China,the advances in processing methods is the key for potato to become staples;The rational layout of industries and the correct guide of the government are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optimized development of potato farming;Technology advances of breeding and panting are the fundamental for improving the yield and quality.Seen from the word experience and its own strengths,potato as staple have broad prospect and significance.
Potato,Staple food,Localization,Dietary Habits
陈桂权,四川平武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田水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