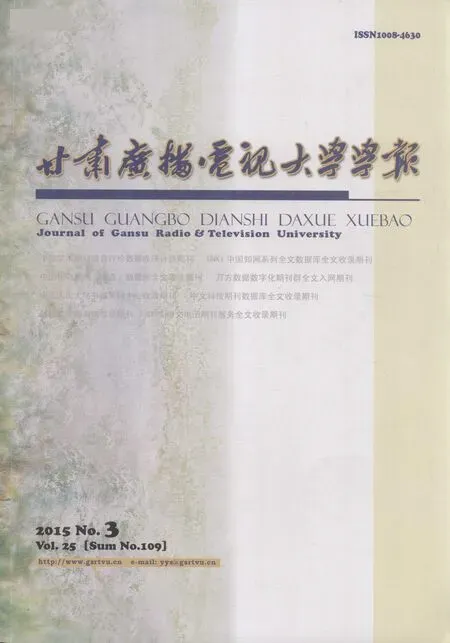毡帐-蒙古包
——游牧民居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2015-03-20洪思慧
洪思慧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毡帐-蒙古包
——游牧民居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洪思慧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毡帐-蒙古包的创建和使用是游牧族群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其构造设计体现着草原民族的自然观和时空观,成为游牧民居文化特有的标志性符号。从文献记录、传承应用或现实价值来看,毡帐-蒙古包始终是游牧文明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0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游牧经济不可逆转的衰微导致毡帐-蒙古包逐渐被定居建筑替代,但其留存的文化符号功能则具有永久意义。
毡帐-蒙古包;草原民居文化;标志性符号
不同地域的人类群体在适应不同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一般都会创造并传承各自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民俗文化,其中一些文化事象因其普遍性与典型性而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毡帐-蒙古包便是草原游牧族群民居文化中最主要的标志性符号。有学者将民俗文化的存在形态归纳为:一是保留在文献资料中的历史民俗记录,再是已经消失殆尽或行将消失的民俗,三是当前民众正在传承、享用的活态民俗[1]50。这三种形态,在毡帐-蒙古包文化现象的历史与现存状态中都具备。
一、文献记录里的毡帐
毡帐式建筑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普遍使用的可移动居室,也是我国蒙古、哈萨克、藏等民族中从事牧业生产者的传统民居。中国历史文献中一般将这种篷帐式建筑称之为“毡帐”,清代以后在口语中多惯称为“蒙古包”,故本文连称为“毡帐-蒙古包”。毡帐也称为毡包、毡房,文献中亦作“旃帐”、“毡幄”、“毡庐”、“穹庐”等等,是以毛毡或兽毛为主要材料搭建的篷帐式建筑。我们从史籍中可以看出,毡帐在先秦和匈奴时代已经被广泛使用,此后一直成为亚欧草原游牧或半游牧族群主要的居室形式并延续至今。数千年来,这种最适合游牧民生产、生活需要的毡帐-蒙古包虽然基本结构稳定不变,但其形制、大小以及建构材料多种多样。
毡帐的最早记载出自《史记·匈奴传》的“穹庐”二字,南朝宋人裴骃在《史记集解》中引《汉书音义》解释说——穹庐就是毡帐[2]。而后历代史书及诗文中都有对毡帐频繁的记述,如“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归心》),“逐水草畜牧,居毡庐”(《新唐书·北狄传》),“毡帐起自北朝穹庐之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花烛》),“一辞椒屋风尘远,去毡庐沙碛深”(宋·曾巩《明妃曲》),“毡帐秋风迷宿草,穹庐夜月听悲笳”(元·马致远《汉宫秋》),“白草黄沙,毡房为住家,胡儿胡女惯能骑战马”(元·施惠《幽闺记》),“经年马背安居地,每夕毡庐托宿家”(清·赵翼《潞江》)等。此外,“毡墙”“毡幕”等词也常被用来借指毡帐,如“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隋书·炀帝纪上》),“穹庐毡幕,抵北阙而为营”(南朝陈·徐陵《陈公九锡文》),“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清·纳兰性德《菩萨蛮》)。而“毡乡”则指称整个北方游牧民居地区,如“北眺毡乡,南晒炎国”(南朝宋·鲍照《爪步山楬文》),“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宋·张孝祥《六州歌头》)。类似这样对毡帐的描述不胜枚举。
从造型上说,毡帐以木材为支架,覆盖毛毡,这是它的基本制式,在此基础上因地域、时代、用途的不同而多有变异。例如,南宋人彭大雅在1232年曾经随从南宋使节北上到蒙古汗国,写有《黑鞑事略》,该书记载说:“穹隆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罣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用柳木织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3]他说毡帐有两种,燕京地区的毡帐,可以拆卸,移动用马匹搬迁(与现在的蒙古包无异);塞外草原上使用的毡帐,不能拆卸,移动要靠车辆载行。其实毡帐无论大小,都必须能够移动,这是草原民居的根本特性。普通牧民的蒙古包拆卸搬迁比较简单,蒙古可汗与贵族的帐殿规模很大,往往需要数十头牛拉的大车才能移动。1253年,法兰西基督教修士威廉·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汗廷,在南俄草原上见过巨型车载毡帐,他在行记中描述道:“我有次亲自测量一辆车的轮距为二十二英尺……每辆车用廿二头牛拉一所屋,十一头和车并行,另十一头走在前头。”[4]从这些中外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蒙元时期的欧亚大草原上大量使用车载毡帐,这与近现代草原地区鲜有车载的固定蒙古包形成鲜明对比。显然,这与13世纪的蒙古人连年四处征战扩张、处于需要经常迁移行走的生存状态有关。
从外在形态上看,毡帐有两大类型:平面为圆形的蒙古包和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的黑帐篷。二者结构存在较大区别,蒙古包的框架和篷毡相互独立,黑帐篷的支撑结构和篷毡互为一体。藏族的毡房属于典型的黑帐篷,外覆牦牛毛编织的帐篷,帐内用几根木柱支撑,四周用绳子张拉固定。唐宋文献中称之为“拂庐”,是唐人对藏语“氆氇”的音译。我国两大类毡帐的分布界限比较清晰,蒙古包的使用范围遍布内蒙古草原和新疆的草原地区,黑帐篷则主要流行于西藏以及四川西部牧区,青海、甘肃等地则为两大帐篷类型的交错地带,既有使用白色蒙古包的牧民,也有以黑牦牛帐篷为日常居所的牧民。
毡帐有大有小,小的够一户人家生活之用,大者可容千人,供统治阶层们专用。威廉·鲁布鲁克记述道:“他们把这些屋舍造得很大,有时宽为三十英尺。”[4]一般牧民的毡帐因游牧需要都是星星点点分散开的,而王公贵族们的毡帐往往集中搭建,所以古人常将游牧民族王庭所在处称之为“毡城”,大型的毡帐称之为“毡厦”。如“毡城南望无回日,空见沙蓬水柳春”(唐·张籍《送和蕃公主》),“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宋·王安石《明妃曲》),“又送他江南太史,去游毡厦”(宋·刘克庄《贺新郎·送黄成父还朝》)。蒙古汗国时期,大汗与诸王居住在蒙古语称为“翰儿朵”的宫帐里,帐幕容积很大,可供两千多人宴饮聚会。元上都和大都皇宫中搭建的棕毛殿,也是一种巨型毡帐。清朝帝王十分注意与蒙藏贵族阶层的关系,康熙、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附近的开阔草地上搭建大型毡帐,常在毡帐内接见蒙古王公大臣与外国使臣。
毡帐建筑虽然基本上使用木料和毛毡,但从古至今在建材和样式上也有因地制宜的各种变化和特例。古代草原贵族的毡帐往往修建得富丽堂皇,尤其是汗王的帐殿。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记载王汗的帐殿叫“金撒帐”,即用细毛布装饰做成的金碧辉煌的巨帐。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建立的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统治着中亚北部草原和南俄草原,因其可汗帐殿内的构件为金饰,被称为“金帐汗国”。今天在乌兰巴托的博格多汗博物馆里,陈列着8世哲布尊丹巴活佛的一顶蒙古包,是用珍贵的雪豹皮制作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地区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毡帐多用木材,他们的蒙古包四围用圆木搭建,外观自然不能成圆而呈六角蜂窝形。另外,从文献记载看,中古时期的毡帐一般门朝东开,近现代的毡帐-蒙古包多南向或东南向开启,至于当代旅游点的所谓蒙古包则一律南开门。我们由此可见毡帐建筑形式的变异与发展的多样化。
二、现实传承中的蒙古包
汉语“蒙古包”之称清朝以前文献无此记录。在蒙古语中,草原牧民从古至今始终将自己的居所称为“格日”(ger),意谓家、房屋。满语将家、房屋称为“博”(bo),将蒙古人的居所称为“蒙古博”。清代,满语“蒙古博”被借用到汉语中,又因“包”字音近“博”字又能象形地关联到毡帐,故“蒙古包”这一称谓得以广泛扩散使用。“蒙古包”在口语中用来代称穹顶毡帐,不过三百余年的历史。
北方游牧民使用的传统蒙古包虽然大小、质量、装饰有差别,但基本结构相同,都由支撑材料、覆盖材料和紧固材料三部分构成。支撑系统用木制材料搭造成穹隆形的骨架,包括长方形门、圆形天窗(蒙古语叫“套瑙”)、伞状顶架(蒙古语叫“乌尼”)、圆形围壁(蒙古语叫“哈那”)、支撑木柱等构件。整个木框架结构的核心是包顶中央圆形环状的天窗,用来通风、采光、排烟。伞状顶架是支撑天窗的组件,顶杆上端与天窗相连,下端与围壁相连,形成辐射状支撑穹顶的造型。围壁是用木枝条编成的可伸缩木栅,一片围壁一般高1.60米左右、长2米多,包的大小由围壁的数量决定。普通牧民一般多搭建6至8片围壁、直径4至6米的蒙古包,超过8片围壁则要附加支撑内柱。围壁的高低可以调节,一般雨季搭高一些,风季搭低一些。蒙古包的覆盖物有多种,在支撑框架的外面,一般多用绵羊毛与骆驼毛压制而成的毛毡来包裹,有些地区还使用羊皮、芦苇等缚设材料。毛毡有多种名称和式样,盖毡用来遮盖天窗,顶毡用以覆盖顶架,围毡则包裹围壁,还有挡风保暖的门毡。蒙古包的紧固材料主要是结绳,是由马鬃、羊毛或驼鬃拧结而成的鬃毛绳子。结绳用来连接缝合毛毡,勒紧固定全包。通过调整结绳捆绑的松紧度,可以调节包内的通风和温度。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搭建和拆卸非常容易,移动搬迁格外便捷,特别适合于转场放牧居住。首先是搭建容易。四季游牧的牧民搭盖蒙古包没有什么特定的限制,在水草好的放牧场地选择平坦之地后,按照包的尺寸画上圆圈,平整好地盘即可架设。架设时将围壁拉开成为圆形围墙,南向竖立包门,将围壁和伞状顶架按圆形衔接绑好,外面覆盖毛毡,再用毛绳加固拴牢即可。一座普通的蒙古包两三个人用一两个小时就能搭盖起来。其次是拆卸迅速。蒙古包是各部件单独的组合式建筑,解开活扣结绳,毡子和架木就自动分离。围壁、顶架、天窗都是分片分根的,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拆开折叠,拆卸比搭盖还要快捷方便。再者是装载搬迁轻便。蒙古包的支撑材料都是独立的固定套件,覆盖材料都是分开的单个组件,除天窗以外,架木全用轻木头做成,一般成人都能将任何一件材料搬放到车上。一顶普通的蒙古包用两三峰骆驼或一两辆“勒勒车”(草原上常用的双轮牛车)即可搬运,车装和驮运千百年来已经形成固定程式,对牧民来说如同家常便饭。
蒙古包的外形看起来不大,但内部使用面积却不小,空气流通,采光好,冬暖夏凉。包内的布局规范兼有实用性和艺术性,各种物品的摆放和陈设都有特定的位置及一定的含义。大体说,蒙古包内的空间分配通常是男西女东,以西北为尊,平面可分为九个方位:(1)北位,放置卧被、毛毡、案桌等物;(2)西北位,供奉善神像、佛龛和祖先灵位;(3)西位,放置衣物类男人用品,依次往西南摆放放牧和狩猎的用具;(4)西南位,挂物的地方,如马鞍、马鞭、弓箭、猎枪等;(5)东北位,放置酒壶、妇女箱柜之地;(6)东位,摆放绘有各种图案的竖柜,放置衣服食物类; (7)东南位,放置饮食器用,炊具、奶具等;(8)南位,蒙古包门入口处;(9)中位,正中央正对天窗的是火位,放置供煮食、取暖的火撑(蒙古语叫“图拉嘎”),天窗与火撑是蒙古人崇拜的太阳和圣火对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牧民十分讲究包内装饰,往往在地上铺厚厚的地毯,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画,除了一些常用家具外,现在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也进了蒙古包。
毡帐-蒙古包建筑蕴含着游牧民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智慧,其中最基本的建筑元素通过物象圆形、白蓝色彩、遵循自然和护佑环境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物象圆形”是最突出的外观特性,组成蒙古包的三大部件天窗、顶架、围壁都是圆形构造,它不仅包含着实用的科学原理,也积淀了深厚的民俗内涵。蒙古高原处于典型的大陆季风气候区,冬春多大风,夏秋多暴雨,圆锥形的毡包造型减少了任何角度的受风阻力,能够快速排出雨雪的积压。按照游牧民的古老传说,天窗是太阳的化身和造型,是毡房与苍天连接的通道;呈放射状排列的顶架寓意着太阳四射的光芒,带给包内光明和温暖;围壁的菱形网格象征着草原上起伏的山陵,遮挡四面来风呵护休息的人们。“白蓝色彩”是蒙古包质朴、专一的用色。以羊毛与驼毛原有的灰白色为毛毡的主基调,其上配用蓝色为装饰。白色是草原人民期望生活富裕美满、吉祥如意的基本象征,因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奶食品、羊毛等多是白色。象征永恒和坚贞的蓝色则是蒙古族的标志性颜色,经常应用于各种美术图案和建筑装饰中。在蓝天、白云衬映下的白色蒙古包配以蓝色图案的点缀则更加凸显出草原民居鲜明的独特风格。“遵循自然”体现在蒙古包的形态构建上。蒙古包的内部造型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与遵行,是对天地日月星辰的组合再现。圆形穹庐是基本形态,脚下是大地,天窗白天是太阳、夜晚是月亮之形,围绕天窗的伞状顶架如同日月之光,围壁四合成天幕穹顶形状,这些反映出游牧民的时空观念和对自然界的崇敬。而且,从日出到日落,天窗上射入的阳光顺时针绕包内一圈,牧民根据四季不同时段太阳升降时间,对比照在围壁和顶架上的光线,能够准确测定时辰。“护佑环境”是指蒙古包由毡制材料、绳索材料和木制材料为基本构件结构而成,不用砖瓦不动土,绝不破坏四周生态环境。毛毡由羊毛或骆驼毛梳理压制而成,结绳用动物皮革和鬃毛制成,木材的使用也非常有限,这些物品就地取材应用,源于自然并归于自然,充分体现出草原民众崇拜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同生共存的传统风俗及理念。
总之,毡帐-蒙古包建筑的深刻内涵与寓意充分诠释着游牧民居文化的独特性。蒙古包可谓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观,是草原民族的一大贡献。它既是游牧民族的神奇摇篮,也是他们谨遵自然、崇天敬天观念的物质表象,正如一首赞颂蒙古包的草原民歌所唱:
因为模仿蓝天的样子,才是圆圆的包顶;
由于仿照白云的颜色,才用羊毛毡制成;
因为摹拟苍天的形体,天窗才是太阳的象征;
由于模拟天体的星座,吊灯才是月亮的圆形;
这就是穹庐——我们蒙古人的家庭。[5]
三、毡帐-蒙古包的未来
清朝末年以后,随着蒙禁政策(禁止关内人口进入内外蒙古地区)的松弛,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面貌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草原被开垦种植,草场逐渐衰退,农业种植经济逐渐逼退传统的游牧经济。清末到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出现了许多半农半牧区,蒙古包的形态也开始渐渐发生改变,出现了固定式的蒙古包。纯粹的游牧区依旧使用传统蒙古包,以适应“春洼、夏岗、秋平、冬阳”的迁徙生活,即牧民们每年随季节变化驱赶牲畜大迁徙4次,局部小迁徙10余次。春牧场选择低洼的地方,夏牧场选择高地草原,秋牧场选在山腰、山麓或河流两岸的平地,冬牧场选择平坦避风、向阳温暖的多草地区。固定式蒙古包则多建于半农半牧地区,是受农耕民居影响而修建的,有土筑和柳编两种。土筑的用土坯或草坯砌墙、抹泥,柳编的用柳条编框架、抹泥,上用苇草搭盖而成。这种固定式的蒙古包,蒙古语叫“崩布根格日”,汉语俗称为“崩崩房”。
进入20世纪,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业受到工业化的强烈冲击,游牧民从事其他行业者增多,定居生活者也日渐增多。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移动游牧渐渐被改造成定居养牧,蒙古包逐渐被砖瓦房所代替。特别是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草场划片承包,草原被网围栏分割得支离破碎,牲畜与人都失去了许多自由,牧民们已经无处迁徙无法游牧,传统放牧形态已经成为不可复现的历史。牧民的定居生活已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这就彻底改变了蒙古包的命运,“定居下来的蒙古族一定选择汉式住房做他们的住所。这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更是住房文化的影响使然”[6]。
时至今日,随着人口增长,草场资源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蒙古包加速淡出社会生活。除了纯粹的牧区和偏远地区,传承数千年的毡帐-蒙古包在草原上越来越少见,仅仅成为旅游区的景点设施。几十年间,许多地方在城镇周边和旅游景区建造的蒙古包,使用了很多新的材料,如石材、钢材、胶合板、混凝土、薄膜、塑料等,这些建筑已经失去了毡帐-蒙古包民居文化的内涵。对于如何认识民众生活中体现地方文化特征或者反映文化中诸多关系的事象,有民俗学者提出“标志性文化”这一概念,认为标志性文化具有三个条件:“一、能够反映这个地方特殊的历史进程,反映这里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二、能够体现一个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共同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内在生命力;三、这一文化事象的内涵比较丰富,深刻地联系着一个地方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1]55毡帐-蒙古包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确实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标志物。“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毡包好似白莲花”,“蒙古包的缕缕炊烟,轻轻地飘向蓝天”,每当这些悠扬的歌声响起,人们的心境便会被带进茫茫的草原,思绪被引入辽阔的境界,心底会涌起对草原的向往。这就是标志性符号所具有的功能。
四、结语
毡帐-蒙古包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可以拆卸搬运,适宜于游牧经济的生产、生活用品。然而,当人类在今天已经失去游牧生活时,毡帐-蒙古包的使命便宣告了终结。“从蒙古包变迁的过程来看,物质文化变迁是有一定规律的,即创造阶段,鼎盛阶段,变迁阶段,如果要真正保护一种物质文化长期存在下去确属不易。”[7]可以肯定的是,毡帐-蒙古包传统的物质功能已经失去,而无法肯定的是,作为游牧民居文化特有的标志性符号,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象征之一,毡帐-蒙古包是否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1]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2]司马迁.史记·匈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01.
[3]许全胜.黑鞑事略校注[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22.
[4]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M].耿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210.
[5]王迅,苏赫巴鲁.蒙古族风俗志[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0:24.
[6]陈烨.内蒙古民居:一种文化与历史的认识[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4):61-65.
[7]苏浩.草原传统物质文化的变迁——以蒙古包为例[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3):53-56.
[责任编辑 张泽宁]
2015-03-27
洪思慧(1994-),女,蒙古族,北京人,专业方向:民俗文化与民俗文学。
K892.25
A
1008-4630(2015)03-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