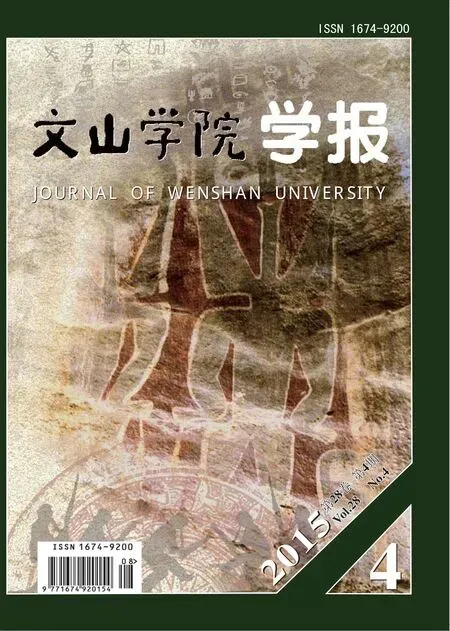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述评
2015-03-20马亚辉
马亚辉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
——《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述评
马亚辉1,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2.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摘要: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可谓相互促进和影响。杨永福教授的《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一书从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的变迁入手,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两千余年间不同时期西南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过程。从秦汉初步经略西南夷,到清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等同于内地,这一切的发展变化皆在中央(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中得以完成。该书的出版,在西南交通史研究领域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古代;边疆;经略;交通;西南;滇川黔;治边
交通是将内地与边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是内地与边疆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载体和媒介。历代王朝皆非常重视对边疆的经略,若要取得良好的治边成效,拓建交通首当其冲,这是任何时期的政府都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古代的西南边疆远离中原,地处遐荒,壤接外域,交通十分不便,在清雍正时期仍是“水路不通,陆路甚险”[1]445的情形。历朝出于对西南边疆地位的认识而对西南交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拓建,而交通状况又反过来促使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与经略发生进一步变化,二者在漫长的两千余年中互为因果,共同发展。方铁先生指出:“从秦汉至明清的长时期里,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在经济上开发和利用的价值,以及经营边疆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何种意义,其观念和认识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提高,有时甚至是反复的过程”,[2]而这个过程则表现为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在不同时期的互动。关于边疆经略史与边疆交通史的研究已有论著问世,如马大正先生的《中国边疆经略史》,[3]陆韧教授的《云南对外交通史》[4]等,但有关古代西南边疆滇川黔毗邻地区交通变迁的研究却不多见,而杨永福教授①的著作《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5]的问世,可以说填补了史学研究的这一薄弱领域。该书根据西南边疆交通发展历史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三个时期,详细探讨了不同时期中央(中原)王朝的边疆经略与滇川黔区域交通变迁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等内容。笔者试对该书进行简评,请杨永福教授与史学前贤批评指正。
一、汉晋南朝时期的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
秦汉至南朝时期为西南边疆交通的最早开拓年代,许多重要的交通线在这一时期首次拓建。早在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兵指西南,“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6]卷116。可知先秦时期内地与西南边疆便已有道路相通。时至秦代,秦朝常略通五尺道,拓建了内地与西南边疆的首条官方陆路交通,并在西南置吏。[6]卷116五尺道虽宽仅五尺左右,在当时却可与现在之高速公路媲美。五尺道的拓建标志着内地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的开始。然而,秦朝享国时间不长,未能对西南边疆进行深入治理。及汉兴,由于西南的人文与地理环境复杂,交通极为不便,西汉认为此地不值得经营,于是皆弃此国。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食蜀枸酱,得知从蜀地有路可达于南越,上书请求通夜郎,经营南夷,以制南越,西汉才再次重视夜郎所在的南夷地区,并在西夷“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6]卷116。后来公孙弘当上御史大夫,适逢西汉正修筑朔方城以“据河逐胡”,公孙弘于是“数言西南夷害”,应该放弃经营,专门集中精力对付匈奴。汉武帝于是遂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6]卷116汉武帝虽成功实现了对南夷的经营,但在对西夷短暂经营之后,遂罢之。汉武帝经营南夷之原因,是为控制南越,经营西夷之原因,乃是西夷与南夷相邻,顺便而已,此时南夷对西汉而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西夷之战略地位还未曾认识到。
西汉再次经营西夷是出于打通蜀身毒道,联合大夏夹击匈奴,并“广地万里”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因而得知此物由蜀商贩往身毒(今印度),再由身毒运至大夏。张骞回到长安,盛言大夏在汉西南,仰慕中国,但是苦于匈奴隔绝道路,如果通过蜀地前往身毒国,不但道路便近,且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曾问汉使者:“汉孰与我大?”夜郎也是如此问。汉使者回去后,于是“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6]卷116汉武帝已经初步认识到西夷的战略地位,若经略西夷,不但可以打通蜀身毒道,与大夏联手,共同遏制匈奴,“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夷,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7]卷61汉武帝权衡利弊,复事西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之兵击灭劳浸、靡莫,兵临滇国。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又征服昆明夷(今大理一带),属益州郡。综览以上史实,西汉经略西南是出于战略目的,杨永福教授在书中写道,“军事和政治的原因居于首位,经济的原因反而是次要的”[5]33。这些军事和政治因素是西汉经略西南边疆的重要内容,而西南边疆交通的开发也围绕着边疆经略而展开,五尺道、灵(零)关道、南夷道、蜀身毒道、进桑縻泠道等交通路线的拓建便是西汉经略西南边疆的产物。
虽然西汉未能打通前往大夏的便捷通道,未能实现最初的军事、政治目的,但对西南边疆交通的拓建,客观上加强了中央(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治理。该书指出:“西南夷地区的交通线开设以后,其首要职能主要是便于朝廷更好地实施军事和政治控制、输送军队及各种军用物资,保证中央政府在西南夷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威慑力。这一时期西南夷地区发生过多次反抗当地官府的行动,两汉政府凭借顺畅的交通平定了叛乱,有效地维护了在西南夷地区的政治存在。”[5]40同时,这些交通线的拓建还为西南边疆诸族及徼外诸国赴内地政治中心朝贡提供便利,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这一时期许多僧侣、商人、使者经由蜀身毒道往来中外。而当北方丝绸之路被梗阻时,秦汉开拓的西南交通在联系中国内地与中南半岛、印度地区的作用更显突出和重要。
该书还分析了汉晋南朝时期边疆交通对西南夷的社会、经济产生的重要影响。在西汉经营西南夷之前,西南发展落后,部落林立,编发之民从事着比较原始的渔猎耕牧生活。拓建交通之后,西汉在此设置郡县,“军队、官吏、商人等移民随之陆续进入西南边疆地区,沿交通线分布,营城立邑,垦殖生产,并与当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僰人相互交融,产生文化涵化,导致内地政治观念、经济、文化等因素流播西南边疆”。[5]47- 48该书为证实这一论断,引用了汉晋至南朝时期大量翔实的史料,并指出西南经济社会开发的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空间上先北后南的开发格局”,[5]56而这种开发格局的形成便是沿着交通线由北而南渗透的。西南边疆交通的开拓使得汉夷文化空前交融,进而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与新的族群的形成,还促成了南中大姓的形成,并使南中大姓称雄西南几百年之久。
二、唐宋时期的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
唐宋时期,由于中央(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不同,未能施行直接治理。唐朝前期积极经营西南,但吐蕃兴起后,唐朝为构建西南防线,牵制吐蕃,扶持西南地区的蒙舍诏建国,是为南诏。南诏灭亡后,大理国接位,继续控制西南边疆广大地区。而唐朝灭亡后,宋朝立国,宋太祖主张守内虚外的治边政策,手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将西南边疆诸多地区划为外域。总体看,唐朝的边疆经略并未对西南的交通开拓起到多大作用,正如该书所言,“与秦汉相比,唐代西南地区通道格局没有大的变化”,[5]77但也对清溪关道、石门道进行了修整,并派重兵把守,还曾筹划开通从蜀地至安南都护府的步头路。相对唐朝而言,宋朝的边疆经略却对西南交通重心的变迁有着较大影响,尤其在南宋偏安东南的时期,由蜀地至云南地区的清溪关道、石门道交通趋于衰落,从广西地区至云南地区的邕州道因马匹交易地位日益上升。关于大理国内部的交通,可谓四通八达,虽然从云南驿“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5]799基本也未改变秦汉以来的交通格局。这一时期的清溪关道即汉之灵关道;南诏、大理的通天竺道,则为蜀身毒道的一部分;西汉时的进桑縻泠道,在汉晋时期又称交趾道,唐代称为安南道。而石门道与秦汉时期的五尺道,黔州道与汉之南夷道之间的区别尚未有专门研究,但大致应该差别不大。邕州道在唐代就已开通,只是官方使用不多,时至南宋,邕州道因马匹交易而兴盛,有三条路线连接滇粤,该书对此三条路线进行了详细考证,[5]90- 92并着重探讨了唐后期至宋代西南地区交通线嬗变的原因,即当时的战争、政治局势,从深层次来看,也就是中央(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疆经略发生改变所致。交通线地位的嬗变对滇川黔相邻地区的社会、经济、地缘政治关系、族群演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无疑也反过来又影响着西南边疆经略的再次改变。
由于滇川黔地区的交通在唐代以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为唐朝进一步经略西南创造了便利条件,也就是说影响着唐朝初期在西南的边疆经略。唐初就在今川西南地区设立了嶲州、戎州等,并以此作为经营云贵的前沿。后唐朝扶持南诏牵制吐蕃,以构建西南稳固防线,更是注重对西南地区交通的拓建和维修。随着南诏的日益强盛,开始与唐朝交恶,并通过滇川黔相邻地区的交通线进入到唐朝直辖的四川等地,且多次发生战争,滇川黔相邻地区成为唐朝与南诏争夺的地区,南诏异牟寻为向东部拓展疆域,在滇池附近建拓东城(今昆明),并拓修昆明至周边各地的交通要道,而唐朝为控制和防守南诏,也十分重视滇川黔相邻地区的交通路线。不难看出,唐朝与南诏对西南交通的拓修是建立在对西南边疆经略的基础之上,交通的拓修就成为唐朝与南诏执行边疆经略的最重要的媒介。唐朝与南诏在滇川黔相邻地区的交通线上进行了长久的战争,双方皆损伤惨重。
宋朝与大理国都不主张对外扩张。大理主动与北宋修好,北宋却对西南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划大渡河外的西南地区为外域,对大理国严加防范,宋朝的边疆经略使得滇川黔相邻地区交通线的开发受到了抑制。至南宋时期,宋朝与大理的官方往来更是稀少,仅有邕州道还勉强可通,至南宋后期,即使邕州道也渐趋断绝,南宋邕州地方官派人潜入大理国打探军情,只能进到特磨界(今云南广南一带)。[5]124
安南的独立也可以说是中央(中原)王朝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互动的结果。杨教授在书中指出:“根据距离耗损理论,控制力强弱是与距离远近成反比的,距势力核心越近,控制力度越强;反之,距势力核心越远,控制力度越弱,其控制力随着距离的延伸而耗损。”[5]125决定政府对边疆控制力度强弱的最关键因素并非是强大的国力与军力,而是边疆经略与交通的便利与否。边疆经略反映出政府对边疆地位的认识,交通的便利与否决定着边疆距离的远近。南诏强盛后脱离唐朝的控制,隔绝了唐朝至安南的交通线,唐朝对安南的经营力度逐渐减弱,安南大姓势力得以迅速发展,也逐渐脱离中央(中原)王朝的管辖。宋挥玉斧之后,在西南全面推行消极保守的边疆治策,不但影响边疆交通的开发,也使得安南最终脱离宋朝版图。
唐宋时期,滇川黔相邻地区不同政治势力的边疆经略与交通线地位变迁的互动同样影响了西南地区乌蛮族群及其势力的演变,该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考证。
三、元明清时期的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互动
元明清时期是西南地区政治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古代西南边疆交通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元朝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建立云南行省。从整体来看,云南由羁縻变为直辖,从云南地区内部看,又是一种全局直辖,局部羁縻的状态。元明清三朝出于对西南地区的不同认识而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开发,包括对滇川黔相邻地区的交通开发,而交通的不断发展又促使中央王朝的西南边疆经略发生进一步的改变。
西南地区在元朝统治者眼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元跨革囊,先攻大理,再陷南宋,西南在元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作用巨大,因此元朝非常注重对西南地区的经营治理,建立了云南行省,这种边疆认识影响着元朝对西南交通的开发力度,可谓是远超前代。当时比较发达的交通线有中庆(今昆明)到成都、叙州、泸州、黄平、邕州、大雪山、车里,甚至通往大罗城(今越南河内)的道路,这些交通既有沿旧路再次开通的,又有全程新建的。该书指出,由于全国政治中心迁移至大都(今北京),传统交通线艰险难行,为便于治理西南,元朝开辟了“入湖广道”,即由中庆经贵州普安达黄平的道路。[5]142- 144为加强云南与内地的密切联系,维护政府对西南地区的牢固统治,元朝还修建了遍布西南,管理严密的驿站,通过发达的交通线将军队与物资频繁调动。《元史·地理一》中不无自豪地夸耀:“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5]147。许多内地各省百姓也通过滇川黔地区发达的交通线不断移入西南边疆,与土著居民进行着经济与文化交流,甚至融入这些族群,加快了西南边疆“大杂居、小聚居”民族分布形态的形成过程。
元朝的交通开发给西南边疆带来了较大变化,也影响着明朝西南边疆经略的制定,而明朝的西南边疆经略又给西南边疆的交通带来进一步开发,从而又进一步影响清朝边疆经略的制定。明朝鉴于元灭南宋的教训,同样十分重视西南边疆的管理,命沐氏家族世代镇滇。清朝为平灭南明政权,收滇、入缅,更是看重西南的战略地位,从清初就开始对西南边疆的社会尝试以内地的模式治理,交通的开发自然成为西南地区的首要任务。可以说,明清两朝对西南战略地位的认识使得滇川黔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线在元朝的基础上得到更广泛的开发。
该书认为,明代西南边疆地区的交通格局基本沿袭元代,[5]148而清代以云南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交通格局基本上沿袭元明两代。[5]155明清时期的主要交通干线有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建昌路、粤西路,道路名称与元代不同,但路线大体相同,仅从以上来看,明清时期西南交通的开发似乎并未超越前朝。众所周知,交通开发不只是开拓新的交通线路,还包括对交通线路的维护,如对道路的加宽、加固,增设驿站等,这些基础建设在交通开发中的作用同样很重要,从这点而言,明清两朝对西南交通的开发比前朝更深一层。
事实上,清朝对西南地区大规模的交通开发是在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改土归流是西南边疆交通开发的一个历史分界点。[8]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任云贵广西总督,说:“云贵远居天末,必须商贾流通,庶地方渐有生色。”疏请清世宗开发西南交通,云:“纵一时难措,而日积月累,未始不可以小济……即迟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实云贵永远之利也。”清世宗极力支持,朱批:“见处信得,及便动数十万帑金何妨?朕不惜此等之费也。”[1]清朝不但在西南地区拓宽和维修了旧路,也曾开修一些新的交通路线。如为运送滇铜的金沙江水道,滇粤河道等,随着清朝直辖地区向云南南部的拓展,元代从中庆到车里的交通在清朝中期演化为迤南大道,把今天西双版纳、普洱等广大地区与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滇粤河道在耗费了多年财力、人力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废弃,但并不有损清朝在开修西南边疆交通路线中超越前朝的功绩。清朝对西南交通线的建设同样影响着民国政府(云南军阀)在西南地区的边疆经略。
四、余论
该书所研究时段,上起秦汉,下迄明清,长达两千余年,不可谓不长;研究地域以滇川黔交界为中心的三省全部地区,甚至延及西南周边国家,范围不可谓不广,可以说该书是在长时段与整体史的基础上进行的边疆经略与交通变迁的二维互动研究。边疆经略影响着边疆交通的开发,而边疆交通的开发又引起下一个王朝边疆经略的改变。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西南疆域的形成和巩固都是在二者的互动中得以造就。因此,该书中的观点是经得住检验的。该书还有着其他诸多优点,如翔实的史料,深入的分析,慎密的考证,长时段与整体史的研究方法等。该书涉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很多,最为明显的当为历史地理学,但交通史、民族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也有充分反映。
任何论著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不足,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该书也存在着个别微小缺憾。如在叙述汉代五尺道的路线时,方位表述不是很准确。书中认为五尺道至曲靖后,“从此向西到达滇池地区”,[5]24而实际滇池位于曲靖西南方向,从僰道至滇池的五尺道整体来看是大致南北方向。还有个别古地名未标注现在的地名,不便于初学者与其他研究领域的读者进行阅读。当然,瑕不掩瑜,以上微小缺憾并不影响该书在西南交通开发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 杨永福教授是云南的一名傣族学者,本科硕士均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学专业,博士阶段师从云南大学方铁先生,现为云南文山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西南边疆史、民族史研究。其著作《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一书是基于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研究深入且多有新意。
参考文献:
[1]张书才.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方铁.论唐朝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及对西南边疆的治策[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2):51- 54.
[3]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4]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5]杨永福.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以滇川黔毗邻地区为中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
[6](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M].
[7](东汉)班固.汉书·张骞传[M].
[8]马亚辉.开发交通以密切云南与内地的联系[D]//康雍乾三朝对云南社会的治理(第三章第四节).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3.
(责任编辑杨永福)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rontier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Traffi c Changes: A Review on A Study on the Traffi c Changes in Ancient Southeast Frontier Regions of China
MA Ya-hui
(1.Research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99, China)
Abstract:Frontier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traffi c changes interact and improve mutually. The book discusses their interac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periods over 2000 years in detai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ffic changes in ancient Southeast frontier regions.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preliminary govern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 dynasty to the same governance polic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inish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rontier governance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raffic changes. It is worth saying that th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contributes a lot to the study of the traffi c history in Southeast regions.
Key words:Southeast region; Dian Chuan and Qian; frontier governance
作者简介:马亚辉,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客座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政策研究”(14YJA850007)阶段性成果;文山学院“中国历史”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收稿日期:2015 - 05 - 13
中图分类号:F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15)04 - 0041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