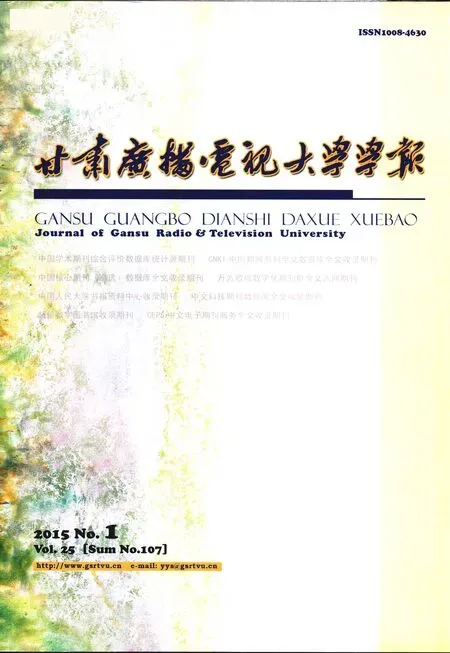从《野狐岭》看雪漠的探索精神
2015-03-20吴浪
吴浪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从《野狐岭》看雪漠的探索精神
吴浪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雪漠于2014年7月推出新作《野狐岭》后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这一作品是他继“大漠三部曲”与“灵魂三部曲”后的又一尝试性作品。该作品在文本形式、思想内容上,体现出与其之前的作品所不具备的鲜明探索性精神。本文拟从这部作品的灵魂描写、信仰的探索性、形式的创新性、文本的独特性、人物符号化以及雪漠的少年心性与脉脉温情等方面对该作品进行简要解析。
雪漠;野狐岭;灵魂叙事;西部描写
在当代作家群体中,雪漠的创作以其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别样的文本题材而独树一帜,成为甘肃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雪漠多年来一直坚持文学的西部叙事,在作品中融入了对于宗教(主要指佛教文化)、灵魂维度、历史等方面的深刻理解。文学批评家陈思和先生曾如是说:“雪漠的小说展示给我们一些没有被商品经济污染的善良的心,有一种让人心醉的美。而惟有这种当下小说中所缺乏的善良与单纯,才能具备唯美的力量。”[1]而雪漠的新作《野狐岭》的问世无疑给外界一种之前未有过的惊奇与欣喜——它展示了一个新的雪漠和一个新的西部。作者本人在作品后记中曾有过自我评价,“贡献了别的作家不一定能贡献的另外一种东西”[2]417。下面笔者拟对这部作品从四个方面进行简要解析。
一、灵魂叙写的探索
灵魂叙写是雪漠创作的利器和法宝,纵观其作品,可以发现雪漠一直在尝试并发展着灵魂叙写的方式。从《猎原》、《白虎关》开始他就有意转变叙述视角,尝试从更为广阔的生命视角对笔下众生重新审视,在《西夏咒》、《西夏的苍狼》的行文叙事中弥漫着浓郁宗教神学的氤氲,以悲天悯人般的神性视角观照西部风土人情,给荒地大漠增添一种不可知的神秘感。可以说,灵魂叙写既是作者在数十年的佛教智慧学习过程中所习得的个人感悟方式,同时也是作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意无意所依托的一种凭借,它为西部叙事开启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维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从“眼中的西部”到“心中的西部”的独特世界。在《野狐岭》中,雪漠所进行的灵魂叙写不仅仅是精神内涵,连同文本内容与情节设置也都被植入了“灵魂化”的进程。
“灵魂化”在《野狐岭》中最为直观地表现为人物的“灵魂化”。如果说雪漠之前的作品,其人物都是具有实体的思想载体,那么在《野狐岭》中,作者则大胆地直接赋予了人物“幽魂”的身份。作品中“我”前往野狐岭,将百年前的“幽魂”招来,请他们说出过去的故事。为了实现人物的“灵魂化”,作者干脆将这些“幽魂”设置为没有实体的存在,它们只是一团光、一截影子,或者是一种感觉,“我”通过与之进行精神的交流而肯定对方的存在。倘若说在雪漠之前的作品中,他只是以单一的精神性或灵魂性(宗教神性)对灵魂世界进行高度观照,那么在《野狐岭》中,不同身份的“幽魂”的出现则代表了不同属性、不同功能、不同体系的精神力量。以陆富基为代表的汉驼队象征着人性中的狡黠无知、功利热情,以巴特尔为代表的蒙驼队象征着人性的粗狂直率、暴躁野蛮,骆驼象征着严酷自然中为了延续生存而彰显出的生命活力与原始欲望,杀手象征着重新解构一切、破坏一切,与物质世界相悖的潜意识力量,木鱼妹象征着走在朝圣路上,历经磨难而心境日趋完满的朝拜者,马在波则象征着看透一切、心神通明而不得不为物质现实所束缚而挣扎的“半神”……作者通过有意识地将不同形态的精神汇集到野狐岭这个地方,以采访的形式,让“幽魂”向“我”——同时也是向读者——展示出不同的面貌与角度。在不同视角与不同立场下,对同一件事的描述大相径庭,这正是雪漠所想要在文本中表达的,他需要读者从中筛选出符合个人思想观念与精神内涵的剧情,让读者在不知觉中与自己完成一次完美的互动。而这一方式正如雪漠自己所言,《野狐岭》的整个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另一种探险”[2]417。在这场“探险”中,他实际上是以一种更为隐晦与更为超越的姿态,对包括文本中的人物、情节以及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和反应等从整体上进行不动声色的观照,这是一种超越了神性精神、灵魂思维的更高境界。此前他在其他作品中用以充当全文基调与冷静观察者的灵魂视角,在《野狐岭》中摇身一变成为用来进行直观表现和对比的工具,这就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作者的大胆创新与叙写自信。
灵魂叙写在《野狐岭》中还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客观求索。文中的“我”失去了主人公的身份,只是一条连接不同层次精神力量与灵魂维度的纽带。“我”既带有作者本人鲜明的烙印,同时也是众灵魂展现自我意识的真实写照。作为招魂者与采访者的“我”,主要任务除了客观记叙每一种灵魂视角下所观照的世界之外,“我”找寻自己的前世也作为全文的另一条重要线索与整个采访过程并行不悖。在对不同灵魂视角下的“真实”进行筛选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保持了一种客观甚至类似于“零度”的状态,虽然直到最后“我”也没能找到自己的前世,但是至少“我”知道了自己的方向,“……我可以容忍自己是动物,但不容忍自己在前世里当过小人”[2]413。这其实正是作者在文本中释放的一个明显信号,即对于现实意义上进行灵魂探索与修炼的追寻者而言,或许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灵魂展现自我意识的基本方向与原则依然需要明确和坚守。另一方面,也正如作者所言,“我只能选择将来,我选择不了过去”[2]413,这是雪漠自身探索灵魂所得出的答案,而读者自己的答案仍然隐藏在《野狐岭》之中。
二、形式的创新
《野狐岭》与雪漠之前的小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令人耳目一新的文本形式。雪漠在《野狐岭》之前曾得到过一些“不会写故事”的评价,而《野狐岭》的诞生则回应了这一质疑。与之前采用现实主义直叙表现手法所不同的是,《野狐岭》更像是一篇扑朔迷离、疑团密布的侦探小说。作品开篇“百年前,有两只驼队,在野狐岭失踪了”,这等于直接设置了悬念,激发起读者继续阅读的欲望。而这一设置的巧妙之处在于,读完全篇的读者会发现整部作品竟然是围绕着开篇的这一句而展开的,“当时在野狐岭两只驼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带着疑问,读者化身为侦探借此不断地向下追寻,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文本中所营造出的悬疑氛围其实暗藏着一种轮回与救赎的主题意识,而这种意识实际上又大大丰富了悬疑表现的方式,进而使得情节的拓展充满了无限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采用了另一创新性形式,即幽魂叙述,这一方面强化了文本中的西部神秘性色彩(这种神秘性色彩在西部文学中古已有之),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西部文学与推理小说相结合的风味,另一方面又展示出一种对于文本内容与文本本身所进行的不断建设和不断解构的思维过程。读者在追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世界与文本世界发生激烈的碰撞,不断产生更多疑问,文本随之进入了一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叙述模式,像是一个巨大的同心圆流沙,不断把人往最中心拉扯,令人欲罢不能,享受到巨大的阅读快感。
幽魂叙述即是雪漠在《野狐岭》的形式上所做出的最大突破。设置悬疑,营造气氛,小说中选用灵魂叙述的方式是有其必要性的。首先,灵魂叙述是雪漠一贯的写作手法,在《野狐岭》中则进一步得到升华。其次,灵魂叙述更加符合小说的行文逻辑。百年前驼队消失,百年后“我”来追寻真相。“我”要采用何种方式才能了解到当年的往事?可以走访当地的村庄、询问老人,可以查阅相关资料、文献,然而这样便失去了小说原有的风味,同时也无法满足作者本人想要展现小说趣味性的强烈愿望。通过“与灵魂对话”这样看似鬼魅的方式,让一个个代表不同象征意义的灵魂上场,从自己的视角来观照自己所理解的世界,作者则躲在文本后面,采用一种不慌不忙、游刃有余的态度,时不时将一些关键信息抛出来一点,而转眼间在另一种视角下所谓的关键信息又变得一文不值。读者就在这忽而提心吊胆、忽而大失所望又忽而满怀期待的状态中充分领悟到幽魂叙述与文本故事性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便是小说的责编陈彦瑾女士所言的“好看的小说”。不同灵魂的不同叙事其实是一个不断建设又不断解构的过程,读者在这一过程中也跟随着“我”不断经历着相信-质疑-旁观的过程。而之所以称之为“好看的小说”,更在于《野狐岭》不仅仅在叙述形式上呈现出与作者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的特点,而且体现为叙述末尾的开放式结尾上。经历过末日般的沙暴,作者笔锋一转,将走出野狐岭的过程简略为“我们吃驼肉、吞雪,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野狐岭”[2]400。故事的最后,不仅“飞卿终于活在了凉州的传说中”,所有文本的人物亦是“活在传说里”。作者自己所构想的结尾仍然隐晦地存在于不动声色的文本叙事中,而读者所要追寻的结尾,或者与作者不谋而合,或者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读完仍然搞不清楚当年两只驼队究竟在野狐岭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对《野狐岭》,你也可以成为话题小说,里面会有很多话题和故事。……无论你迎合,或是批评……或是剖析,或是虚构,或是考证……我都欢迎……这时候,你也便成了本书的作者之一。”[2]416这里作者表明《野狐岭》的悬疑,既在于幽魂叙述所营造的神秘性、悬疑感,又在于引导读者将自己融入文本中进行文学再创作的可能性。
三、叙事地域性的超越
雪漠的小说一向带有浓厚的西部地域风情,展现出西部荒凉沧桑的自然环境和惊心动魄的人事。这与作者的甘肃籍作家身份及其“家乡责任意识”是分不开的:“关于木鱼歌、凉州贤孝,关于驼队、驼场、驼道、驼把式等许许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中的一些东西,小说中的描写又有着风俗画或写生的意义。这一点,在本书中显得尤为明显,也跟我以前的小说‘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定格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一脉相承。”[2]417小说中,作者依旧将故事发生的舞台投向了西部荒漠中的野狐岭,但其在叙述地域性上则体现出了明显的超越,而这一超越源于其西部写生与岭南叙事相结合的新型视角。
《野狐岭》中与地域性息息相关的关键词有二,即凉州歌谣和木鱼歌。雪漠身为凉州人,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第十三会《纷乱的鞭杆》中,作者不惜采用大量的笔墨来复述凉州歌谣《鞭杆记》当中的内容来表现人民暴动的场景。单独将这一话以及每一话开头所引用的驼户歌拿出来,毋庸置疑是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的。而将其置于整体的文本当中,作者笔下的故乡便有了一种厚重朴实的感觉,这种浓郁的凉州文化底蕴与作者之前的“大漠三部曲”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孙英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雪漠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虔诚的‘西部乡土情结’,自觉地肩负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几十年如一日奔走在大漠乡土中……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直面人生的精神风格与审美向度,成为乡土小说在新世纪的重要收获。”[3]而即便是同样写西部,写凉州,其超越性则体现为,《野狐岭》中的大漠与作者其他作品中的大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于作者在该作品中尝试采用了全新的写作手法与叙述方式,因而原本荒凉、无情、严酷的大漠,在《野狐岭》中多了一分神圣、庄严和肃穆,这即是陈彦瑾女士所言,“创造了有一个新鲜的大漠……《野狐岭》里的大漠……涌动这一股快意酣畅之气。”[2]426由于不同灵魂视角观照下的野狐岭千姿百态,因而《野狐岭》本身也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不可知的神性特点,这是作者想要呈现的“新的大漠”,也是他由“眼中的家乡”到“心中的家乡”创作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木鱼歌是《野狐岭》中贯穿全文的另一关键词。作品中的重要人物木鱼妹出身于岭南,是木鱼歌的惟一继承者,也是齐飞卿、马在波等人心目中“圣母”的形象。实际上木鱼妹之所以被视为圣母,正因为她是木鱼歌的载体,或者说她是木鱼歌的化身。木鱼歌是岭南民间(以东莞地区为盛)盛行的一种歌谣,在文中木鱼妹不厌其烦地以“珍贵”、“伟大诗篇”等词语来形容木鱼歌,这即是说,木鱼歌是岭南风土人情、传统精神文化的真实记录形态。小说中木鱼妹的坎坷遭遇实际上也象征着岭南木鱼歌的流离,象征着岭南传统文化在历史浮沉中饱经起落的真实命运。而另一方面,作者还不遗余力地分别在第五会与第七会中,用大篇幅集中描写了土客械斗的场景。尽管械斗的地点发生在岭南而非凉州,在作者的笔下,一样地惨绝人寰,一样地灾难深重。这其实也隐晦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人文关怀:即天南海北不同地域之间的人群纷争,都是一样的残酷野蛮,同样的触目惊心。岭南与大漠本相隔千里,在作者的安排下,吟唱着木鱼歌的木鱼妹来到民歌民谣盛行的凉州,最后又跟随众人消失在野狐岭,这既给岭南木鱼歌增添了了几分传奇色彩,又间接地指出了岭南木鱼歌与凉州歌谣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与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岭南土客械斗与凉州暴乱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此外,木鱼妹亦是岭南劳动人民的化身,她顽强、坚毅的性格可以看作是岭南人的真实写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木鱼妹的形象与西部女子的形象更为贴近,这说明作者在写木鱼妹时,依然有意无意地将其当做一位西部女子来写,所以说,木鱼妹是披着岭南人外衣的西部女子。而就叙述视野而言,作者一改之前单纯集中于西部大漠的习惯,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凉州与岭南两地联合起来。而这一结合作为雪漠的第一次尝试,很明显地存在着些许不足。实际上,作者更习惯于西部写生,虽然他开始尝试着描写西部之外的风土人情与世相百态,对土客械斗与木鱼歌进行了一定的阐释,然而全文仍然笼罩在一种浓郁的西部风情文化氛围中,雪漠在岭南风物、风情的描写上,对于客家人文化心理特质的挖掘上仍显笔力不足,这与作者在岭南的客居人身份有关,也为他之后的作品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深化的可能。
四、雪漠的少年心性与脉脉温情
《野狐岭》的问世标志着雪漠在一条新的文学道路上重新出发,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充满可能性的天地。这一尝试性、探索性与作者的少年心性和脉脉温情是分不开的。一直以来学界对雪漠的研究,大多着眼于“灵魂叙写”、“西部写生”等方面,鲜有人探析过雪漠的创作心境与内心激情。在雪漠的作品中,有一种少年心性的特质隐含其中。雪漠濡染佛教智慧数十年,其心性逐渐趋于一种澄明自得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与物质世界中少年的纯真心性是异曲同工的。他在《野狐岭》后记中这样写道:“一进入写作状态,灵魂就自个儿流淌了,手下就会自个儿流出它的境界。”“写这些书时我很快乐,我在享受那份文学独有的快乐。”[2]415这说明雪漠在创作上开始有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味道,而这便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野狐岭》中会采用一种超越灵魂视角的视角,这种“有意而为之”是一种创作上的大胆突破,也是作者心性的真实表现。此外,针对自己在文本中有意铺设的各种剧情伏笔,他说:“我甚至欢迎你续写其中的那些我蓄势待发、却没有完成的故事。”这颇有推理小说中“挑战读者”的意味,隐藏在文本后的雪漠是一个狡黠甚至说有点调皮的角色,他正躲在舞台角落悄悄关注观众的反应,期待着读者的互动。另一方面,他这样评价自己:“雪漠既有扎实的写实功力,更有超凡不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我已经看清了横的世界和纵的历史那个坐标。我不是闭着眼盲目地偷着乐。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局限,也清楚地明白自己的优势。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在那儿。”[2]418这一评价恰是其少年心性的凸显。率真的言语或许容易遭人误解,却极为真诚。真正的谦虚是知道自己的能与不能,既肯定自身之长,也不回避不足。倘若遗失了自己的少年心性,雪漠是不会有这般坦率的境地的。
雪漠的脉脉温情是相对于当下的青年而言。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经济背景下,尝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青年在纷繁的选择面前难免会感到无所适从,雪漠在代后记《杂说<野狐岭>》中给予读者真挚的鼓励,寄予了希望:“相信你要是像雪漠这样努力的话,也一定会成功的。”他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写作习惯,即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进行实地考察,搜集必要资料信息,对所要描写的对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大漠三部曲”如是,“灵魂三部曲”如是,《野狐岭》亦如是。这实际上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艺术的根源在于现实,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五、结语
“真正的文学,其实是为自己或是需要它的那些人写的。老是看世界的脸色,定然写不出好东西。”这是雪漠的文学观,同时对于当下正在进行文学求道的青年而言也是有着重要的鼓舞和教育作用的。《野狐岭》展现了一个发现新天地的雪漠,也让读者对雪漠有更进一步的期待。
[1]陈思和.“西部文化与文学精神”讲座上的讲话[N].东方早报,2005-9-8(A15).
[2]雪漠.野狐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3]孙英.论雪漠文学创作及其时代精神[D].兰州:兰州大学,2012.
[责任编辑 龚 勋]
I247.5
A
1008-4630(2015)01-0016-04
2015-01-06
吴浪(1991-)男,江西南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