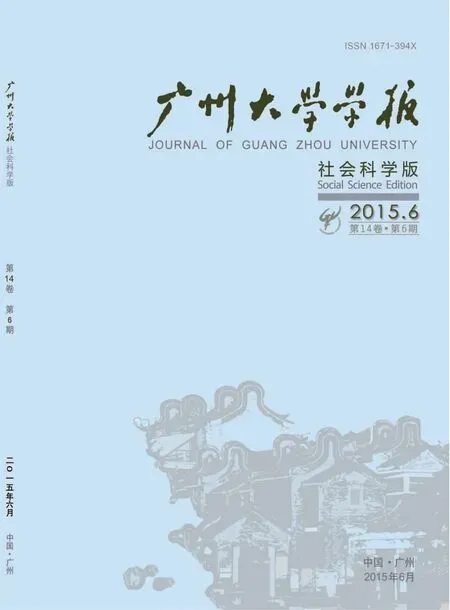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者
2015-03-20仝婉澄
仝婉澄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006)
关于舞台演出的记载,自然以演员为中心。元人夏庭芝的《青楼集》,是我国古代仅存的主要记载元代戏曲、曲艺、歌舞艺人事迹的专书。明代万历年间潘之恒的《亘史》《鸾啸小品》中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清朝中后期北京的戏曲活动进入极盛期,各种各样类似观剧指南的出版物大行其道。随着欣赏者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和优伶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品花”为主的戏曲批评慢慢走向了对流派的鉴赏评析和对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王梦生的《梨园佳话》(商务印书馆,1915)、穆辰公的《伶史》(宣元阁,1917)、周剑云的《鞠部丛刊》(交通图书馆,1918)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
戏曲活动繁盛一时,不仅受到国内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也引起长期居住于北京的日本人的兴趣。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中国剧》与《中国剧及其名优》的出版在当时受到了不少关注。
一、辻听花与《中国剧》
1898年,辻听花来华视察教育情况时即开始看京剧,对京剧一见钟情。他说:“我第一次看京剧为什么那么喜欢,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理由,只是身处剧场中面对舞台,听到演员的唱腔、道白,看到他们的表演时,自然而然地被吸引了,只是感到戏里有有趣的东西。”[1]446-447辻听花在1909 年至1910 年前后创作京剧剧本《兰花记》。1912年供职于北京《顺天时报》社,成为文艺副刊的编辑,次年设“壁上偶评”栏目,发表了大量戏曲评论。辻听花在对中国戏曲逐渐了解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意识到记载这段戏曲发展史的重要性。1914年,辻听花在《年头初感》一文中写道:“我想奉劝戏曲界的有志者,乘上述著名演员健在之时,若能将近五六十年间中国戏曲的变迁、各名伶的艺术及其自身的详细经历、知晓的轶事奇闻编成一书,一定是件好事。”[1]474辻听花的《中国剧》(北京顺天时报社,1920)即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
早期的剧评家冯叔鸾为辻听花《中国剧》作序,序中对该书大加赞扬,现择其要点摘引如下:
扶桑听花君有《中国剧》之作,遗书于余,以内容、节目见示,分章凡六,子目五十有八,冠以绪论,缀以表式,虽尚未睹其书,而据此亦足悉其梗概,不能不叹其致力之深,探索之勤也。
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始稍稍有以谈剧文字见诸著述者。然以研究无素,故多隔靴搔痒之词。其能述伶官之旧闻,纪歌场之轶事者,已称凤毛麟角,然祗历史上之观察,而非艺术上之研究。惟王梦生君所著之《梨园掌故》,号称博洽,顾其实,则亦粗示涯略而巳,未能纲举目张也。今兹听花君之作,不知较王氏为如何,然就其节目观之,似比较的有统系。
而听花君此作,乃同时并有英文、日文刊本,是他日我中国剧得列一席地于世界的美术界者皆出于兹编之介绍,此尤我国嗜剧同志所应同声致其感谢者也。是为序。[2]170-171
冯叔鸾将辻听花之作与王梦生之《梨园佳话》相比,认为其结构有系统,自是言而有据。王梦生的《梨园佳话》分“总论”“诸剧精华”“群伶概略”“余论”四个部分,基本上呈现出了对戏曲界概况做梳理的意识,然而这种叙述更多地带有随意性。比如“诸剧精华”一章就题目来看,应是围绕诸多演剧剧目所作。然其中杂入了“生旦等称名之义”“老生唱法”等小标题。而对演出剧目的论述,作者着重在给读者讲述自己的主观感受,如《空城计》一剧结尾处说“此等字句中皆有精意,惟在能得其意而肖其口吻以出之,全剧之佳,乃叹观止矣。若不分析及此,宁不负此佳剧耶?”[3]与之相比,辻听花的《中国剧》分“剧史”“戏剧”“优伶”“剧场”“营业”“开锣”等多个部分,表述清晰,结构严谨,确是有系统的开创之作。
《中国剧》自1920年由顺天时报社刊行以来,颇受欢迎,一版再版,1925年第5版后改名为《中国戏曲》。时至今日,辻听花的《中国剧》仍在继续发行,中文方面有浙江古籍出版社据《中国剧》第5版排印的《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2011),日文方面有东京大空社据1923-1924年中国风物研究会版的复印本(2000)。
二、波多野乾一与《中国剧及其名优》
稍后波多野乾一出版了《中国剧五百番》(北京中国问题社,1922)和《中国剧及其名优》(东京新作社,1925)。《中国剧五百番》收录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京剧剧目600余种,从剧种数量来讲,已达到了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1957)收录1 295种的近一半之多。它按照故事发生的时代顺序排列,以日语写成,对于近代京剧走向海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4]如果说《中国剧五百番》主要是为日本读者写作,那《中国剧及其名优》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颇具影响。该书的突出优点亦在于结构,试将其与同时代的《伶史》相比较。《伶史》按本纪十二、世家二十分类,以传统的传记体形式为32位演员立传。虽对于每位名伶的家世、风格、趣闻都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师承、流派进行纵向的系统梳理。《中国剧及其名优》则弥补了这一点。该书分十一章,分别是“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旦”“老旦”“武旦”“正净”“副净”“武净”“丑”。以行当为分类标准来统领全书,且在每章中按照时间先后编排,对程长瘐、张二奎等重点人物以单节介绍。
在此需要辨明的是,如果说辻听花有着写作中国戏曲史或是演剧史的意图,那么波多野乾一自身则并没有这种想法。他在出版《中国剧五百番》时,向读者许诺会再出关于中国名优评传的专书,说明他只是将《中国剧及其名优》看作介绍中国演员性质的专著。只是鹿原学人姚伯麟在看到此书后,认为其系统井然、编纂得法,更名为《京剧二百年历史》,并补充了部分伶人事迹,1926年由上海启智印务公司刊行。此后,该书被视为京剧史研究学者的必读书目,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的附录中列出了“京剧二百年史中伶人的详细籍贯”,亦是对此著作的认可。幺书仪认为,经过全书11章的条分缕析,京师舞台上二百年间生、旦、净、丑各个行当的京剧名伶的身世、派别、风格、师承,都有了交代。称其为“戏曲史”或“演剧史”并不过分。[1]433
三、写作背景及素材来源
以上均从结构方面肯定了日本学者撰写有关中国戏曲的相关著作,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写作上有着这种不同之处呢?首先日本人在面对异国戏曲进行写作时,更侧重传达的是中国戏曲的特有的东西是什么,有一种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客观性。不放过任何的细节,重视对背景知识的介绍,都是与之关联的反映。比如在谈到戏班中戏剧行头的管理和放置问题,辻听花根据赴剧场实地调查之结果列举了详细的目录。“作为日本人,观察中国的戏班子,自有一种新鲜感,自己记录也好、面向日本国的读者介绍也好,如实的记录中国戏班子的一切详情,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视点。”[1]85同理,波多野乾一在每一个行当前都有关于这个行当历史及变迁的详细介绍,也是因为面对的大多是对京剧一无所知的日本国民。另外,日本学者试图在比较中国戏曲与日本、西方戏剧的异同中揭示出中国戏曲的独特性。辻听花在《中国剧》第二部分“戏剧”中首列“戏剧之特色”一节,谈到“歌曲与喉咙”“听戏与看戏”“歌与调”“一人剧”“无帐幕”“布景与戏具”“脸谱”“做派与说白”等中国戏曲中独特的部分,并对比了中国戏曲与日本剧、能乐、西洋剧的异同。
这些日本学者关注中国戏曲也带有了解中国国民性的目的。辻听花在《中国剧》的绪论中说:“关于剧戏内容及观客方面,仔细研究,可以知华人之国民性质何如矣。”“故予对于中国戏剧,既目之为一种艺术,极力研究,又以之为知晓中国国民性之一种材料,朝夕穷究,孜孜弗懈”。[2]1-2
两位日本学者还将自身对于演员演技的评价融入书中,体现出了日本人的审美倾向。例如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都十分欣赏郝寿臣,赠送他“活孟德”之称。波多野乾一称郝寿臣为“中国剧界第一副净”,认为他在现存名伶中,如武生杨小楼、旦角梅兰芳、老生余叔岩,与之比较短长,亦一步不让。波多野真矢在《民国初期在北京的“日本京剧通”》一文中比较了出版于1918年的《鞠部丛刊》与《中国剧及其名优》对于郝寿臣的不同评价,认为波多野乾一对郝寿臣的评价与众不同,有着独特的眼光。[5]
“评剧最难,无戏学知识者,不足以评剧;无文学知识者,不足以评剧;看戏不多,不足以评剧;戏情不熟,不足以评剧”。[6]这几句话确实道出了评戏之难,对于中国人是如此,那对于日本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中国剧》和《中国剧及其名优》都涉及到对演员的评价,后者尤多。这两位日本学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主要得益于与中国演员的密切交往。辻听花钟情于京剧,常住北京并终老于此,与当时的剧坛人物多有联系。其在《中国剧》一书的凡例中说:“除自己研究外。由汪笑侬、小连生(即潘月樵)、刘永春、崔灵芝、王瑶卿、孙菊仙、时慧宝、熊文通、小桂芬(姓张)诸名伶,及杨鉴青、陆文叔诸君所获者甚多。兹谨谢其隆意。”桥川时雄编之《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其中搜罗戏剧界资料较多,与辻听花的交际有直接关系。[7]波多野乾一长期生活在北京,与梅兰芳、尚小云、郝寿臣、刘如山交情颇深。
演员之外,他们还受到当时戏曲研究的影响。汪笑侬是与老生“后三杰”同时期的老生演员,他的唱腔另辟蹊径,亦称汪派。辛亥革命后,汪笑侬在天津戏剧改良社,专门致力于培育新演员和戏曲改良运动。1914年,辻听花为汪笑侬《戏曲讲义》作序,“余披而阅之,觉中国戏曲之源流、音调之标准以及剧家之状态、粉墨之规矩,言简意赅,使人一读了然,诚破天荒之杰作,而中国剧界之宝筏也。”[1]476可知汪笑侬的《戏曲讲义》对辻听花的触动。精通日本音乐与中国音乐关系的少少,在为《中国剧》的题词中说:“余三年前曾草《中国戏剧史发凡》一编,剑堂见之,颇有契合。”[2]166亦可知辻听花的友人对中国戏曲的梳理应当对《中国剧》一书的写作有所影响。齐如山是梅兰芳身边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傅芸子称为国剧的整理派。[8]波多野乾一亦是梅党成员之一,梅兰芳的两次访日均亲自陪同,且与梅家有通家之好。齐如山为梅兰芳访美准备的《中国剧之组织》(1928)共分八章,分别为唱白、动作、衣服、盔帽靴鞋、胡须、脸谱、切末物件、音乐,即是经波多野乾一翻译成日文。[9]
中国当时资料性相关书籍陆续出版,也为日本学者的写作提供了不少帮助。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剧五百番》,介绍了五百个京剧剧本的内容梗概,出自民国初年陆续出版的《戏考》。波多野乾一曾在《中国剧及其名优》一书序言中说到书中材料来源之一即“中国人断片的著述记录”,有学者指出波多野所用之材料多出自《鞠部丛刊》[10]。
四、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的影响
放置到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整个历史中来看,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对于中国戏曲的热情及其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日本学者有着直接的影响。以写作《中国近世戏曲史》而闻名的青木正儿,研究路数与辻听花不同。但青木正儿1925年以戏曲研究为主题赴北京游学时,迫切地想要拜访听花先生,向他请教。[2]192这也说明了辻听花在当时还是取得了日本后学的认可。受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影响较深的是滨一卫,他1933年毕业于京都大学,1934至1936年在北京留学,喜好中国戏曲,流连于各个剧场,搜集相关资料。滨一卫于1936年出版了《北平的中国戏》,1944年出版了《浅谈中国戏剧》,他在《浅谈中国戏剧》一书的序言中,对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的两部著作推崇备至,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品。[11]序而仔细查看滨一卫的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著作的痕迹。该书共分为十六部分,依次是序论、中国戏曲的种类、中国戏曲的演员、剧场、脚本、中国戏曲的约束、扮像、场面、腔调、道具、戏班、科班、观剧的实际、话剧、中国戏曲三十种大意及评价、其它。其中关于剧场、脚本等的论述皆可从辻听花的《中国剧》中找到根源,而第三章“中国戏曲的演员”,从生、旦、净、丑等行当划分,又与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剧及其名优》相近。现将滨一卫《浅谈中国戏剧》一书第三章“中国戏剧的演员”中关于老生的论述细目,与波多野乾一书中的相关细目列举如下:
波多野:老生的定义—分类—唱工老生—衰派老生—红生—以人为代表的派别—程长庚派—奎派—余三胜派—汪派—孙派—潭派—刘派—汪笑侬派
滨:老生的性质—程长庚—汪桂芬、孙菊仙和王凤卿、时慧宝—谭鑫培—谭腔的由来—谭腔成立的好机—谭腔的特长—谭腔今日依然占有王座
不仅是在结构上,具体到对演员的评价上,也可以看出这种传承。例如,滨一卫对郝寿臣的评价也是相当高的,这与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的影响也是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滨一卫有意识地向齐如山、周贻白学习。滨一卫《北平的中国戏》中征得齐如山的同意转载了不少齐如山著作中的插图和照片,并尝试翻译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惜未完成。[12]这些也可以用来解释滨一卫在辻听花、波多野乾一的基础上有所超越的部分原因。
综上,辻听花和波多野乾一从实际的观剧感受出发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北京剧坛,他们的成果为此后的中国戏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是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1]幺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辻听花.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王梦生.梨园佳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4]李莉薇.波多野乾一与中国京剧在日本的传播[J],日本研究,2012(4):122-128.
[5]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418-431.
[6]冯叔鸾.啸虹轩剧谈[M].上海:中华图书馆,1914.
[7]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17.
[8]傅芸子.中国戏曲研究之新趋势[J].戏剧丛刊,1932(3).
[9]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200.
[10]苏移.京剧二百年概观[M].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348.
[11]浜一衛.支那芝居の話[M].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
[12]中里见敬.滨一卫看到的1930年代中国戏剧——一个开拓表演史研究的日本学者[C]∥中国戏剧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代戏曲学会2014年年会论文集(上),2014: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