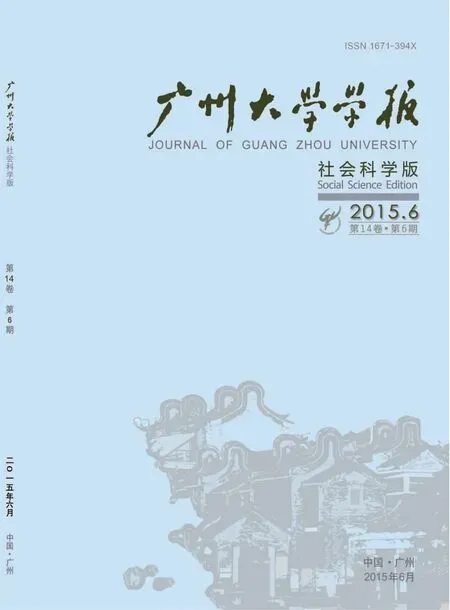印顺“人间佛教”伦理观刍议
2015-03-20谭苑芳
谭苑芳
(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006)
自20世纪初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理念以来,“人间佛教”已经逐渐为中土佛教界所广泛接受而为公认的当代佛教发展方向。1983年,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今后中国佛教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人间佛教”[1]。与传统佛教相比,“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其“人间”指向。亦即是说,佛教一切精神信仰都将落实于现世的、具体的、可以感知的“此岸世界”,而非飘渺且难以认识的“彼岸”。就其源而言,太虚“人间佛教”的理念之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应对策略色彩,乃是针对中土佛教长期的窳败和民国时期战乱的时代需求。[2]9-20尽管它有着长远而深厚的原始佛教教旨依据,但其实质却是特殊时期的非常构想;这一构想的现实指向性使其天然具有伦理属性。而“人间佛教”之所以存在并深入民心的实践性也在于极力彰显、贯彻其佛教伦理意味于种种信仰的行为之中。
作为太虚学生的印顺法师继承了“人生佛教”的精髓,并进一步将其完善为“人间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人间佛教”;甚至有学者认为,“而成熟的‘人间佛教’理论形态则是在释印顺那里才得到明确建立”[3]。因此,剖析印顺“人间佛教”的具体内涵和实质,特别是从不同侧面切入印顺“人间佛教”思想,有助于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社会语境中展开“人间佛教”建设,发挥宗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而这恰是以往的“印顺研究”或“人间佛教”研究所忽视之处。本文拟就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伦理观做初步探析,辨析其伦理观的主要内容,并着力从中找寻与西方伦理学思想相契合之处,以求通过比较的视野与方法,能够更好地把握印顺“人间佛教”的丰富内涵。
一、印顺人间佛教的实践理智属性
“人间佛教”的伦理观首先强调的是其现实精神,即在社会实践中完成人格的超越(成佛)。这当然是“对治”的要求,但也显现出某种精神上的指引。印顺说:“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而且还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4]125。前者可以认为是“人间佛教”的实践品质,而后者则表现为精神、意志上的作用——人的理性选择。佛法并非俯拾即得,而是需要主体去“求”“习”“修”才能得到的,这就为个体精神的理性参与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从这个根本意义上来讲,“人间佛教”乃具有实践理性的属性。
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概念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划分了人的不同属性:实践理智(明智)、技巧理智和理论理智(理智),其中实践理智属性是人的理智运用的重要表现。它表现为人在对他者交往的事务中进行理智的思考,进而决定在其中求得正当(真)与善的方式,即“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5]1140。而在“人间佛教”的理念框架中,既定的“佛法”即是衡定真与善的标准,也是真与善本身。《菩萨璎珞经》云:“顺第一义谛起名为善,背第一义谛起名为恶。”[6]1021这里的“第一义谛”与西方的逻各斯(Logos)也有类似之处。因此,可以认为,“人间佛教”的实践理智乃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意识(心),将其作为“行为善恶之决定者”。“人间佛教”认为,心(理智)对实践的意义表现为“心对根身的主宰力、心为善恶的发动,以及心能影响报体等”。[7]36-40这些方面突出了人的理性意识在实践——包括对个体(根身)、社会行为道德(善恶)和行为效果(报体)的实践——中的作用,是一种指向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理念。
在“人间佛教”中,实践理智主要表现为《金刚经》所言的“应住”或“降服其心”。人的主体理智可以有两种面向,向内则是应对个体的内心烦恼,向外则是以对待种种事物,即实践。后者既是前者产生的原因,也是其所处的语境,还是检验主体“发心”善恶的试金石。换言之,乃是外向的社会实践使得人的烦恼被理智感知;外向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伦理判断(善恶、正当与否等)促成或阻碍了主体的社会行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实践理智与道德德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其直言:“明智是一种德性”[4]1140。实践理性的属性并非外在于人的道德制约,而是内在于实践之中的,具体说是作用于人心的。实践理智所追求的“善”并不具有强制性,而是实践本身所要求的,也是主体的伦理意识所要求的。通俗地说,“人间佛教”的实践理智即是印顺所言:“要老老实实地觉得自己有种种烦恼,发心依佛法去调御它,降服它。”[4]127可以说,主体所抱持的“老老实实”的态度和行为就是印顺“人间佛教”实践理智属性的典型表现。
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宗教形态的“人间佛教”之实践品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之间可以画等号。二者仍是出于不同时代需求和不同思想传统所提出的哲学—社会命题,它们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佛法”本身兼具外在于人与内在于心的双重属性。事实上,这也是西方哲学逻各斯与“佛法”的根本区别所在。佛教经典强调“佛法”必须“求”“习”“修”,即主体必须依照佛教教义而行事、运思,这是“佛法”外在于人的表现,“人间佛教”也不例外。印顺指出,“佛法,只可说发见,不像世间学术的能有所发明。因为佛已圆满证得一切诸法的实相,唯佛是创觉的唯一大师;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温故知新而已”[4]125。这与西方伦理学重视个体精神与自主力量的传统是迥异的。同时,印顺的“人间佛教”特别强调个体依品次第进修的重要[7]75-76,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轻视了个体独立思考能力的。更为重要的是,“人间佛教”理念成立的根本前提还在于,承认“佛性本人人自有”的命题,主张成佛乃是一种生命的超越性体验。这显然与西方先验的逻各斯中心是大相径庭的。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实践理智、技巧理智和理论理智,后两者在大乘佛教的教义中并未付诸阙如,只是“人间佛教”,尤其是印顺的“人间佛教”在教旨上不是那么强调人的主观意识、逻辑判断中对“技巧”和“理论”的把握。传统大乘佛教中,“五明学”乃是“慧”的主要内容。《瑜伽论》言:“菩萨求法,当于五明处求”[8]227,其中“声明”“因明”“内明”当属理论理智;“医方明”“工巧明”等实用的社会知识则可归于技巧理智。然而,“人间佛教”其意之所指却并不在于“技巧”或“理论”。印顺的远见在于,他已经意识到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技巧”或“理论”早已不是缺乏而是远远溢出了人们固有的需求,不断通过媒介技术而膨胀,甚至成为统治人的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所认为的人之“异化”正在于此。“人间佛教”理念于此有着巨大的精神超拔作用。
总而言之,印顺“人间佛教”理念的实践理智是综合了技巧理智与理论理智的一种居间形态。所谓“佛化的道德在般若”[9]212,它并非纯粹实践的,也非纯粹沉思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引导主体寻找正当与善的意义。它同时作用于人的理性与感情,形成了完整的宗教信仰。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三分法具有明显的递进色彩,即理论理智最高,实践理智次之,技巧理智最次;而印顺“人间佛教”伦理观则以“实践理智”为居中,调和了“理论理智”与“技巧理智”,绝不偏废,显示了后发佛教理论的圆融。因此,印顺“人间佛教”的伦理色彩显然更具说服力。
二、印顺人间佛教的交往伦理学意涵
伦理学是研究社会交往事务的学问,而“人间佛教”正是发自社会交往的一种宗教诉求。佛教立意之初,即是为了应对人生之苦。印顺说:“世间无处不充满忧苦,就人类来说,最严重的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了。”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印顺将人间关系之苦归为“个人”“家”“国”和“全世界”四类,[9]114分别予以评析。这一思路的出发点是原始佛教的基本观念,《中阿含·苦阴经》即云:“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仗转向加害。”[10]585印顺认为,这一状况“千古如此,于今尤烈”,现代社会在通过“世间一切学术——医药、教育、竞技、工巧、政治、法律,以及科学的声光电化”来“解除苦厄”之外,“又有新的忧苦”。[9]116-117因此,应对社会问题的根本方式不在于科技的“解厄”,这一点早已为西方哲学为现代性“祛魅”之说所证实。“人间佛教”提出的应对方式,仍是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具体而言,印顺提出,欲诤、见诤、慢和痴四种因素构成了人际交往的主要障碍和危机产生根源。[9]118-126显然,尽管这四种因素是由人心之兴发感动而生成的,但其作用对象都是指向外在的他者,是主体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之中才发生作用的。
这一点与晚近以来兴起的交往伦理学间有着颇为相似之处。随着多元文化的出现,对话与跨文化交流成为共识,伦理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了对交往理性的探讨。其中,哈贝马斯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必须以相互可理解的环境因素为背景;交往的目的在于寻求协调与合作;交往行为也寻求建立共同的理解。[11]99-100这与印顺“人间佛教”所倡导建立的“佛化人间”(或称“在家的佛教”),即以和敬为目的的人类群体生活是相一致的。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却并不是单纯的“日常交往”,而是带有哲学意义的反思性交往。这在操作层面上就排除了从事诸如以经济、政治等为目的的交往活动进入其所关注的范畴,从而阻断了社会伦理在交往伦理中发挥根本性/指导性的作用。
印顺的“人间佛教”之交往伦理意味,着眼点在于“法味同尝”。以家庭为例,“一个在家的正信弟子,如果对佛法有正知见,有真信仰……家庭的每一分子都能信受佛教,领受佛法的利益。”这就要求在家的佛教徒与其家人有相互可理解的环境,并其目的都在于推动家庭的幸福;通过在家佛教徒的解说与引导,一个家庭建立了共同理解的基础,在此之上而寻求现实的突破:“一位在家弟子,皈依三宝以后……对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夫妇,更体贴、更亲爱,更能尽着在家庭中应尽的责任。这样,家庭因此而更和谐,更有伦常的幸福,大家会从他的身心净化中,直觉到佛法的好处,而自然地同情,向信佛者看齐,同到三宝的光明中来。”[12]28-29如是建立一种“交往的循环”,不断由社会实践的行为(不仅是哈贝马斯所谓反思性的哲学交往,而是包括重复性的日常交往)推动社会认知的基础,再由对社会认知的意识来促进社会实践的“佛化”,最终都指向佛法之所认同的“善”与“正当”,由家庭而及国家,由国家而及国际,这样,“人间佛教”才有得以全面实现的可能。这当然是一种日常的、重复的,并在重复中不断深化的伦理作用。因此,可以说,印顺“人间佛教”的基本构思都是立基于社会交往的伦理意义基础上的。需作说明的是,“人间佛教”所强调的家庭伦理,同样是以情感为基础的,是一种“正当”的情感。[13]135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也试图沟通所谓“三个世界”,即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他说交往的参与者乃是“对三个世界中行为语境的不同因素进行归整”[11]100。这说明哈贝马斯并不仅关注人的主观反思,他的理论也兼具有生产性的“技巧理智”,又具有哲学性的“理论理智”,前者以外在的目的性为特征,后者则重视内在的目的性,二者都关注社会行为的内在善恶问题。但是,哈贝马斯却将其局限于反思性而非重复性的哲学交往之中,这就决定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难以对全社会产生普遍而深远的影响,难免最终沦为精英哲人的沉思与独白,或知识分子为社会开出的一厢情愿的药方。与之不同的是印顺“人间佛教”理论中切实的伦理指向。印顺说:“在水中救人,是不能离水上岸的。要学会浮水,也非在水中学习不可。菩萨要长在生死中修菩萨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学习,要有一套长在生死而能普利众生的本领。”[14]94菩萨行的关键是慈悲,即是善的利他行;“人间佛教”作为大乘佛教的教义就在于它要从现实的利他行中去成就自我。印顺说:“大乘道,发愿以后,就应该见于实行。”[14]95这种“实行”就是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是一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之上的善行。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单方面沉思,而是由深厚的佛法积淀来完成“沉思”或“反思”的功能,个体只需要按照既定的“善法”经行即可成就。
更为重要的是,“人间佛教”将交往不仅看成是人类群体(如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是一种成就自我的修行方式。这一点是非宗教的交往伦理学所无法兼容的。换言之,在善与正当之上,“人间佛教”的交往伦理还具有超越性的指向,它由“人间”指向“天国”,由“此岸”指向“彼岸”,具有很强的形而上色彩。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人间佛教”理念就会被庸俗化为社会慈善精神或志愿品质,从而成为仅具有伦理意义的一般社会理论。
三、印顺人间佛教伦理的形而上指向
就伦理学的目标而言,其规范性的论述之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个体的道德觉解。[15]217可以说,一切哲学思辨的目的,都是在于使主体精神能够“觉悟”或“理解”。伦理学如此,宗教更不例外。印顺“人间佛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人间净土”,但其路径也是通过作用于个体的心性,来实现从“有漏”到“无漏”的转变。因此,就修行方法上来讲,强调交往、强调他者和群体的伦理最终要回归到个体的心性伦理上来。亦即是说,“人间佛教”伦理的实现与否,乃是维系于个人的道德觉解。个体的问题,是“人间佛教”超越性指向的核心;个体的善恶观,是“人间佛教”伦理所要涵化的主要内容。
一般认为,个体的道德觉解要经过由对规则的觉解到对正当性的觉解,进而才是到德性的觉解。[15]221这三者之间是一种逐层递进的关系。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一“三段论”可以发现,此种伦理论断的标准是由外而内的,其所建立的基础并不是主体自我,而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实践规则。这与印顺“人间佛教”的伦理观很不一样。印顺说,佛教道德的“三增上”,首先是建立在自我基础上的。“时常唤起自尊心……尊重自己,扩展自心的德行,负起自救救他的重任。尊重自己,不甘下流,便是促进道德的主要力量。”[9]21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法增上”与“世间增上”,由外在环境的力量对个体的道德选择形成某种规范。这意味着,“人间佛教”将人视为可以通过先验的精神加以调教的个体,不断强调“学佛即是道德实践”,以充分的戒律来保证烦恼的断除,消灭“散乱、失念、不正知”[9]215;《华严经》所云的“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16]847,乃是诸多大乘经典所共同奉持的金律。而西方伦理学则认为,许多道德品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某个年龄段里“自然地获得的”[5]1143。从此可见,西方伦理学重视的个体经验、强调个人主义,但在具有超越性指向的一面中,西方哲学家却是断然拒绝从个体入手实现转变的伦理规划的。他们或寄希望于从制度、体制等客观方面对社会进行的种种改造,或对科技未来抱持着伦理上的乐观主义。
印顺“人间佛教”对这种伦理思想是有极大的不满的。“人间佛教”认为,学佛或修持佛法的起点和关键都在于“发愿”“发心”,即是率先由自我入手,从“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17]750的真慈悲入手,破除自我,扫荡执见。之所以要从内在的心而非外在的物入手,印顺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解释,他说:
一切文化施设,对于人类忧苦或福乐的关系,异常密切。佛法并没有轻视这些的重要性,而是说:老、病、死引起的忧苦,虽仅是个人的,却是最基本的(也可说最原始的);一切问题、一切苦痛即使解除了,而每个人的老、病、死苦还是存在的。佛法是说:物产的增加、政治的革新等,对人生苦厄的解除、幸福的增进虽极为重要,而最根本的,还是每个人理性的智慧与道德的提高。消除种种不良的心理因素,净化自己的身心。重视个人——根本的革新与完善,才能彻底解除苦厄,实现个人、家庭、国家、国际的真正幸福……以佛法的观点来看,一切忧苦,一切问题,是依人类自己而存在的。唯有从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改善,自己的解决中,才是根本而彻底的办法。[9]117
可见,“人间佛教”的伦理指向并非是一种普遍性的立法,不是康德所言“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18]38-39,而是极其重视个体经验的、从个体出发而抵达群体的关怀。这一点,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特征。印顺也认为,“直觉有我,这种‘我痴’,为‘我慢’、‘我见’、‘我爱’的根源,为‘见诤’与‘欲诤’的根源。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依自己存在而有的一切存在”[9]126。佛教的基本伦理观是建立在一个悖论的基础之上的:它看似承认“自我”的存在,并以此为信仰的立足点,要个体从“心”发愿;同时,它又要求打破“自我”,摒弃“我执”。因此,佛教的伦理指向始终在“自利”与“利他”之间摇摆,大小乘、菩萨与担板汉的区别就此而生。而印顺的“人间佛教”则大不相同,他“以最高之人格安立佛格,让佛陀永远留驻人间”[3],“佛在人间”就意味着人的即身成佛,就意味着成佛的进阶途径是通过利他而实现自利。这是一种在次第间将自利与利他合一的伦理指向。因此,学者周贵华所认为的,印顺的“佛在人间”说乃是对大乘佛教的直接否定,这一观点仍值得商榷[3]。至少在形而上的伦理意义上,“人间佛教”与“大乘佛教”是相融洽的。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说:“趣求诸欲人,常起于希望;所欲若不遂,恼坏如箭中。”[19]176这形象地说明了,自救是救他的前提,而自救的方式乃是去欲,也就是印顺所言的“祛除私我”。此为“人间佛教”伦理的形而上指向之路径。印顺说:“不知者以为佛法的修持与世间与人类无关,这是重大的误解。要化除我、我见,要依戒、定、慧——三学去修习。”[9]214所谓“戒定慧”三学其实包含了技巧理智、实践理智与理论理智三种类型的伦理观,通过修持把握三学就可以稳健地控制自己的德性,运用佛陀所设立的“法”来作为一种内化的尺度。这有类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明智给具体的实践设立“靶子”,人的德性会在明智的引导下“自然地”瞄准,并争取能够“命中”。[5]1138其所不同的是,印顺“人间佛教”为明智设立了不同的境界与层次,要求修持者依品次进行。最终做到“私我净尽,般若现前”。这是“人间佛教”伦理的最高指向,即依靠“般若智慧”来保证善与正当的实践,因此,印顺说:“佛教所说的一般道德,与其他相通;唯有从般若而流出的无漏德行,才是佛化的不共道德。”[9]214而这一切都是要在自家心田里下功夫才能实现的。由上可见,印顺“人间佛教”的形而上指向的主要意涵在于个体心性的调整,以般若智慧为伦理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地实现“即身成佛”的目标。
印顺“人间佛教”的伦理关怀,既有与世间伦理相似之处,也有其鲜明而独到的特征。这些特征甚至与太虚的“人间佛教”也有所不同。或者说,印顺与太虚在为佛教规划应对时代的挑战时,都具有昂然屹立的佛教人格,将铮铮铁骨响彻于圆融博大的佛性慈悲之中。继承“人间佛教”的传统,印顺丰富而深刻的精神遗产尚有待多方面的耙梳与辨析。
[1] 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J].法音,1983(6):13-21.
[2] 罗同兵.太虚对中国佛教现代化道路的抉择[M].成都:巴蜀书社,2003.
[3] 周贵华.释印顺“人间佛教”思想之特质评析[J].哲学研究,2006(11):47-52.
[4] 释印顺.人间佛教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菩萨璎珞本业经:卷2[M]∥大正藏:册24.
[7] 释印顺.学佛三要[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 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3[M]∥大正藏:册39.
[9] 释印顺.佛在人间[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中阿含经:卷25[M]∥大正藏:册1.
[1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2] 释印顺.为居士说居士法[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 布劳德.五种伦理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 释印顺.菩萨心行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5] 廖申白.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6]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0[M]∥大正藏:册10.
[17] 金剛般若波罗蜜经[M]∥大正藏册8.
[18]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9]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34[M]∥大正藏:册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