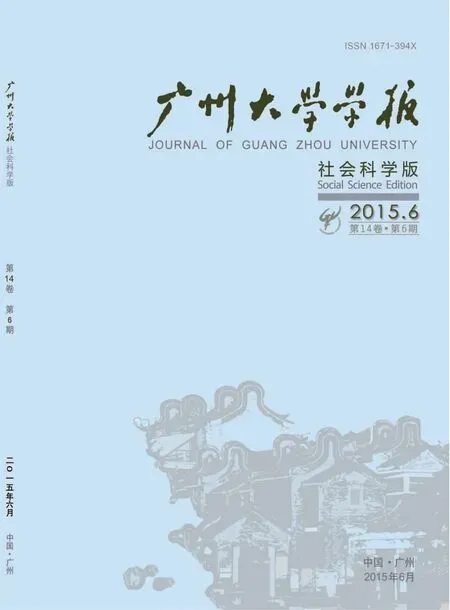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身份建构的质性研究
2015-03-20毛延生
毛延生,虞 锐
(1.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语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新疆大学 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引言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的不断发展壮大。随着2013年第十届城市语言研究会议的召开,“城市语言研究”成为连续入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十一五”(2006)和“十二五”(2011)规划的语言学重点研究方向之一。其中,以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语言研究为对象,进而描述中国社会转型期“城乡互动”语境中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上自我身份建构与解构同语言之间的相互表征问题[1],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农民工”实际上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它使人们难以明白其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现如今,“农民工”概念包括两层内涵:第一,“农民工”的劳动具有季节性、兼业性特点;第二,“农民工”的身份仍然是农村居民,这些人的户口仍在农村。[2]可以说,农民工群体是由我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需求催生的一个身份特殊、数量庞大的流动群体,其身份维度值得学界关注。一直以来,对农民工关注、研究较多的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界的学者,他们关注和研究农民工群体本身,以及这一群体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方式逐渐变为“举家迁徙”,出现了所谓的“农民流动的家庭化”现象。
从语言适应的角度讲,生存物理空间的转换带来其心理格局的重组,方言所建构起来的“自我”遭遇到城市普通话的瓦解,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遭到破坏,他们在破碎的语言世界中无法通过词语使存在得以呈现、出场[3],由此沦为城市化中的“失语”一族[4],而这势必在其身份感知与建构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由于农民工的自我身份建构状况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状况,进而影响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这些又反过来对城市社会产生反作用力,因此基于质性的语言材料来探究农民工的身份维度就显得格外必要。就其意义而言,一方面可以超越一般语言研究“为语言而语言”的研究不足,进而实现“为社会而语言”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有关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决策提供参考。尽管学术界已然意识到农民工多维研究的重要性,并且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研究有一定积累,但是面向农民工的身份建构的质性研究还有待深入展开。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基于访谈类质性研究语料①本文使用的访谈语料全部来自于徐旭初的《生存故事:50 位农民工访谈实录》和魏城的《中国农民工调查》,后文实例不再赘述。我们之所以参考这两部访谈文献进行质性研究原因有两点:第一,所选50 位农民工均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因此也最能体现农民工群体的集体特点与身份特征;第二,访谈内容记录详实、适用于展开深入的质性文献分析,并且为历时性对比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前期基础。[5-6],从语言表征视角出发,分别从身份觉知、身份判断以及身份质疑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群体身份建构情况。
一、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觉知
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的身份建构首先表现为基于城市认同基础上的身份觉知。城市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要素。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即对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文化、市民价值观念群体的日常运作逻辑等的赞同、认可、渴望与同化[7];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认同是农民工对城市地域、市民群体的接纳和归属,以及对市民态度观念的内化[8]。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其对于城市认同的感知程度以及内化程度对于他们身份觉知将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对不同个体来说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在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有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时间较长,城市化程度较高,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里人”;有的农民工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比较大,在城市生活的时间相对较短,在农村生活时间较长,他们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农村人”。我们可以在访谈语料中观察他们对群体身份的具体觉知过程,并将其归纳为“从打工者到流浪者,再到农村人,最后定性为弱势者”这样一个逐层深入的身份觉知过程。
(一)身份觉知一:打工者
觉知(awareness)是一种对某物有所认识或有所意识的内部主观状态[9],身份觉知是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往往表现出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在城里谋生的经历使得农民工群体首先将自身定位为“打工者”。这一点在群际接触的经验性反思中体现得格外明显。
语料1
[受访者:黄叔叔;籍贯:浙江宁波;身份:农民工;职业:装修工人;地点:浙江省杭州]
我都是老打工了。我是1990年2月份出来的,到现在都17年了。1990年那时候我的待遇还行。我是在一家香港公司,就是戎氏公司里打了大概8个月工。那时候是一个朋友介绍我去的。他在北京接到一个活,是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打工,就把我叫过去。他那时候是领班的。当时的管理还是很好的,香港的公司嘛,你去打工要两个介绍人,两个人签字以
后,然后登记,然后才能到公司里工作的。[5]238
从上面的反思性语料1 中不难看出,农民工在个体身份觉知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城市里的打工者,这一身份觉知特点伴随其打工经历的始终。即便是同伴位居公司领导层,仍然将其看作是打工者,这体现出农民工身份觉知的深层次属性。换言之,社会既定身份的原型并未因为城市打工经历的变迁而发生任何改变,这一点在反思性话语当中得以充分彰显。农民工自身的这种打工者身份觉知在与其直接相关的薪酬印象和记忆上同样有着直接的体现。
语料2
[受访者:同语料1]
那时候在外面打工是13元一天的工资,15元一天的伙食补贴,6元一天的住宿补贴,一共34元一天。我们的加班费是怎么算的呢?是两个半小时算三个小时,中途不吃饭的。3元一个小时相当于9元。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加班的,那也就是43元一天。公司一个月发两次工资,一般是3~5 号,然后是16~17 号发一次。那个公司还蛮不错的,感觉还可以。在家里的话,一般只有10元一天。外边工资是不高,13元一天,但是加上伙食补贴和加班费,就有1 000 多元一个月了,那时候还不错的。[5]238
由此可见,对于薪酬印象的深刻可以看作是农民工群体打工者身份觉知的重要标记。他们对于自身的薪酬的深刻印象,如数家珍。数字在反思性话语中的频繁出现,揭示了其作为打工者同老板之间的雇佣关系,这可以看作是其自身身份觉知的宏观参照,并且在语言上集中表现为数字的高频使用以及叙事话语的详细铺陈。依据一些学者最早对自我觉知在自我标准差异之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自我觉知会使个体行为趋向于“正确标准”,所谓“正确标准”即为恰当行为、态度和特质的心理表征[10],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于自我身份的觉知导向体现了社会原型化标准根深蒂固的特点。
(二)身份觉知二:流浪者
自我觉知在心理过程中的适应性体现在促进自我了解、理解他人、提高自尊等维度[9]。无论是私我觉知角度,还是从公我觉知角度,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工还倾向于将自我身份觉知为“流浪者”。就私我觉知而言,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身份的流浪者属性觉知主要体现在反思性语言中的“弱势隐喻性框架”的博喻性建构。例如在下面的语料3 中,农民工将城市管理者同自己的关系看作是“猫和老鼠”的天敌性对立关系,农民工所处的弱势群体处境不言自明。就自身属性的个体深度认知而言,“猫”让“老鼠”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根隐喻色彩的表征命题:在农民工自己看来,“作为农民工”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种生存状态(只能拼命地跑)、是一种情感体验(从心底产生了一种恐惧)、是一种连锁反应(万一被抓到,那就是好几十天的白忙活,甚至是好几个月)。除了“猫和老鼠”弱势隐喻性框架的博喻性建构之外,农民工群体还倾向于给自己贴上“游击队员”的标签,甚至上升“敌我矛盾”之上,以反映自己在城市当中“居无定所”的流浪特点,具体如下面语料3 和4 所示。由此可见,农民工群体自我觉知的流浪者身份流淌于反思性话语的字里行间。
语料3
[受访者:张老伯;籍贯:河南;身份:农民工;职业:气球小商贩;地点:浙江省湖州]
城管就像是“猫”一样,而我们则像是“老鼠”一样,老鼠见了猫只能够拼命地跑。如果被这些城管抓住的话,不仅手头还没卖完的气球要被收缴,可能还要被罚款……因此渐渐地我们对城管已经从心底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万一被抓到,那就是好几十天的白忙活,甚至是好几个月。[5]227
语料4
[受访者:马龙;籍贯:安徽;身份:农民工;职业:杂货小商贩;地点:浙江省杭州]
到哪儿都有城管,城里嘛多一点,像武林门啊什么的,到处都有人管。这里就好很多,少些,不过还是会有,而且基本上每天都会碰上。至于每天能碰上多少回,这个倒不一定,多的时候一个上午就五六次,他来赶你就得跑,没跑远他就又来了。我也被城管抓过,那次罚了50元钱才回来。……有时候城管要没收东西的,不过通常就是罚款。他来赶你,你乖乖地跑掉就是了,城管也懒得追。……这游击战一打就是十多年,反正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今天还好,到现在还没有碰上。[5]281
(三)身份觉知三:农村人
就身份觉知机制而言,一般当个体的注意力集中于其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消极自我经验时,往往会产生有益的、适应性的结果,因为延长对消极情绪的注意一般被认为是成功调整情绪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11]。但是,农民工群体对于自身身份觉知的“农村人”污名化处理则不符合这一社会心理学论断。依据下面的语料5,我们发现:即便是在公司当中身居中层岗位,农民工内心深处依然将自己觉知为农民。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对于自身身份觉知的污名化处理并未衍生成后来的积极的身份适应效应,因为“老板说怎么做,我就必须怎么做,即使明知道是错的也得做。”这显然是一种消极的有悖社会道义与道德的适应性结果。换言之,当农民工将自我身份觉知焦点指向自己内部的“农村人”范畴属性时,不但增加了个体一般的自我图示或自我概念,并进而促进了个体信息的收集和强化[12],从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因此落叶归根的思想在上了年纪的农民工群体内深入人心,具体见语料6。
语料5
[受访者:李叔叔;籍贯:浙江萧山;身份:打工者;职业:建筑小包工;地点:浙江省杭州]
我过去是在一个建筑类的公司当项目经理。……老板说怎么做,我就必须怎么做,即使明知道是错的也得做。……刚开始还好,后来慢慢发现上面太黑了,我就开始倾向于农民工这边了,毕竟我也是农民出身啊。[5]58
语料6
[受访者:陈和德;籍贯:江西;身份:农民工;职业:小包工头;地点:浙江省宁波]
问:叔叔,您以后是有什么打算呢?
答:准备回家去种田了。人老了,做不动了,不如早点回家去种田。大概过几年就回去了。
外地人,就是不一样。[5]340
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判断
身份判断可以指个人在特定语境下的自我认同,强调统一性、确定性和稳定性。特别是现代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判断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判断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自我认同过程[13]。农民工因为自身工作的流动性和边缘性决定了其自我身份判断的独特性。在访谈性语料当中,针对“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判断,受访农民工不但自我身份判断意识清晰,而且可以列出具体的判断依据。下面将依据访谈材料对“农民工”这一身份本身的动态性进行具体分析。
(一)“我是城市人”的身份判断
时至今日,农民工“进城”已不再是问题,其关键在于自己如何认识城乡巨大差异带给他们的“身份重组”及“认同焦虑”。城市文明作为一种诱惑,一种目标,时时吸引着大批的乡村追随者;而乡村追随者为使自己能融入城市,必须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历程[14]。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文化空间的转换及文化差异性的凸显,自然导致了农民工对“我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别人认为我是谁”“我与他人有什么不同”等问题的追问都集中地体现在其自我身份判断之上。不同被访者关于自己是“城市人”的身份解释依据有所不同,影响其内在解释的外在条件也各有侧重。例如下面语料7 和8 中的受访农民工均倾向于将自己的身份判断为城市人。语料7 中反映出进城时间长短对于农民工身份判断的影响性。
语料7
[受访者:张连平;籍贯:甘肃;身份:农民工;职业:建筑工人;地点:浙江省苍南]
问:你来这里打工多久了?
答:三个月又十二天了!
问: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答:那是肯定的,像我们这么打工的也很不容易,能过一天就是一天吧。[5]16
语料8
[受访者:赵仙秀夫妇;籍贯:湖南;身份:农民工;职业:灯具厂工人;地点:浙江省绍兴]
问:对了,今年过年怎么个安排,回老家吗?
答:(赵仙秀的丈夫抢着回答)不会回老家了。到湖南的车费太贵了,火车到了湖南还要转好几趟车才能到家,来来回回费用将近2 000元,这么一来,我们半年的积蓄就没有了,还是给老人寄点钱,自己在这里过年来得实惠。再说,如果回家过年,回来之后工作是否还有也不一定,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可能会“一无所有”。[5]47
城乡文化的冲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错位感、异化感、无家可归感显得空前强烈[15],这在农民工自我身份判断的话语当中表现为被动性与外化性。从上面两段访谈语料的内容可以发现,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城市人”这一身份类别的判断解释均来源于外在标准,并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特征——外出时间长而成为习惯、通过对自己新生活环境的肯定等等。相应地,农民工对于自己“城市人”身份可变性解读的“外部环境”归因使得自身身份判断得到合理化操作。农民工自我身份判断的质性材料却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这一群体的城市适应性并非想象的那么乐观,从“被动”融入城市到“主动”加入城市、“外化”归因到“内化”归因尚需一定的时间,这可以看作是后续农民工心理疏导工作的重点。
(二)“我是农村人”的身份判断
如果说农民工在自我身份判断过程中,将自己看作是“城市人”更多依靠的是外在生活环境的话,那么被访者将自己看作是“农村人”的划分标准则主要侧重内在心理原因。其解释主要围绕个人情感、家庭牵挂(如语料9 所示)以及乡土情结(如语料10 所示)等维度。这似乎正好证明了周明宝的观点:“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16]
语料9
[受访者:刘孝文;籍贯:江西;身份:农民工;职业:玻璃切割工;地点:浙江省宁波]
问:您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或者说是憧憬吧。
答:打工毕竟不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打算再过几年就回江西老家去。这里很多保障的事还是不好,我们医疗没有,保险也没有。我那个小孩(儿子)这几天咳嗽了,我算算过年回家到现在花在看病上的钱已经一千多块了,没赚进什么钱,昨天才看病回来。……我不想他们再走我这样背井离乡、出来讨生活的日子,毕竟这样的经历是不好的,我希望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孩子对老家的印象也没多少了。像我小时候在家那边捉鱼、游泳、爬树,现在的小孩这些都没了。现在女儿回老家,还是盯着台电视看。她回老家看到那边的小孩,很自豪的,觉得自己是城里回来的,每次回去都要穿最好看的衣服,跟他们说这里有多好什么的。其实我有时听着还真不是滋味。对她来说,老家跟这里没什么区别吧,可能以后回不回老家对她都没什么关系,或许觉得还是这里的生活好。可是,我还是喜欢老家。再说那边房子装修过了,挺好的。[5]154
语料10
[受访者:王芳萍;籍贯:安徽;身份:农民工;职业:化纤厂工人;地点:浙江省宁波]
问:你们会回去吗,还是打算在这里定居下来?
答:说真的,谁不想自己家乡也发展起来啊……不过,总有人,尤其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会回去的,而且我们出来的人多了,大家知道我们那个地方了,说不定有大老板会去办厂的,那时候我也会回去的,也出一份力。现在就当是在外面积累经验好了,有本事了我们都会回去的。还有,我们那里也有出来了赚了蛮多钱的人,不要以为他们会在城里定居,他们都在村里盖房子,他们也都是想着回老家的人,真的,他们都把房子盖在老家。我们那里现在已经在好起来,以后还会更好的[5]165-166。
从以上的质性访谈语料中可以得知:农民工自我身份判断往往以“城市人”为参照群体,在比较中(如语料9 中“孩子对老家的印象也没多少了。像我小时候在家那边捉鱼、游泳、爬树,现在的小孩这些都没了。现在女儿回老家,还是盯着台电视看。她回老家看到那边的小孩,很自豪的,觉得是自己是城里回来的,每次回去都要穿最好看的衣服,跟他们说这里有多好什么的。”)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身份判断,即对自我“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确认。并且,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判断过程中表现出自己作为行动者对于社会环境的积极建构,而非被动的消极接受(如语料10中“还有,我们那里也有出来了赚了蛮多钱的人,不要以为他们会在城里定居,他们都在村里盖房子,他们也都是想着回老家的人,真的,他们都把房子盖在老家。我们那里现在已经在好起来,以后还会更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在身份判断维度上不仅表现出乡土性的“私我身份意识”,还在城市化环境的催化下,形成了一些习得性的“公我身份意识”[17]。
三、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身份批评
在与“城市人”的他群体对比中,“农民工”这一称呼已经从单纯的职业名称演变成带有身份标识的概念,并被赋有“穷”“脏”“乱”“笨”等污名特征,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身份污名[18]。在被访的农民工中,对用“农民工”这一被污名化的身份标签指代自己,他们的异议并非体现在对于具体名称的标签之上,更多的是关注背后的“城市性待遇”(如下面的语料11 所示)。
语料11
A[受访者:吴胜发;籍贯:江西;身份:农民工;职业:粮库搬运工;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
问:你在这里有归属感吗?
答: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问:为什么不买房啊?
答:在哪里买啊?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的很勉强。[6]19
此外,基于质性的访谈语料我们还发现,农民工对于自身身份的建构维度并未跳出“农村人—城市人”的二元对立范畴,其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与建构均局限于这一“二元对立命题”的显性或隐性语义网络当中:“农村人(弱势群体、素质低、生活质量差、粗俗、流浪、恐惧)—城市人(优势群体、素质高、生活质量高、体面、稳定、安全)”,具体如下面的语料12 所示。
语料12
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我们的调查中,被访者普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我们失业也不算下岗,我们失业是没有人管的。调查员追问:城里人也会失业啊……他们回答:城里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们在外面的吃住都要花钱,压力大,十天半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6]23-24
对于有着长期“迁徙”经历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固有的文化身份已经无法得到传统文化语境的支持。或者说,他们也刻意与自己的“农民”身份保持一种距离,而在城市化这一新的文化语境下,他们的文化身份又难以真正建立。因此,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不得不在“城不城,乡不乡”这样的边界身份中挣扎前行。在没有获取城市身份之前,中国的农民在认识和想象城市身份的问题上总是带有梦幻般的色彩。因此,当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势必对自我身份进行调试和重建。但与城市文化整体上的隔绝、游离等状态迫使他们难以真正地与城市文化产生互动。因此,生活环境的动态性决定了农民工的身份维度绝对不应该局限于简单的“乡下人—城市人”的二元对立当中。从中国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正在逐步打破。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维度对于现实的映射必然反映出这种二元对立的解构,并且在“农民工”这支促动城乡一体化的生力军身份动态演化中得以体现。届时,农民工身份维度将在真正意义上从“二元”走向“多元”。
以上我们基于质性访谈语料,借助过程分析视角探讨了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建构机制,具体表现为身份觉知、身份判断以及身份批评。就身份觉知而言,农民工群体将自己的身份分为三类:打工者、流浪者和农村人,带有典型的负向语义属性以及消极的社会心理特征,这在其质性话语维度的博喻式建构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就身份判断而言,农民工群体往往依据外在环境来界定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借助内在心理来框定自己的“农村人”身份——公我身份与私我身份判断的并置揭示了农民工身份判断上的两极性归因倾向。就身份批评而言,农民工群体身份建构始终局限于“城市人—乡下人”的简单二元对立当中,相对于城乡一体化进程而言,表现出滞后性的社会心理特点,其身份建构由“二元”介入“多元”似乎还需要时间的推动与检验。由此可见,身份问题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关照而言,是一个长久的命题和难题。农民工受访时间、地点等,以及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家乡、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等影响身份觉知、判断、批评的因素缺失,对结论的客观性、普遍性必将产生影响,涉及研究结论的信度、效度和推广度等,这些都应该成为后续研究的关注重点。总而言之,后续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动态的历时话语语料针对其身份建构的可变性、商讨性与适应性展开研究,进而更为丰实地揭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身份建构的“复杂景观”。
[1]毛延生,辛丹.农民工群体语言适应研究:现状与展望[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1-4.
[2]王孟孟.“农民工”的身份界定与法律保护[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1):16-18.
[3]钱冠连.外语研究新阶段的标志(续)[J].中国外语,2005(3):10-13.
[4]赵翠兰.语言公正视野下城市学校农民工子女精神家园建构之探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 (2):65-69.
[5]徐旭初.生存故事:50 位农民工访谈实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6]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7]刘爽,牛增辉,孙正.家庭农场经营体制下的“适度规模”经营问题[J].农业经济,2014(1):10-11.
[8]黄延廷.现阶段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最优模式:家庭农场经营——兼谈发展家庭农场经营的对策[J].理论学刊,2013(10):33-36.
[9]程蕾,黄希庭.自我觉知与情绪、心理健康的关系[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1):14-18.
[10]DUVAL S,WICKLUND R A.A Theory of Objective Self-awarenes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2:10.
[11]MICHEL FERRARI,ROBERT J.Sternberg,Self-Awareness Its Nature and Development[M].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London,1998:2-3.
[12]程蕾,郑涌,等.自我倾注与情绪障碍关系述评[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1):12-16.
[13]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89-94.
[14]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 (3):34-47.
[15]雷达.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雷达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N].解放日报,2007-01-21.
[16]周明宝.城市滞留型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J].社会,2004 (5):4-12.
[17]NILLY M,JENNIFER W.Self-focused attenttion and negative affect:A meta-analy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2,128:638-662.
[18]吴莹.群体污名意识的建构过程[J].青年研究,2011(4):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