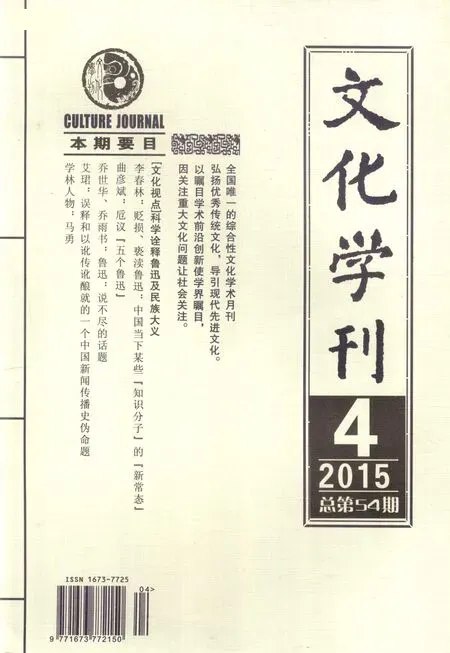中国传统的“四时”观
2015-03-20董恩苗
吴 芳 董恩苗 王 攀
(三峡大学,湖北 宜昌 443002)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的“四时”观
吴 芳 董恩苗 王 攀
(三峡大学,湖北 宜昌 443002)
中国“四时”概念萌芽极早,并很快形成了庞大的“同实异名”体系,这些别名各司其职,完美呈现了民族丰富而鲜活的生命体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上古先民的四方与四时概念紧密结合,整齐匹配,在传统历法中完美呈现中国人的时空框架。人们依据历法,筹划生活,趋利避害,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四时事务。
四时;时空框架;生活方式
社会存在于三维立体时空当中,一切行为都有时间和空间的刻痕,在表达中,产生了揭露这种痕迹的需要。尤其是远古时代,生存环境恶劣,时间的概念显得尤其重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来播种,秋来收耕;夏日田猎,冬季藏弓。每一个生存活动都凝结着无数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时间经验,这些经验口耳相传、代代积累,离不开这一语词符号的中介表达作用。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时间语词,人们如何正常交际、趋吉避凶、传承经验、回顾历史、把握当下、筹划未来。唯有时间词满足社会生活中时间表达的需要,才能促成上述社会生活中的必然事件发生。
时间词产生之前,人类只有懵懂的时间直觉,对自然界的万千征候,依赖于机体内部的各种知觉,这种应对具有偶然性、应激性和不稳定性,缺乏传承性、应对性和准确性。当人们将最影响生存的时间因素从万千时间范畴中分离开来,并给予一个名称来指称后,这个名称所指称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就成为人们规划筹谋自身存在的必不可少的符号化工具。譬如,在没有“春”“夏”“秋”“冬”四时概念之前,先民凭靠经验进行原始渔猎采集,并不能准确地把握何时兽肥鱼厚、何时硕果累累、何时万物蛰伏、何时冰雪封山,只能一代代地依靠朦胧的生理感知能力去生存、挣扎。可是当时间词“春”“夏”“秋”“冬”填补了这一时间概念的空白,进入先民的语言系统后,这种情况就得以改善,满足了先民时间表达的需要,将那些朦胧的时间意识以语词符号的形式在人的思维当中固定下来,人们从此可以运用这些符号来指称时间当中可能会经历的特定阶段。将世代积累的生存经验与特定的时间阶段挂钩,以趋吉避凶、传承经验、回顾历史、把握当下、筹划未来。
一、四时的异名
殷商时期汉语当中就有了“春”“秋”,先秦时期,四时之称已备,不过先民的命名活动并未就此止歇。随着生产技术和农耕文化的不断前行,对四时的粗略划分无法满足上古先民的表达需求。人们发现,生活中的事物很多都有时间效应,只有在“保质期”内完成方能达成所愿。于是,先民对四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划分:根据劳作与否,时间可分为农时、农歇;四时之间可进行任意组配;四时之后添加“日、时、季”等标明属性的后缀;且四时内部还可进一步细分,以孟、仲、季来作区分,各代一月;四时也分早晚,于是开、上、发、毕、暮、杪均可修饰四时;按照四时的特殊物候,四时有很多个性鲜明的异名,如玄英、阳春、白藏、朱明等等。在敝作《先秦汉语时间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1]中曾收录六组最能彰显中国传统农耕时间观念的词汇:
农时、农隙、休时、四时之隙;
春秋、冬夏、秋冬、寒暑;
春日、春时、夏日、夏时、秋日、秋时、冬日、冬时;
孟春、仲春、季春、中春、孟夏、仲夏、季夏、中夏、孟秋、仲秋、季秋、中秋、孟冬、仲冬、季冬、中冬;
孟陬、开春、发春、发岁、上春、青春、春气、阳春、毕春、莫春、朱明、秋气、既烝、白藏、麦秋、廪秋、杪秋、玄英;
富岁、乐岁、宁岁、多岁、岁定、丰年、登年、大年、小年、饥岁、岁凶、凶年。
同一所指对象拥有为数众多的能指符号(亦即别名),从命名活动本身就说明了农耕社会的认知之本。所谓的同实异名、同实异类,虽是词汇语言现象,但实质上都是人们认知范畴化的产物。先民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不断对生存时间进行范畴化,以协调生产生活、适应自然社会,最终使民族重农尚农这一传统实现语言层面的外化。
人们为何要不厌其烦地再造新词指称同一对象呢?在这些新造之词的词义结构中,蕴含着人们对一年当中的四个时节的体味、诠释和顺应;揭示了先民对存在方式的独特领悟与表达。例如:
春为青阳,取春阳送暖,万物回青之意象。《易纬通卦验》也说:“震,东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气”,春因此而得名。夏为朱明,取烈日炎炎,赤红如火之意象,“朱明”本身还指“夏阳”。《广雅》在列举太阳的别名时说:“日名耀灵,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乌”,分别指称春阳、夏阳、秋阳、冬阳。夏以“阳”为名,恰恰因为这是炎热时节最引起人们关注的形象。秋为白藏,秋于五色为白,序属归藏,故称。唐魏征《五郊乐章·白帝商音》云:“白藏应节,天高气清,岁功既阜,庶类收成。”形象地描绘了令人欢欣鼓舞的秋高气爽、丰收待藏的景象。冬为玄英,《尔雅·释天》曰“冬为玄英。”邢昺疏:“言冬之气和则黑而清英也。”玄即是黑,有人认为冬日夜长昼短、百草凋尽,因而得名玄英。
二、四时与四方的组合认知
中华先民具有独特的时空认知框架——四方时认知图式,亦即四时概念与四方概念的整齐搭配。汉代扬雄《太玄·文》中云:“罔、直、蒙、酋、冥。”范望注云:“此五者为《太玄》之德,犹《易》‘元,亨,利,贞’也。”《太玄》进一步说明:“直,东方,春;蒙,南方,夏;酉,西方,秋;罔、冥,北方,冬。”“直”之为言殖也,为繁殖,故以为春;“蒙”为蒙覆,草木修长,故以为夏;“酋”为蓄聚,万物成就,故以为秋;“罔”“冥”为闭藏、无形,故以为冬。行唐尚秉和先生云:“盖天之体,以健为用;而天之德,莫大于四时。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即东南西北。震元、离亨、兑利、坎贞,往来循环,不忒不穷,《周易》之名,即以此也。”[2]
四方时概念古来已有。据学者们考证,《山海经·海外经》中的四方神实为四时神,而所谓的东、西、南、北四方概念在古图中实则代表春、夏、秋、冬四时时间概念。《管子·四时》有云:“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南方曰日,其时曰夏”,“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北方曰月,其时曰冬”。《礼记·月令》分一年为五时(夏秋之间插入季夏),与五方、五帝、五神、五声、五色、五味等相配。同时,《管子·五行》和《礼记·月令》都记载了四时神位于四方,司职四时,只是神的名字各有不同。据当代学者考证,天干地支也糅合进四时四方体系。
四时:
甲乙木配春季,丙丁火配夏季,庚辛金配秋季,壬癸水配冬季,戊己土配四季(这里四季指四时末的一个月,即三、六、九、十二月)。
寅卯辰配春季,巳午未配夏季,申酉戌配秋季,亥子丑配冬季
五方
甲乙木配东方,丙丁火配南方,戊己土配中央,庚辛金配西方,壬癸水配北方;
亥卯辰配东方,巳午未配南方,辰未戌丑配中央,申酉戌配西方,亥子丑配北方。[3]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将四时四方、阴阳五行、干支八卦整齐相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相互牵制、相互生发的时空秩序,先民的一切生存活动都发生在这种时空秩序之下。《管子·版法解》中记载,“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行有常,序列而行”,故“圣人法之,以建经纪”。《礼记·礼运》亦载,“故圣人作责,必以……四时为柄”,“夫礼……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这些无疑昭示人类族群的进化与世间物候的变迁,极早就被先民纳入原初时空认知框架中,繁驳地交织为一体,却在语词符号中留下文化的遗迹——四时概念与四方概念的整齐搭配。
三、先民对四时的期许和筹划
人们使用四时时,总赋予其丰富的含义和期望,如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忠、乐、礼、信;罔、蒙、酋、冥;生、长、收、藏,每一季都蕴含了先民细腻的体验认知。
烛于玉烛,饮于醴泉,畅于永风。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时和,正光照,此之谓玉烛。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其风,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方盛,冬为安静,四气和,为通正,此之谓永风。(《尸子》)
春为忠。……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夏为乐。……夏,兴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秋为礼。……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冬为信。……冬,终也;北,伏方也。是故万物皆伏,贵贱若一,美恶不减,信之至也。(《尸子》)
春言生,夏言长,秋言收,冬言藏。(《吕氏春秋·十二纪》)
《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左传·隐公五年》:“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杜预注:“各随时事之间。”《国语·周语上》:“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韦昭注云:“农隙,仲春既耕之后,隙,闲也。”人们以农业生产为参照,筹划生活。“农时”劳作关系全年收成,国家之本,因此上至统治者,下至底层劳动者达成共识——勿夺农时。在“农时”,一切非农行为悉数从简,包括国家的重大祭祀,农时发动战争被视为不仁。据《逸周书》所载,练兵、猎兽等事宜,概须待得仲春既耕之后,亦即“农隙”时分。这种对时间的分类,亦即对生活的筹划,表现在语词当中,就是在既有的“四时”概念之外,以人们社会生活中新的关注焦点为理据,创造出的赋有特殊意义指向的新词。
上古先民习惯根据四时来筹划自己的生活。并为重大事件“正名”。以祭祀为例:《尚书·尧典》有云:“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商人尊崇祭祀,纪年为“祀”,不同时令举行不同的祭祀活动,“春祀户,夏祀灶,秋祀门,冬祀行,中央土,祀中溜”(《月令》),故有祠春、礿夏、尝秋、烝冬之说,各种祭祀周而复始,一年一个周期。与此类似的是,古时诸侯觐见君主,亦因四时不同而得名有异:朝、觐、宗、遇。
上古人们为四时走猎分别命名为搜、苗、狝、狩。《周礼·夏官司马》有云:“中春搜田、中夏苗田、中秋狝田、中冬狩田”,依周制,天子、诸侯在国无大事时,可行搜、苗、狝、狩之礼。唐杜预在《通典·卷 76》中对此作出详细解释,“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搜狩而习之”,“春习振旅,兵入收众,专于农”。春季农忙之时,练兵不可止歇,于春田中以搜捕猎物的形式训练兵士,“中春搜田”因此而得名;“夏田为苗,择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实者云”,盛夏时节,草木长赢,兽禽肥壮,繁衍生息,狩猎时宜择取未孕者捕之,如掐除无穗之苗,“中夏苗田”因之而得名;“秋田为狝”,“狝,杀也”,“主用网”,“皆杀而网止”,走兽良禽经过一个夏天的囤积,无不膘肥体壮,准备过冬,秋天出猎,此时最宜张网设陷,大杀四方,“中秋狝田”因此而得名;“冬田为狩”,“言守取之无所择也”,深冬岁末,天寒地冻,鸟兽绝踪,猎兽无其他选择,只能靠“狩”,“中冬狩猎”因而得名。
四时流转,征候各异,人类对四时的筹划也随之不一。流传至今的月令文献如《逸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等等,[4]均有“因时行政”的论断,认为政事、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管子·四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认为人类有意牺牲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简便性原则,以追求对已知事物的多元化理解,毋宁说是人们基于生存和表达的需要,将“顺应时节”这一生存经验的精髓直观地外化于命名活动中。先民的“四时观”远不止对时间进行简单描绘和指示,而是更深刻地昭示了民族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独特领悟与体验,为华夏先民的民族性划下了一个符号的圆周。
[1]吴芳.先秦汉语时间词汇形成发展的认知·文化机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87.
[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
[3]周蓉.干支符号所代表的时空观[J].兰州大学学报,1999,(2).
[4]刘宗迪.失落的天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584.
【责任编辑:王 崇】
B83-0
A
1673-7725(2015)04-0166-04
2015-03-10
本文系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项目“汉语时间词的认知·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2246);2015年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认知的汉语词义引申完形解释——以‘看’和‘就’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吴芳(1981-),女,湖北黄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