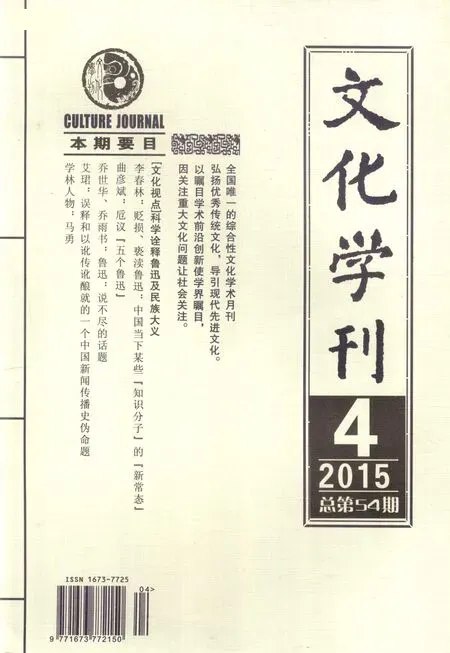流亡体验中的文学发生——20世纪30年代女性作家萧红的小说写作
2015-03-20任晓兵
任晓兵
(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范畴中,有一个语词概念“认同”,指的是“在主体间的一种关系中确立自我的某种意识,并在对普遍有效的价值承诺之中和特殊认同意识的张力之中获得自我的归属感和方向感的过程”。对于处在流亡生存体验中的流亡者而言,其写作活动的终极目的即是寻求对自我的“认同”,以便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一种“在家”的感觉。这样的“认同”有三个层面。其一,一种主体性的反思意识,是一种自我否定,最终抛弃他者、重归自我的过程。其二,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诉求具有生存论上的意义。其三,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它不但会受到性别、阶级、民族、种族等话语的影响,同时也会被文化、历史、社会的想象所塑造。
一、流亡者萧红
萧红,一位文学创作活动集中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从1930年秋天,萧红因为逃婚而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她开启了自己短暂的生命旅程中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涯。
萧红的父亲是传统儒家守旧知识分子,思想上有双重征候。遵照年幼时期萧红的记忆,她父亲永远是一个“恶魔”。九岁时生母不幸去世,之后父亲很快又娶了一个老婆,这样的行径,使得本就脆弱的父女关系进一步恶化。“要么是恶人,要么缺失”,父亲的形象就这样在萧红的脑海中被定型。在这个幼年的时期,萧红唯一的快乐来自于她的祖父。老人给予了萧红幼年时期最温情的关怀,对萧红的一生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祖父一天到晚在他的后花园中,萧红也从早到晚在后花园中。1929年,萧红的祖父去世,彻底斩断了萧红与家庭的纽带,毅然决然踏上流亡之旅。
童年、少年时期的不幸经历和老祖父的离世均在萧红的心里播下痛苦的种子,因此,当孑身独处社会上的时候,萧红不得不让自己成为彻底的流亡者:肉体上的流亡——背井离乡;精神上的流亡——无所依托。因为流亡者在流亡生活中都会产生挥之不去的认同意识;必然会通过小说创作这种抽象的方式来使得正处于“流亡”生活情境里的自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得到一种“在家”里的心理状态,获得自我在精神上的归依感和历史感。在这种归依感和历史感的获得中,又获得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反省。
二、萧红的文学活动:始于流亡、终于流亡
萧红的文学活动起始于一九三三年,小说《王阿嫂的死·九一八致弟弟》这篇带有绝笔性质的散文作品,是萧红流亡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段时间之内,萧红的全部小说文本都是在她在个人流亡颠沛的情境中完成的。《生死场》是萧红的经典之作,也是她的成名作。这篇小说是萧红流亡青岛期间完成的。《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这两篇作品是萧红战乱时流亡香港时期完成的。正如作者本人流亡困苦颠沛的人生一样,其小说文本中,被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身世命运同样凄惨。基于以上原因,在萧红创作的小说散文文本里,“流亡”成为了这位命运凄惨的女性作家最基本的潜在叙事动机。
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萧红与她生命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引路人相见,这位引路人就是鲁迅。鲁迅以一位长者的身份,给以流亡生涯中的萧红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这份关怀和温暖,使得饱受人间凄苦的萧红倍觉温馨,就如幼年时期祖父给予她的爱和温暖一样,可是幸福并没有太多地垂青萧红,不久,萧红即与自己的丈夫,同属于文学家的萧军,在感情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不得不再一次陷入了新一轮的情感纠葛痛苦之中。
接连不断地流亡生活经历,无形中促使这位悲苦的女作家将自己在流亡道路上对人生、对生命、对爱的全新解读诉诸文字,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她经典的小说文本《呼兰河传》。这部小说里,在自己家荒凉的院子之中,萧红描述了一些流浪人物的形象与他们漂泊的生命形态。在第六章里,萧红又记叙了本族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奴流浪汉“有二伯”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这些书写,都毫无例外地描述着流亡的生活情境。由此可见,萧红的叙述处处透露着“流亡”,毕竟流亡生活、流亡者的身份让萧红感受到了太多宿命般的生命裂变。然而,萧红注定“流亡”,她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一旦她听到别人说起“家乡”就立即会让她心慌的呼兰县城了,1941年的冬天已不再属于她,尽管那座小城里埋葬着她的祖父,那个给予她温暖和爱的老人。
三、结语
萧红创作小说的时候,话语都是极具个体性的私密话语,她不断地书写关于自己、家族、乡土的故事。然而无论描写哪一种类型的故事,都呈现着萧红感怀自身命运最基本的心理情结。
然而,萧红流亡者身份符号中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日寇侵占东三省。在异族打压和驱逐下,从东北故土逃入关内的难民这类描写说明,萧红的流亡亦有着被动的因素。萧红的小说话语是流亡话语,而任何流亡话语都隐含人的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的话语形式,因此,个体的发声就可以被看作一类人的发声,从而使个体性的话语演变为公共性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萧红在流亡体验中的文学发生与文本表现,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