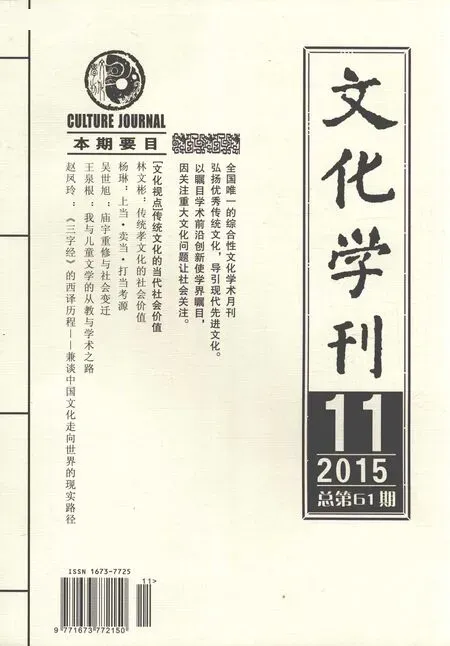异域文化对中国传统设计艺术的影响
2015-03-20殷玲玲
殷玲玲
(泰州学院,江苏 泰州 225300)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吸收、改造的过程。每个民族、地域的发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的民族或文化被其他文化所同化或取代,而有的则通过兼收并蓄、吸收借鉴并成功改造,使异域文化成为启发和丰富本土文化的有利因素。纵观中国传统设计艺术的发展,异域文化的输入为其注入了生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设计艺术的内容和形式。
一、早期影响(春秋战国、两汉时期)
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民族,有资料证实,先秦之前中国就与境外存在贸易文化上的交流。现有考古发现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装饰设计就明显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甘肃、河北等地出土的这一时期青铜翼兽形象表现出明显的西亚、埃及风格。有人认为,翼兽题材很可能是中国人自觉吸收外来样式的结果,后来的麒麟、辟邪一类瑞兽装饰主题的发生与此亦有一定的渊源。
两汉时期,由于加强了对西域的经营,因此,国家不仅扩大了疆域,更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进一步交流,西北地区发现的同期织物设计就明显有中国与希腊风格混合的特征。
二、大分裂时期的影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丝绸之路的开辟也拓宽了佛教进入中国的通道。中国的佛教装饰艺术兴起于南北朝时期,繁荣于隋唐,是当时装饰艺术的主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上极为动荡混乱,但文化面貌格却格外生机盎然,南北、中外文化大融合,儒学、玄学、道教、佛教多元发展,尤其是佛教的传播,使这一时期的艺术设计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装饰由印度经西域至河西走廊,再辗转至平城、洛阳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模仿到吸收改造以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如佛像造型,传入伊始,受古印度犍陀罗、笈多艺术的影响,多具有高鼻深目,面相方圆,肩宽体壮等“胡貌”特征,如山西大同云冈北魏早期第20 窟佛像,就颇具异域风情。至5 世纪后半叶,佛的造型已然成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南朝士大夫形象。信众的目光改变着佛的形象,现实社会对佛教装饰的影响显而易见。佛教在华夏大地传播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其中,如印度佛教造像中的突乳、扭腰等特征被消解,儒家思想中的“仁”观念直接影响佛教造像的表情和外观,成为佛陀之爱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观音造像,就由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男性域外形象逐渐转变成宋时温存柔美的典型中国妇人形象,更发展出水月观音、送子观音等世俗化造型。这一扬弃、取舍的过程,正说明佛理教义及作为其物化形态的佛教造型艺术,无不以中华文化为标准进行改造。
此外,还有一些佛教中的象征性符号,如菩提、莲花等,在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引申出象征和审美的双重意义。如莲花,在佛教中象征“弥陀净土”,佛教传入前,虽然鲜见,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中也有萌发,如春秋战国时制作的以莲花作为装饰题材的“莲鹤方壶”,但直到南北朝时期,莲花才随着佛教的兴起,作为一种纹饰发展并衍生出丰富的形式,从北魏石窟中颇具印度风情的莲花装饰,到明清时期莲花与莲蓬、荷叶、鸳鸯、白鹭等的组合,莲花已完全世俗化、中国化了。在华夏大地,莲花的吉祥寓意内涵早已超出佛教名物的范畴。又如狮子,也是从威严的佛教护法者发展成仅次于龙凤的中华传统装饰重要题材。在逐渐摆脱异域风情,从象征性的佛教符号发展成华夏俗世吉祥图案的过程中,它们既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又蕴含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最终都消融于华夏文化的观念意识中。(佛教)
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甚至开始改变传统的生活起居习惯。佛教造像中的倚坐和须弥座,以及外来文化中的高足家具,对中国古代家具设计由低型向高型发展有重要影响。人们由席地而坐逐渐改变为垂足而坐,生活起居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生活器皿的造型风格。如原先的陶瓷壶类器皿一般都没有把手,造型矮胖,这是因为它们当时是放置在地上或较矮的几案床榻之上,使用动作主要是捧,而随着高型家具的普及,捧壶改为执壶,壶身也逐渐变得修长。
三、大发展时期的影响(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繁荣期。国家强盛,经济发达,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个时期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和之后的伊斯兰文化,以波斯为主的异域文化一度成为当时的时尚潮流。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瓷器、金银器和织物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唐朝是瓷器大发展的时代,瓷器的造型和纹饰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如著名的青瓷凤头龙柄壶,壶身装饰有联珠、莲花、忍冬、宝相花、舞乐胡人和力士等纹样,龙身作柄,凤首为盖,风嘴为流,是中国传统装饰风格与波斯风格的融合。其实这种长颈带柄有流的器皿造型是波斯从古希腊陶壶造型中借鉴而来,只不过波斯式装饰替代了原先的神话纹样,经波斯传至中国后,中国传统纹饰凤首,螭龙又代替了鸟头、鸟尾。可见,各民族在设计艺术的相互交流影响过程中,都有一个逐渐适应本土文化审美习惯的改造过程。(隋唐,瓷器)
金银器制作,我国古来有之,但直到南北朝时期,随着西方(主要是罗马和萨珊波斯)金银器皿的大量输入,我国金银器皿的设计和制作才迎来发展的高峰。从造型上看,唐代早期的金银器皿多具有明显的萨珊波斯风格,因为萨珊波斯艺术中带有浓郁的希腊罗马风格,使得西方设计的因素也间接影响到中国的传统设计,如带把杯、高足杯、长杯都是前所未有的器型。纹饰方面,如海兽葡萄纹、联珠纹、忍冬纹等也反映出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输入到师仿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外来文化的逐渐认同。到唐代中晚期,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进行了中国式改造创新。如联珠纹这一典型的波斯样式,在隋唐时被广泛应用于金银器和织物上,并不断进行改造和创新,如在联珠纹内加入吉祥文字“吉””贵”等进行装饰,或是取圆团外形发展出“团窠”纹,或是将圆形外框变化成菱形、椭圆形或波曲弧形,这种变化后的面目,形式丰富,花团锦簇,至宋元后完全中国化,最终消融于华夏民族审美传统中。又如忍冬纹,作为佛教装饰中的重要样式,可溯源至古希腊、古埃及纹饰,到了唐代被逐渐演化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卷草纹,这种纹样与传统龙凤纹样有异曲同工之妙,集多种花草植物的特征于一身,结合中国传统的云气纹,通过对形式的夸张变形,追求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抒情性和意象性,成就了闻名于世的“唐草”纹。
四、成熟期的影响(宋元明时期)
宋元明时期,中国的陶瓷艺术逐渐成熟,逐渐市场化、商业化。这一时期注重开拓海外市场,近代考古发掘表明,日益繁荣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使中国这一时期的陶瓷工艺对伊斯兰世界陶瓷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彼时,为适应外销的需要,伊斯兰的文字图案成为瓷器重要的装饰纹样,伊斯兰国家传统的扁瓶、折方瓶、执壶等器型也被大量仿制,这些异域风情无疑对中国传统样式具有启发。这一时期元代青花瓷在继承唐宋传统艺术设计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蒙古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的精华,大放异彩。受波斯装饰艺术的影响,在装饰构图上,元青花以繁密饱满著称,往往在瓶、罐、壶的器表从上至下绘满纹样,装饰区可达八九层之多,这种装饰风格为后来明清彩绘瓷器上的繁缛纤细装饰之风开了先河。
五、衰退期的影响(清朝)
18 世纪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与风行欧洲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同期。这一时期清王朝对文化实行禁锢,文风泥古,影响到艺术设计上则表现为过于追求手工技艺,设计繁缛精巧,审美格调庸俗。至此,中国古代的设计艺术日渐衰落。清代的这种装饰风格与凸显女性化装饰趣味,追求纤细轻巧、繁缛华丽的洛可可艺术审美趣味相投,二者多有交集。早在巴洛克盛行的17 世纪,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壁纸等工艺美术用品就以精致优雅的装饰风格赢得了欧洲人的青睐,对18 世纪洛可可风格的流行具有明显的启发和推动作用。来自于东方尤其是中国清朝宫廷的装饰风格在洛可可艺术中被广泛应用,追求中国趣味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随着中西方贸易文化往来的加强,清代的艺术设计中也出现了明显受西方装饰风格影响的现象,主要突出表现在瓷器、建筑和家具上。瓷器上的西洋风格装饰主要出现在外销瓷上,欧洲的神话宗教故事、纹章花卉等纹饰常以五彩、粉彩等彩绘手法装饰于器表,西洋画法也常用于宫廷专供的洋彩瓷“瓷胎画珐琅”。
建筑上,清代最富有西洋风格的当属圆明园中的长春园,虽然这座欧式宫殿已毁于1860 年的英法联军大火中,但从残存的瓦砾断垣中华丽的涡卷叶饰及盾牌、盔饰等西方常见装饰仍清晰可辨。另外,从清代家具豪华壮观的造型,纤细繁缛的卷曲纹饰设计中也可看到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影响。
六、结论
历史告诉我们,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集体审美取向,中华民族也有自己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那就是在不断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发展新的样式,拓展新的技艺,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当传统和现实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时,外来文化的影响就突显出来,审美情趣也随之发生改变。在从模仿到中国化改造的过程中,只有找到最适合国人审美观念的外在形式,并与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相匹配,才能获得普遍认同。
当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观念、新思想、新技术的变革。外来文化的涌入,正在于启发我们以宽容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逐渐改变自己的观念和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新、旧、中、外”等概念终将模糊消失,久而久之,附着于外来文化之上的意识形态之争也终将被淡忘,在波澜壮阔的文化交融与变迁中,世界将变得愈发精彩。从这一意义来说,这正是本文所要阐述之宗旨所在。
[1]倪建林. 中西设计艺术比较[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75-197.
[2]郑岩. 中国表情——文物所见古代中国人的风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21-129.
[3]勒内·格鲁塞. 中国的文明[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76-83.
[4]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45-353.
[5]高丰. 中国设计史[M]. 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13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