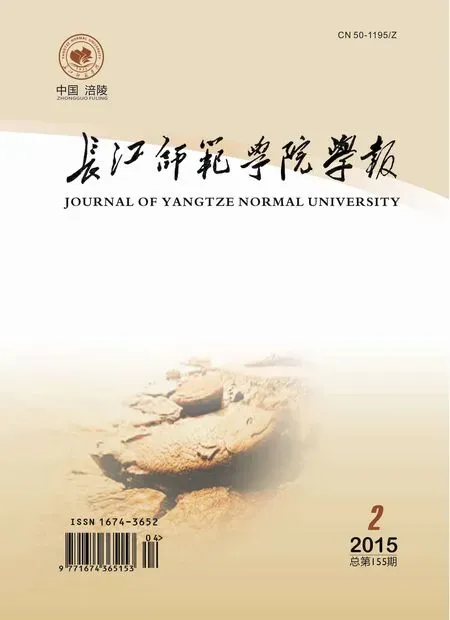关于诗歌“运动”的内在观照
2015-03-20韦文韬
关于诗歌“运动”的内在观照
韦文韬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要]自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盛行以来,诗歌研究已经真正的从外部研究进入到内部研究。诗歌“运动”当属内部研究的范畴。然而这种内部研究仅仅停留在具体的几个抽象概念之间的关系上,无法取得一个统一的整体。事实上,诗歌总是处于不断持续运动的过程中,并且由各个成份之间相互交错而产生诗意。这种诗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指向和转换方式,两者构成了诗歌内在的运动状态。
[关键词]“钟表”结构;回旋;隐含;转换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52(2015)02-0094-04
[收稿日期]2014-12-20
[作者简介]韦文韬,男(壮族),广西罗城人。主要从事文学诗歌研究。
一、引言
艺术首先存在一个结构,它通常贯穿着艺术家们的主体创造意识,尤其在“新批评派”看来,是作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区别于其他种类的艺术。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结构的艺术存在,即便是解构理论的开创者雅克·德里达也认为:“即使在今天,无中心的结构的想法,也是不可思议的……结构的中心通过引导和组织该结构的内在一致性,会允许其构成成分在总体形势的内部自由嬉戏。”[1]然而结构内部是如何嬉戏的?这是诗歌内部研究面临的根本问题。自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研究伊始,诗歌研究就已经真正地从外部研究进入到内部研究。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仍局限于语音、格律和节奏等韵律层面,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诗歌的内部研究才算深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诗歌由此也被更多人视为一种“势能”或“动能”。新批评更着重的是诗歌的整体结构、符号代码的深层意义及其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翁》中就以“结构”区分了各个诗人的不同。他认为结构不仅仅是一个外壳,更是一种意义、评价和阐释,在他的结构观里包含着“运动”所产生的无限意义。瑞查兹着意于诗人在心理上对诗歌中对立统一事物的调和,在他首先强调诗歌中存在着相互干扰、相互冲突又相互独立的各种组织,而后诗人加以平衡,生成整体协和的效果。瑞查兹的弟子燕卜荪继续发展了老师的“对立统一”之说,强调诗意含混、模糊,实际上和泰特的“张力”如出一辙。只不过“张力”更在意的是诗意的产生,而“含混”则限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作为诗歌内部研究的领军人物,兰色姆似乎有些另类,他更重视的是肌质。肌质就是细节,可以充实构架,比结构更为重要,实际上这是推崇“运动”。温特斯最为具体地阐释结构,他甚至将诗歌分为六种结构法,其中反复法、逻辑法和质的推进,都是内在变换的体现。综观他们的诗歌观,显然都将诗歌看作一种戏剧化的运动,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却又自我封闭,孤立独行,缺乏整合,失去了方向性,无法构成一种更为有效的诗意运动状态。尽管如此,从各家诗论中,我们仍不时可窥视到诗歌运动的大概轮廓,触摸出诗意的运行指向及转换原则。实际上,早在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提出了诗意的“对立统一”说,到柯勒律治开始,诗歌便有了具体的运行方向。美国汉学家奚密则以“环形结构”来探讨了现代诗歌内部运动的某一回旋特征,中国老一辈诗人成仿吾、穆木天、郑敏等也很具体地论析了诗歌的整个转换过程。综合这些观点,我们认为可以用诗歌的“钟表结构”来对诗歌的诗意运动问题作一次试探性的观照。
“钟表结构”的概念,不是沿袭他者的概念,而是我们为了下面探讨之需要所预设的一个机械时间。自
然而然,“钟表”是通常意义下的指涉时间的圆形器具,同时圆形器具中含有秒针、分针和时针的相互牵制。用“钟表结构”来解释诗歌结构不是为了设立一个普遍性原则,而是寻找如弗里德里希所说的“不同的共同之处”。自然,“钟表结构”要涵盖以下两个层面的意思:
二、钟表中的“环形结构”
所谓“环形结构”是指诗歌运动的情感指向。诗人在创作时的情感处于不断的回旋往复之中,以开端感受为旨归,从而不断地推移、深化,在诗末悄然完成了诗意的转换和整体性意义的升华。
奚密认为,“所谓环形结构,就是情感的回旋,是开端与结尾的意象和母题的重现。这种意象和母题在他处不曾出现过。”[2]这种结构上的认识对诗歌的创造来说有失偏颇。偏颇之处何在呢?他是把“意象和母题的重现”等同于“情感的回旋”。他首先是从表象的字面意义上去推断诗歌的情感流程。照此假设,如果首尾没有相同的“意象和母题”,诗歌就没有“情感回旋”了?而从诗歌艺术创作的过程来看,始终都存在情感上的回旋。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此诗同样出现了情感的回旋情形,即最后一句又回到了“河流”的中心,以“河流”为主体意象将首尾情感对照升华,很多古诗(尤其好诗)都如此。实际上,即使出现了相同的“意象和母题”,这个尾部的“意象和母题”也不是和首段的“意象和母题”意义简单重复,而是情感回旋加强了,“意义”变化了。柯勒律治认为,“一切记叙文字,甚至所有诗篇,……在诉诸我们的领悟时,应呈现出破方为圆的运动,即环形运动。”所谓“破方为圆”,是指在阅读过程中,从个别具体的事物中体会到永恒的思想。这种永恒的思想一开始将主客观统一起来,最后呈现出回旋的状态。
情感上的回旋结构,首先就关涉到诗意的转换和统一的问题。这种统一是思想的本质意义,它代表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早在20世纪初的穆木天就在他的《谈诗——至沫若的一封信》中说到:“我主张,一首诗是表一个思想。一首诗的内容是表现一个思想的内容。”[3]他进而从内在的联系上说明:“一个有统一性的诗,是一个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内生活的象征。心情流动的内生活是动转的,而他们的流动动转是有秩序的,是有持续的,所以它们的象征也是有持续的。一首诗是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4]穆木天至少告诉我们,诗意是统一完整并且是持续流动的。统一完整必然会涉及到首尾情感的回旋对应等。也就是说,开端往往涉及到在何种程度上何种时空里可能会产生具有代表诗歌意图的诗意,依着这种诗意,诗意的推移才有目标和动力。“新批评”派的领军人物兰色姆认为,“如果第一个短句出语不凡,引人注目,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根据短句文法所提供的线索,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临时建立起来的语境上去……我们发现它和其它更多的短句在语法上相互联系,使语境得到不断的拓展。”[5]如“移舟泊烟渚”,只有在移舟、泊烟渚的时候,才有最大的产生诗意的可能性。尾联“江清月近人”既衔接了“野旷天低树”所升华起来的感觉,又转回到首联的真实的情感之中:孤独寂寞,无依无靠。情感回旋,诗意才能统一完整,才能如司空图所认为的“超以象外,得其圜中”。郑敏认为“有了最后一段的升华,开端那些平淡的都有了感情。”[6]郑敏暗示了开端的诗意设置是在尾联的一定的感受程度上产生的诗意,是与诗歌的结尾情感吻合的诗意。假如结尾没有情感回旋,开端的诗意就变成了脱缰之马。
情感的回旋实在是创作者的需要,如果更深一点说,是“文学逻辑推动力”所致。诗歌的批评很少注意逻辑推动力和内在意义的转换问题。结构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批评所谈的基本上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囿于诗歌中的某一个肌质“张力”,失去了构架。他们避开了诗歌另外一个极为艰难的话题即诗意转换的话题。实际上,情感的回旋恰好是诗歌逻辑推动的一种表现。正如远远而来的海潮,除了浪花,还有那来自海水深处的回环往复的推动力量。叔本华曾在《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中认为,作为表象的世界是在对立中产生的,要感受到自我,就要从与对立物触碰的结果中寻找其原因。诗歌总有一个结果,结果总有原因,原因和结果是重合的,他们构成一个整体。所以说,只有情感的回旋,才形成情感物质性的链条,造成情感逻辑的推动力,意义才可以转换升华!至于以不以“相同意象和母题”回旋却可另当别论。
三、钟表中的“隐含结构”
钟表的“环形结构”是要通过钟表中的“隐含结构”的具体体现来使其最终完成的。而“隐含结构”所包含的是诗歌字面意思隐含的意义及其转换方式。正如秒针、分针、时针一样,秒针的转动并不代表真正的
时间,而是代表一种情感的符号,真正隐含在背后的是分针和时针。如果说秒针是主客体的错落演变,分针则是段落的推进,而时针才是真正的诗意体现者。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位置上来说,秒针是变化不定的变形词,推动着段落的意义的形成,段落的意义的形成又不断地穿透了整个诗意的产生。成仿吾认为诗歌里有一种“暗示的推移”,艾青更为具体地认为“诗都是从抽象到具体,具体到具体之间的一个推移,一个跳跃,一个转化,一个飞翔。”[7]他们的诗观实际上和新批评理论的“张力”“含混”“曲线”殊途同归,指向了隐含结构里的诗意产生和运动状态。
(一)秒针的变幻莫测
在诗歌的结构元素中,如同秒针速转不断的词语,涵盖了地点、人物、事件、景物等等元素。这些元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诗歌的内在情感流动。
1.主体“我”的参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多有“我”的出现。“我”就是“自我表现”。自我表现可以达到感觉,进而达到感受,这是诗意产生的基础。由于主体“我”的参与,往往会造成时空错置。而时空错置又极易造成情感的抑扬顿挫。或者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在抒情诗中,主体“我”带动了情感的跨越,接通了因异时异地情感变化所带来的阻拒感。首先,由于“我”的主动参与,可以直接地进入到诗歌的情感本质当中,导引着诗意的律动及其脉络,并在转换诗意的时候,“我”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实际上,“我”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在浪漫主义诗人群里,“我”就是诗意的导火线,很直接地、通俗地将诗歌传播到社会群众当中。其次,“新批评”的理查兹认为“我”可以起到平衡诗歌中相互矛盾的事物的作用,带有更多的主观心理倾向。例如余光中的《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我”掌控了整个诗意的节奏。“我”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从“从前,一个中国青年……”开始,诗意便转换得令读者回想到整个过去的时间,诗人是如何苦苦地望穿黑夜思念大陆的,也突然理解了我对未来的“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的各种幻想。同时,“我”可以通过调和,最后抵消这种矛盾的心理反差。
2.客体的贯穿。20世纪后,世界呈现出不稳定、对立的特征,意识处于失序状态,诗歌意识也潜移默化。但在形式上基本落于“客体的贯穿”。“客体的贯穿”意味着主体的渐渐消隐。主体的消隐不等于主体的退场。主客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体的,只是当生活变得千头万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主观不得不稍微让与客观,诗人不得不小心深入,重新观察生活的细微变化。越是细微的变化,可能越是穿越了人的内心。于是,碎片、反常、非逻辑、不对等、晦涩等现代诗歌艺术有意导向着读者的阅读。实际上,这是从“自我表现”到“客体的贯穿”,是从“外部世界”进入了“心理世界”。回到个人的内心,这是诗歌更真实的体现。看似颠覆了整体统一,但是并没有真正地丢掉有“意味”的形式。尤为出现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弗里德里希所说的:“现实世界的贬值。……,现实世界破碎成个单像,被描写出来,取代了某个整体的位置。……,通过实物和风景让一个与人近似的灵魂说话的中介抒情诗几乎不再出现。”[8]各种各样的诗歌形态相依并存,而且越来越成熟壮大。而中国古代的大多数诗歌也都是客体的贯穿,诗言情、言志都落于客观景物的描绘之中,这种“客体的贯穿”和现代诗歌稍有不同,即很少内心曲折微妙的变化,很难深入内心的绵缈之处,反而是外在志趣情感的普遍抒情,诗意常常被稀释为一种情趣、释然。
(二)分针的顺序推进
分针可以定义为“段落”和“分层”的意思。有些诗歌有好几个段落,没有段落也会有好几个层次,它们各含的意思相互映衬、对比,从而顺利地推动了诗意的转换。分针和秒针的区别在于秒针是匀速奔跑性的,而分针是定点跳跃性的。分针和秒针又具有非同一般的联系。秒针的匀速奔跑带动了分针的定点跳跃,它们的共同的方向是往前。诗歌亦然,许多词语的并列组合完成了段落的意思,并同时推动着段落的转换。巴甫洛夫说:“词,由于成年人过去的全部生活是与那些达到大脑半球的一切外来刺激或内起的刺激物相联系着……因而词也随时能引起那些刺激所制约的有机体的行为和反应。”[9]语词这种引起了人们内心情绪变化和行为反应的能力,直觉地带动了声音、色彩及其嗅觉的各种组合,使人感受到了诗意段落的进程。正如艾青的诗:《树》: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离地兀立着/风与空气/告诉着它们的距离/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生长着/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整首诗只有两段,但是却用了对比的转换手法。第一段用了四行表达了树孤立地兀立着。从“一棵树,一棵树”和“风与空气告诉……”可以看出,它们有着真正的距离。第二段用“但是”转换到了泥土下,实际上是深化了“树”的思想,使“树”具有了生命的力感。这种推进的叙述正如郑敏的“展开式的结构”里所说的“诗歌结构有些像我国传统的庭院房屋,通过一进到二进、三进、四进……一直到后花园;又像我国的庙宇、寺院,从第一个大殿到第二个大殿、第三个大殿……当你读这种展开式的诗时,你的惊讶可以说是一步步加深加大,也可能是对前面几个大殿的陈列感到平淡、一般。但突然,在你跨进最后一个大殿时,你猛然发现眼前是一尊极美的如来坐像,……好像将你引入了一个深博的智慧的世界。”[10]在“新批评”的文本研究中,温特斯同样用“逻辑法”来表明,从一个细节到一个细节,逻辑推进脉络分明,各个环节间的顺序推进最为关键。所以说,不同词语的组合,可以推动层次意思的转换。
(三)时针的静态映现
时针其实是动的,但是表面看来却总是静态的。因为静态,所以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它的存在。我们一般会忽视了秒针和分针,直接地捕捉到跟我们现实有关的明确的时间的东西。人类的语言最终指向的跟时针一样有意义。就算日常语言,总是直接或者暗含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所谓的诗意。生活通常要求我们领会这样的诗意,仿佛生活通常要求我们明白一个准确的时间。当然,诗歌的诗意要高于生活的诗意。生活的诗意更多的在于情趣,而诗歌的诗意除情趣之外,更多的在于个人的感受和生存的况味的体现。朱光潜在《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说:“诗与实际的人生世相之关系,妙处惟在不即不离。惟其‘不离’,所以有真实感,惟其‘不即’,所以新鲜有趣。”[11]例如舒婷的《神女峰》,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词语的重组,但最终要知道的却是“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如何理解这诗句的意思?那是凭着生活的经验无法得到解释的,因为这里暗含的意思比日常语言更深远,要通过前边的诗的语言来加以理解方能够明白。正如苏珊·朗格在《情感与形式》里说:“运动在逻辑上与线性形式有关;而且,在线条连续、支承的图形又倾向给它以方向的地方,人们对它的感知就充满了动的概念,体现了抽象的趋向原则。”[12]
诗歌中的“秒针”“分针”和“时针”的互相牵制,推动了诗意的有序变化。至于读者看到“不同时候的不同时间点”,那正好说明了诗歌作为艺术的一种开放性、超越性。尽管这里面意思多变,内容深晦,但诗意是往前推进,并且是统一有序的。尽管在现代诗歌艺术结构中,似乎出现了混乱、变动不居、碎片化、滑稽、不对等、非逻辑等等不统一现象,这里面仍然暗含了作者有意味的形式,是无序中的“有序”。兰波就曾经在纸上反复修正他的作品,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因此,钟表中的“环形结构”和钟表中的“隐含结构”这两种结构的统一构成了诗歌的“钟表结构”,也就构成了所谓的诗歌运动的整体的动态的结构。
参考文献:
[1] [法]德里达.最新西方文论选[C].王逢振,等,编;李自修,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133.
[2] [美]奚密.现代汉诗[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1.
[3][4]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册)[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387、349.
[5] [美]约翰·克劳·兰色姆.新批评[M].王腊宝,张哲,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65.
[6][10]郑敏.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34、251.
[7]艾青.艾青诗论全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49.
[8]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M].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84.
[9]李泽厚.美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7.
[11]朱光潜.谈美书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10.
[12]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8.
[责任编辑:黄志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