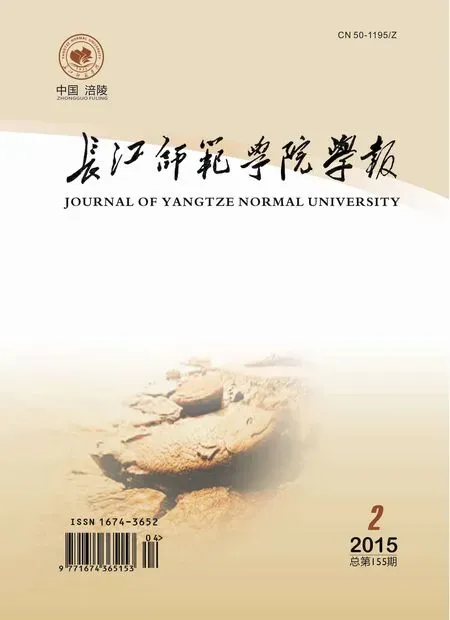亡灵的虚构——欧阳江河诗学浅探
2015-03-20毛靖宇
陈 婉,毛靖宇
(义乌工商学院 人文旅游分院,浙江 义乌 322000)
欧阳江河是20世纪90年代诗坛比较有影响的诗人和批评家。众所周知,由于国内外文化语境的改变,中国诗歌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使得原有的诗歌评价与阐释体系在仓促之间难以适应。但同时,诗人与理论家仍然没有放弃从纷繁复杂的时代表象中抽绎某种主题进行诗学建构的努力。比如,孙文波提出了 “中国话语场”的问题,韩东、于坚、伊沙、徐江等人对 “口语诗歌”“后口语诗歌”的提倡,等等。在种种对于诗歌的写作观念、立场与构想模式的百家争鸣中,欧阳江河的声音显然不可忽视。他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如《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虚构这边》《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等在当时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对于 “知识分子写作”的 “两层意思”的概括,在1998年发生的 “知识分子”与 “民间”两大阵营的论战中,不仅为同一阵营的知识分子战友所引用,也成为 “口语派”的论敌频繁攻击的对象。这里试图对欧阳江河1990年代的诗学理论进行简要的概括,以便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照。
欧阳江河的诗学理论可以简要概括为 “亡灵”与 “虚构”这样两个关键词的搭配。这两个关键词——“亡灵”和 “虚构”都是在他的文章中频频出现的语汇,而选择这两个词作为对他的诗学理论的概括,是考虑到 “亡灵”一词可能隐喻了他对20世纪90年代语境下诗人主体身份的认定;“虚构”一词则包含对于诗歌本体论、方法论的暗示。而无论是 “亡灵”或是 “虚构”,都隐含了一种对于诗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价值判断。从而,这种对于欧阳江河的诗学理论的概括与理解,能够充分地与同一阵营中的其他诗人、理论家的诗学理论区别开来。
首先,“亡灵”一词隐喻了本身作为诗人的欧阳江河对于1990年代诗歌活动的主体:诗人的自我身份的判断和理解。世界是在世界中活动着的人的世界,文化是在世界中活动着的人的行为的痕迹。所以,对于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类文化行为的考察,首要的也是必要的一环是对于这种文化行为的主体的认定与考查。这也是具有某种 “正名”意义的工作。
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1]一文的结尾部分,欧阳江河以诗性的语言对 “亡灵”的概念和性质作了详细的,甚至是不厌其烦的阐述和说明。
记住:我们是一群词语造成的亡灵。亡灵是无法命名的集体现象,尼采称之为 “一切来客中最不可测度的来客”。它来到我们身上,不是代替我们去死而是代替我们活着,它证实死亡是可以搭配和分享的。在语义蕴藏和内在视域这两个方面亡灵都呈现出追根溯源的先验气质,超出了存活者的记忆、恐惧和良心,远远伸及一切形象后面那个深藏不露的形象。亡灵没有国籍和电话号码。它与我们之间不问姓名、隐去面孔的对话被限制在心灵的范围内,…… (对话)既不达成共识,也不强调差异。……最终在无可无不可与非如此不可之间建立起了自我的双重身份……
从以上引文来看,将诗人称之为 “亡灵”,首先是具有一种在身份认证上的自我分裂的策略性模式。其次也表现出了一种自嘲自渎的无奈的时代之痛。而在这种自我分裂的策略模式和自嘲自渎的情感体验之下,深藏着的是在其大无外、其细无内、无处可逃的时代语境之下的冷峻锐利的理性的控制性力量。对于这种理性的控制性力量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知识分子写作以及评论的那种 “非个人化”的路径和风格。
不过,在这里继续追问的是产生这种 “亡灵”的时代语境。在1998年郑州召开的关于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讨论中,欧阳江河指出了 “现时”文化艺术界所面临的双重影响,即跨语际交流及国家主义的影响[2]。这种双重影响可以粗略地理解为产生这种 “亡灵”的国内和国外的语境。对于跨语际交流语境的应对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诗歌创作中 “影响的焦虑”,这是中国现代新诗从 “娘胎”里就带来的,而在一个后现代全球化的语境里被不断强化的问题。对于国家主义的应对考虑则是诗人在国家体制和文化、政治甚至是经济生活中的定位问题。这两个问题对诗人们来说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无疑都联系着一个 “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的问题,而且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只要一个共同的答案就足够了。
对于前者,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中写道:“对国内的诗人来说,以下问题无法回避:我们的写作处于怎样的影响之中?我们是在怎样的范围内从事写作的,我们所写的是世界诗歌,还是本土诗歌?”他对这一问题的自问自答是:“……诗歌界受到外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所有这些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作之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
外来影响的焦虑在欧阳江河看来并不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现代阅读、阐述、翻译、传播的新兴理论已经足够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思路和方法。他着重关注与思考的还是第二个问题。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在各种场合被频频引用。这段话概括了当时诗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理解和焦虑,“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以往的写作……几乎成为一种隔世之作……”这段话虽然直接说的是 “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但是对于和 “作品”具有血肉和灵魂上依存关系的诗人来说,以往作品的实效显然具有 “腰斩”之痛,甚至这种痛楚是不便言明的。一种时代的失落和焦虑之感从诗意的叙述之中曲折而强烈地透露了出来。
众所周知,从 “文革”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诗人的写作和主流意识形态曾经面对共同的目标,并达成过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但是,特别在中国社会的价值目标和知识构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之后,敏锐的诗人们迅即感受到了原有价值体系的失落和身处边缘的孤独。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下,那种传统的 “权力与文字的联姻”从而给文人写作 “注入持续不断的、类似于使命幻觉的兴奋力量,赋予他们的作品以不同寻常的胸襟和命运感”的时代结束了,从而暗示了与传统形态有所不同的新型的写作主体和诗歌追求、审美风格的产生。
理解这种新型的写作主体和审美风格,关键在于对 “亡灵”的理解。对于 “亡灵”的宣谕和召唤是《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的总结性的收结,它同时提供了对于上述国内国外双重语境压力的回应,其实也是一种对于新的诗歌写作型态的宣谕和召唤。“亡灵”是通过一种智慧的锋刃从 “我们”的肉体存在、世俗存在、现实存在身上剥离出来的一种 “不可测度”的存在。这是一种否定性、批判性的存在。通过从 “我们”身上剥离出这种“先验气质”的、“超出了存活者的记忆、恐惧和良心,远远伸及一切形象后面那个深藏不露的形象”的、“没有国籍和电话号码”的,“在无可无不可与非如此不可之间”进行自我对话的 “词语造成的”亡灵,诗人的写作变成了一种时代的边缘人与坚守者在古今中外广大浩淼的文本世界之中,以及在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互文性的漫游。这或许可以被称为一种 “非人”化的写作。这与王家新在他的《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一书书名中透露出的浪漫煽情气质不同,欧阳江河的 “亡灵”透露出一种知性的、冷峻的,当然还不乏某种程度的悲怆的精神格调。
“虚构”一词是一个现代小说学的概念。欧阳江河在一篇解读张枣的诗歌《悠悠》的文章中,以 “站在虚构这边”为标题,并且将此标题作为他的一本论文集的命名。理解 “虚构”在欧阳江河那里具有一种诗学本体论的性质。当然,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想象,从而也可以说是一种虚构。欧阳江河的 “虚构”是以诗歌与现实的特殊关系为参照的。这种 “虚构”和将写作主体定位为 “亡灵”的前提构成了必然的逻辑关系。
欧阳江河说,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老而又老的理论问题。在1998年的诗歌论战中,诗歌与现实、诗歌与生活的关系成为双方论战的一个焦点。谢有顺说:“(知识分子写作)所代表的将诗歌写作不断知识化、玄学化的倾向,是当下诗歌处境日益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写作的资源是西方的知识体系,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集体记忆式的,里面充斥着神话原型、文化符码、操作智慧,却以抽空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为代价,从中,我们看不到那些人性的事物在过去的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将怎样走过去……”面对这种挑战,知识分子阵营如臧棣则强调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放弃 “对日常经验的重视和对日常事物的探索”,并认为诗歌的日常性问题是一个风格问题,不是一个关于诗歌的本质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有意味的是,作为知识分子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欧阳江河似乎自始至终都未发一言。我们的理解是,按照他的诗学观念,他认为对民间阵营的指责不值得回应。问题在于对现象的观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对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却因诗学立场和追求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在1998年郑州举行的关于 “九十年代诗歌”的讨论会上,欧阳江河在《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3]一文中讨论了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
自由空间的延展,人们对新的时间观、新的生存节奏及新环境的逐渐适应,以及迁移的普及化,削弱了地域特质对诗人写作的影响,诗人不再局限于某时某地进行创作,诗人可以基于词的立场——发明或虚构的立场——去制作,评论及命名自己的作品,并且,文本的意义可以衍生自写作本身,而不必在 “预设的现实”中去寻找资源。
但这种诗学原理及写作方法,不一定是相互协调的。因为诗人不大可能逃避地方性的特有阳光、空间、地貌及节奏,以及口音、民俗,隐性宗教及教育交融累积的历史因素,还有地域经济的特色,种种因素构成那些难以界定却有迹可寻的国家认同意识。而且,众所周知,中国诗歌历来欠缺 “物质性”。即使是直接描述生活状况的及物写作也不大可能唤起这种物质性,如何能奢望在写作过程中持虚构的立场呢?
……在我看来,在宣言和常识的意义上认同历史、认同现实是一回事,通过写作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是另一回事,现实感是个诗学品质问题,它既涉及了写作材料和媒质,也与诗歌的伟大梦想、诗歌的发明精神及虚构能力有关。我的意思是,现实感的获得不仅是策略问题,也是智力问题。
在这里,首先确定的前提是,写作是一种 “虚构”,一种 “基于词的立场”的 “制作、评论及命名”行为。其次才考虑怎样 “虚构”的问题,即以一种 “智力”性的因素加工处理国际性的以及本土性的 “阳光、空间、地貌及节奏,以及口音、民俗,隐性宗教及教育”种种因素获得作为一种诗学品质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那么,究竟如何虚构呢?这种虚构的现实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在欧阳江河那里,现实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国际化、全球化压力之下的 “本土化”问题。欧阳江河以陈东东等人的诗为例,指出这种虚构的现实是文本意义上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场景的客观呈现以及事态的自然进程,而是写作者所理解的现实,包含了知识、激情、经验、观察和想象。
这种虚构现实的载体不再是一种 “诗意辞藻”的语言,而是一种 “复合性质的定域语言”,即 “基本词汇与专用词汇、书写词根与口语词根、复杂语码与局限语码、共同语与本地语混而不分”的语言。这种观点的提出实际上回答了诗歌界一度引起讨论的口语语汇与书面语汇、古典语汇优劣之争的问题,也实际上是对民间诗派口语化写作立场的一种应答。所以,欧阳江河说,这是汉语诗歌写作在语言策略上的一个重要转变。
在这种语言的操作问题上,欧阳江河说:“它涉及语码转换与语境转换,这两种相互重叠的转换直接指向写作深处的现实场景的转换。”转换的结果是作者 “借助改变作品的上下文关系重新确立了写作的性质”。欧阳江河说这种语言是界于书面语言与口语之间的一种中间语言。它的引人注目的灵活性主要来自于对借入词语的语码转换。这种转换看似是即兴的、不加辨认的,但实际上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种语言的操作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因为现代语言学对观察世界方式的介入而产生的以智性想象为主导,包融感性想象的,在现实与文本、世界与本土之间的互文性写作过程。
欧阳江河对张枣《悠悠》一诗的细读分析文章《站在虚构这边》[4]使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这种互文性写作的内在流程以及欧阳江河本人的诗学思想。在分析了张枣诗中的 “超声音”后,欧阳江河说:
张枣为《悠悠》找到了这样一种方案,它既属于诗,又属于理论。读者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实际上《悠悠》的写作涉及到两个不同的诗学方案。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深感一个诗人在体制话语的巨大压力之下,处理与现代性、历史语境、中国特质及汉语性有关的主题和材料时,文本长度、风格或道德上的广阔性往往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把诗学方案的设计、思想的设计、词与物之关系的设计考虑进来的话。……张枣是从诗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场景的角度去考量的。《悠悠》为读者提供的诗学角度,简单地说就是坚持文学性对于技术带来的标准化状况的优先地位,同时又坚持物质性对于词的虚构性质的渗透。
在这里,词的意义既不在于它在词典中的意义,也不是它在现实场景中的指涉意义,而是一种在与其他语汇的交织关系中被确定的互文性意义。物质性和词的虚构性质的相互渗透造成的既不是现实生活的空间,也不是诗人、批评家、读者个人精神世界中的孤立空间,而是一个在与其他文本互文性关系中被不断阐发的诗歌空间。这个空间或者可以说是一个由诗人、读者、环境 (也是一种文本)以及已经进入人类文学史、文化史的诗歌与理论文本序列共同造成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张枣诗中的语音室,在欧阳江河那里变成了一种 “展示了由高科技和现代教育抽象出来的后荒原风景”的场所,语音室里耳机传出的声音,是一种被过滤了人的自然属性,只与播放系统和收听系统的机器质地、技术指标有关的 “超声音”。语音室里怀孕的女老师,是语音室里唯一不用戴耳机的人,但是,她从语言室的超声音中游离出来,想要听听原汁原味的生活,听到的却也不过是全球化时代毫无特色的晚报的叫卖声。再如,在分析 “‘晚报,晚报,’磁带绕地球呼啸快进”一句时,欧阳江河注意到磁带只有按照预先设定的转速才发出声音,如果 “呼啸快进”的话,它将是无声的。他追问道:“一个失去了声音的声音词,会不会转移到别的语义层,作为一个时间语码起作用?”他由此在西方文学视野中展开了广泛的联想:从阿喀琉斯的盾到渔王的圣杯、济慈的希腊古瓮、布莱克的轮子……这些意象全都有一种 “乡愁般”的诗歌仿型倾向。通过与进入文学陈列馆的经典意象的相互指涉,欧阳江河发掘或言拓宽了原诗构筑的诗性空间。
从以上所引的例子来看,欧阳江河对原诗语言、意象与结构的解读分析,虽然有情感感受的成分在内,但主要还是基于一种建立在阅读经验与逻辑思维基础上的理性联想。显而易见,这种理性联想的心理流程和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欣赏的心理流程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打破了阅读主体的主观限域,并且同理在创作中是打破了创作主体的主观限域,广泛地出入在众多的语境和文本之间,这种写作无疑为诗歌表现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人感受的兴趣,自己阻断了通往更多读者的道路,因而导致了诸如民间派诗人的不满与揶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写作可以称为一种 “非人”的写作,一种 “亡灵的虚构”。也许,在欧阳江河的诗歌抱负里,诗本来就和现时性无关,他要造就的是一些能够在时间中静止下来的东西,这正如他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一文中最后引用的一句诗所宣示的:诗歌教导了死者和下一代。
[1]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M]//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45.
[2][3]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写作:认同什么?[M]//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273、273.
[4]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