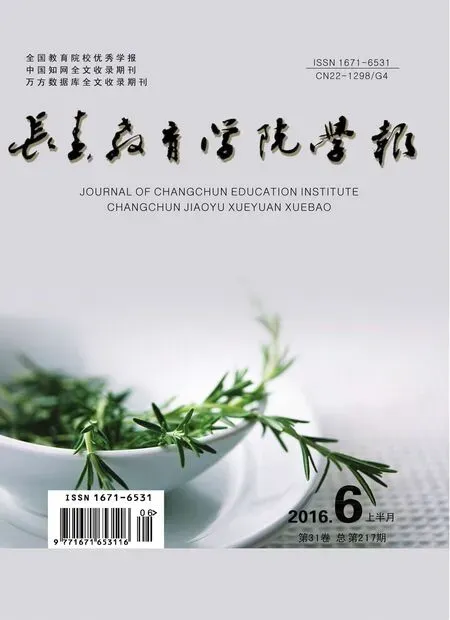清末法律翻译中的翻译标准与方法
2015-03-20伊纪昌
伊纪昌
伊纪昌/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山东曲阜273165)。
清末的法律翻译活动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法律翻译的肇始时期、洋务运动时期的法律翻译和甲午战后变法修律时期的法律翻译(屈文生,石伟,2007:58-62)。在各个阶段均涌现出了一批法律翻译实践家。他们既有外来的传教士,也有国内的翻译人才。同时,这些翻译实践家们也提出了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翻译理论。归纳起来,这些法律翻译理论大体分为两个方面:法律翻译的标准和法律翻译的方法。
在清末法律翻译活动中所产生的翻译标准和方法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这些实践意义不仅体现在法律翻译领域,甚至还扩展到了整个翻译领域。当时的学者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和方法,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鉴或使用。
一、法律翻译标准的演变
1.马建忠的翻译标准。马建忠是一名具有维新思想的语言学家,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精彩的关于翻译的文章,即《拟设翻译书院议》,建议设立翻译书院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同时有计划地进行译书。他说:“译书一事”乃“当今之急务”“如欲不见欺于外人”,必须了解外人的“情委虚实”。
马建忠认为,有三类书是亟须翻译的:第一类为“各国之时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等;第二类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生财、交邻诸大端所必须者”;第三类为“外洋学馆所应读之书”,包括各国历史类书籍、数学书籍、物理与化学书籍等。他还强调,翻译书院必须以教、学、译和出书相结合。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清廷所采纳。
他指出当时译员在翻译奏折中存在的问题是只懂一点点外语,或精通外语但中文造诣不高,又或请稍通汉语的外国人进行口述。在他看来,当时的翻译质量并不高。因此,他提出了一种翻译标准,即“善译”。所谓的“善译”,是指在进行翻译前要反复阅读原文,充分理解其“意旨”,然后再进行翻译,对译文的要求是“无毫发出入”,与阅读原文没有差异。“善译”的观点与严复的“信达雅”有些许类似。但这篇文章写于1894年,比严复的“信达雅”观点问世还要早。只是用词没有严复那么明确、简洁。
2.严复的翻译标准。严复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严复提出的这三条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信”指的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思想;“达”指的是译文必须清晰流畅;“雅”指的是使用雅言,即使用“汉以前的字句字法”。前两条标准被广泛接受,但第三条“雅”却争议颇多,因为汉朝以前的古汉语在当代中国已被弃用。因此,我们应客观地来看待他的翻译标准。
严复共有9篇比较重要的译作,其中《法意》一书是唯一一部属于法律范畴的书。那么,他对《法意》的翻译符合自己所提出的翻译标准吗?客观来说,严复所译的《法意》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翻译标准。傅斯年曾说过:“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傅斯年还说:“严几道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是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
严复所译的《法意》确实有不足之处,这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想让那些传统中国学者读懂他的译作,所以他不能用一些太新的词语,因为这是这些学者茫然无所知的,因此他只能选择古汉语进行翻译。第二,《法意》是他的早期作品之一,而在他的早期翻译生涯中,当时他所追求的不是直译,而是要“达旨”,这就造成了他的翻译可能不是很“信”。
3.沈家本的翻译标准。沈家本,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考中进士,留刑部补官,并开始攻读法律。1902年,清政府变法修律,设立修订法律馆,命沈家本为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熟谙中国古代法律,并热心学习西方法律。他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源,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在他主持修律期间,积极组织力量,翻译外国法律。为了能够制定为中外所共同接受的法律,他设立法律学堂,聘请资产阶级法学家担任教学和实际立法工作。如此一来,研究西法的风气打开,这一时期也成为清朝立法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因此,清末修律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法制史的第一篇章。
沈家本认为“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并举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说:“当时日本,群臣上下,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精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由于沈家本通晓中外法律,深知“译书以法律为最难”,无论“语言之缓急轻重,记述之想略偏全”,都将造成不同的后果,甚至“抉择未精,舛讹力见”。为了避免“失实”,他除要求译员所译之书“力求信达”以外,还亲与“原译之员,逐句逐字反复研究,务得其解”。
在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期间,先后译成26部外国法律,已开始翻译但未完成的法律也有10部之多。虽然他也未能提出明确的翻译标准,但为译员制定了严格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在实践中也是行之有效的。
总的来看,严复的翻译标准要比马建忠和沈家本提出的翻译标准更清楚、更完整。但三人都特别重视“信”和“达”。这两个标准在法律翻译当中尤为重要,即便是今天仍然是很好的借鉴。
二、法律翻译方法的演变
(一)常用的翻译形式——合译
合译,是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进行翻译的一种群体行为(郑延国,1995:22-28)。合译的翻译形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它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
在清朝末年,由于缺乏既精通汉语又精通外语的人才,合译就成了一种常见的翻译形式。在法律译作中,合译作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星轺指掌》的翻译工作就由当时在同文馆学习的联芳、庆常进行初稿翻译,然后交给荣贵、杜法孟稍加润色,再经丁韪良审定,最后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审定后出版;《公法会通》由联芳、庆常、联兴等负责翻译了大部分,其余为丁韪良口译,荣贵及贵林笔述,最后由荣贵审定而成;《公法便览》的翻译工作则是由汪凤藻、汪凤仪、左秉龙和德明四人共同完成。
傅兰雅所采用的翻译形式也基本相同。对于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官的翻译形式,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有所叙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句,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谨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则精。”如《各国交涉公法论》就是先由傅兰雅口译,再由国人俞世爵笔述,最后经汪振声等校正而成。
在使法律翻译成为可能并使效率提高的同时,合译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误译和语言晦涩等。然而,随着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质量也在逐步提高。
(二)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
在翻译特定的法律术语时,有些翻译方法在当时是经常用到的,例如音译法、造词法、类比法等。
1.音译法。音译法是一种以音代义的翻译方法,在英汉翻译中指用具有与英语相似发音的汉字来翻译相应的英语文本。在清末的法律翻译当中,由于很多外语词汇缺乏相应的汉语对应词,所以很多都是采用音译法来翻译的。例如,“law house”曾被翻译为“律好司”“president”曾被译为“伯理玺天德”“parliament”曾被译为“巴厘满”。
2.造词法。造词法指的是利用新创造的词语来进行翻译。清朝末年,中国已经被西方远远甩在身后,在法律领域也是落后于西方。就连一些外语法律术语,都找不到相应的汉语对应词。在翻译这些词语的时候,除了使用音译法外,造词法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例如“民主”“政体”“批判士”这些词语就是在当时创造出来,用来翻译“republic”“regime”和“juror”这些词的。
3.类比法。在翻译方法当中,类比法指的是使用原来已经存在的词语来翻译一些新的概念。在清末法律翻译当中,很多汉语词汇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来翻译相应的外语词汇。例如“内阁”“尚书”“大学士”这些中国古来已有的词语被用来翻译 “cabinet”“minister”和“premier”这些新的概念。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时法律英语翻译所采用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下《万国公法》中的几个句子:
例句 1:Legislative power of the union—The legislative power of the Union is vested in a Congress,consisting of a Senate,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chosen by the local legislature of the several States,and 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elected by the people in each State.
丁韪良译文:上国制法之权:合邦制法之权,在其总会。总会有上、下二房。在上房者,为各邦之邦会所选;在下房者,为各邦之民人所举。
例 句 2:Executive power—To give effect to this mass of sovereign authorities,the executive power is vested in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chosen by electors appointed in each State in such manner as the legislature thereof may direct.
丁韪良译文:首领行法之权:其主权职事如此之繁,即有合邦之首领以统行之。首领乃美国之语,所称“伯理玺天德”者是也。其登位也,系各邦派人公议选举。所派之人,亦为各邦之民,遵循其邦会之定例而公举者也。
例句 3:The judicial power extends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e constitution,laws,and treaties of the Union,and is vested in a Supreme Court,and such inferior tribunals as Congress may establish…The judicial power also extends to all cases affecting ambassadors,other public ministers,and consuls.
丁韪良译文:司法之权,在上法院,并以下总会所设之法院。所有关乎公使、领事等案……皆属上国法司之权。
丁韪良采用音译法将“president”翻译成“伯理玺天德”。而“president”一词的另一译法“首领”则是采用了类比法,丁韪良给“首领”这个旧词注入了新的概念—一名由选举人选举的领袖。造词法在这三句例句中更是随处可见,例如制法之权(legislative power)、合邦(union)总会(Congress)、上房(Senate)、下房(House of Representatives)、行法之权(executive power)、司法之权(judicial power)、上法院(Supreme Court)以及领事(consul)等。
作为翻译学科下的一个分支,法律翻译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对清末法律翻译活动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在法律翻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了大量的翻译文本及翻译思想,这在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总之,清末法律翻译活动在促进法律翻译理论的发展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翻译标准的演变和翻译方法的应用都离不开翻译实践。同时,这些翻译理论对于当时翻译实践的改善,尤其是翻译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些术语的翻译与今天的翻译基本一致,甚至保留到了现在。另外,当时的一些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在今天仍然适用,我们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可以进行借鉴。
[1]屈文生,石伟.论我国近代法律翻译的几个时期[J].上海翻译,2007(4).
[2]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郑人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4]严复.法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沈家本.寄簃文存[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6]田涛,李祝环.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J].中外法学,2000(3).
[7]郑延国.合译:佛经翻译的一大特色[J].现代外语,1995(4).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出版社,1998.
[9]何勤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法学[J].法制与中国社会发展,2004(5).
[10]丁韪良译.万国公法[M].惠顿著.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1]尹娇龙.法律翻译的若干策略运用[J].法制与社会,2001(1).
[12]孙迎春.翻译简史[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