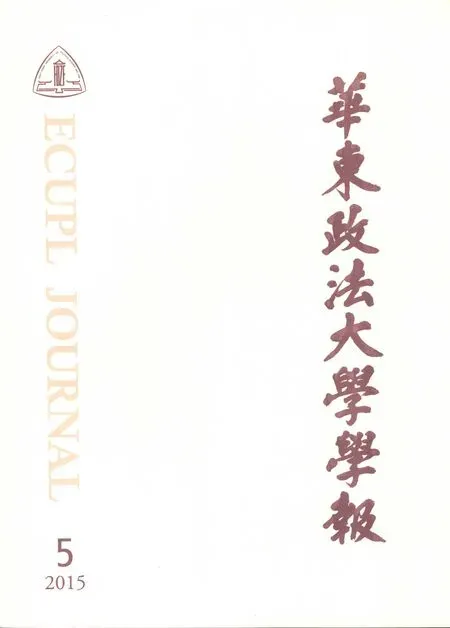和解合同的实体法效力——基于德国法视角的考察
2015-03-19庄加园
庄加园
一、引言
和解现象在法律词源学上被解读为友好解决纠纷的基本形式。〔1〕HKK/Hermann, 2013, § 779 Rn. 1.法律上的和解并非为了产生或消除良好或不快的情绪,满意或愤怒等情感,而是为了解决法律上的命运,作用于法律效果层面,旨在实现一定的法律效果。具体言之,若双方当事人基于不同立场对某个法律关系发生争议,可借助和解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解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正如其他合同那样,都是旨在发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即发生、变更、消灭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或具有法律属性的人或物。〔2〕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00.和解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不依赖国家公权力,直接作为社会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人们之间的纠纷。为此,现代立法者使得他们达成的合意能够发生约束当事人的效力,以便不仅调整人们当前所面临的冲突,而且也能更好地防止潜在的冲突。〔3〕HKK/Hermann, 2013, § 779 Rn. 4.
最高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2号“吴梅案”似乎也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在诉讼外由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西城纸业公司(以下简称“西城纸业”)按照约定还款,吴梅则放弃支付利息的请求。协议达成之后,西城纸业申请撤回上诉,相关争议似乎得到最终解决。但当西城纸业不履行还款协议时,吴梅能否要求被告履行原来(含利息)的债务。对此,民事诉讼法学者撰文探讨颇多,而民事实体法则问津寥寥。〔4〕诉讼法的代表性论文如严仁群:《二审和解后的法理逻辑:评第一批指导案例之“吴梅案”》,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王亚新:《一审判决效力与二审中的诉讼外和解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号指导案例评析》,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吴泽勇:《“吴梅案”与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机制——兼与王亚新教授商榷》,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1期;吴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的程序法理》,载《法学》2013年第1期。不过,学界大多认为吴梅案当事人所订立的“和解协议”并非诉讼和解,而是诉讼外和解,由此直接对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由于我国《合同法》并未规定和解合同,国内文献对此也论述不多,和解需要具备何种构成要件、发生何种效力以及发生给付障碍时的救济方式,都无法在我国制定法中直接觅得。〔5〕实体法的论文如隋彭生:《诉讼外和解协议的生效与解除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的实体法解释》,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贺剑:《诉讼外和解的实体法基础——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载《法学》2013年第3期。正如法律继受过程屡屡被提到的“金鸡纳霜”比喻:“……只有傻子才会因为金鸡纳霜不是生长于自己苗圃而弃之不用。”〔6〕Jhering,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Erster Teil, 2 Aufl age, 1866, S. 8-9. 转引自朱哓喆:《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的立场与使命》,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基于当前日益发达的比较法文化,笔者拟借鉴与我国民法体系较为接近的德国民法,基于比较法的教义学路径,〔7〕有关比较法与教义学的关系,详见朱哓喆:《比较民法与判例研究的立场与使命》,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针对“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予以探究。
二、构成要件
(一)以解决法律关系的争议或不确定性为目的
和解属于所谓的确认行为(Feststellungsgeschäfte),其目的在于使当事人之间有争议或不确定的法律状态变为无争议或确定的法律状态。〔8〕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 1 Allgemeiner Teil, 14. Aufl age, München 1987, S. 89.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合同也涉及法律关系,它们之所以不能被列入和解,在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之前未就相关法律关系发生争议或不确定性。〔9〕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1.因此,法律关系与基于该关系发生的争议或不确定性是和解合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 法律关系
和解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可想象的法律关系: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法律上的联系。这一概念基本类似于民事诉讼法中确认之诉的标的: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的法律关系。按照拉伦茨的概括,“法律关系至少必须包括一个主观权利”。〔10〕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age, München 2004, S. 227.和解的法律关系既包括具体权利的狭义法律关系,如租金债权,也覆盖整体权利的广义法律关系,如租赁关系。〔11〕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98 f.狭义的法律关系不限于现在的具体权利,甚至包括将来的请求权、附条件、附期限的请求权。〔12〕MünchKommBGB/Habersack, 2004, § 779 Rn. 3.广义的法律关系更多地作为“有机体(Organismus)”,包括权利、义务、负担等内容。〔13〕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99.
债务关系虽然是和解合同的重要内容,但和解对象不仅限于债的关系或债权。因为法律关系的概念外延要大于债之关系,如合同、侵权之类的债法关系。〔14〕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01-102.以所有权为典型的物权,乃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法律关系、劳动者与雇主的劳动关系、继承法的请求权等都可被和解所囊括。〔15〕Hamme, Aussergerichtliche Vergleichsvereinbarungen in den USA und in Deutschland S. 127.这一概念之所以作最广义的理解,是为了尽可能地解决人们之间的法律争议。
实践中要区分的是所谓的事实和解。法院更多地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不愿调查这些事务。有关事实的争执与一致见解至多涉及事实层面,即请求权事实上的前提,以致概念上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和解。然而,若特定事实涉及具体的法律关系,如其涉及请求权或抗辩、抗辩权的构成要件,对其发生的争议可能成为和解对象。〔16〕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03.比如双方争议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究竟多高,甲说400米,乙说500米。这样的纯事实争议不涉及法律关系,自然不构成和解对象。但若双方达成买卖某画的合同,价款数额根据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的高度而定,那么对该事实争议所达成的和解,因涉及买卖价款的数额,可以成为《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的和解合同。
2. 争议或不确定性
争议存在与否,并不取决于法律关系客观上是否难以判断,而是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视角而定。〔17〕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2; MünchKommBGB/Habersack, 2004, § 779 Rn. 14.主张其立场的当事人不必相信其所主张内容,只要当事人面对相对人坚持其立场即可。一方当事人很可能在面临对方驳斥其主张时,发现没有足够理由,或者自己也不相信其所主张的内容,但这并不能改变不同立场的客观事实。债务人可能明知其具体的债务数额,依然与债权人就债权数额发生争执,因为他可能知道,债权人由于缺乏证据,难以证明债权的数额。
争议要求双方当事人就相关的法律关系提出不同的、至少部分驳斥对方立场的主张,〔18〕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2.或者当事人各自主张不同的事实状况或法律状况(Rechtslage)。〔19〕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d. 22; 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3.比如,债权人要求债务人还钱,债务人主张债务已经清偿或清偿期限尚未届至。正因为存在争议,当事人才需要达成和解,以消除争议。〔20〕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3. 倘若双方认为不存在争议,仍然达成和解合同,则缺少确认目的,这样的协议只是“表见和解”,应由《德国民法典》第117条第2款来调整。此时,应以当事人隐藏的目的作为意思表示的内容。
法律关系除有争议之外,还可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21〕德国普通法时期曾对和解对象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存在对和解对象的争议,另一种观点认为仅需要法律关系不确定即可满足。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在立法时偏向了第二种观点,在第779条第1款规定了法律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第2款则规定请求权的实现有不确定性。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4.它是指法律关系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存在完全的明确性(Klarheit),不确定的判断标准仍然是当事人的主观认识。即使旁人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只要它们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依然不受第三人认识的影响。〔22〕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4.不确定并不以争议为前提,当事人即使对法律关系没有争议,而是存有合理怀疑,如将来的权利发展或条件的发生,法律关系也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23〕MünchKommBGB/Habersack, 2004, § 779 Rd. 24.不确定虽以当事人主观认识为准,但要求双方都处于不确定状态。债权人若确信其债权而向债务人要求履行,债务人怀疑债务数目是否如债权人所主张的那样。双方为避免诉讼而达成合意,债权人同意减少债权数额。即使双方达成合意,若债权数额的不确定性仅存于债务人一方,不符合双方都对法律关系存在不确定的要求(因为和解的法律效果要求双方当事人都要对和解对象存有共同的设想),难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 779条。〔24〕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5.
本案事实并未提到和解双方当事人对债权的存在存有争议。事实中只提到原告吴梅“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由此得到的理解只能是吴梅向被告主张履行债务,被告拒绝履行。“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这一事实也只提到还款安排,没有提到双方争议内容究竟是什么。仅从以上事实出发,并不足以推出吴梅与西城纸业公司存在争议的结论,至多只是一方催讨债务,另一方拒绝履行。倘使西城纸业公司否认吴梅债权的存在,或认为原告主张的债权数额高于实际数额,《德国民法典》第779条所要求的法律关系的争议才能得以满足。
《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2款还将请求权实现的不确定(unsicher)与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同等对待。第2款的“实现”并不包括关于请求权存否的争议,或者请求权是否存有抗辩权(因为这都由第1款来调整),而是指有关请求权的实现可能性(Realisierbarkeit)。〔25〕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36; vgl. MünchKommBGB/Habersack, 2004, § 779 Rn. 25.如果当事人对敌意或强制性的履行存有怀疑,那么请求权的实现就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一怀疑可能具有经济上的理由,如债务人是否缺乏履行能力,或者存在诉讼上的理由,如一方当事人存在证明上的困难。若以请求权实现的不确定性来考察,西城纸业需要缺乏履行能力,如资金不足以致难以清偿吴梅的债权,或吴梅缺少证据证明其与西城纸业存在债务关系或具体债务数额(实际证据佐证的债权数额小于吴梅主张的数额)。但吴梅案的事实部分却对以上事实只字未提,因此请求权实现的不确定也无法得到证明。
(二)互相让步
争议和不确定性或者请求权实现的不确定,必须通过双方当事人互相让步(Gegenseitig Nachgeben)而被消除。早期观点从实体法律关系出发来理解让步,甚至将和解视为双方互相免除债务。由此,和解被定性为双务、有偿合同。也有观点主张,让步必须从经济上理解,它包含着财产给予(Zuwendung)和财产损失(Vermögenseinbüße)。财产给予一般通过免除、债务承认、债权或物权设立等行为而得到实现。〔26〕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42 ff.
但这一经济上的观察方式即使在最简单的和解情况下也会陷入困境。例如,甲要求乙偿还100元债务,乙只同意归还50元。双方为此达成合意,乙向甲支付75元,以解决此债务纠纷。考虑到和解所具有的经济潜在性(wirtschaftliche Potentialität),不禁让人怀疑,双方的财产是否遭受到真实损失。可供假设的情形无非存在三种:第一,最初的债权高于75元(如90元),甲事实上免除乙的部分债务,乙由此享有财产上利益(15元);第二,最初的债权低于75元(如60元),乙多清偿了其本来没有负担的部分债务,甲为此享有财产上利益(15元);第三,最初的债权正好为75元,双方的财产状况都没有任何变化:无人获益,也无人受损。〔27〕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43.
从这一简单的例子来看,和解双方要么一方获益,要么双方的财产状况都没有变化,所谓双方互相免除债务的情形并未发生。因此,所谓单方的财产给予可能更符合以上情况。但财产受损是针对当事人事实上的财产状况,它需要探知当事人初始的财产状况,才能知道当事人如何让步。而和解恰恰是以放弃探究初始的财产状况为代价,以换取争议的最终解决。和解虽以双方当事人的初始主张作为出发点,但和解之后的实体法关系却未必与双方的初始主张有关。和解之前的实体法关系究竟如何,对于当事人而言已经没有意义。当事人并不关心这一关系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而是将其束之高阁,不再理睬。有意义的只是和解之后的实体法律关系,就此而言,让步的前提正是当事人放弃继续探寻初始立场的正确性。〔28〕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48.
时至今日,学界和实务界已放弃从客观的实体法角度判断让步,让步未必与和解合同的内容同一,也未必与和解所引起的法律效果相同。〔29〕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254.让步转而根据当事人的主观视角来判断,即使是当事人误认作出牺牲,也构成和解。〔30〕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27.让步意味着每一方要为对方的利益全部或放弃之前所持的立场,〔31〕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27.更多地被理解为每个对于对方友好的当事人行为(jedes Gegenfreundliche Parteiverhalten)。互相让步意味着,每个当事人都必须从自己当前所主张的立场,偏向另一方的立场,〔32〕Medicus, Schuldrecht, I AT, 18. Aufl ., München 2008, S. 148.并不意味着双方的“让步”必须具有同等的价值。互相让步必须要达到消除争议或不确定的程度,以至于争议得到最终解决。〔33〕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27.
“互相让步”的概念并非从法学意义而是更多地从日常语言来理解,〔34〕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27.这就使得和解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模糊程度,由此加剧了判断困难。尤其在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债权,另一方同意撤回上诉时。从公报案例的事实来看,西城纸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后撤回上诉。双方并未于协议中约定西城纸业公司负有撤回上诉的义务,而只是约定西城纸业公司按照约定期限还款,吴梅放弃利息。若将撤回上诉和放弃利息作为相互让步,仅就该案的“和解协议”而言,还是缺乏明显的依据。另外,案例事实也没有说明当事人初始主张的内容。因此他们的初始立场究竟如何偏向另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也缺乏必要的事实。
根据本案的事实,仅有吴梅一方免除部分债权,而另一方没有作出任何让步或牺牲,以此为内容的协议不足以构成和解合同,〔35〕Medicus, Schuldrecht I AT, 18. Aufl ., München 2008, S. 149. 假设吴梅案双方对归还欠款的数额发生过争议,若仅有一方让步,就消除了争议或不确定性,那么至多存在单方的“确认行为”,类推适用《德国民法典》第779条。Vgl.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28.至多是“以清算为目的的合同变更(Vertragsänderung)”。〔36〕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债权人眼见强制执行无望,而同意债务人分期清偿执行的债权,仅含有债权人一方的让步,不构成和解合同。〔37〕OLG Hamburg MDR 1973, 683; OLG Köln NJW 1976, 975.在汉堡州高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作为被告人的债务人表示以每月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剩余债务的意愿,但这却不构成《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的和解;债务人的支付义务已由发生既判力的判决所确定。尽管有观点认为,在经济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债务人的让步“表现为诚实的支付意愿,而且尽力去履行其支付义务”。但债务人尽力去履行支付义务只是许诺了将来的行为,其纯粹表示履行债务的意愿,并非可见的让步。即便是懒惰的债务人,也可以进场重申(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给付意愿。此外,该案的审理法院指出,如果执行尚未发生既判力,或执行措施存有疑义,债务人明确表示对此放弃上诉或起诉、放弃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或重审之诉,也有可能构成让步。〔38〕OLG Hamburg MDR 1973, 683.
在科隆州高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债务人也是在“和解”协议中同意分期还款。尽管原告放弃了立即执行债权,并允许债务人部分给付,使得原告满足了让步的构成要件。法院仍坚持认为,由于债务人没有放弃任何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地位,无法认定债务人作出让步,《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的和解也就无从谈起。倘使债务人放弃提起对请求权的抗辩,如针对本案延迟判决的上诉,才有可能构成让步。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债务人表示支付的意愿也可被视为让步,如债权人担心其请求权以强制执行的方式可能无法实现。若针对债务人的强制执行错误可能无结果,债务人表示支付的意愿也就意味着放弃使其安全的地位。〔39〕OLG Köln NJW 1976, 975, 976.
根据本文的分析,吴梅案从构成要件与法律效力都与《德国民法典》第779条所定义的和解合同相去甚远。虽然,我国《合同法》未如欧陆国家的民法典那样,将和解合同作为有名合同吸纳其中,但和解作为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不应否认其效力。既然如此,和解合同作为无名合同,究竟具备何种要件,发生何等法律效力,则需要根据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加以解释,而不是根据合同名字是否为“和解协议”来盲目判断。
三、性质与效力
(一)和解的性质
《德国民法典》制定后的早期学说将和解当作债法上的合同,甚至根据其双方互相让步的特征认为其属于双务合同。〔40〕HKK/Hermann, 2013, § 779 Rn. 9.主流学说虽已抛弃双务合同(《德国民法典》第320条)的认识,但坚持将其作为有因的债务合同(Kausaler Schuldvertrag)来对待。倘使和解合同发生了实施处分行为的义务,那么必须单独实施这些处分,如移转动产所有权、设立不动产抵押权、让与债权。假使和解合同无效,这些处分行为根据抽象原则仍然有效,只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12条以下的不当得利规则进行清算。〔41〕Medicus, Schuldrecht I AT, 18. Aufl ., München 2008, S. 149.这一观点来自于19世纪德国的抽象原则,当事人由此以和解方式进行处分。作为原因行为的具有债法性质的和解合同与以处分面目出现的履行行为相分离,抽象原则方得以彻底表现。〔42〕HKK/Hermann, 2013,§ 779 Rn. 10.
虽然和解处于《德国民法典》债编的有名合同行列,〔43〕有些学说则认为,和解应被置于债法总则,而不应列入有名合同行列。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 1 Allgemeiner Teil,14. Aufl age, München 1987, S. 89.但并未能说明各种具体和解中可能出现的特殊因素,以及由此引发的多样性。这些都是旨在实现解决争议所必需的内容:互相放弃请求权、确定债权的数额与内容、债务免除与负面的债务承认等,也有可能是混合了以上多种内容。和解的性质也应根据其内容而定,或是负担行为,或是处分行为,也可能混合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和解的变更若能作为处分合同,那么变更对象不仅是单个债权,而且包括整个债的关系。〔44〕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71.
主流学说忽视了和解的多重功能所引起的归类模糊性(“体系上的流浪汉”)。〔45〕HKK/Hermann, 2013, § 779 Rn. 10.和解根据其内在的规则因素,可能表现为不同内容的集合体,若将其统一定性为仅具债法性质的法律行为,则未免有削足适履之感。〔46〕HKK/Hermann, 2013, § 779 Rn. 12.新近的观点认为,和解合同的性质应视其内容而定,没必要在纯负担行为发生时又同时假设概念上独立的处分行为。〔47〕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 1 Allgemeiner Teil, 14. Aufl age, München 1987,S. 89.由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僵硬区分难以得到延续,而是要视和解合同内容而定。无论采用哪种见解,和解合同至少都会使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请求权与相应的义务。就此而言,和解合同发生创设性效力,似乎并无争议。
(二)确认性效力或创设性效力、变更或更新?
和解的效力究竟是确认原来的法律关系而使其继续,即仅有确认的效力,还是发生新的法律关系,也即具有创设性效力,学说存有争论。《德国民法典》对此未设规定。若比较新旧法律关系的内容,以此来决定和解是否具备创设效力或确认效力,和解合同一般都会使得初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通常都具有创设效力。就承认债务数额为例:当新债小于旧债时,和解合同发生债务部分免除的效力;当新债大于旧债时,当事人通过和解合同又设立新的债务。仅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当新债与旧债完全相同时(实体法上内容不变),〔48〕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13.和解合同才发生所谓的确认效力(deklartorische Auswirkung)。
由于和解具有确认行为的特征,因此它只是针对法律关系中有争议或不确定的方面重新约定,其他部分仍然保持不变。尽管就确认与重新发生的法律关系而言,和解产生了新的诉因,但仍不构成更新。对于判断和解确认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内容,最初的法律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只要原来的抗辩没有经由和解而消灭,和解当事人依然主张这些抗辩。一般而言,消灭时效仍适用原来的时效,除非和解中包含着债务承认,时效才会重新起算。在旧债上所设定的担保通常也继续存在,即使和解提高了债权数额,担保人的责任也不会随之自动扩张。〔49〕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38.
尽管和解会发生新的权利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更新(Novation),并导致新债丧失同一性。〔50〕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38.不过,和解当事人根据契约自由原则,也可使和解发生更新的效力。由此,原有的担保权便告消灭,消灭时效则取决于新的法律原因。和解是否发生更新的效力,则需要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进行解释。〔51〕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39.除非当事人明示,终止争议的法律关系,并发生新的法律关系。在当事人意思存有疑义时,和解不能被推定具有更新的效力,是为了避免原有法律关系终止,以便既有的担保权利继续适用于和解后的法律关系。〔52〕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44-145; vgl. HKK/Hermann, 2013, § 779 Rn. 14.
(三)潜在效力
和解合同如何作用于和解对象(争议或不确定的法律关系),需要比较合同订立前后的法律关系才能确定。然而这一方法在和解中却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当事人往往对于真实的法律关系存有争议或者不确定。虽然争议或不确定因素被和解所解决,但其效力确系向将来发生,即今后对当事人发生某种拘束力。因此,当事人对作为和解对象的初始法律关系具有何种权利,难以经由和解得到解决。〔53〕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10.鉴于和解所具有的潜在效力,需要区分争议对象分别讨论。
倘使当事人未对债务关系的存在发生争议,而仅就权利发生、消灭的抗辩、抗辩权或债的履行方式存有争议,则和解作用于初始法律关系的效力较易确认。〔54〕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12-113.例如,甲乙双方都承认,前者曾给予后者1万元无息贷款,双方争议的只是乙提前归还的是2千元,还是4千元。最后,双方达成和解,算作归还3千元,剩余贷款为7千元。该例中,和解当事人对作为债务关系的贷款没有争议,只是无法确定乙归还的债务数额。和解所发挥的潜在性仅在于,究竟甲被免除了1千元债务,还是乙又负担1千元的新债务(当然也存在其他债务数额的可能性)。在此,和解的潜在性意味着和解合同是关于债务数额的“风险交易”(Risikogeschäft),却不能知晓和解对初始法律关系的具体效力。因为,双方之所以选择和解来解决争议,就是放弃对真实法律关系的追求和调查,以和解后达成的法律关系作为基准,以追求争议的最终解决。
若双方当事人就债务关系本身是否存在发生争议,可以适用“全有全无”原则。〔55〕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21 ff.若一方当事人主张,根本没有发生债务关系(合同未订立、加害人未实施侵权行为)或者债务关系自始无效。按照另一方的主张,合同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早已发生。例如,甲向乙出卖某画一幅,作价5千元。订约之后,甲拒绝向乙交付该画,因为该画按照他的预期应为复制品,后来发现该画为原作,价值1.5万元。由此,甲对标的物的重要交易性质发生认识错误,主张撤销与乙达成的买卖合同。乙则主张买卖合同有效,甲应立即交付原画。由于双方当事人不愿负担专家鉴定费用,就原画达成1万元的买卖合同。本例中争议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发生,但甲主张撤销合同的依据在于该画是否为复制品。若为原作,则甲有权撤销买卖合同,使得原合同自始无效;即使双方达成和解合同,也只是重新订立价款为1万元的买卖合同(《德国民法典》第141条无效法律行为的认许Bestätigung)。由此,和解发生类似更新的效力:原债务消灭、新债务发生。假使该画为复制品,则甲无权撤销合同。和解只是使得原买卖合同的价款由5千元变为1万元,由此发生债的(内容)变更。
若双方当事人就权利归属发生争议,其所达成的和解合同具有移转争议权利(如物权、债权)的效力。假使和解合同确认权利的归属人事实上就是权利人,那么和解就不能发生争议权利的变动。如果争议权利事实上不属于该人,那么只有当他满足获得该权利的前提要件时,才能发生争议权利的变动。这是和解合同使得另一方负有义务,协助确认权利的归属人得到这一权利。因此,这一合同仅具有负担行为的效力,不能作用于享有争议权利的和解外第三方。该权利的处分还需要第三方权利人的协助,才可能得到实现。〔56〕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34 ff.
例如,若甲、乙就究竟谁享有对丙的债权存有争议,双方后通过和解一致认为,债权人为甲,但他须向乙支付1千元。甲究竟是否享有对丙的债权,对双方而言都是不确定的事实。双方都会估计到,倘若这一债权在事实上归属于乙,甲就需要将该债权让与给乙。但若该债权属于甲,和解无非只是确认债权归属,并未引起债权移转。除却之上的两种情况,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甲乙可能都不享有对丙的债权,而是第三人丁享有对丙的债权。即使甲、乙的和解合同被认为是债权让与约定,作为无权处分人的乙也无权让与丁对丙的债权。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以上和解合同作为债权让与约定,只是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只有等到第三人丁同意时,才能移转丁对丙的债权。上例中的争议标的物若为不动产或动产,其潜在可能性基本相同,只是动产或不动产的移转适用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原则上需要依照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才能发生物权的移转。〔57〕Vgl. 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36 ff.
以上的情形表明,和解可能发生变更、更新、认许、免除、新债设立、物权移转或债权移转等各种效力,也有可能发生其中几种效力的混合。和解如何作用于初始的法律关系,并无统一的公式可供适用。由于其不同的效力形式表现丰富,只能根据具体的和解类型,来分析其对初始法律关系所发生的效力。
四、和解效力
(一)确定效力
从和解合同的发展历程上看,早期人们将和解合同视为双务有偿合同。当时的和解之所以具有确定效力,在于双方互相免除对方的债务。现今的和解合同虽不再以实体法上的双务有偿作为出发点,但仍要求双方作出让步或牺牲,即使仅为形式上的让步也在所不问。只要双方都为让步,和解对象与真实法律关系不符的风险无论落在哪方头上,都是双方订立和解合同时所应预料到的,自然也不得反悔。
这样的确定效力,其实就是意思表示解释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发展之中,立法者将这一和解合同通常所包含的意思提炼到成文法,因此逐渐出现《普鲁士一般邦法》的45个条文,以及发展至《德国民法典》的1个条文(第779条)。所以,诉讼外和解在面临解释时,法律人需要根据不同的和解对象,基于当事人的利益衡量来探求真意,即他们是否要终局地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准任何一方反悔。这才是对和解合同的解释中最为棘手,也是最富争议的地方。
根据笔者妄断,在仅有一方让步的情况下,德国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的协议不能构成和解合同,可能是考虑到和解对象具有约束双方当事人的确定效力。具体言之,一旦双方达成和解合同,也就意味着和解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具有约束双方当事人的效力。任何一方都不得反悔,也不能认为和解合同由于不符合和解对象的真实性而拒绝履行和解。因为和解对象不符合真实性,本就是和解当事人必须承担的风险,否则和解将会失去解决争议的主要功能。仅有一方让步的情形中,若使得双方达成的协议发生约束双方的效力,则实际上导致让步的一方必须承受和解对象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风险,而另一方则可坐享和解对象确认效力的利益,这会有违和解合同作为风险行为的目的。
仅有一方让步的“和解协议”,其实质与单务合同并无二致。若使得该合同发生拘束义务人的确定效力,则未免对义务人过于严苛。在仅有一方给付义务的单务合同中,如赠与合同,义务人通常在给付之前享有反悔的权利。即使权利人可向义务人要求履行债务,但该请求权通常也不具有强制履行的效力。债权人吴梅若要主张初始的法律关系——债权加利息,最有可能的解读便是还款约定只是免除了债务人的利息债务。而且,这一免除的条件为债务人按照还款约定履行债务,其性质为附解除条件的免除。当债务人不按照约定还款时,解除条件生效使得利息债务复活。〔58〕Staudinger/Riebel, 2005, § 379 Rd. 142.只有这样,债权人吴梅才有可能要求履行原判决的债权。〔59〕本文只是旨在探讨和解的实体法效力。吴梅案究竟能否解读为附解除条件的免除,可能需要详细调查当事人的相关意思表示。仅从指导2号案例的事实来看,还不能得出明确的附解除条件的意思表示。
和解旨在排除不确定性,最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即便和解当事人就此发生错误,也不可行使撤销权。否则,解决争议的目的将由于和解合同的撤销而无法实现。尽管和解的确定效力在历史上具有深厚根源,但《德国民法典》仍未全盘接受,而是允许存在例外的情形。〔60〕Vgl. HKK/Hermann, 2013, § 779 Rn. 20.学说针对和解错误,采取区分和解对象(caput controversum)与和解基础(caput non controversum)的标准。前者即使发生错误,也不会发生撤销或无效的结果;后者的错误仍能引起效力瑕疵。
《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的和解无效规则只是针对和解基础,而非和解对象。考虑到后者引起了争议或不确定性,和解合同就争议对象所达成的法律确定效力不能因为嗣后撤销而消灭。〔61〕Vgl. HKK/Hermann, 2013, § 779 Rn. 20.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一个和解案件中,原告向被告主张因占领军当局命令、为清除渡口废墟所支出的费用,被告认为该费用不应由自己承担。双方于1947年4月17日达成和解合同:原告减免一小部分费用(由6155.52马克减少为5265.12马克),被告同意支付减免后的费用。嗣后,被告又以种种理由拒绝支付该费用,理由之一便是他对是否承担费用认识错误,由此根据《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而主张和解合同无效。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被告主张与理由,因为被告是否承担支付费用的义务本就是和解合同的对象,而非和解基础。〔62〕BGHZ 1, 57, 61.若允许当事人主张和解对象错误而和解无效,旨在解决争议和不确定性的和解合同也就失去价值。因此,即使和解对象发生错误,通常也不会影响和解合同的效力。
(二)双方动机错误
和解对象的确认效力也存在例外,如《德国民法典》第779条规定,当根据合同内容作为确认的和解基础的事实不符合现实,且在知道该事实时就不会发生争议,和解合同无效。这一规则与《德国民法典》第313条规定的交易基础障碍相比,在效果上具有特别法的特征。立法者之所以采取无效,而抛弃可撤销的立场,是为了避免撤销权人未在法定除斥期间行使撤销权,就会使得原本可撤销的合同最终有效。假使和解合同自始无效,则不会发生以上合同未撤销所导致的偶然性结果。同时,若适用错误规则,表意人将有权行使撤销权,由此必须承担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德国民法典》第122条)。这会导致双方错误的信
137赖利益赔偿显得过于偶然与不公正,因为谁先发现错误,谁就先行使撤销权,但撤销权人必须赔偿由此发生的信赖利益损失。〔63〕Vgl. HKK/Hermann, 2013, § 779 Rn. 20.
《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所要求作为当事人和解基础的事实必须是确定的。因此,将来情况的发展若同当事人的一致设想不符,不会导致和解合同无效,而且它也并非确认的和解事实。〔64〕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63.如果将来的事实也构成双方共同设想的基础,则可能适用嗣后的交易基础障碍,而不适用《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的和解规则。〔65〕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85.这一错误的设想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设想,而非单方的错误设想。否则,会导致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23条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规则。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错误必须是和解合同内容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当事人的想法必须成为和解合同的动机。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和解合同时,必须都根据错误设想而出发。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在于,当事人内在的想法必须转化为外部可辨认的动机。法律要求根据合同内容加以确认,并不要求人们在和解合同中提及作为基础的事实,而是需要内在的想法可能从外部得以识别,从和解合同的目的、意义与关联中可以被推断出来。〔66〕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66.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779条,这一共同的和解基础还必须能够排除争议,即双方当事人要是知道这一情况,就不会发生争议或不确定性。这一构成要件不能被误解为,当事人要是知道和解基础的实情,就不会订立和解合同,而是他们假使知道实情,就不会发生争执。在此,法律要求双方动机错误与争议或不确定性存在原因上的关联。〔67〕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67.比如,甲认为被乙所养的狗咬伤,要求后者赔偿500元,乙只愿意支付100元。两人互相让步,达成赔偿250元的和解合同。之后发现,其实是丙所养的狗咬伤甲,甲乙的和解合同由于作为其基础的事实不符合真实情况——不是乙的狗咬伤甲,而且双方若知晓丙所养的狗咬伤甲,就不会发生甲乙之间关于赔偿数额的争执,而是可能发生甲丙之间的争议。因此,这一和解合同由于适用《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而直接无效。〔68〕真实案例为甲乙就涂销债权人甲的抵押权所需要付出的数额达成和解合同,结果却发现该抵押权不属于甲,而是属于第三人丙。(RGZ 114, 120,121)
倘使当事人在和解中发生法律错误,可否援引《德国民法典》第779条主张无效?主流意见认为,该法第779条规定的事实,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为一般意义的事实,也包括法律关系。〔69〕BGH NJW 1959, 2109.但不是每个涉及确定的和解基础的法律错误都值得考虑,只有对订立和解合同具有很大影响的法律关系,即确定作为和解基础的法律关系才能被考虑。当事人单纯的法律错误不会影响到作为和解基础的确定事实,如当事人误认和解涉及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而非合同关系,这时并不构成《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的双方动机错误,也不会影响和解合同的效力。〔70〕BGH NJW 1961, 1460.
(三)其他的交易基础障碍
假设双方当事人订立和解合同后发现,其中一方其实对争议的法律关系享有真正的权利,即使以交易基础障碍的学说来看,也是无足轻重。因为交易基础障碍也不能作用于和解对象,它不能使得对某方当事人不利的和解得以改善,也不能使某方当事人得以摆脱和解的约束力。双方当事人既然订立和解合同,就必须承担相较于最初法律地位的不利风险,以至于即使他今后发现,和解在经济上使其承担利益损失,也不能援引交易基础障碍学说。就此而言,嗣后的交易基础障碍如同自始的交易障碍一样,都不适用于和解对象的错误,至多运用于和解基础的错误。〔71〕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77.
由于《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仅单独适用于交易基础障碍的部分领域〔72〕BGH 2000, 2497, 2498; Medicus, Schuldrecht I AT, 18. Aufl ., München 2008, S. 149.(自始的主观交易障碍),客观的交易基础障碍就被排除在外。最典型的便是《德国民法典》第313条规定的嗣后的客观交易基础障碍,例如,夫妻双方由于婚姻期间没有孩子而离婚,双方由此达成和解合同,女方放弃要求男方的扶养费补偿。但女方却在离婚后生下双方的孩子。〔73〕Vgl. BGH NJW 1985, 1835, 1836.其他常见情形还包括补偿和解、抚养费和解等。〔74〕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80 ff.双方当事人对于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倘使损害事件的严重迟发结果(Spätfolgen)显示,和解合同中达成的补偿数额与实际损害相距甚远,这就首先需要探究当事人在和解合同中的意思表示。实践中的补偿协议经常包括这样的条款,明确拒绝由于不可预见的迟发后果所引起的追加补偿。由于迟发结果已经被和解合同所规范,受害人不得不承担迟发结果所引起的风险。要是结果极其不公正,受害人也只能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主张对方当事人存在权利滥用的行为(见四)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
如果双方当事人仅在和解合同约定,基于此次事故发生的所有损害都获得补偿,若是发生迟发后果,如巨大的经济基础变化,以至于不能期待双方当事人继续遵守该合同。此时,当事人只能借助于嗣后的交易基础障碍以求救济,调整最初和解合同中约定的补偿数额或扶养费数额,以符合实际的损害。之所以排除适用《德国民法典》第779条,〔75〕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82-383.是因为双方当事人发生错误设想的事实是将来发生的情况,而不是订约时的情况。而且,即使双方订约时知道迟发后果,他们仍会发生争议,而且争议很有可能会加剧。〔76〕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80.所以,显著的经济变化既不能排除争议,又非当事人订立合同确定的事实。
即使是存在主观的交易基础障碍,这类障碍也必须能够排除争议,才能满足《德国民法典》第779条无效的要件。〔77〕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85.当事人共同的法律错误作为自始的主观交易基础障碍,有时则会排除适用《德国民法典》第779条,而适用第313条。因为当事人的法律错误针对将来情形或权利发展,当事人即使知道正确的法律,也会发生争执。例如,男女双方在离婚时,误以为法律会给离婚妇女以养老金,因此没有将离婚后的扶养费计入和解合同。事后,双方发现法律并非如他们当时设想的那样。此时,最佳的处理方案便是根据交易基础障碍理论,由法院假想他们若知道正确的法律,会如何调整离婚协议的补偿数额。〔78〕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81.另外,法律错误还会发生于事故和解中。例如,受害人与第一个加害人达成了赔偿数额极其低微的和解合同。因为他们认为,第二个加害人作为连带债务人也要承担责任,并且他在内部关系中要单独负担。后来,他们却发现,第二个“加害人”根本不必承担责任,而是第一个加害人单独负责。《德国民法典》第779条也不会在此适用,因为双方当事人即使知晓真实的法律状况,也会对赔偿数额发生争执。如果继续坚持和解合同的赔偿数额对于双方不可期待,交易基础障碍的理论就应得到适用。〔79〕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82.
(四)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
一般的无效要件也适用于和解合同。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1款规定,和解会因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或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3条规定由于欺诈被撤销。若当事人对和解对象缺少处分权,则和解合同也可能沦为无效。此外,假使作为和解对象的法律关系本身无效,和解合同本身也会无效。〔80〕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75.
和解中较为常见的是(单方)意思表示错误。不过,如同《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的双方动机错误一样,若意思表示错误涉及和解对象,表意人通常不能依据《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23条主张撤销,其理由主要是考虑到和解的目的与功能。因为和解是在不考虑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事实情况的条件下,通过重新建构法律关系而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当事人为解决争议,已通过和解承担由于错误所引发的和解对象与实际情形不一致的风险。所以,即使双方当事人就和解对象发生错误,也不得行使撤销权来恢复原来的法律关系。〔81〕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402; 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80.
若表意人已经考虑到其设想可能不正确或存有漏洞,那就不存在错误。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和解对象有时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和解当事人自己也不能确信,其关于和解对象的设想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既然他们同意以和解方式解决争议,就表示放弃探究有关和解对象真相的想法。由此,和解当事人就要接受自己设想不正确的结果。〔82〕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402.此外,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和解对象的错误多为不重要的动机错误。因为当事人有关和解的法律关系与和解合同正确性的相关想法,只是订立和解合同的动机,还未成为合同内容。这样的动机错误一般尚不足以引起合同撤销。
有关和解基础的错误,还是要借助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予以解决。和解基础范围内的错误始终只是动机错误,若单方和解当事人发生该错误,原则上并不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撤销权。〔83〕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403.只有当和解基础的错误作为内容错误时,和解合同才能被撤销。内容错误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一方当事人明知或估计到还有其他请求权时,却相信该请求权并未为其所表达的“全部放弃”所包括在内。该方当事人在和解合同中表示,其所有已知或未知的请求权均告消灭。他所指的是在这个争议中所有进入诉讼系属与未起诉的请求权,而不包括在其他平行诉讼中进入诉讼系属与未起诉的请求权。这时,内心意思与客观表示的涵义并不一致,由此符合内容错误的要求。〔84〕BGH NJW 1983, 2034, 2035.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每个当事人在和解合同使用“整体放弃”的文义,以此确信地放弃全部债权。倘使和解当事人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的请求权,那只是涉及不重要的动机错误。这一错误不是意思表示的内容,因为他确实想要全部放弃债权。由此所带来的风险,并非涉及撤销权所要纠正的误解,而是表意人由于轻率所发出的整体表示(Pauschalerklärung)所引起的风险。他本可通过仔细计算或精心草拟的和解合同条款,以避免这一风险。〔85〕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405.因此,此时的错误只是不重要的动机错误,表意人不得行使撤销权。
欺诈不同于错误,即使是表意人就和解对象发生欺诈,也能行使撤销权,使得和解合同溯及既往的无效。这里的关键在于,只要表意人在没有欺诈时,就不会与对方当事人订立和解合同,欺诈就成为撤销的原因。在此,需要具备欺诈与订立和解合同的关联。〔86〕BGH NJW-RR 1986, 1258, 1259.当前妻向前夫隐瞒其每月收入与其已经和其他男人同居的事实时,依然与前夫订立扶养补偿协议。虽然女方存在着欺诈行为,但前夫知道她即使得到每月300马克的扶养补偿与每周从劳动局得到的14.64马克,也不足以维持目前的生活,势必能猜想到女方还有其他收入。所以,前夫订立的扶养费支付协议并不依赖于前妻究竟具有多少收入,女方的欺诈行为与和解合同的订立并无因果关联,基于欺诈的撤销也并不成立。〔87〕BGH NJW-RR 1986, 1258, 1259.和解合同中的胁迫与欺诈类似,即使针对和解对象,受胁迫人也可行使撤销权。当然,胁迫行为与受胁迫人订立和解合同也需要满足因果关联的要求。〔88〕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n. 82.
权利滥用旨在修正有关危险承担范围内的严重错误(grober Missgriff),〔89〕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384.其仅在狭窄范围内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发挥着补充作用。权利滥用(《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作用不应被过高估计,只有《德国民法典》第779条、第313条都不能适用时,这一原则才能被适用。考虑到一般条款的适用可能侵入“约定必须遵守”为基础的私法自治范畴,适用权利滥用通常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在基于特殊情况的需要“避免不可忍受的、与公平正义完全不能相容的结果”时,才有适用的可能性。正如《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诚实信用原则那样,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式,而是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予以衡量。
五、履行迟延的救济
吴梅案的重点在于,假定双方达成的还款协议就是和解合同,如果债务人西城纸业发生履行迟延,如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债权人吴梅应如何寻求救济措施?具体言之,当事人能否从对己不利的和解合同中解脱,还是要求履行原来和解前的初始法律关系?此时,合同法履行障碍的一般规则能否适用?
和解合同的确定效力意味着原合同内容发生变更,债权人通常只能要求债务人履行和解后的法律关系。若由于被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原告则能依据合同法的法定解除规则,使得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便回复到和解前的实体法状况,势必会违背和解最终解决争议的目的。除非当事人在和解合同中早就约定了履行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意思自治的结果则应优先适用。若和解合同已经预先含有如下的失权条款:当债务人迟延履行约定给付时,和解合同就将失效(hinfällig)。该条款作为法律行为所附的解除条件,既可被明示地包含于合同文本之中,又可以采用合同补充解释的方式,根据合同的意义与目的来探究。〔90〕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414.
然而当事人并非法律专家,假使他们所起草的和解合同并不包含失权条款,合同解除权能否以默示约定的方式被推断得出?如果合同相对人在债务人迟延履行时还有选择的机会,决定相对人是否需要遵守约定,那么约定解除权将处于优先于失权条款的地位。因为和解合同是否失效,还要取决于相对人是否行使解除权,和解合同并不是自动失效。和解合同中究竟是否包含一个附解除的条件,取决于意思表示的解释。解释的结果通常会倾向于自动解除的结果。〔91〕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416.
当事人能否行使法定解除权,要根据和解合同的具体目的予以认定,重点在于当事人是否以默示方式排除法定解除权。考虑到和解旨在将有争议的、不确定的权利状况转变为稳定的、无争议的权利状况,若和解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还能主张其合同约定的义务要多于实际上负担的义务,或者主张其合同确定的权利要少于实际享有的权利,那将与和解合同的目的发生矛盾。就此而言,债务关系已由和解合同变更,当事人不允许回复到初始的权利状态。〔92〕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 1 Allgemeiner Teil, 14. Aufl age, München 1987, S. 96.原则上,法定解除权与和解目的不符,应当被排除。〔93〕Staudinger/Riebel, 2005, § 379 Rn. 143.
也有观点主张,应区分和解目的来判断法定解除权是否排除。如果和解合同仅在于确认最初的法律关系,那么双方当事人在这样的合同并不负有对待给付的义务,〔94〕参见贺剑:《诉讼外和解的实体法基础——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号》,载《法学》2013年第3期。《德国民法典》第323条以下的解除权也就失去适用余地。倘使当事人通过互相让步,负有对待给付的牵连性义务,法定解除权规则在不违背和解目的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空间。〔95〕Staudinger/Marburger, 2002, § 779 Rd. 52; Bork, Vergleich, Berlin 1988, S. 172, 173. 参见第172页脚注5文献。一旦债务人陷入履行迟延,债权人便有可能行使法定解除权。不过,德国法上的解除权行使,并不能直接导致处分行为无效,只是发生所谓恢复原状的债法义务。当事人已经实施的所有权移转、债权让与、债务免除等处分行为,并不因解除而无效。〔96〕Staudinger/Kaiser, 2004, § 346 Rd. 67.根据合同而受益的当事人负有义务,返还因受领处分而得到的利益。就此而言,债权人行使解除权的效果仅使当事人负有义务,恢复到初始法律关系,并不能如失效条款那样直接复原。
本案的关键在于,债权人吴梅在债务人西城纸业迟延履行且向其催告无果后,依然有要求履行原判决确定的权利。这一结果恰恰印证了双方订立的协议并非和解合同。因为和解旨在通过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解决争议,除非具有以上的特殊情况,和解合同依然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吴梅与西城纸业所订立的还款协议既不包括失权条款,又难以推断出默示的解除权,根据和解目的也不允许当事人回复到初始的法律关系。即使这一协议能够符合和解的构成要件,而且根据目的解释也有存在法定解除权可能,但仅有债权人一方关于免除利息的让步,债务人虽负有按约还款的义务,并不构成与免除利息相对应的对待给付义务,《德国民法典》第323条以下的双务合同解除权由此被排除。
六、结论
和解合同并未在我国成文法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实践中的和解却层出不穷,法律适用者面对形形色色的和解现象,陷入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也许就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的2号指导案例才应运而生。2号指导案例的结果似乎符合实体正义,吴梅得以主张原判决确认的债权也能符合人们的感情。但一旦法律人仔细地进行逻辑推演,则会发现和解的框架内总是难以容忍2号指导案例,因为它与实体法的和解合同理论完全背道而驰。如果和解当事人在和解之后还能继续主张初始的法律关系,和解究竟如何最终解决人们关于法律关系的争执?学界为了破解以上的理论难题,不免绞尽脑汁,尽力去搜寻和解的例外情形,但很少考虑和解合同最基础的构成要件。《德国民法典》对于和解合同虽只规定了第779条一个条文,但学界和判例经由民法理论的发展,早已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从德国法的经验来看,吴梅案不符合和解合同的构成要件。而且,这一协议若归入和解合同则会制造不必要的例外,徒生法律续造的事端。与其庸人自扰,不若将其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既能符合实体正义,也可省却违背目的与逻辑的论证,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