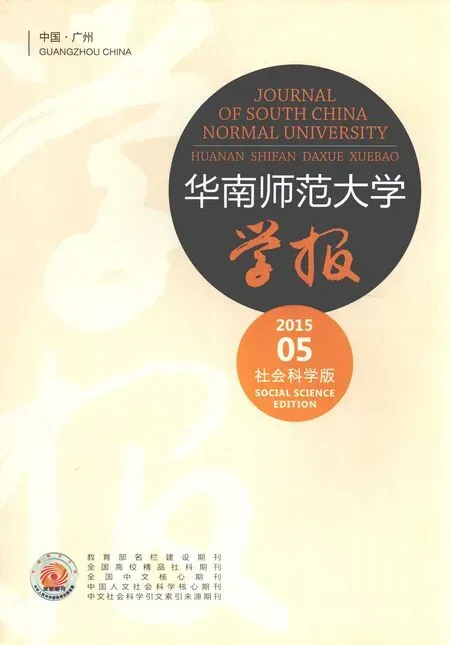学术救亡:抗战时期的魏晋六朝之学
2015-03-19徐国荣车孟杰
徐国荣, 车孟杰
学术救亡:抗战时期的魏晋六朝之学
徐国荣, 车孟杰
【摘要】抗战时期,对于魏晋六朝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学人们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体味到相似的“南渡”情怀,对魏晋六朝学术作“理解之同情”的探究,体现了他们关怀现实的爱国热忱。同时,对魏晋六朝文化中历来存在的“清谈误国论”的争议,无论是褒是贬,不同的研究角度均指向同一的文化关怀。而对于魏晋六朝文学文化中的精神解放与人格美的刻意强调与学术论证,尤其可见魏晋六朝之学在抗战时期作为特殊的传统学术资源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魏晋六朝之学学术资源文化意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强敌压境,家国危如累卵,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种形势下,抵御外族入侵、振兴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军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在各自不同的战线上共御外侮。处在学术战线的爱国学人们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学识,自觉地以学术活动加入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主题中,以学术振兴民族文化,从精神上鼓舞着国人救亡图存。这一时期,历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学人,都能理性地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此特殊时期自觉地从中找寻学术救国的资源话语,弘扬民族精神,为抗敌救亡发挥出巨大的精神效用。此期的魏晋六朝之学研究,因其特殊性,正是发挥这一效用的重要领域,其资源性意义尤为突出。在学术史上,魏晋六朝之学往往颇多争议,既是衰世、乱世,又极为自由解放;或谓其文浮华靡丽,或尊为“美文”时代;或斥其“清谈误国”,或赞其自然率真。同样的学术资源,往往可作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且皆能自圆其说。然而,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抗战时期,学人们不仅从中寻求关怀现实的学术资源,且几乎不作无谓的学术争论,而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择其“为我所用”而有利抗战救国的一面,使得魏晋六朝之学以纯学术的方式发挥出巨大的现实性的文化意义。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南渡”情怀与学者的现实关怀
魏晋六朝政权更迭频繁,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衰世之一,尤其是发生在西晋的永嘉之乱,外敌入侵中原,迫使汉族政权南徙的史事,更是给历代士人诸多的历史感喟。晚清张之洞曾作《哀六朝》诗,感叹“神州陆沉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张之洞:《张之洞诗文集》,第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并因时世而恨及其文其艺,史载其“论文最恶六朝,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无根柢,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拗涩字句强凑成篇者,必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糅假托包派者,亦然。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宇矣”。*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文学类》“张文襄恶六朝文字”条,第389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对六朝文学文化的判断基于清末的列强入侵而致“神州陆沉”而发,但抗战时期的中国与清末的历史形势又自不同。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历经着如同魏晋六朝的混乱苦痛,北方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到西南,更是类似于永嘉之乱时的晋人南渡。所以,当时流徙到西南的学人们常常不由自主地在他们的著述中使用了“南渡”一词。抗战初期,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的冯友兰在游览衡山时就写有一诗:“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8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面对着同样的家国沦丧、政权南迁的历史局面,遥想起过往永嘉之乱后的晋人南渡与靖康之变后的宋人南渡,不禁怀古伤今,借“南渡”来抒发“半壁江山太凄凉”的感慨。冯友兰还将其在抗战时期撰写的学术论文结集并命名为《南渡集》,突显出厚重的时代气息。而同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诗人吴宓,也把自己在抗战初期的诗歌集取名为《南渡集》,集中有《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吴宓:《吴宓诗集》,第32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当时赵仲邑写给吴宓的诗也说:“哀吟应使肝肠热,野哭遥连鼓角寒。最是相随南渡日,几人挥泪望长安。”*赵仲邑:《奉赠雨僧师》,见《吴宓诗集》,第340页。后来,日军步步紧逼,长沙日危,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战时大后方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徙途中经过桂林,朱自清作有《漓江绝句》,其一为:“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朱自清:《犹贤博弈斋诗钞·漓江绝句》,见《朱自清全集》,第五卷,第24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南渡”成为了当时能让知识分子产生共鸣的词语,他们哀叹战乱的沉痛神经也得以借此舒展,魏晋六朝文学与文化也由此进入了他们的学术研究视野。
1938年6月,面对着抗战不利的时局,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忧心忡忡地有诗云:“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第24,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蒙自南湖》)抗战一周年时,他又写道:“南朝一段兴亡影,江汉流哀永不磨”⑥陈寅恪:《陈寅恪集·诗集》,第24,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七月七日蒙自作》)对战时社会形势深有感触的陈寅恪,通过研究魏晋六朝文史之学以达到鉴古知今的目的。在对这种“不古不今之学”的研究过程中,他流露出了其浓烈的人文关怀精神。1940年7月,他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昔晋永嘉之乱,支愍度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此道人寄语愍度云,心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耳。无为遂负如来也。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在《世说新语·假谲》篇中,创立“心无义”的支愍度,是以曲学阿世的负面形象出现的。对此,陈寅恪在1933年《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通过考辨,为支愍度翻案,认为他创立“心无义”实有其事,但不一定是为了“救饥”而“负如来”。可在此时给陈垣所作的序文中,陈寅恪还是使用了《世说新语》的原意,表明了他们在战时共赴国难的共同信念。当时陈垣在北平沦陷区的辅仁大学任教,陈寅恪虽与其“南北相望”,却均“未树新义,以负如来”,各自坚守着学术良知与学人应有的气节,没有曲学阿世。对于这段学术公案,1938年在云南蒙自听过其课的陈氏弟子翁同文曾追忆道:“第一课,寅恪师开始讲授的,乃东晋初年从北方南渡的僧人支愍度所立‘心无义’。……我当时听讲以后,对于寅恪师当国难南渡西迁以后,开这‘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在第一课就先讲一个关涉东晋南渡的故事,殊觉不无巧合之处。后来查悉寅恪师早于1933年就已发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才发觉那并不是巧合,而是寅恪师面对当时南渡西迁局面下的特意安排,所以不循往例,将已经发表过论文的专题,再行讲授一次。寅恪师讲授这一课题的用意,到此已有较深一层的认识,后来获读全集中的诗文,尚有更深一层的发现。即寅恪师对于支愍度渡江故事意兴向来不浅,对于伧道人寄语,切莫妄立新义以负如来云云,尤其再三致意发挥。后而领会寅恪师当年南渡第一课讲授这一课题,也有忠于学术良心,不妄立新义而藉以曲学阿世或哗众取宠的深意。”*翁同文:《追念陈寅恪师》,见卞僧慧编:《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卷五,第190—19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这段话尤能体察陈氏的“南渡”情怀及其探究魏晋南北朝文史的文化用心。
同样,昆明《清华学报》1941年第13卷第1期刊载陈寅恪《读哀江南赋》(或谓此文实作于1939年),对于庾信此赋的深衷巨痛别有体会,以为“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34,2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联系到当时的形势,他对庾信“哀江南”情怀的体味,实即正是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②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34,23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当时,另一位任教于辅仁大学的学人余嘉锡,则在深感亡国之痛之余,借着陶渊明《桃花源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语,自题其书斋名为“不知魏晋堂”,以表达“人心思汉”之意。*周祖谟、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见《余嘉锡文史论集》,第678页,岳麓书社1997年版。同时,他还通过笺疏《世说新语》,品评魏晋六朝之人事,寄托自己的愤慨之情与拳拳爱国之心。如在《德行》篇“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条中,余嘉锡说:“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5,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对虚矫伪饰和叛国趋荣的行为旁敲侧击,为的是借魏晋之人事来警醒身陷日寇铁爪下的国人,不可屈节做亡国之奴。正如其婿周祖谟所指出的,该书经始于1937年,“余时国难日深,民族存亡,危如累卵,令人愤闷难平。七月七日卢沟桥事迹作,北平沦陷,作者不得南旋,书后有题记称:‘读之一过,深有感于永嘉之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他日重读,回思在莒,不知其欣戚为何如也。’”*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第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而“作者注此书时,正当国家多难,剥久未复之际,既‘有感于永嘉之事’,则于魏晋风习之浇薄,赏誉之不当,不能不有所议论,用意在于砥砺士节,明辨是非。”⑥周祖谟:《世说新语笺疏·前言》,第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这里,他对永嘉之乱的感怀,正是“以晋人永嘉南渡类比抗战时北方沦陷”*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第8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然而,与西晋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晋室永嘉南渡不同的是,抗战时期的“南渡”,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这不仅意味着国土的沦丧,而且华夏文明与民族文化也会受到灭顶之灾,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所以,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借学术研究之机而阐发的时代感怀,是利用魏晋之学的学术资源以砥砺国人坚守民族气节而奋起抗敌,同时也流露出了战时学人们的苦闷悲愤心情。诚如牟润孙所说:“所有《笺疏》中抨击反礼教思想,涉及亡国、亡民族的,都因为季老身处沦陷之区,触目惊心产生的愤慨言论。必须这样去知人论世,始能正确地理解季老在抗战时的心情。”*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见《海遗丛稿》二编,第227—22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余先生身处北方之沦陷区,尚常有此“南渡”情怀,而真正“南渡”和流离失所的学人,对此更是感同身受。钱穆在1945年撰文《魏晋玄学和南渡清谈》,其实材料并无新的发现,观点也难说深刻,只是不满“南渡”以来东晋清谈家之空谈与矫情。而对历史上魏晋名士之“清谈误国”的争议则更加突显了魏晋六朝之学在此特殊时期的资源性意义。
二、“清谈误国论”的现代阐释
清谈误国之论,古来有之,实则东晋人自己早有此论,甚至将当时放达之风归罪于何晏、王弼,认为他们的罪过“深于桀纣”。不同的历史时期,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作不同的解释。明末清初顾炎武于易代之际深有感触地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见《日知录校注》,第72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此说影响甚大,《世说新语·政事》篇第八则中,山涛劝说嵇绍出仕,并陷其于不义之境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就引了上述之言,然后评曰:“顾氏之言,可谓痛切。使在今日有风教之责者,得其说而讲明之,尤救时之良药也。”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5,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正是有感于“风教之责”与“救时之良药”,他在笺疏此书时,考证确审,论断精到,却也不失时机地对空言误国之辈加以讥诃,如《世说新语·任诞》第五三则曰:“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他加案语说:“《赏誉篇》云:‘王恭有清辞简旨,而读书少。’此言不必须奇才,但读《离骚》,皆所以自饰其短也。恭之败,正坐不读书。故虽有忧国之心,而卒为祸国之首,由其不学无术也。自恭有此说,而世之轻薄少年,略识之无,附庸风雅者,皆高自位置,纷纷自称名士。政使此辈车载斗量,亦复何益于天下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63页。其忧时忧国之心昭然可见。
实际上,历史上虽有如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那样的平情之论,然大多还是认同“清谈误国”之论。而就学理来说,刘师培于1907年撰写的《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章太炎于1910发表的《五朝学》,已彻底地为此翻案。章氏甚至说:“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五朝学》,见《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76—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认为东晋南朝风俗优良、士人讲究节操,正是玄学滋养的结果。他们处于清民时期,所论虽有现实目的,但可自圆其说,以理服人。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贺昌群则有感于时世,通过研究魏晋清谈思想“以发潜德之幽光”,撰成《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他在该书序言里说:“观近代政治文化尚权竞力之趋势,殆已积重难返,故世变日亟,战乱方兴。兹编之作,或正郭子玄所谓‘有不得已而后起者’在也。”*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1,11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抱有着极强的现实责任感与现实目的。对于清谈本身,他认为:“魏晋清谈之本旨,岂徒游戏玄虚离人生之实际而不切于事情也哉,乃此一段思想为世所掩没而蒙不白之羞者,垂一千七百年,悲夫。”④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第1,113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他认为,魏晋清谈作为一种在混乱时代产生的特定学术思想,是对人生社会意义的发现与探索,而非仅仅是空谈之言。因此,他在魏晋清谈思想中发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价值以及抗战学术视野中的资源性意义。正如贺昌群后来讲述该书的主旨时所说的:“大抵大一统之世,承平之日多,民康物阜,文化思想易于平稳笃实;衰乱之代,荣辱无常,死生如幻,故思之深痛而虑之切迫,于是对宇宙之始终,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义,人我之关系,心物之离合,哀乐之情感,皆成当前之问题,而思有以解决之,以为安身立命之道,此本篇论述魏晋清谈所欲究其内容者也。”*贺昌群:《贺昌群史学论著选》,第1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可见,他对魏晋清谈内容的探讨,同样也是对抗战时期衰乱时势人生问题的一个借题反思。
同样,身困于上海“孤岛”时期的刘大杰,也将研究目光集中于魏晋时期的思想学术。对于“清谈误国”的观点,他也持反对意见。同时,在魏晋时代产生的将经学玄学化的玄言清谈中,刘大杰发现了其进步意义之处。他认为,将经学玄学化的清谈,使老庄思想得以复归到学术讨论的轨道上,打破了汉代儒学一统学术界的束缚,从而活跃了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思想。因此,他认为魏晋清谈“是一种进步,一种思想的自由”*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第28,36,38,10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而非误国、亡国的根源。
刘大杰对清谈中的自由思想的肯定,是有其人文关怀意义的。魏晋时期,正是思想的自由,才使得“学术界产生了怀疑的精神,辩论的风气”⑦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第28,36,38,10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从而促进了魏晋学术的成熟发展。在提到魏晋人对宇宙本体和人生意义等问题的看法时,刘大杰说:“这些问题,在当日学术界,都是使青年们怀疑而苦闷着的问题。正如今日的唯物唯心观念论辩证法之类相像。怀疑的提出来,有的口辩,有的著书,你辩我驳,学术界因此便有了生气。”⑧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第28,36,38,10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刘大杰对抗战时期学术界“你辩我驳”的自由争鸣状态,是持肯定态度的。正是由于学人们在抗战时期能够自由地争鸣,才形成了当时繁荣的学术局面,并增强了“学术救国”的力量。
当学术思想得以自由表达,个人的自我独立意识也就会随之明确,在主观上也就力求突破传统僵化思想的束缚,追求自我独创而获得全新的思想价值。刘大杰看到,思想自由活跃的魏晋学术界,“反对人生伦理化的违反本性,而要求那种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追求的是“真实自由的生活。”⑨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第28,36,38,10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所以魏晋人用老庄学说来推翻汉儒腐朽过时学术而形成的魏晋玄学,“在学理上虽是复古的,但在态度上,却是革命的”⑩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第28,36,38,103,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革命的态度,表现出的是魏晋学者对学术独立的自觉追求,是他们个体意识觉醒后的反映。与之相似的是,处在抗战时期的学人们也都以自身的努力共同促进学术的独立发展,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与继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魏晋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不仅实现了他们追求学术独立的夙愿,也让研究者从中寻获到了思想独立和人格独立的学术资源,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学者们还从魏晋六朝之学中找到了民族精神和自由解放的学术资源。多少年之后,刘大杰的弟子林东海在论析《魏晋思想论》的写作时说到:“自‘八·一三’事变之后,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民族救亡运动蓬勃展开,民族精神空前高涨。困于沪上因失业而著书的刘先生,其民族精神,自然而然地从笔底流露出来。”*林东海:《〈魏晋思想论〉导读》,见《魏晋思想论》附录,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并举例说明他“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之‘嗜杀好战’,表现出凛然的气节和精神”。②林东海:《〈魏晋思想论〉导读》,见《魏晋思想论》附录,第16,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本来就是学者所应坚守的学术原则,也是魏晋六朝之学中的应有之义,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与现实的客观需要相契合,于是,对魏晋六朝之学中精神解放与人格美的因素,也就成了抗战时期学人们所乐于开拓与强调的学术资源。
三、精神解放与人格美:六朝苦难诗学的美学意义
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所指出的,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267,281,28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魏晋人得到了“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他们对前人的经学权威由怀疑而趋向否定,并最终挣脱神学谶纬的禁锢,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展现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人格美。这种人格美可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突出的体现便是魏晋人对乡愿的极力抗拒。乡愿(或作“乡原”),是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礼教统治下形成的虚伪道德和平庸人格精神。而热爱美、热爱自然、性情率真、追求精神解放和独立自由的魏晋人,则“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④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267,281,28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从而形成了一种“洋溢着生命,神情超迈,举止历落,态度恢廓,胸襟潇洒”⑤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267,281,28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的人格美。
宗白华对魏晋人身上这种带着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格美是饱含赞美之情的,而这份赞美之情实则蕴含着他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目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原刊于1941年1月《星期评论》第10期,后来作者又将其修订,发表于《时事新报》1941年4月28日《学灯》第126期上,并在此文前面的“作者识”中说:“魏晋六朝的中国,史书上向来处于劣势地位。鄙人此论希望给予一新的评价。秦汉以来,一种广泛的‘乡愿主义’支配着中国精神和文坛已两千年。这次抗战中所表现的伟大热情和英雄主义,当能替民族灵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发扬人格底真解放,真道德,以启发民众创造的心灵,朴俭的感情,建立深厚高阔、强健自由的生活,是这篇小文的用意。环视全世界,只有抗战中的中国民族精神是自由而美的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编者注,见《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267页。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宗白华在探讨魏晋美学的过程中不忘融入个人与时代之思,希望以魏晋人的人格美激励抗战中的人心,在抗战中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性情、真道德。他借着魏晋人的狂狷个性,结合当下中国的抗战语境,批判了中国数千年来的“乡愿主义”之余,谱写了一曲精彩的“自由而美”的、追求精神解放的民族灵魂之歌。正是怀着这样的现实目的与强烈的人文关怀,几天后的1941年5月5日《学灯》第127期又续登此文。对于魏晋人这种“人格的唯美主义”的高度礼赞,有论者认为:“宗白华正是用‘唯美主义’的目光来识鉴魏晋思想和魏晋人格的,这是美学家的长处,却是思想家哲学家的短处。”*李建中、马良怀:《本世纪魏晋思想研究的两次高潮》,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1期。时过境迁,以今天纯学术的眼光来看,对这种“人格的唯美主义”评论的分寸自可见仁见智。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对作者作“理解之同情”,了解其炽热的文化关怀,则可明白这未必是“思想家哲学家的短处”,或许正是其长处。
时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冯友兰,同样对魏晋人格美投以热切的学术关注。1943年,冯友兰撰有《论风流》一文,该文是其在西南联大的一场学术讲演之作,后来收在《南渡集》里,是冯友兰在抗战时的经典学术之作。*冯宗璞:《冯友兰先生与西南联大》,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第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文开篇就说:“风流是一种所谓人格美。”*冯友兰:《论风流》,见《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09,3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从《世说新语》中的真名士所表现出的言行举止中,冯友兰看到了其蕴含的真风流,指出“是真名士自风流”⑩冯友兰:《论风流》,见《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09,31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并将构成真风流的条件归纳为四点,即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而这四点也正是魏晋人身上的人格美的最好体现。魏晋人的人格美,最能体现在深情之中,冯友兰认为:“真正风流底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①冯友兰:《论风流》,见《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310页。这里的“有情而无我”,正是一种注重人生、社会、宇宙的感情,是个人私情的升华。冯友兰在随后所写的另一篇论文《论感情》中指出:“有情有我,是为个人而有底喜怒哀乐,是有私底。有情无我,是为国家社会,为正谊,为人道,而有底喜怒哀乐,是为公底。前者普通谓之为情,后者普通谓之忠爱或义愤。”②冯友兰:《论感情》,见《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431页。对魏晋真名士的“有情而无我”的人格美发现,再到对“为国家社会,为正谊,为人道”之感情的阐述,可以说是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学术研究中的一种人文关怀的介入。面对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不义侵略,在学术研究领域奋战的冯友兰等学者心怀家国民族大义,将魏晋人的精神解放与真性情诉诸于文字,从传统学术中吸取资源,以激起国人“忠爱”“义愤”这些共同抗敌救国的民族感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的研究有着强烈的现实目的,但始终不以曲解文义为手段,也始终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方式。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发挥魏晋六朝文学文化的学术资源的作用与意义。
处在抗战时代中的学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以抗敌救国,而且也以自身的人格品行诠释着中华民族内在的真性情、真道德。如朱自清就“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的收买和拉拢,躲开了国民党在昆明的‘司令’‘要人’的拜访,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在那些趋炎附势、巴结官场的文人面前,在那些对抗战悲观失望的颓废文人面前,高洁地站立着”③陈竹隐:《追忆朱自清》,见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第66页。。这不啻为魏晋真名士的人格美在动乱的抗战年代的最好写照。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八年抗战岁月里,国人于炮火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生活物质也极度的匮乏,在这种环境里人心是苦闷且压抑的。而这样的情形正是千年前魏晋六朝那段时期的隔代嗣响。因此,人们也就将更多的目光投向魏晋六朝文学文化,从中找寻各自所需的学术资源,将其与现实互相比照,以契合着当下民族抗战的时代主题,在抚慰苦闷压抑的人心之余唤醒国人崇高的民族精神。正如宗白华对魏晋六朝文学艺术的关注,为的是让国人“从中国过去一个同样混乱、同样黑暗的时代中,了解人们如何追求光明,追寻美,以救济和建立他们的精神生活,化苦闷而为创造,培养壮阔的精神人格。”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见《宗白华全集》,第二卷,第286页。而范宁回忆起西南联大的往事时,也提到共学于联大的学子们“聚在一起时大都谈论魏晋诗文和文人的生活。”⑤范宁:《昭琛二三事》,见《范宁古典文学研究文集》,第662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悲凉,到“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阮籍《咏怀诗》)的孤哀,再到“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庾信《哀江南赋序》)的凄艳,相似的时代环境,同样的悲苦心境,甚至相似而更加严峻的民族文化传承之端绪,抗战时期的学人与魏晋六朝的文人获得了历史的共鸣。当然,美仑美奂的六朝“美文”也是他们乐于谈论与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正是魏晋六朝文学文化自身内含着的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蕴,才使其成为抗战时期学术研究中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
1945年,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晋人永嘉南渡偏安一隅的历史,历经宋人南渡、明人南渡之后不再重演。以古观今,冯友兰感慨道:“稽之国史,历代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吾辈亲历南渡,重返中原。其荷天之休,可谓前无古人也已。”⑥冯友兰:《南渡集·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239页。中华大地沦丧之山河得以光复,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又一次展现强大的生命力,并在学术研究中焕发着厚重的民族精神力量。而作为抗战时期学术研究的一部分,魏晋六朝文学文化作为传统的学术资源,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鼓舞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士气,显现出其在战乱时代所特有的人文关怀意义。
【责任编辑:赵小华】
作者简介:(徐国荣,安徽庐江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车孟杰,广东茂名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5)05-0168-06
【收稿日期】2015-04-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学术史意义下的六朝文学研究”(14BZW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