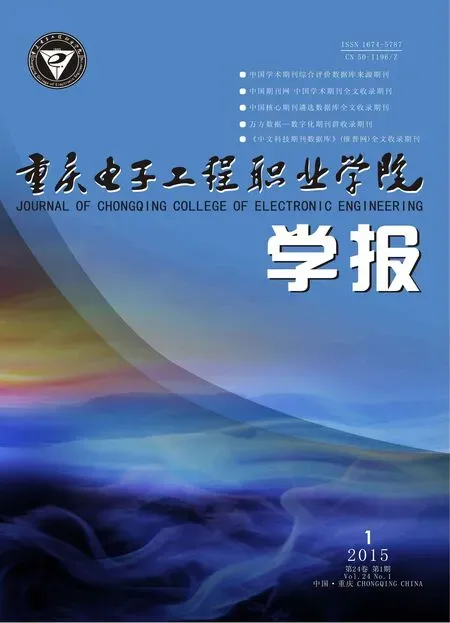张爱玲与张小娴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比较
2015-03-19谭冰雪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
谭冰雪(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400031)
张爱玲与张小娴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比较
谭冰雪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400031)
张爱玲和张小娴是不同时期的女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显露出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关注。但不同的个人经历、审美取向以及时代背景造就了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意识也各不相同。对此,本文通过她们几部代表作品展开比较和分析。
张爱玲;张小娴;女性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包括对自己心理倾向、个性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的认识与评价。它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我意识能使生命主体把自身领悟为一种此一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把自己领悟为一个不同于并且独立于任何他者的不可替代的、完整的存在物。”[1]
女性自我意识是自我意识中的一个细分,它是女性所特有的,是女性对自我的全面认识。它包括女性关于自身思想、情感、心理状态、自我价值、能力特征、行为方式、自我控制、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全部意识和思考。
张爱玲和张小娴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关注。由于两人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她们笔下的女性角色在对待自我的情感问题、婚姻生活以及两性关系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女性自我意识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
1 个体经历影响下自我意识的觉醒
作家的个体意识、思想和自我情感是作家个体经历的集中反映,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或多或少把个人的经历隐射在作品中。女作家的个体经历是创作主体意识的一种呈现,也可以说是创作的一种基础,将创作者自身的经验融入到作品中,依靠这种经验使得文本更具有亲和力和真实感,这是读者与作家产生共鸣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所描绘的聂家公馆很明显是来源于上海张爱玲与父亲一起居住时的家,聂传庆的父亲和后母也是现实生活中张爱玲的父亲与后母的写照。散文《私语》用了大段的文字来回忆她被父亲禁闭的黑暗时日,长篇小说《十八春》则把这段经历还原在了曼桢身上。她被父亲禁闭时恨不得全家都死,她也愿意赔进去;死了也许是埋在园子里;睡梦里都听见铁门打开声;还有那条用煤屑铺成的路……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她给了曼桢[2]。
张小娴的成名作《面包树上的女人》一直被读者视作张小娴的情感自诉。2011年10月张小娴做客“杨澜访谈录”时说:“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虚构的创作,没有完全一样的故事,完全一样的场景。但是里面有一些情节,一些场面是我自己真的去经历过。创作的时候,有时也可能已经分不清小说跟现实之间的分野。”[3]小说里面女主角程韵和林方文是大学同学,性格内向的林方文并没引起程韵过多的关注,当她意外发现林方文竟然是自己喜欢已久的词曲家林放,于是暗生情愫,两人坠入爱河。但是林方文始终放不下前女友(画家费安娜),这成了两人关系中的一个隐患,最后林方文还是跟前女友重修于好。故事情节虽然比较老旧,但是这其中包含了张小娴的朋友、同学以及她自己的亲身经历。1985年,张小娴考入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主修媒体学,不久便结识了同学王孜,而他正是歌曲《金背斑鸿》的作词作曲人,张小娴当时非常喜欢这首歌。从此,情窦初开的张小娴对王孜多了一份仰慕之情,而王孜则被她的才女气质所吸引,两人很快坠入爱河。两人恋爱后,王孜又认识了一个比他年长但是更具社会地位的女画家,因此背叛了张小娴。张小娴将此真实的女性经验创作为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这部小说因有了张小娴的个体经历而变得真实、感人。“女性作家是自己思维和行为的主体,她有着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自省意识,同时由于女性观照和介入,她们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表现出一种更为女性化的同情、理解和宽容,更多一份女性的细致和关怀”[4]。
2 社会环境影响下的自我意识
社会环境是时代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赋予作家的不同于其他时代作家的个性体验。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无可避免地会在文本中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特征。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剖析女人的婚姻处境时,即认为传统女人除了婚姻之外,并没有其他可以开展的空间。“在婚姻中的女性成了没有自我意愿、自我决策权和自我行为体现的物化了的附属,成了男人所欣赏、玩弄的被占有的物,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和自觉,只能是攀附在男人这种大树上的青藤”[2]。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表现了时代更迭交替之际女性生存的困境。由于中国长久以来的宗法父权思想禁锢着女性的成长空间,加之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权,她们始终无法摆脱命运的枷锁,想要获得人格上的自主就注定要走一条艰难的道路。
张爱玲的作品中关于女人依附于男人的话题以各种各样的模式在进行演绎。例如《等》中,奚太太不仅对丈夫在外养小老婆的事情只能忍气吞声,同时还要担心自己年老色衰,最后只能在幽怨中等待丈夫回心转意。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孟烟鹂在家庭中的地位本就卑微,还要容忍佟振保带着妓女回家拿钱,但又对丈夫无可奈何。从《倾城之恋》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想要占得一席之位实在是可望不可及,这就让“结婚”成为了一种“比较有利的事业”。与此同时,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自主权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战火纷飞的香港虽然成全了白流苏,但张爱玲的笔下依然流露出对女性出走的讽刺,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仍旧没有改变。
对于现代女性而言,当她们以“娜拉”的形象走出封建父权或夫权的控制之后,她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进与退更多地表现出无力和绝望。“女性作家强烈的生命意识使她们在描述现代女性面对婚姻‘围城’时很自然地构设出现代女性在事业与家庭、婚姻与爱情、自我与他人、灵与肉之间的心理困惑”[4]。
张小娴的作品中,大多是自我独立意识较强的女性角色。她们具有不输于男性的思考力和个人能力。但由于女人天性中对于爱和安全感的极度渴望,又很难摆脱对男性的依赖。《面包树三步曲》讲诉的就是女性摆脱依附后自我意识逐步成长的过程。现代女性由于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独立,她们不再像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那样完全依附于男人与家庭,但对爱情的过度看重,致使“爱情”成了女性的精神依赖品。
《面包树上的女人》中女主角程韵把爱情视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将一切都寄予男人和爱情之中。6年后,张小娴创作了《面包树出走了》,小说里男性的自私让女性承受了爱情的沉痛,女主角开始思考自我存在的意义。到了《流浪的面包树》,程韵开始展现出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在事业上丝毫不逊于男性,而且更加懂得享受生活中除爱情以外的其它乐趣。当她发现林方文用“假死”来欺骗她时,她用宽容成全了对方。最后她选择用“流浪”来疗伤,这无疑是成长后的女性精神因爱受伤后的一种拒绝。
张爱玲的白流苏依附于婚姻,张小娴的程韵则依赖于爱情。然而,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经济实力而有着不同的命运。这表明,随着时代语境的不断变化,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进步和成长。
3 病态身体审视下的自我意识
一直以来女性的身体在男性作家的创作中作为一种艺术空间想象下欲望化的存爱对象。而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评价与言说,则是女性在精神和生命意识方面的双重觉醒。如涉及女性身体的疾病,有论者指出这是“表达了一种人们对事物不满的感觉”,“疾病是通过身体说话的个人意志的表现,它是展示内心世界的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形式。”①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为了揭示女性精神上的焦虑与压抑,表现女性受迫害的时代现状,故多将女性身体进行丑怪化的描写。在《花凋》中,张爱玲着重突出了川嫦生前死后容貌、身体上的差异,以此反讽她“美丽的悲哀”:女儿的身体在死后变得真实美丽[5]。川嫦生前卧病在床,全家人以保护她为借口,剥夺她的自由,又不给她治疗,她对这个世界感到深深的绝望,这充分反映出女性遭受迫害的社会现实。“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一个拖累”,在自责的表象下,隐藏着女性的身体是父权文化压抑的场所②。当她拖着病躯走在大街上,从旁人异样的眼光中,她窥探到了自己丑怪的身体——冷而白的大蜘蛛。这样的丑怪经验令她终于体会到了虚假的悲哀和真实的悲剧之间的真相。川嫦的丑怪反映出女性的焦虑、压抑和受迫害的长期性与苦痛性。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不少作家笔下女性身体则成为主体面对世界,以主体行动的力量表达生命本质的自由。身体不再是屏障,而是生命与灵魂的窗口。张小娴《面包树出走了》的女主角葛米儿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即使她要忍受左脑里恶性肿瘤对她的病痛折磨,但在生活中也依然保持乐观、积极的状态。“她站在那里,戴着我(程韵)给她挑的那个齐肩弯曲假发,身上衣服松松垮垮,看上去比从前小了一圈。她脸上涂了粉,除了有点苍白,看来并不像病人。”[7]同样是面临死亡的年轻女性,葛米儿与川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川嫦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压抑的环境中,性格悲观、焦虑,因而“丑怪”;而葛米儿一直是一个比较开朗、乐观的形象,即使面临死亡,她所想到的是极力维护自己的形象,继续做好自己的事业。这样的行为和思想体现了现代女性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自我关怀:女性身体是女性生命个体的权利与快乐的来源,而不是自我的“怪物”和“禁忌”。
4 以“出走”为抗争的自我意识
1879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创作了其不朽名作《玩偶之家》。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玩偶之家》列于其中,娜拉形象迅速在中国形成“娜拉热”。《玩偶之家》塑造了一位所谓追求个性解放的勇敢女性——娜拉。娜拉出走是《玩偶之家》的高潮,也是一系列矛盾冲突发展的结果。娜拉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在这个家里她与丈夫并没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剧中最后的关门声震撼了19世纪的欧洲,其余波也在20世纪的中国引起了回响,娜拉这一新女性形象也从此移植于中国土壤上。受其影响,一大批具有新的价值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现代新女性,以全新的姿态纷纷从中国作家的笔下走出来,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鲁迅的《伤逝》等。
女性在爱情和婚姻中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女性常常会因为性别而遭遇困境,在与男性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对此张爱玲选择用出走作为逃离困境的手段。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从活动场所到婚姻状况,都处于“出走—回归”的模式中。流苏反复往返上海与香港之间,出而复入的经历中,每一次“出城”,都是又一次的“入城”,每一次的胜利(或失败)都隐伏着下一次的失败(或胜利)。出与入、成与败、悲与喜,如此这般地既叠合又歧出、既对映又互涉。这就如同她原已离开了婚姻的牢笼,却又再一次进入婚姻的“围城”一样。
张小娴《面包树三步曲》中的程韵也有“出走”的经历,却有着与白流苏完全不同的结局。第一部《面包树上的女人》中,程韵与林方文在一起之后发现林方文仍旧放不下前女友,一气之下从他家搬了出来,那是她第一次出走。但友人的意外死亡使两人都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都产生了要珍惜眼前人,珍惜爱情的念头,于是女主角又回到了林身边。第二部《出走的面包树》里,理想化的爱情在现实中遭到考验,第三者的插足让程韵在爱情这条路上再次出走。第三部《流浪的面包树》中,女主角有了自己的事业,思想上也逐渐成长,最后用自己的遗憾成全了对方,至此,他们的爱情之路再也没有回归了。女主角选择用“流浪”来逃离眼前的困境,这是她能为自己想到的唯一出路。从程韵反复出走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现代女性在精神上的成长,而这种成长往往伴随着苦痛的生命体验。
综上所述,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总是一些被压抑、受迫害的形象,她们都是一群在男权宗法社会里依附于男人的女性,尽管有自我意识的苏醒,但因受制于主客观条件,她们始终无法真正成为拥有完全独立自我意识的女性,依然摆脱不了附庸者的角色。而半个世纪之后的张小娴用她独特的女性话语,勾画出从传统父权或夫权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经济独立、事业成功、勇敢追求爱情权利的现代女性群像。从她们的精神成长和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生存中的嬗变与成长。
注释:
①转引自刘文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身体意象解读》,《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2期。
② 林幸谦 《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第69页。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四版[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冯祖贻.百年家族 张爱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3]杨澜访谈录20111015主角叫张小娴的爱情故事[EB/OL].http://v.youku.com/v_show/ id_XMzEzMzMyMDQ0.html,2014-08-20.
[4]刘思谦.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5]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杨泽.阅读张爱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张小娴.面包树三部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闫桂萍
Comparison of th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Works of Zhang Eileen and Zhang Xiaoxian
TAN Bingxu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1,China)
Zhang Eileen and Zhang Xiaoxian are female writers in different times,and the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is concerned in their works.But each consciousness is not identical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personal experience,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background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they created.All of these will be discussed through their representative works.
Zhang Eileen;Zhang Xiaoxian;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I206.6
A
1674-5787(2015)01-0068-04
10.13887/j.cnki.jccee.2015(1).20
2014-11-10
谭冰雪(1989—),女,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