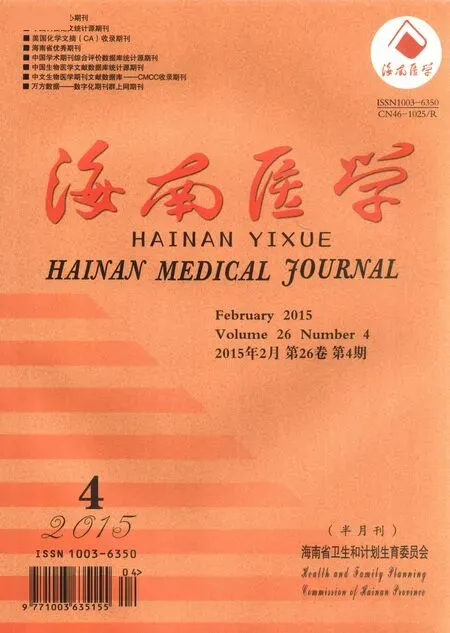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研究现状
2015-03-19王家艳黄宏敏
王家艳,康 宁,黄宏敏
(1.海南省中医院脑病科,海南 海口 570203;2.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 100029)
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研究现状
王家艳1,康 宁2,黄宏敏1
(1.海南省中医院脑病科,海南 海口 570203;2.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 100029)
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是临床常见急危重症,相关的中医药研究不断,本文通过查阅古籍,阅读近十年临床研究文献百余篇,将主要治疗方法及成果进行总结。在治疗上,经验传承加理论创新,多有不错的疗效;在研究中,引入了先进的研究方法,提高了科研质量。目前还存在一定问题,如研究结果的循证医学证据质量较低,在将来的临床研究中需要更严谨的设计及规范统一的平台。
出血性中风;急性期;中医药;治疗;综述
中风一病源于《内经》,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代医家将出血性中风和缺血性中风统称为中风,近代三张(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认为中风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肝阳化风,气血并逆,直冲犯脑所致,比较接近现代医学对中风病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CT出现简便明确分清出血性与缺血性中风。出血性中风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急性期的有效救治能大大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故急性期的治疗一直是关注的焦点,现就近十年来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中医药治疗文献进行整理做一综述。
1 治则治法
1.1 化痰通腑法 中风病“腑实”学说始于金元,张元素首创三化汤(厚朴、大黄、枳实、羌活)把通腑法运用于中风病治疗,《丹溪心法》中提出“痰热生风”及“治痰为先”。20世纪80年代,在大量实践及科学证据基础上,王永炎等[1]院士首先提出了化痰通腑法治疗中风病痰热腑实证,创立了代表方剂星蒌承气汤,并进行了一系列临床研究。现代医学也证实,通里攻下中药可能改善血液流变性,增加脑动脉血流量,降低血管压力、降低颅内压等作用[2]。钱艳[3]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用星蒌承气汤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痰热腑实型30例,并与西医传统治疗方法对照,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临床疗效显著(P<0.05),提示化痰通腑法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具有重要意义。朱青霞等[4]选取了早期出血性中风患者98例,随机将其分为两组,两组给予同等的脱水降颅压、控制血压、抗感染等基础治疗,治疗组加用中药汤剂鼻饲或灌肠,以清热化痰通腑为立法,随症加减,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5%,治疗组疗效显著。赵虎成等[5]认为出血性中风急性期多因风火痰壅实于内,燥结中焦阳明,升清降浊失司,多有燥热内结可下之证,对24 h以内入院的60例脑出血患者进行临床观察,这些患者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应用通腑降气法,结果总有效率为87%。在理论指导、临床研究及多年临床应用经验的基础上,目前化痰通腑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出血性中风病急性期的治疗中,其有效性得到认可。但化痰通腑法药效刚猛,需严格把握其适应证,否则适得其反。邹忆怀教授[6]经过多年临床研究和应用实践后指出,化痰通腑法只可以迅速去除浊邪,不宜久用,中风病急性期虚证表现明显者不宜使用化痰通腑法。
1.2 活血化瘀法 活血化瘀法治疗出血性中风的理论基础为“离经之血便是瘀”,“凡治血者必以祛瘀为要”等。脑出血患者多有血液流变学增高而无凝血障碍[7],因此很多医家主张以活血化瘀法为主治疗。活血化瘀法在缺血性中风的治疗中认可度较高,但出血性中风因其“出血”的特殊性,尤其在急性期,很多医者不敢根据中医理论应用活血化瘀法施治,担心加重出血,还有部分医者主张慎用活血化瘀药。聂志玲等[8]认为出血性中风急性期血瘀已形成,在此阶段瘀血新结,易化易祛,应当重视活血化瘀的应用,治疗以活血祛瘀为主,根据个体不同,配合通腑、平肝、凉血等方法。刘君[9]认为出血性中风急性期也可活血化瘀,且宜及早使用,选择适当药物,掌握合适剂量及合理给药途径,不仅不会引起颅内再出血,而且可改善脑部微循环,降低颅内压,减轻脑水肿,促进颅内血肿的吸收,解除脑组织受压。李杨[10]选取急性出血性中风患者74例,随机将所有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7例。对照组采用内科常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研究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法进行治疗。治疗后,研究组的总有效率及血肿的吸收量明显优于对照组。陈志刚等[11]将77例脑出血患者按是否在急性期运用活血法分组进行回顾性分析,对照组30例予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47例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法治疗,以1个月为观察终点,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病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并可以肯定活血化瘀药物无加重出血及扩大血肿之嫌。陈松深等[12]对活血化瘀方药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却存有不同看法,其认为唐容川的理论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脑出血的离经之血所形成的血肿,在颅脑这一特定生理环境下也可能起到一定程度上防止继续出血而保障了“新血”不再“离经”且有“化机”的作用,还强调祛瘀之法可引血离经。李彬等[13]观察了336例发病12 h内入院的急性出血性中风患者超早期应用活血化瘀法治疗的情况,发现继续出血的发生率与应用活血化瘀治疗有关,提示超早期应用活血化瘀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有可能促使血肿扩大。因此,其认为应当不用或慎用活血化瘀治疗。不过近5年类似此类研究报道较少。可见,活血化瘀法应用于脑出血急性期存有一定争议。但是近年随着大量临床及实验资料的报道,活血化瘀法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逐渐被人们接受,而对于使用的时间窗、禁忌与适应证等问题应更进一步被规范和解决。张根明等[14]认为离经之血虽然清鲜亦为瘀血,脑出血病机为“瘀停脉外,压迫神机”,最先出现的症状系由瘀血所致,在此基础上,钟立群等[15]尝试从影像学角度阐述脑出血活血化瘀药的应用时机。
1.3 平肝熄风法 对中风病因病机的认识,唐宋之前以外风立论为主导,唐宋之后以内风立论为主导,叶天士认为“精血衰耗,水不涵木……内风时起”,提出了中风病“肝阳化风”的理论。平肝熄风历来是出血性中风治疗常法,更有学者把其看作出血性中风治疗的根本大法,其他治疗均在此基础上加减,镇肝熄风汤、天麻钩藤饮均为代表方。常晓[16]将120例出血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60例,对照组60例。治疗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加口服或鼻饲方药镇肝熄风汤;对照组仅采用西医常规治疗。结果治疗后两组在神经功能缺损积分、日常生活能力、中医证候等观察项目方面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P<0.05或P<0.01),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或P<0.01)。赵辉明等[17]用镇肝熄风汤治疗脑出血颅压升高症42例,总有效率为97.6%,对照组为86.7%。洪秀珍等[18]将64例出血性脑卒中患者采用天麻钩藤饮加减,口服或鼻饲、灌肠,结果总有效率达93%以上。徐新菊[19]认为“肝风”是出血性中风的主要病机,将36例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患者均以天麻钩藤饮为主方,随证加减,结果认为疗效显著。平肝熄风法适用于病理因素突出表现为肝风、火热、阳亢等,而出血性中风急性期因其自身的病机特点而呈邪实突出,故急性期应用争议不多,但风证多见病情数变,中风病病理基础复杂,平肝熄风法的应用时点及方法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明。
1.4 醒脑开窍法 中风是在气血阴阳失调基础上风、火、痰、瘀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逆乱于脑部而发生的,其病位在脑。尤其是出血性中风急性期,多表现为“窍闭神昏”重症,醒脑开窍自然成为治疗大法。开窍药具有辛香走窜之性,以开窍醒神为主要作用,常用的开窍药有麝香、石菖蒲、冰片等,受使用局限,临床常用的多为中成药,清开灵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安宫牛黄丸为代表。王海荣[20]将出血性中风93例随机分成两组,治疗组与对照组均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入醒脑静注射液40ml静点,两组疗程均为两周后,临床疗效治疗组优于对照组(P<0.05)。马慧等[21]将103例急性丘脑出血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在对照组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醒脑静,结果提示醒脑静对急性丘脑出血患者出现的意识障碍、发热及神经功能缺损等有明显治疗效果。马丽虹等[22-24]运用系统评价方法,分别对安宫牛黄丸、清开灵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治疗中风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检索,筛选合格研究,评价研究质量,采用异质性检验、Meta-分析、敏感性分析、倒漏斗图等方法统计相关数据。得出结论为安宫牛黄丸、清开灵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均有益于改善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状况。醒脑开窍药在脑出血急性期的应用已有多年,有些学者担心醒脑开窍药走窜之性加重出血,万永奇等[25]从药代动力学角度阐述了其减少脑损伤的机制,加之近年大量的临床试验,均证实了醒脑开窍药的安全性,但其毕竟芳香走窜,应中病即止。
2 综合方案
综合方案又称复杂干预或综合干预,是由多个要素或干预措施组成的,贯穿于中医诊疗过程的始终[26]。综合方案遵循方证相应原则,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结合了中医特色治疗方法,有力提高了出血性中风的临床疗效。
综合方案是在证候、治疗方法、单方单药等研究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规范的辨证论治为其核心和基础,《中风病诊断与疗效标准》的产生与不断优化发展为其提供了可能。郑全章[27]对138例急性出血性中风患者按《中风病诊断与疗效标准》进行分型论证,结果治疗总有效率为86.23%,说明了规范辨证论治的有效性。张根明等[28]也指出出血性中风急性期证候变化迅速,一方一药贯穿始终的治疗思路不符合病机和临床实际,需要采用综合治疗方案,既要体现病机特点又要兼顾病程和证候变化,做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中医优势与西医优势相结合。目前进行的出血性中风综合方案研究多为辨证选择口服中药、中药注射液、针灸、推拿、中药熏洗等中医特色治疗方法的不同组合。胡跃强等[29]采用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设计方法,将258例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患者分为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组(试验组125例)和西医综合治疗组(对照组133例)治疗,观察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及生活质量(QOL)等相关指标。辨证论治参照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中医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制定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治疗后28 d试验组的MBI、QOL评分改善优于对照组(P<0.05)。还有一项国家“十五”攻关课题[30],观察了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理治疗方案对急性脑出血的疗效,结果与对照组比较,综合治疗组在28 d和90 d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均改善(P<0.05),90 d后严重致残及病死率降低(P<0.05),90 d后完全康复和轻微致残率提高(P<0.05)。目前,中风病综合治疗方案广受认可,已被纳入中医内科学指南和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临床实践指南。其核心辨证论治蕴含着“方证相应”的理论基础,方证相应观源自《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方证相应”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强调了方药与病证之间的高度的对应性,是一种经典的临床思维模式。但综合方案包含了多种中医治疗方法,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即使同一种组合方式,其选方用药或针灸推拿选穴及手法也不同,因此,综合方案还需要不断优化,才能更接近于具有疗效最佳、毒副作用最小、花费最少、应用最方便[26]。
3 理论创新
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病机表现以“实”为主,基础的治则治法囊括了中风病“风、火、痰、瘀”等证候要素,一些医家在以上四法的基础上,将创新的理论思维用在出血性中风治疗上,形成新的理论方法,也取得较好疗效。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31]首先较为系统地将“瘀”和“热”结合起来,提出了瘀热阻窍是出血性中风急性期基本病机。随后进行了诸多研究,张兰坤等[32]将135例出血性中风急性期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73例和对照组62例,两组均采用西医内科常规治疗,治疗组同时服用凉血通瘀方,疗程均为21 d。疗程结束后统计并比较两组中风病类诊断评分、瘀热阻窍证候积分、综合疗效及脑出血量情况。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1%,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7.4%,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故此认为凉血通瘀方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瘀热阻窍证能显著提高疗效,降低中风病类诊断评分及瘀热阻窍证候评分,促进脑出血吸收。
在已故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经验总结的基础上,长春中医药大学赵建军教授提出“血瘀髓虚”的病机学说,确立破血化瘀填精补髓法的治疗方法,并进行临床研究[33]。以破血化瘀填精补髓为法,将96例出血性中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48例和对照组48例,两组均使用西医基础治疗,治疗组同时口服中药脑出血Ⅰ号方(急性期)及脑出血Ⅱ号方(恢复期)评价两组中风病中医证候积分,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治疗后各项指标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且以治疗组下降为著,治疗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
在继承传统的发病理论基础上,总结既往研究成果,结合现代科研究,王永炎院士提出了“毒损脑络”病机假说,邹忆怀教授[34]在研究发现在中风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症状的突然波动、持续加重和疾病的复发,是毒损脑络的体现过程,在疾病状态下局灶症状的弥散化,是毒损脑络可能的症状特征。综合药性理论,在此基础上创立“解毒通络方[35],实验结果显示解毒通络方能够有效地诱导脑损伤修复过程中神经元生长相关蛋白的合成而促进神经再生。“毒损脑络”的提出不仅对中医脑病学科的发展具有要意义,而且对中医学领域多个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根据对中风病“病因本原为本虚内邪乘之,病性为本虚标实,病位在脑”的认识,孙塑伦教授等[36]提出中风病急性期的“扶正护脑”治则,即在中风病发生的急性期,尤其是超早期遵循“急而不足则治其本”原则尽一早采用扶止固本法则,顾护人体正气,救护脑髓、维护其主神明、主五脏、六腑、经络、四肢百骸的功能。在此大法指导下研发了“扶正护脑胶囊[37],研究证明,其既可固护严重受损的脑髓,又可兼顾受累心脏,对于脑心综合征的治疗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治疗思路。该理论符合仲景“未虚先防,己虚防变”的治疗思想,在中风病预防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有益补充和完善了中风病治法治则,为中医药治疗中风病急性期开辟了新的思路。
4 展望
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上千年的中医学发展中,总结的基本治则治法如今在临床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经典的不断深入研究及理论创新体现了现代医家的智慧,促进了中医学的不断发展。而随时代及科技发展形成的综合治疗方案有着极大的优势,规范了出血性中风的中医治疗,提高了临床疗效,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
出血性中风来势凶险,中医药治疗有着肯定的疗效,其优势在于治疗方法的综合性、安全性,且可以较好的促进患者神经功能的恢复,提高康复效果,减轻病残程度,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能有效降低病残率与死亡率。但在临床科研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病机认识尚未统一,很多立法用药出于医家的个人经验,方剂众多,不适合推广;有些治法尚有争议;综合方案的研究滞后于缺血性中风。对于出血性中风这样的常见危重病,中医药治疗有着不言而喻的优势,目前在理论研究、治疗方法及综合方案方面都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有效的治疗方案是突破的关键,也是全球研究的热点问题,Lapchak等[38]在他的中风转化研究中指出临床研究阶段规范的致盲、随机化,动力分析,准确的统计分析,和有效的利益冲突规避是能成功转化的基础。在统一公认的研究平台上,遵循循证医学原则,大规模规范化的研究是发展的出路也是未来的趋势,相信将来会有科学的证据使中医药治疗出血性中风得到广泛的肯定。
[1]王永炎,谢颖桢.化痰通腑法治疗中风病痰热腑实证的源流及发展(一)——历史源流、证候病机及临床应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13,20(1):1-6,24.
[2]张向红,程黎晖.大黄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中国药业,2009,18(21):76-78.
[3]钱 艳.星蒌承气汤治疗痰热腑实型出血性中风30例[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8,22(10):21.
[4]朱青霞,崔红生,苗增欣.清热化痰通腑在治疗早期出血性中风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1):869.
[5]赵虎成,刘洁萍,杨文斌.通腑降气法在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应用体会[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7,16(28):4239.
[6]邹忆怀.王永炎教授应用化痰通腑法治疗急性期中风病的经验探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22(04):69-70.
[7]高慧娟,黄永勤,王宏伟.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液流变学改变的临床研究[J].微循环学杂志,2005,15(4):48-51.
[8]聂志玲,张 腾.活血化瘀法在出血性中风急性期之应用[J].中国中医急症,2012,21(9):1449-1450.
[9]刘 君.活血化瘀法在出血性中风中的应用[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3,27(1):76-78.
[10]李 杨.活血化瘀法治疗出血性中风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2):288-289.
[11]陈志刚,王双玲,孟繁兴.活血化瘀法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临床回顾性分析[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7):15-17.
[12]陈松深,邱浩强.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慎用活血化瘀方药[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10(11):1096-1097.
[13]李 彬,路 健.急性出血性中风超早期应用活血化瘀治疗临床观察分析[J].山东中医杂志,2000,19(8):461-462.
[14]张根明,周 莉,马 斌.脑出血中医活血化瘀法治疗方案及其理论依据[J].中国药物警戒,2013,10(6):352-354.
[15]钟利群,张根明,邹忆怀.从高血压脑出血的影像进展看活血化瘀法的应用时机[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11,18 (2):5-7.
[16]常 晓.镇肝熄风汤加减治疗阴虚风动型出血性中风60例[J].河南中医,2012,32(7):912-913.
[17]赵辉明,隆 献,刘美容.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出血颅压升高症42例总结[J].湖南中医杂志,2004,20(2):3-4,8.
[18]洪秀珍,刘学武.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出血性脑卒中64例[J].现代中医药,2004,2(2):17-18.
[19]徐新菊.天麻钩藤饮加减治疗出血性中风36例[J].河南中医, 2003,23(9):25.
[20]王海荣.清热开窍法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52例[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0,24(11):65-66.
[21]马 慧,张永葆.醒脑静治疗急性丘脑出血52例临床观察[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12,31(2):16-20.
[22]马丽虹,李冬梅,李可建.醒脑静注射液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13,40(2): 204-206.
[23]马丽虹,李冬梅,李可建.安宫牛黄丸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2): 60-61.
[24]马丽虹,李冬梅,李可建.清开灵注射液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随机对照试验系统评价研究[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1): 64-66.
[25]方永奇,李 翎.醒脑开窍中药治疗脑病的共性作用概况[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5(5):470-473.
[26]阚保红,高 颖,周 莉.从转化医学角度谈中风病中医综合方案的转化应用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13,22(2):186-188.
[27]郑全章.中医药为主治疗出血性中风疗效观察[J].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3,12(11):1150-1151.
[28]张根明,周 莉,马 斌.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临证思路[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2):158-159.
[29]胡跃强,刘 泰,吴 林.出血性中风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方案临床研究[J].辽宁中医杂志,2010,37(6):1091-1093.
[30]高 颖,周 莉.中风病中医药防治研究的回顾与现状分析[J].环球中医药,2009,2(1):15-18.
[31]周仲瑛.出血性中风(瘀热阻窍证)证治的研究[J].中医药学刊, 2002,20(6):709-711.
[32]张兰坤,过伟峰,徐 丹.凉血通瘀方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瘀热阻窍证患者73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12,53(1):28-30,44.
[33]张轶丹.破血化瘀填精补髓法治疗出血性中风临床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12,21(9):1380-1381.
[34]邹忆怀.“毒损脑络”学说的症状学研究思路探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9(7):448-450.
[35]PT Li,YSh Pan,QF Huang.Effect of Jiedu Tongluo Recipe on synaptic plasticity in hippocampus after cerebral ischemia injury[A].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次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论文摘要集[C].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2002:1.
[36]张 壮,孙塑伦.中风病急性期扶正护脑治则的理论基础初探[A].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2005全国中医脑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C].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2005:3.
[37]赵彦青,孙塑伦,高 颖.扶正护脑胶囊对脑出血大鼠心肌组织中TXB_2/6-Keto-PGF_(1α)的影响[J].中国中医急症,2006,15(3): 281-282,340.
[38]Lapchak PA,Zhang JH,Noble-Haeusslein L.RIGOR Guidelines: escalating STAIR and STEPS for effective translational research [J].Ranslational Stroke Research,2013,4(3):279-285.
Curr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hemorrhagic stroke at acute phase.
WANG Jia-yan1,KANG Ning2,HUANG Hong-min1.1.Hainan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aikou 570203,Hainan,CHINA;2.China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Hemorrhagic stroke at acute phase is a common dangerous critical disease.A lot of research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documented.By reading ancient books and a decade of clinical research in the treatment of hemorrhagic stroke at acute phase,we sum up main treatment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article.Learning and innovation help generate good therapeutic effect and new methods and als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high-quality research results,which arouse us that more careful design and unified platform in future clinical studies are needed.
Hemorrhagic stroke;Acute phase;Chinese medicine;Treatment;Review
R743.34
A
1003—6350(2015)04—0550—05
2014-06-04)
10.3969/j.issn.1003-6350.2015.04.0198
王家艳。E-mail:295964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