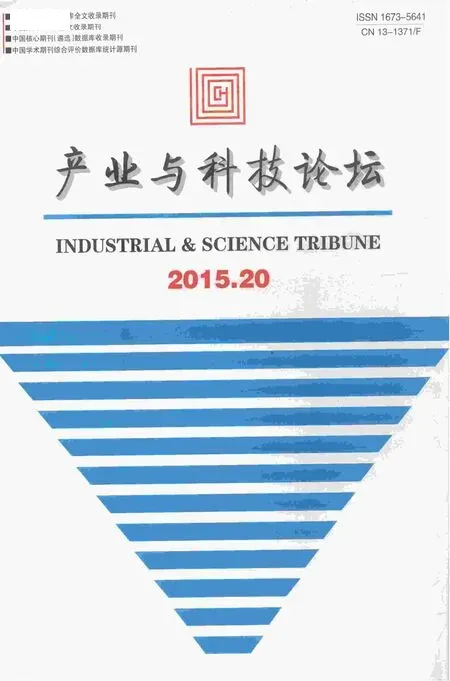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情况实证分析——以南京市家政业流动妇女为例
2015-03-19卞国锐郭梦笛葛文慧
□卞国锐 殷 洁 郭梦笛 葛文慧 吴 慧
一、引言
伴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阶段。由原来的快速发展时期逐步转变为较为缓慢、稳步增长的常规发展状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中小城镇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心,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对带动现代化发展、解决农村农民问题以及特大城市人口疏散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家政业流动妇女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典型代表群体,试图描绘出她们真实的生活现状,了解她们的居留意愿,并由此来透视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乡迁移行为特征。
二、研究区域、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调查数据来源于对南京市家政业外来务工人员的实地走访调研,调查的主要区域为主城内发展较成熟的鼓楼区,秦淮区,玄武区,建邺区四个行政区。由于家政人员居住较分散,大部分时间都在雇主家或在中介等地,因此,我们在家政人员的工作地(中高收入阶层居住小区)和中介机构共发放问卷160 份,有效问卷147 份,有效率91.8%。其中重点访谈了20 位家政人员,5 位中介人员。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总结发现受访者中有65.5%来自江苏省内,20.7%来自于安徽省,13.8%来自于其他省份包括贵州、河南、四川、湖北、山东、陕西、重庆、湖南,其中以中老年妇女为主,41 ~50 岁年龄段的占到受访者的63%,且受教育水平偏低,有近八成的受访者学历水平为初中以下。受访者中有75%是在南京租房居住,居住环境较差,还有18%的家政业流动妇女在没有工作时会回到家乡,没有城市中的落脚点。
三、南京市家政业流动妇女生活现状分析
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1]。家政业流动妇女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作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共性问题,也有其作为女性群体特有的生命周期及家庭角色所带来的特定问题。
(一)经济收入较低。与男性相比,农业转移人口中的女性群体不仅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中户籍壁垒的限制,还受到农村区域长期以来“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造成了这一群体受教育水平偏低,往往因自身素质的限制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2]。在被调查的人群中,51%的家政人员是初中水平,21%的家政人员是小学水平,还有14%的家政人员没有上过学,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家政业流动妇女受教育水平仅达到中小学水平。学历的限制和技能的缺失使家政业流动妇女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除此之外,家政业流动妇女还面临着工作流动性强、不稳定的境况。在经济收入方面,家政业流动妇女的平均收入整体偏低,约38%的家政人员每月的工资集中在2,000 ~3,000 元之间。3,000 元及以下的总共占到了70%。
(二)权益保障缺失。处于城市边缘的家政业流动妇女群体,由于受到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下户籍制度的限制,她们在城市的诸多方面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并且维权意识和法律意识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处境。另外,我国《劳动法》中也明确指出,家政服务人员并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畴。而目前,我国还未出台关于保障家政服务人员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一旦家政业流动妇女和雇主发生劳动纠纷,她们的合法权益便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目前,在家政业中有两种经营模式,一是员工制,即家政公司先聘用家政人员作为员工,再与雇主签订服务合同。二是中介制,在中介制中,家政公司是以一个中介者的身份来促成服务协议的签订。但无论哪种模式,所签订的劳动合同都不具有正式法律效力,更无法维护家政人员的合法权益。而劳动合同缺失的现象更为普遍。调查发现,约有66%的家政人员没有与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在大多数的家政公司中,保险金基本上是由家政人员自己缴纳,但由于大部分家政人员的月收入较低,往往难以支付较高的社会保险,导致家政人员在城市中社会保障的缺失,调查中发现69%的家政人员无任何劳动保障。
此外,家政业流动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也同样令人担忧。家政业流动妇女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她们希望能够像普通市民一样参与到城市的管理中去,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权益。
(三)行为适应遭遇瓶颈。家政业流动妇女在来到大城市之后,离开了朋友及熟悉的生活环境,缺乏家人的关怀,再加上经济方面的制约,使得她们无法适应大城市的生活节奏与环境,行为适应遇到瓶颈。家政业流动妇女作为流动妇女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其社交能力,环境及行为适应能力偏低,致使其主动进行社会融入的程度较低。调查数据显示有86%的家政人员年龄分布在31 ~50 岁之间,可见中老年妇女是家政业流动妇女的主要组成部分,她们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往往难以改变在家乡常年以来养成的行为习惯,造成其文化生活及日常行为中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了家政业流动妇女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遭遇行为适应瓶颈问题。
(四)身份认同缺失。身份认同(Identity)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是评价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依据,分为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一是在社会身份认同方面,家政行业作为城市中新兴的第三产业,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潜意识中,家政行业从业者往往与旧时仆人的角色画等号,致使家政行业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较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身份认同。二是在自我身份认同方面,一方面从家政业流动妇女角度来看,由于家政业流动妇女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及自我价值定位的偏颇,造成了其与城市居民日常交流的隔阂及社会归属感的缺失;另一方面,从社会及政府角度来看,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相挂钩的社会福利及保障的不健全,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群体社会身份认同感的缺失。
四、南京市家政业流动妇女未来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
数据表明家政人员虽然大规模向城市流动,但受制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城市认同等约束,家政人员很难在城市安家定居,逐渐形成了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两栖流动模式。
(一)留在(特)大城市的影响因素。43%的家政人员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是城市就业机会多、收入高,收入在6,000 元以上的家政行业高级技术人才愿意留在大城市生活。另有40%的家政人员是随同亲友迁移而来,17%的家政人员由于其他原因如医疗,教育等因素选择留在(特)大城市。由此可以看出,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居留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性因素,即城市就业机会多,可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状况。
(二)迁往中小城镇的影响因素。对于家政业流动妇女来说,由于(特)大城市的房价高,而中小城镇的房价在她们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中小城镇是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的折衷选择。在希望迁往中小城镇的家政业流动妇女中,一部分以35 ~40 岁的年轻妇女为主(占63%),她们既不想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活动,又无力承担(特)大城市的昂贵房价及物价水平;另一部分以40 ~55 岁的中年家政妇女为主(占35%),她们希望迁往中小城镇投靠子女生活。
(三)回乡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有回迁意愿的个人及家庭进行研究,得知他们回流的主要原因是对家乡土地的依赖。被调查者中有土地的有110 人,其中64%的田地现由亲友耕种,也有29%的家庭选择每年定期回乡耕种,该类人群大都为中年人,对土地有很高的依恋性;而家乡的房屋有53%的现由亲友居住,剩余部分多为空置。以上可看出,家政人员大多是“离乡不离土”的外出模式。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屋是他们生产生活及回迁的主要原因和保障。
五、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策略
(一)经济职业融入。在积极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新的就业空间的同时,提倡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一方面,积极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开办文化知识班,达到有效提高其基本素质、文化素养和务工技能的作用,增强其社会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培训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政策。针对用人单位,规范其运行体制,健全保障制度,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职业上的合法权益,推动其在经济职业上的城市融入。
(二)行为适应融入。培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意识,让其享有市民待遇。增设公共活动场所,并开展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学习与交流的大型活动,增强其城市融入的意识。同时提供福利待遇,如对生活特别困难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提供临时救助;加大农业转移人口集中居住的城中村、产业园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6],形成社会对农业转移人口关怀的良好氛围。同时开办相关的学习培训班,通过学习与自我提升,让农业转移人口加快跟上城市的步伐,促进其行为的融入。
(三)身份认同融入。媒体与政府应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正面宣传,通过客观介绍其在城市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利用正确的舆论,引导社会各界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意识和排外思想,营造一个倡导公平公正,全社会理解支持并帮助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良好氛围。打消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过客”心态,激发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愿望和主观能动性,构建良性社群网络。
(四)社会制度融入。总的来说,积极推进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的构建,削弱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公民权益的城乡差异,对住房保障进行必要的改革。缓解部分转移人口在城市中仅可“立业”却无法“安家”的社会问题。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将促进这些常常游离在体制之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一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上进行改进完善,如健全我国社会农业转移人口的养老保险体系,提高其在城市生活的安全感,从而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积极性和归属感。二是在教育制度上,应改变分配资源的偏向方式,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助,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创造更好的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条件,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真正体会到城乡教育的公平性,有力推进融入城市的节奏。
[1]易宪容.“过客”定居可让中国GDP 再翻番——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市民化[J].人民论坛,2013,4:26 ~27
[2]杨书.“消费的城市”与“边缘”的“她们”——转型社会中进城家政女工生存境遇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8
[3]王竹青.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立法的必要性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1):65 ~74
[4]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一种社会互构论的视野[D].华中师范大学,2009
[5]马久杰,孟凡友.农民工迁移非持久性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J].农村改革,2003,4:77 ~86
[6]曹玉娟.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路径[N].广西日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