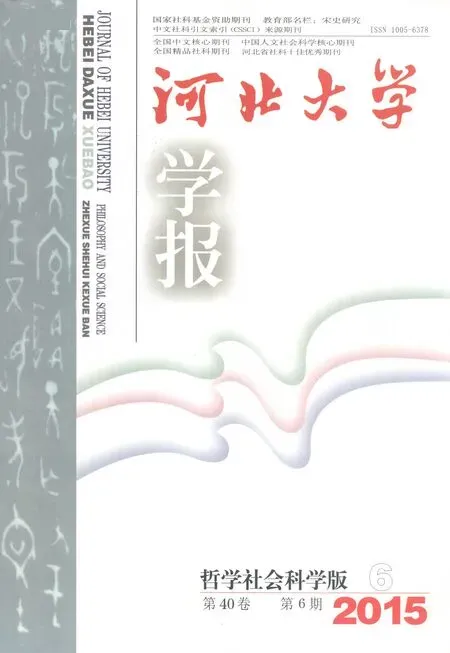关于公共保障与社会保障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与余斌先生商榷
2015-03-19孙健夫陈丽莎
孙健夫,陈丽莎
(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管理学研究
关于公共保障与社会保障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与余斌先生商榷
孙健夫,陈丽莎
(河北大学 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公共保障与公共财政支出存在密切联系,它是由政府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市场机制无力解决的社会需求的手段。无限制地扩大公共保障的内涵,过度扩大公共保障的功能,会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形成挤出效应。社会保障作为公共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工业化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大创新。它所体现的价值在于由政府主导对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进行制度性安排。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也需要在坚持普遍性原则的同时,防止脱离经济承受能力,盲目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适度原则应该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公共保障;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社会再生产;资源配置;保障原则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发表了余斌先生的《试论公共保障与社会保障》(以下简称《保障》)一文。文章超越于社会保障学理论的基本思想,从公共经济学的视野上论证了公共保障比社会保障更加重要的理念,并且就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因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现存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仔细拜读全文,从中颇受教益。但是,对余先生的一些观点也有几点不同看法,特在此求教。
一、关于公共保障与社会保障内涵的认识
从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来看,公共保障作为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概念,一般出现在公共财政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相关问题的分析之中。因为从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求的性质出发,它只能由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通过财政资金予以保障。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所属公共部门的基本职责。《保障》开门见山地指出,“公共保障是公共支出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支出必须实现的目标”。这与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接下来作者的论述却偏离了这个研究的基础,指出,“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一般只提社会保障而不提公共保障或者将后者与前者混为一谈”[1],并对公共保障和社会保障并列做了概念的界定,即公共保障是“社会所采取的维护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社会保障是“社会所采取的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1]。在这里,至少有三点值得讨论。
其一,所谓公共保障是“社会所采取的维护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缩小了其应有的外延。如果从狭义上理解社会再生产,它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的统一,与经济活动的口径具有一致性。这显然无法覆盖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照我国的预算支持项目来看,财政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资源勘察电力信息等事务、商业服务业等事务、金融监管等事务、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国土资源气候等事务、住房保障支出、粮油物资储备事务等20多类支出。这就是从国家财政预算法的角度对财政支出所确定的保障范围,也就是所谓的公共保障范围。在这些保障支出的项目中,的确包含着交通运输、资源勘查、电力信息、商业服务业等经济领域的内容,要求财政对这些需求予以支持,但是更多的部分在性质上属于社会发展和一般公共服务的范畴。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关系已有清楚的界定,市场需要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职能则是对市场机制的失灵与缺陷给予纠正和弥补,为市场主体更顺利地投资、生产、经营创造外部良好的环境。因此,通过财政提供的公共保障主要目标不是经济活动需求,而是市场主体无法涉足、无力涉足的非经营性、非营利性活动需求。如果从广义来看,社会再生产还有人口再生产。它是指新一代人口出生、成长和老一代人口衰老、死亡不断重复的世代更替过程,实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财政、一个国家的政府向社会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都是用来提升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假如以这样的观念来分析财政支出的用途,我们当然可以说它维护了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需求。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国防、外交、行政管理、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卫生、市政建设乃至于民族问题等需求与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都存在着种种联系,就将其归入社会再生产的需求范畴,那就否定了公共经济学的科学内涵,是对公共经济学体系的简单化和模糊化。照此逻辑,人类所从事的什么活动还有不是社会再生产的要素吗?
其二,西方公共经济学只提社会保障而不提公共保障或者将后者与前者混为一谈吗?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所谓“西方公共经济学”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或者统一的认识。作为一门经济学的分支,绝大部分公共经济学理论都建立在公共财政理论基础上,甚至很多教材只是在题目上换了一个不同的称呼。十几年前,公共经济学开始引入我国。就笔者所接触的研究进展看,应该说,公共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基本上沿用了“西方公共经济学”的架构和理念。中国人民大学郭庆旺教授、中国社科院赵志耘教授在其《公共经济学》的序言中写到 :“在我们看来,财政学、公共(部门)经济学、政府经济学是同义语,即使有人有新的叫法,其实在内容上也是换汤不换药。”[2]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在他出版的《公共经济学》一书的封页上,则直接冠以《财政学》的副标题,并在前言特别指出“公共经济学就是财政学”[3]。但是,无论是“西方公共经济学”还是我国的公共经济学,都找不到专门阐述公共保障的概念和章节,而是都用一定的篇幅专题论述了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支出的内容。那么,这样一种分析方法是否是这些学者们真地忽略了公共保障,或者将公共保障与社会保障混为一谈了呢?
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公共经济学既然主要是围绕着公共财政为核心内容建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那么,它所研究的对象客观上都属于公共保障范畴,或者说是用公共财政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提供的保障。以吉恩·希瑞克斯、加雷思·D·迈尔斯的《中级公共经济学》为例,作者从公共经济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讨论入手,顺次地阐述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公共部门的增长及其合理性、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公平与分配的关系、税收问题、多级政府问题[4]。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中,让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公共经济学如何从政府和公共部门存在的价值及其功能出发,来论证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所要考虑的效率和公平,以及实现这样的功能所依赖的手段和方法。所有这些内容,不正是对所谓公共保障内容的解析吗?如果考察我国学者对公共经济学的设计思路,这样的结论会显得更加明确。郭庆旺、赵志耘所著《公共经济学》一共有十四章内容,第一章的题目是“政府的经济活动”,阐述了政府经济活动的公共性及其活动目标和最优规模,其余十三章完全是现代财政学研究的体系和内容。其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实现最佳的政府财政分配路径和分配效果,保障政府公共经济活动实施的目标和条件。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公共经济学没有专门提到公共保障就是忽略甚至有意不研究公共保障问题,而是将公共保障与整个研究体系融为一体了。至于说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中会涉及到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支出的内容,笔者认为,这不是对公共保障的一种替代和混淆,而是其中必须研究的一个公共经济现象或公共经济问题。它和公共保障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公共保障远比社会保障的内涵更大,社会保障只是公共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认为把社会保障写入公共经济学,而没有专门分析公共保障的内容,就是试图以社会保障替代公共保障,未免就过于牵强了。
其三,社会保障是“社会所采取的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吗?应该说,对于社会保障学内涵的认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分析,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科学、规范的结论。众所周知,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哪个部分,它们都有这样的共同点,即都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其他成员提供的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的货币收入或实物;都是通过法律做出的制度安排;政府不仅是社会保障的组织者,也是制度运行的支持者,需要借助财政预算资金承担必要的投入责任。正是以上关于社会保障的规定性,决定了社会保障属于公共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相对于《保障》一文关于社会保障的定义,即“社会所采取的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存在很大差别。从现代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看,其提供保障的人群都包含着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另一部分是社会居民。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险为例,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分为企业职工保险和城乡居民保险。如果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反映了维护劳动力再生产要求的话,那么,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则脱离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范围,最多可以视为人口再生产的范围。如果分析社会救助的内容,其主要目标是解决生活困难群体的温饱问题,在性质上属于社会道义、社会关爱范畴,与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关系。至于社会福利,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既包含政府和企业对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如防暑降温费、艰苦行业作业补贴等,也包括对非劳动者群体提供的福利,如计划生育家庭补贴、老年人补贴、婴儿补贴、敬老院的补贴以及残疾人的福利等。因此,把社会保障与维护劳动力再生产联系起来,概念过于宽泛。
此外,《保障》一文还将“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都归于社会保障门下,这种概括也与社会保障的本质相去甚远。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依赖的最主要手段理应是由工资薪金所形成劳动者收入。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的收入来源已呈多元化格局,除了工资薪金之外,还有财产收入、技术转让收入、投资收益等。社会保障收入在劳动力的收入来源中,只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收入。其功能是在政府公共政策干预下,对劳动者主体收入提供的一种补充性支持。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也只是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对劳动力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老年生活经济来源做出的一种延伸收入计划。并且需要强调指出,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的形式就是货币收入或货币补贴,与保障人群的具体生活需求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收入获得什么样的生活资料,什么时间购买生活资料,购买多少生活资料,这些关乎个人生活质量和生命存续的决策,不是由政府代为做出的,而是属于个人的权利。因此,社会保障不可能成为“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否则的话,社会保障就可能变成了人的一生无所不包的全能制度。
二、关于社会保障产生原因的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起始于工业革命进程中的欧洲国家,这是学界普遍认同的事实。为什么会在欧洲国家率先创立这样的制度?《保障》一文的分析如下 :“西方国家的资本家逐渐意识到,以国家的名义对劳动者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维持失业人口的生存,对他们是十分有利的。这样,一来可以压低就业工人的工资水平,限制就业工人的反抗;二来可以方便他们随时找到充足的人手来扩大自己的生意;三来,他们还可以设法将相关费用转嫁到其他人头上。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意识到,一个贫困盛行的社会滋生着不满和革命,具有引起大的混乱和暴力的潜在可能性。收入较高的群体通过货币对穷人进行收入转移支付以保证社会稳定,从而降低暴力革命的可能性。”[1]笔者认为,在以上的分析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误解。前已述及,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险,社会养老保险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劳动者在业期间与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收入分配问题,与劳动者在业期间出现失业无关。所以,把社会保障单纯与失业人口的生存相联系,并且由此引申出资本家愿意提供社会保障的三点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社会保险中的失业保险的确是缓解劳动者失业期间生活困难的重要措施。在早期的工业化社会到来之时,由于市场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性、消费需求的低层次性,使得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经常处于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劳动者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并有助于稳定劳动力市场。但是,无论是从失业保险的规模看,还是从失业保险涉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看,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它都无法与社会养老保险相提并论。
此外,我们注意到,《保障》对社会保障起因的理解,很倾向于从劳资双方的对立关系、而不是从社会保障的功能进行分析。这与公共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理论有较大差异。客观地说,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险这样一种帮助劳动者合理分配其收入和消费支出的社会保险制度,它体现了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的巨大进步,也是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表现。能够形成这样的制度创新,并不是某个资本家良心的发现,也不是为了防止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在一个社会整体利益随着工业化社会到来不断强化,以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农业化社会所不曾见到的风险采取的重大行动。社会保险的目的,就在于把分散的力量整合为社会范围的共同力量,让无力抵御工业社会风险的弱势群体能够得到生活、生存的安全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不仅推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客观上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今天,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更高级的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也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它不仅仅是城市工人的专属制度,也是社会各个群体共同享有的制度。这让社会保障制度带给社会的公平感和安全感更加显著。在我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也已经成为惠及城乡职工和居民的一项重要制度,并且被视为让所有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的实施,使得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从公共财富中更多受益,对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将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
三、关于公共保障原则的理解
《保障》给出了公共保障的四项基本原则,分别是普遍、足额、平等和法治。对于平等和法治原则,笔者没有异议,但对于其中的普遍原则和足额原则感到有必要深入讨论。 文章认为,“所谓普遍的原则,是指公共保障应当是涉及所有人群的,事关衣食住行医和就业的全方位保障,而不仅仅是最低收入方面的保障”[1]。作者以建国初期国家对城镇职工就业、工资、住宅、医药费、福利费提供的相对优厚待遇和农村的公社医院建设、医疗人才培养为例,来解释该原则的含义。指出,这一时期“对劳动者个人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覆盖到了”[1]。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旧的一套已经被打破,新的一套却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较大欠缺[1]。文章认为,“所谓足额的原则,是指公共保障不仅要在数量上足够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在质量上也要保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1]。作者指出,“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规模不足以向全体民众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但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无法回避公共保障的足额原则,否则改革开放成绩何在”[1]?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出疑问的是,所谓公共保障普遍原则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建国初期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我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管理上实行计划经济控制下的城乡之间的分割模式。以国有经济为支撑的城市职工和居民普遍享有就业、粮食供给、免费医疗、住房、退休等象征社会福利的优越条件,但与此同时,以集体经济为支撑的广大农村居民却无权享有同样的待遇,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如果把这样的社会福利区别对待状况也称为普遍性的话,是否意味着在一个国度里只要一部分群体做到了人人受益,就可以不顾其他群体的利益要求呢?脱离开全体国民的普遍,还是真正的普遍吗?再反过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在此期间,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国家从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适时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政策,在社会保障领域陆续建立了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正在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客观地说,这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虽然还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已经普遍实现了程度不同的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大创举!至于制度之间未能很好的衔接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不能也不应该被看成是社会保障迈向全民普遍受益的退步。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期待,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整合,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其次,公共保障(原文作者强调的是社会保障)足额原则里所讲的数量保障内涵应该怎样理解?文章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只是强调了原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能够足额地满足民众的需求,今天,我们的国力已经相当雄厚,实现足额提供公共保障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责任。我认为,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是很不严谨的,不仅会误导社会公众,也无助于政府科学地制定公共政策。近年来,我们已经从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过程和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的事实中,深刻地感受到了上个世纪被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广泛推崇的欧洲福利社会,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而且其影响力不仅是短期的,更是长期的。上世纪7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主动对过高的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2015年希腊作为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被联盟所逼正在被动地进行同样的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要削减过高的养老金水平和其他福利项目,以便降低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和福利成本,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动力。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保障不能有需求就要有供给,这里有一个合理的度的问题。这个度应该如何把握?根本因素要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决定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和生活成本水平。社会保障的功能就是保障国民生活的基本安全,超出这个安全线之后的需求,应该属于市场机制解决的范围。任何国家经济再发达,也无法保障人们提出的所有需求。正是由于这样的道理,我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特别强调了我们的社会保险是“基本”保险,有限的保险,而不是无限的保险。并且,这些保险不是由政府先来承担供给责任,而是由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共同承担责任。任何享有社会保险利益的人,必须首先承担缴费的责任,不缴费者不能获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可以给予补贴,并对其他社会保险给予财政资金的支持。中国社科院钱津研究员针对近年来政府加大民生保障支出、提高民生福利的政策,提出“经济理论界需要给予政府提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承揽过多的经济责任,改善民生需要防止过度依赖政府”“不能让拉美悲剧①指拉美国家在步入快速增长之后出现的国民福利水平过度提高所引起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在中国重演”[5]。这个建议值得经济学界认真思考。鉴于此,我认为,与其把足额作为公共保障(社会保障)的一个原则,不如改为适度原则更为恰当。
[1]余斌.试论公共保障与社会保障[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3):1-5.
[2]郭庆旺,赵志耘.公共经济学[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蒋洪.公共经济学[M].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吉恩·希瑞克斯,加雷思·D·迈尔斯.中级公共经济学[M].中译本.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1.
[5]钱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4) :1-6.
【责任编辑 侯翠环】
Reunderstanding on Public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Discussion with Mr. Yu Bin
SUN Jian-fu,CHEN Li-sha
(College of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Public security is closely linked with fiscal expenditure. It is a mean that the governments use to meet social needs by providing public goods when market mechanism fails to do so. Unlimitedly expanding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curity and over-extending its function will result in the crowding-out effect to market’s resources allocation function.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ystem, social security is a major innovation in the social management field t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ized social production mode. The key value of social security is to mak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social members, especially for the vulnerable groups, leading by the governmen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needs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as well as to prevent bli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level beyond economic affordability. Thus,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ion should be the basic principle f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public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 public finance; social reproduc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security principle
2015-05-20
河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支持。
孙健夫(1955—),男,河北乐亭县人,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公共管理。
C913
A
1005-6378(2015)06-0080-06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6.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