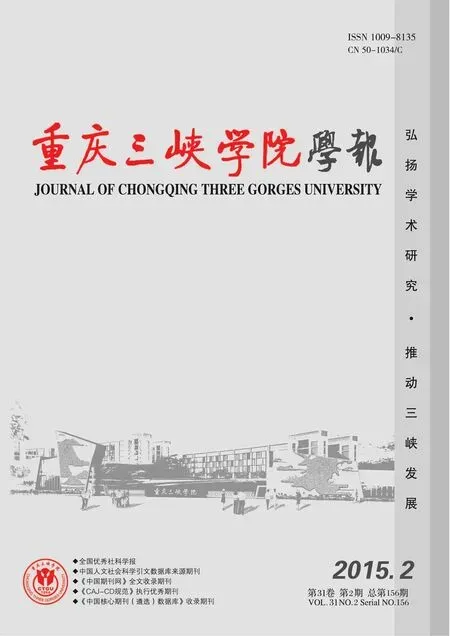论《孽海花》中晚清士人的“卖直”
2015-03-18董伟岩
董伟岩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论《孽海花》中晚清士人的“卖直”
董伟岩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 723000)
“卖直”由古代谏官制度发展变异而来,谏议的场所由朝堂之上转换到朝堂之外的士人之间,并且在儒家传统经世致用观念与晚清科举制度影响下,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兴盛起来,成为一种奇特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孽海花》一方面注意到“卖直”可以启发民众思想、开启民智,还能够展现出晚清士人关注时政的热情和对民族未来发展的关切;另一方面,也对一些士人的荒诞行径给予谴责。
“卖直”;孽海花;晚清;士人
1840的鸦片战争作为历史节点,使中国逐步进入晚清社会。晚清时代的中国,不同于历史上其它朝代:封建专制社会走向末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层面的弊端逐渐暴露;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国格日渐丧失。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同时,它自身也或被动或主动地进行某种演变与革新来克服这种危机。谏官制度面对这种危机也不得不做出反应。作为古代吏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谏官制度自周代以降,历经两千多年直至晚清,在自身走向末路的历史趋势下和载有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产生某种畸变,“卖直”凸显。
一、“卖直”:谏官制度在时空上之异变
“谏官”也称“谏臣”,指通过直言来劝谏君主过失的官员。中国的谏官制度自周代便设立,直至晚清,存在两千多年之久。谏官既劝谏君主避免过失,也上陈国事和人事的政令供君主做参考。谏官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职业道德,他们的直言往往被看做是“忠君”的体现,所谓“忠臣不避重诛”。“做臣子的不能不忠,而忠的体现是谏,谏和忠形成了辩证的统一。”[1]封建社会把直言敢谏作为任官的标准,许多官员为求得赏识也不惜冒死向皇帝直谏。自周以降,历代谏官虽然名称各异,劝谏的本质却始终如一。晚清时代,社会危机加深,列强对中国的欺凌加剧,西方自由、民族思潮传入,使部分士人的思想意识开始觉醒,以一种不同于以往历代士人的新身份走向政治舞台,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晚清士人的人格具有矛盾性,他们一方面深受科举制荼毒,思维僵化,贪图功利,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经验;另一方面又切身感受到“西学东渐”之盛,受儒家忠义思想影响,他们也力图进言献策,“师夷长技”来改变国家和民族岌岌可危之态势。他们梦想像谏官一样当面向君主上陈自己的改良之策,可是能够登上朝堂向君主直面劝谏的士人毕竟少之又少,大部分士人只能默默做一个普通的官吏或者埋首苦读祈求金榜题名。这些无缘向君主当面劝谏的士人不满于自己的“治国良策”无人问津、自己的“忠心”不被人赏识,于是他们互相之间便产生了“卖直”。
“卖直”一词,黄仁宇先生给出过一个定义,是指一些官员不是出于尽忠的目的,而是“出于自私自利”,“把正直当成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作本钱,然后招摇贩卖他正直的声望”的行为[2]53-54。黄仁宇先生提到的“卖直”是针对晚明万历年间部分士人而言,特指通过“诽谤讪议”即言论的形式来获得“声望”。然而到了晚清,社会时局较晚明愈加复杂,那些空有一腔治国良策却无缘向君主当面劝谏的士人便借用了“卖直”这种方式,不过他们所“贩卖”的不单是“正直的声望”,更主要的是经世之策、忠君之诚。这样一来,“卖直”就有了一种新定义,即凭借言论来博取忠心、展现治国才干并赢得正直声望的行为。晚清的“卖直”和晚明的“卖直”还有些许不同,通过黄仁宇先生的解释显然可以看出晚明之际士人的“卖直”具有贬义色彩;而晚清士人“卖直”的初衷虽然不排除有利己的考虑,但也不乏直陈时局之利弊和兴邦安国之良策的义举。
“卖直”可谓是谏官制度在时空上的一种演变。时间上,周代设有“保氏”,可看做中国最早的谏官;秦代的“谏议大夫”“光禄大夫”“议郎”负有劝谏职责;唐代是谏言最盛的朝代,“谏议大夫”是主要谏官,魏征、褚遂良都曾担任过该职;宋代设立谏院,有六名谏官;元代并无专职劝谏的官员,由御史承担其职;明代“给事中”兼任谏官;清代“都察院御史”“给事中”负责劝谏,然而清代的谏官制度却形同虚设[1]。空间上,谏议的场所由朝堂之上君主面前转换到朝堂之外的士人之间,他们没有朝堂之上的顾忌,更不必担心有性命之忧,可以“大表忠心”“畅谈朝政”。晚清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同时,它自身也或被动或主动地进行某种演变与革新来克服这种危机。谏官制度在时间和空间的发展与位移中于晚清之际产生异变形成一个节点,这个节点与晚清特殊时局相应,是为了克服民族危机而产生。“卖直”可以看作是这个节点的直接表现,它带有某种自觉性。那些远离朝堂却怀有经世之策的士人,并不具有真正的政治话语权,他们的言论也很难起到预期的作用,但从某种角度而言,“卖直”是他们自发的一种奇特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
二、“卖直”:经世致用与科举取士之合流
《孽海花》“专纪清季京朝的种种遗闻轶事”[3]214,可谓专为晚清士人打造的一部百科全书。可小说又不全是“遗闻轶事”,它把士人置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特定背景下,通过他们来展现这三十年的时代变化,而“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4]131,因此可以说《孽海花》是一部具有社会史性质的小说。鲁迅先生称《孽海花》为“清末之谴责小说”[5],谴责的主要对象是贪腐、愚昧、功利的士人群体。然而,作者曾朴也毫不吝惜笔墨,对部分士人通过“卖直”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英勇无谓精神大加赞赏。晚清士人选择“卖直”,既出于从小学习儒家经典,有扶危济困和经世致用的人生目标,又缘于中国旧有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科举制度遭遇近代危机,常规的谋官升迁途径受阻。如果说谏官制度在时空上为“卖直”产生创造了条件,那相互影响、渗透的经世致用观念和科举取士制度则是其产生的动因。
(一)
中国历代文人几乎从小就研习儒家经典,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作为提高个人内心修养的途径,进而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是典型的入世哲学,深受其影响的读书人自然把“经世致用”作为最高的人生目标,即能够用己之所学治理天下。“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会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6]179晚清时代,可谓“社会危机四伏”,“中国学生们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就是对儒家经典深刻而又透彻的理解”[7]4,显然埋藏在士人心中的经世致用观念被激发出来也毫无异议了。另外,清代是一个考据学全盛的时代,清中叶以后,考据学派中的新派今文学家留心于经世之学,不像古文家的斤斤自守。晚清之际国势日渐陵夷,内忧外患愈亟,这些今文学家为时势所迫,也愈加务实,而进一步重视经世致用,这样就使得部分士人开始寻求经世之路。与少数决策者相对的是庞大的士人群体,而庞大的士人群体不可能也不能够全部“经世”,真正治理天下的毕竟只是少数的士人。有相当一部分士人空有经世之学而无施展之地,他们又不愿自己对一些时政问题的见地不为人知,于是他们互相不断增加见面的频次,交谈自己对时局的见解,以探讨经世之学的“卖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这种“卖直”“主要表现出一种对于现存政治制度的关爱”[8]51,是士人觉醒和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
第十八回中,薛淑云和他的参赞王子度两人在即将出使“英法义比”四国之际,特邀几个旧友在上海味莼园小聚。名义上薛淑云和王子度是上下级关系,可对世界局势的关注让他们二人更像朋友,“气味甚是相投”[9]242。比他二人更关心时局的还有受邀前来的朋友们,他们大都有国外工作的经历,因此对时局的把握更准确。席间,他们冷静客观地分析时局,直陈自己对中国变革的建议,涉及政治、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为今之计,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自存在这种大战国世界哩!”[9]246在外交方面,“有两件必须力争的,第一件,该把我国列入公法之内,凡事不至十分吃亏;第二件,南洋各埠,都该添设领事,使侨民有所依归”[9]247。
如果“卖直”掌握不好分寸,便会成为空谈,甚至等同于愚昧与无知。晚清政坛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政治派别即清流党,由当时的名士组成。但他们于治国空有虚名,多骛大言,不切实际,缺乏实际建树,还对较为务实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多有攻击批评。第二十四回中,中日开战在即,“人人义愤填胸,个个忠肝裂血,朝励枕戈之志,野闻同袍之歌”[9]333,然而太史闻韵高和新点状元章直蛮却“在这一片轰轰烈烈的开战声中”,“特地跑到后载门外的十刹海荷花荡畔,一座酒楼上,凭阑寄傲,把盏论文。”[9]333闻、章二人虽然谈论的是和日本开战的必要性,却对日本缺乏足够的认知,只泄一己之私愤。“我国若不大张挞伐,一奋神威,靠着各国的空文劝阻,他那里肯甘心就范呢!”他们认为日本区区岛国,“到底幅员不广,财力无多,他既要来螳臂当车,我何妨去全狮搏兔,给他一个下马威,也可发表我国的兵力。”[9]335“卖直”究竟是出于“经世致用”还是“空谈”,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语言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给予一定判断,“空谈”的“卖直”往往是略带嘲讽的叙述语言。作者写闻、章二人的空谈,“两个潇潇洒洒的出奇人物”[9]333、“把个看花饮酒的游观场,当了运筹决策的机密室了”[9]334,嘲讽之态显而易见;写薛淑云邀请朋友在上海味莼园小聚直陈对中国变革的建议,却毫无嘲讽之语。
(二)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科举制和“独尊儒术”相结合,不仅维护着古代社会政统和道统的统一,还巩固和强化着宗法秩序。清代的科举考试较以往有所不同,清代科举考试不仅划定了读书范围、取四书五经命题,还要求考生完全依照朱熹的注作答,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禁锢了考生的思想,使他们的思维日渐僵化,独立思考能力日益削弱,丧失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科举时代,“士的知识结构和行为准则深受君王控制,士失去独立人格,在现实社会中,士的最鲜明的道德规范和信仰追求是忠君。”[10]21从理论上看,科举制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人员流动,一个良性的流动,能够激发读书人学习的热情,敦促他们积极向上,同时他们也能够在备考中完善自身素养,增加各方面知识,为以后的从政之路做好理论基础。不排除有部分士人谋求更大的权柄是为了更好地“经世致用”,然而“科举考试与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士人一旦中试成名,与之俱来的便是良田美宅、峨冠博带、显亲扬名,可以说是名利双收,”[11]20这样巨大的诱惑甚至使一些人丧失理智冒险作弊。近代士人“在科名的诱惑与制度的阉割下,完全丧失了自我,沦为科举的奴隶,人格卑下,精神颓废,”[11]23可见一些士人读书并非为了增加知识、增强做事的能力和提高自身素养,而是受“官本位”思想影响,贪图享乐,单纯为了做官,并且层级越高越好。
晚清政坛贪腐横行,“考官大多贪赃枉法,受贿纳礼,私通关节。”[11]20西方列强入侵,他们把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带到中国,中国旧有的文明受到冲击,科举制也在近代遭遇危机,导致士人很难通过常规途径达到仕途的显赫地位。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对大部分士人而言已实属不易;而那些本已考取了功名的士人又觉得已获利益和心中的高官厚禄相距甚远,于是他们中的部分人选择通过有意识的“卖直”来博取上级的推崇、赢得升迁。向自己的上级“卖直”不失为一种自我标榜的手段,士人可以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对国内外形势的严重关切,进而得到上级肯定获得晋封。
与“经世致用”观念影响下的“卖直”相比,科举制影响下的“卖直”并非一件光彩的事,曾朴在小说中也对其给予了绝妙的讽刺。第五回中,庄伦樵在大考后官封翰林院侍讲学士,然而家中拮据,欠米店两个月账,债主天天来讨。他看不惯大官的贪腐行为,更对自己官阶低下无处可贪心生不平,于是写了个折子,把纳贿卖缺等见不得人的事统统写了上去,即便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强如现在庸庸碌碌的干瘪死!”[9]59庄伦樵因此发迹,连其他官僚的“房闱秘事”也能全端出来,“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9]61。后来,他还成为京城“清流党”的“六君子”,“朝一个封奏,晚一个密折,闹得鸡犬不宁,烟云缭绕,总算得言路大开,直臣遍地,好一派圣明景象”[9]61。这种“卖直”当然不是真正的“圣明景象”,曾朴也无心恭维庄伦樵,最终让他在带领军队和法军对抗中败北,被革职充发。
科举制的衰落导致士人品行不端,而士人的品行不端又加剧了科举制的衰落。在这个悖论中,很难把责任归咎于士人。士人实处于被动地位,旧有的科举制度让他们只管因袭而缺少必要的批判,他们本不具备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改革甚至推翻科举制度。他们也是深受晚清科举迫害的一群人,即便有些人看起来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受益者,但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历史缝隙中寻求一席之地。如此看来,即便“科举考试在近代年复一年大批制造所谓的‘士’”,“这些人大多有士之名而无士之实”[11]22,也只能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他们的“卖直”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于无奈。
三、“卖直”:小说政治功用性之实践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打破以往轻视小说的做法,把小说看成最佳的舆论工具,认为“小说可以决定宗教,决定道德风俗,决定人格人心,一言以蔽之,小说可以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命运”[12]71。他提出“新小说”理论,要求小说创作要重视并且弘扬文学的社会功能,要启蒙民众思想,激励他们的爱国精神。曾朴由于“适应不了官场的阴险狡诈和八面玲珑”[10]99,决心舍弃仕途,拂袖归乡,专门从事文学活动。在1904至1909年间,曾朴“想要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纠集同志,创立一家书店,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他的“不朽杰作《孽海花》也在这时候开始着笔。”[13]167当时包括曾朴在内的一大批职业报人对梁启超新小说理论做出积极回应,“他们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将这些理论付诸小说创作的实践,使这些新小说理论主张借助他们的作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12]88此后的小说创作,大都重视政治功用性,与时事政治联系紧密,小说甚至被作为政治变革的有力工具。《孽海花》正是曾朴在政治功用性的影响下而作。《孽海花》的创作重视政治功用性,把“卖直”写进其中作为启发民众思想、开启民智重要一环。作品中士人之间的“卖直”,无论作者是赞扬还是嘲讽,都可以对民众起到引导和劝诫的功用,让他们了解时局并对做出相应的评判。
即便“卖直”本身存在某种争议,但无疑“卖直”能够展现出部分晚清士人对政治和时局巨大的关切、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曾朴突出要展现的,正是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一部分有志向的士人民族意识的觉醒,“把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危难捆绑在一起”[14]91,寻求解决现实困境之路。第二回中,冯桂芬对新科状元金雯青说道:“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学,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9]15第三回中,金雯青和官场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多谈的是西方的政治和人情,他插不上话,只好默不作声,心里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那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9]25。显然,当时士人群体已意识到走出国门、学识洋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
“卖直”由古代谏官制度在晚清之际时空异变而成,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刺激下,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晚清科举制双重影响下,成为一种奇特的政治话语表达方式。曾朴捕捉到了这一奇特的政治现象,并响应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小说理论,把二者结合写进《孽海花》,完成了自己写一部历史小说兼社会小说的心愿。通览全书,《孽海花》中士人的“卖直”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关照下一种政治话语表达方式,也是他们身处历史夹缝中无缘主流政治舞台的悲凉呐喊和家国情怀另类展现。
[1]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97-104.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包天笑.关于《孽海花》[M]//魏绍昌.孽海花资料.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M]//魏绍昌.孽海花资料(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6]冯天瑜.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方位[M]//葛荣晋.中国史学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朱涛,倪静,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8]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曾朴.孽海花(插图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0]汤克勤.近代转型视阈下的晚清小说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杨齐福.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李亚娟.晚清小说与政治之关系研究:1902-1911[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13]曾虚白.曾孟朴年谱[M]//魏绍昌.孽海花资料(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郑宗荣)
An Analysis of Maizhi in Scholars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A Flower in the Ocean of Sin
DONG Wei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nnxi 723000, China)
Maizhi was evolved from the advisor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in that the advising site was converted from the court to other site outside the court and the target advised converted from emperor to officials. This phenomenon flourish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otion of “put classics into practic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in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powers in Late Qing Dynasty. It evolved into a unique way to express political purpose. A Flower in the Ocean of Sin noticed that Maizhi can on one hand enlighten people’s mind and manifest scholars’ enthusiasm about and attention to politics affai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on the other it lashed the absurd action of some scholars.
Maizhi; A Flower in the Ocean of 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cholars
I206.2
A
1009-8135(2015)02-0062-04
2014-12-20
董伟岩(1989-),男,河北承德人,陕西理工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陕西理工学院2014年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SLGYCX141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