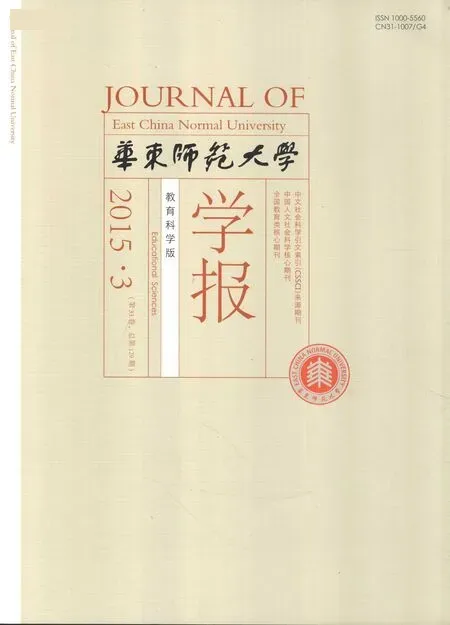论盛宣怀办学与政府的协调关系
——以南洋公学校名演变为视角
2015-03-18欧七斤
欧七斤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上海200240)
论盛宣怀办学与政府的协调关系
——以南洋公学校名演变为视角
欧七斤
(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室,上海200240)
考察解读校名更易的具体过程与内在根源,可以窥见我国现代教育诞生和成长的特殊轨迹。南洋公学(1896-1905)是盛宣怀倾注心力最多、办学成绩最突出的一所学堂,其校名数经变更。在现代教育起步之初,以盛宣怀为代表的绅商阶层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其创办的南洋公学借鉴西方,定名“公学”,采取由工商实业出资支持的“公学”发展模式。然而,当时中国社会还远未形成成熟稳定的工商阶层,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主导社会的传统却异常发达,“公学”办学模式注定缺乏可持续性。在晚清政府主持学制改革后,“公学”模式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转而融入到由国家政府主导的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之中。
盛宣怀;政府;南洋公学;校名演变
一校之校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所学校的性质,体现主办者的办学理念和文化意识。历来中外办学者对于学校名称很是审慎考究,一旦定名绝不轻言变更。然而盛宣怀所办南洋公学(1896-1905)的定名却数次变更。盛宣怀规划南洋公学及筹备初期拟定校名“南洋大学堂”;筹备后期及正式开办时定校名“南洋公学”。1902年奏请改称“南洋高等公学堂”,未果。次年奏准称“南洋高等商务学堂”。1905年春改属商部,相应改校名“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校名不断变更的背后,既体现了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及时调适与各级政府的复杂关系,也折射出晚清社会一种联动式的政治与文化生态。这里利用上海图书馆“盛档”文献、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对南洋公学校名更易的原委经过作一番细致地考察解读,阐释盛宣怀如何在办学过程中不断调适与各级政府部门间的关系,希望从中窥见我国现代教育诞生和成长的特殊轨迹。
一、从大学堂到公学:意在主导办学权
1895年,近代实业家、官绅阶层的代表盛宣怀利用自己在官商两界的独特地位,以不同于中央、地方教育主管者的别样身份,总结其办理电报、矿务等技术实业学堂的经验得失,率先仿照近代西方学校制度系统,提出了体系较完备的全国捐设学堂规划。该计划拟在全国各地捐建大学堂2所、小学堂23所、时中书院3所,全部办学经费由自己管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金矿局等认捐。规划设立两所大学堂即“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①。北洋大学堂当年在天津设立。1896年初春,盛宣怀筹拟在上海创建南洋大学堂。筹备初期,筹建者及知情者均如捐学计划称校名为“南洋大学堂”、“大学堂”,而未见称“南洋公学”。钟天纬是筹建者之一,主要负责购买办学地基,在向盛宣怀呈报购地情形的多封信函中,涉及校名时都称“南洋大学堂”。②
南洋大学堂与北洋大学堂同为盛宣怀一人所办,两堂并称为“南北洋大学堂”。1896年5月,钟天纬函告盛宣怀称三等公学堂办理数年后毕业学生“足以应南北洋大学堂之取”③。盛宣怀亲笔所拟《轮船招商局节略》中也曾言:“北洋即以所还官款拨造开平至唐沽铁路资本,自后该局官利之外,提出余利二成创办南北洋大学堂两座,培养学生数百人,是为学堂之嚆矢。”④以上种种,都说明盛宣怀曾规划于上海设立北洋大学堂性质的“南洋大学堂”。
然而,等到筹办前夕,在1896年8月盛宣怀呈给刘坤一的筹备章程《南洋公学纲领》中,却明定校名为“南洋公学”。为何如此?章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就校名作出了释义:“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今上海学堂之设,常费皆招商轮船、电报两局众商所捐,故曰南洋公学。”⑤1896年10月、1897年1月,盛宣怀先后两次呈请设学的奏片《请设学堂片》、《筹建南洋公学及达成馆舍片》,也均称校名为“南洋公学”。《南洋公学纲领》对于校名的表述,几乎未作任何更动地列入《南洋公学章程》(1898年)第一章第一节“设学宗旨”。1897年4月正式开学时,学校称南洋公学,年底学校启用“总理南洋公学关防”,南洋公学校名遂正式定名,而“南洋大学堂”的称谓同时也“销声匿迹”。
南洋公学可分“南洋”、“公学”来解释。“南洋”易于理解,一是与早一年创建的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是叫人们注意这个新学府的所在地同北洋大学之间的差别”⑥。二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人们通常以长江口为界,南面沿海称南洋,北面沿海称北洋;清政府设立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分别专管南北洋范围内的对外通商、外交、关税等事宜。公学建在位于南洋的通商巨埠上海,所以取名“南洋”。
关键是“公学”两字的释义。依照前述定名来由,参照外国学校的办理模式,经费来源半由商民捐办、半由官方扶助者称公学。盛宣怀所办学堂之经费由其主管的招商、电报两局捐给,而两局性质上是官督商捐的洋务企业,因经费来源之故定名“南洋公学”。
盛宣怀本人对“公学”之名还有一番延伸性的解释。早在1896年6月,他与幕友谢家福就讨论过公学的含义,他认为公学应该是“商捐经费,学资不出于一方,士籍不拘于一省……其学生卒业给凭,与国家大学堂身份无异”⑦。不过,既然公学毕业生与国家大学堂身份别无二致,为何不径称“南洋大学堂”,而将规划中的“南洋大学堂”突然变更为“南洋公学”?
究其细故,在具体的筹备办学过程中,盛宣怀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种种牵制,这违背了他原本依靠所控实业的经费结余自主办学的初衷。于是他另辟蹊径,试图避开政府部门的锋芒,转而借用英国等国的“公学”的名头和发展模式,创建一所自己主导的新式大学堂。
原来,就在盛宣怀筹备开设“南洋大学堂”前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也已“奉谕旨在沪另创大学堂”⑧。当时,清政府采纳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的《奏请推广学校折》,同意在京师、上海各设大学堂一所。
1896年春,盛宣怀专赴南京拜见刘坤一,当面提出要在上海创办大学堂。刘欣然答应,同时指令驻上海的江海关道黄建筦协助办理,意思就是让盛宣怀和江海关道合作办学。这显然不是盛宣怀所期盼的。从此后整个学校的创建过程来看,盛宣怀从未与江海关道商议过办理公学事宜,筹备人选、办理经费、办学章程等,都是其一手经管。既然中央政府也规划在上海创办大学堂,而盛宣怀又不愿意与地方政府合办“南洋大学堂”,那也就只能放弃规划校名,另取其名了。而英国等国的“公学”模式,正好为盛宣怀定名“南洋公学”提供了借鉴。
尽管取名南洋公学,且煞费心思做了周全的释义,然而开办之初将英文名称定为“Nanyang University”,也能反观出其“弃名留实”的涵义,只是到了1897年底监院福开森来校后,才建议改为“Nanyang College”。⑨由此可知,改名南洋公学的背后,反映了盛宣怀希望掌握办学自主权、依靠工商业的经费力量相对独立地兴办新学的意图。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可补充证明上述观点。北洋大学堂是盛宣怀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898年9月北洋大臣荣禄拟将北洋头等学堂更名为“北洋高等学堂”,盛宣怀则指令北洋头等学堂总办王修植将北洋改名为“北洋公学”,后因总教习丁家立激烈反对任何更名而作罢。⑩盛宣怀拟将北洋校名也改为“公学”的打算,其实就蕴涵了抵制地方政府的钳制、保持学校办学相对独立性的意图。
二、奏改高等公学堂:接轨学制的博弈
在经历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等奇耻大辱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宣布实行新政,仿行西法,改革内政外交。在文教领域,1901年颁行“兴学诏书”,诏令全国广设各级新式学堂。1902年8月制订公布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所拟《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因该学制成于仓促之间,内容难免粗疏,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对其予以修改并更名为《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于1904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学制的制订特别是癸卯学制的颁行,解决了各地兴学无章可循的状况,推动了全国各级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
全国性学制的颁布,既给南洋公学发展确立了制度标准,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同时也给南洋公学的定位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如何在新学制体系中找到对应的等级定位?又如何让新式教育主管部门认可这个定位,并能以校名形式体现出来?至1902年壬寅学制颁布时,南洋公学定名已有6年之久,校名已为校内外人士所接受,而要与学制对接,须重新定名,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国家教育体制之内,有利于公学办学层次的确立及学生出路。
依照南洋公学“本系大学”的设学定位,和分设外院、中院、上院三级递升的实施途径,公学应定为高等之列,且参照西方三级学制建立外院、中院、上院与清政府所颁学制正相吻合。但是,南洋公学在获得法定“高等”地位上有几个不利因素:
一是地域关系。设学之地的上海并非省城,而按照学制规定,京师应设大学堂,省城设高等学堂或大学堂,相应称某某省高等学堂或大学堂。
二是经费关系。公学经费出自轮、电两局,并由两局督办盛宣怀个人主管,而学制所定大学堂、高等学堂均由国库、地方政府供款,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
三是衡量标准。公学已经实施多年的中院教学目标、课程设置、肄业年限等,不一定完全符合学制关于中等学堂的具体要求,而学制规定高等学堂所招学生必须为考验合格的中学或预科毕业生。
以上诸端给公学争取进入“高等”的道路上增添了许多曲折。然而,若等级未定,“诸生遂不免长虑却顾,甚或辍业他往,废于半途”⑪。接轨学制、重定校名被盛宣怀及主校者在学制颁行前后视为重要校务,也成为他们急需解决的一大难题。早在1901年“兴学诏书”颁行时,南洋公学就已开始考虑定位问题。9月17日,公学总理沈曾植致函盛宣怀:“学堂诏下,公学似当以省学为比,此节甚有应商事,欲面谈者此也。”⑫1902年10月,盛宣怀获悉“壬寅学制”内容后,即致函公学总办汪凤藻:“公学开办已有数年,应称作何等学堂,尚未奉定。昨阅张野秋尚书陈奉京师大学堂章程,似公学可居高等之列,拟援例即日入告矣。”⑬张野秋尚书即学制的主要拟订者、管学大臣张百熙。盛在信中不免流露出对公学定位问题的自信,随即商嘱幕僚吕景端起草奏稿。吕在拟稿时,恰逢京师大学堂总办、学制参与者张鹤龄前来晤谈。谈及此事,张说“张野翁以下及京师大夫早认南洋公学为南洋大学堂,不妨径请作为大学堂”。吕也认为“公学规模程度,实在各省未设之高等学堂之上”,于是采纳张鹤龄建议,“故折中径请作为南洋大学堂”,并告知“倘钧意以为太僭太骤,则将稿中大字改为高等二字可也”。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盛宣怀在改稿时,又在“高等”后面加了一个“公”,定名“南洋高等公学堂”,于10月18日将这份《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陈报清廷。奏折详述了公学能够位列高等的几点缘由:
其一,办学建制。公学设上院、中院、师范院、蒙学堂、特班、东文学堂、译书院、商务学堂等8个办学组织,其中上院即“视西国专门学校,肄习政治经济法律诸科”,东文学堂即“考选成学高才之士专习东文,讲授高等普通科学以备译才”,筹备中商务学堂即“以中院卒业学生递年升入,并招考外生,另延教习,分门教授,以备将来榷税兴商之用”。⑮意为上述三种办学形式符合高等学堂要求。
其二,参照国内外学堂定位标准。“考泰西诸大学校,多在通都大邑、民物殷盛之区,各省府不能尽建巨黉,各巨黉亦不必尽在省府,其不仰给于国家经费者,若英若美所在多有,并系绅商集款建设为特别之大学堂,其学生卒业给凭与国家大学堂学生身分无异。”就国内而言,“公学创办于奉旨之先,与山东同,其兼备中学小学于一地,亦与山东同,其上院课程较山东学堂且高一级。”“山东”指1901年11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创设于济南的山东大学堂,成立不久即奏准为省城大学堂。
其三,符合学制定章。1902年《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第三节规定:“又如繁富之府、厅、州、县地方,及通商大埠,虽非省会,若能创设与高等学堂程度相等之学堂,亦可称为高等学堂。”⑯公学设于通商巨埠上海,且开办已有6年,建制稳定,成绩优良,设施完善,已基本具备开办高等学堂的各项条件。
鉴于此,盛宣怀拟请朝廷降旨,准南洋公学卒业学生,按照政务处礼部所拟《学堂选举章程》一律办理,给予出身,并明定公学校名为“南洋高等公学堂”。10月30日奉朱批:“管学大臣议奏,钦此。”⑰
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与盛宣怀私交甚好,两人曾换帖结为兄弟。张百熙对南洋公学办学成绩较为肯定,曾在奏折中称:“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⑱但是张百熙敏锐地观察到“公学”依靠商捐的不可持续性,他以私人名义致函盛宣怀:“杏荪宫保仁兄世大人阁下,……南洋公学改为高等学堂奉旨交议,当以未见详细章程,拟俟调查后再行议覆。……惟思南洋公学经执事提倡新机,经营数载,规模既崇宏,条理尤为精密,成效昭著,海内所知。但公学款项向归电报、招商两局筹拨,现在局面稍有变更,未知尊意拟如何办法,尚祈详细示知。”⑲
原来此时,正逢南洋公学爆发了“墨水瓶”退学事件。更重要的是在袁世凯等人的排挤下,盛宣怀逐渐失去对轮电两局的掌控权,轮电两局大幅度削减对南洋公学的资助经费,致使公学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公学”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1903年初盛宣怀答复张百熙质疑经费供给时就坦诚道:“自轮电改章,弟即电慰帅(即袁世凯,笔者注),请其将常年经费十万照拨,未蒙准行。嗣告以前曾另筹每年招商贰万两电局二万元,以备出洋经费,请其照办,免致中辍业,已经允诺。查弟经派出洋学生计北洋大学堂生赴美国者八人,南洋公学生赴英国者五人,赴美国者一人,赴日本者二人,岁需银贰万三千两左右,加以公学洋教习三人,岁薪银八千两,除支该两款外,已余无几。虽有前数节存银八万两,断难持久。”⑳面对危机,一方面公学缩减办学规模、压缩经费开支,另一方面调整办学方向。公学从墨水瓶事件中汲取了办理政学人才不易的经验教训,转而开始注重办理“实学”,并对作为实学科的商务学堂予以重点建设。1903年春夏之际,盛宣怀与张百熙再三晤商,张同意在南洋公学上院开设高等商务学堂,并催令速办。于是,盛宣怀又开始厘定章程,延聘外国教习。1903年9月6日,商务学堂正式开学,由公学美籍教习薛来西(Leacey Sites)、勒芬尔(Leavenworth)等讲授理财、公法、商律等课程。9月29日,盛宣怀上《开办高等商务学堂折》奏称:“时局既以商务为亟,而商学尤以储材为先,现在各省设立高等学堂,考求政艺,不患无人,独商学专门未开风气。窃惟南洋公学款由商捐,地在商埠,若统称高等学堂,则与省会学堂不甚分别,且无所附丽。”㉑鉴于此,盛宣怀奏请将南洋公学上院作为商务学堂,学生毕业后颁给高等学堂文凭。奏折奉朱批“管学大臣议奏”。10月,南洋公学被议定更名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而由“管学大臣议奏”的正式议复直至1904年7月下达公学,同意将上院改为“南洋高等商业学堂”,学科程度、毕业年限应依照新颁学制办理,学生毕业奖励办法与“官设省会高等学堂一律”。该议复8月9日奉旨“依议”。㉒
经过2年多数番争取,开办8年之久的南洋公学与学制中高等实业学堂相接轨,定在高等学堂之列,被正式纳入国家学制系统。被学制接纳之艰难,反映出学制颁行前体制外新式学堂生存与发展的曲折性。南洋公学更校名为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则表明盛宣怀面对现实环境中存在的诸多不利因素不得已放弃了对依靠商捐的“公学”模式的坚守,转而寻求将公学纳入官方体系。
三、隶商部更校名:无奈的归属
南洋公学虽然更名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初步完成了办学定位的调整,但是经费保障问题尚未解决。1905年,盛宣怀在经费不济的情况下,无奈地将学校彻底移交给有意接办的中央政府部门——商部,学校再次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先是1904年10月27日,商部尚书载振函商盛宣怀将南洋公学划归商部办理,函曰:“……沪埠为商业繁盛之区,执事擘画其间,创办学堂造就商务人才,宏观硕画,至为钦佩。本部此次奏办实业学堂,博究工科,因与商政有关,爰由弟咨商学务大臣,拨出此项学堂隶入本部筹办,藉相联属。尊处商务学堂事同一律,且造就商才更为本部应办之事,可否商请台端径行移交本部管理,名实相副,于学务、部务两有裨益。”㉓商部设于1903年9月,是清政府为推行“新政”而专设的一个中央直属机构,主要职能是规划振兴全国商务,并兼办农工商及铁路事务。商部重视实业技术教育,认为欲振兴工商实业,“应先从设立学堂下手”㉔,于1904年10月设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工业制造为主。同时,商部认为中国商学“素未讲求”,亟需筹办高等商业学堂,“以沪埠为商业繁盛之区,议与其间设一高等商业学堂”。㉕急于在上海筹办商务学堂的商部,商请盛宣怀将初具高等商务学堂规模的南洋公学改隶商部。
11月初,盛宣怀复函载振,同意将南洋公学改归商部,并称:“公学开办虽久,无所附丽,兹值商部设立实业学堂,应请隶入商部管理,庶几联属一气,名实相符”㉖,“且毕业学生定有出身,得以陆续派赴外洋肄业欧美大学,蔚成商业通材,公学之光,亦宣怀之幸也”㉗。实际上,盛宣怀同意公学改属商部,其自述理由“联属一气,名实相符”、“毕业学生定有出身”多属虚词。盛宣怀在此时同意改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办学经费危机。
至1903年,盛宣怀已经失去了对公学供款单位——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控制权,公学经费骤减,维持艰难。翌年,“断难持久”的经费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若公学改归商部,可以以部属学堂的名分,借助商部解决经费难题,使学校得以持续下去,于是盛宣怀对于改属“甚所乐从”。1904年冬,商部派员来校预备接收事宜。1905年3月,商部正式接管公学,派杨士琦担任监督,更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盛宣怀经营近10年的南洋公学时期至此宣告结束。
此次更名意味着,学校彻底告别了依靠商捐的“公学“模式,有了正式的中央部属主管单位,而不再由盛宣怀个人所管。南洋公学归属商部,使之成为一所体制之内的中央部属高等学堂,经费来源趋于稳定,管理不因个人际遇而变更,学生毕业出路较优,这些对于学校发展来说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坚持10年后,盛宣怀最终失去南洋公学,这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初,由于工商业阶层远远不成熟、不稳定,绅商主导下的新式教育,面临着因派系斗争、个人浮沉而带来的经费、管理、学生出路等多种困扰。
四、余论
通过对南洋公学校名变更的细致分析,我们不仅可以看出,身处晚清艰难复杂的办学环境之中,盛宣怀办学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和办学活动的灵活机动性,更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教育转型的轨迹和过程的复杂性。
在19世纪末,中国现代教育的诞生之初,像盛宣怀这样的拥有开放视野和雄厚财力的绅商阶层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诸如南洋公学这样的新式教育机构的兴办早于国家启动系统的现代教育改革。在缺乏国家学制指导和财政经费的背景下,南洋公学借鉴西方教育模式,依靠商业捐助经费,定名“公学”,并在一校内率先开始了现代三级学制的办学试验。
到20世纪初,晚清政府开始废除科举,颁布现代学制,并着手对先前零星出现的新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后期的南洋公学正处于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在当时中国,商业化、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刚刚启动,还远未形成成熟稳定的工商业阶层,而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主导社会的传统却异常发达。在此历史大背景下,从西方引进来的由工商业阶层支持的“公学”办学模式注定在中国缺乏可持续性。“公学”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实属必然,它只能融入到由政府主导的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中去。
注 释:
①盛宣怀:《北洋大学堂等捐款单》(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以下简称“盛档”):044280-3。
②如盛档044472:《购买南洋大学堂地基领用银数清单》;044866-1:《将续买南洋大学堂地基经手钱帐单》,等等。
③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896年4月26日),盛档:069926。
④盛宣怀:《轮船招商局节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5页。
⑤盛宣怀:《南洋公学纲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盛档:044964-2。
⑥⑨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1931年5月),《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页;第10页。
⑦盛宣怀:《致五亩园学堂谢家福函》(光绪二十一年五月,1896年6月),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
⑧经元善:《上海经正书院归公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1896年6月),盛档:044280-1。
⑩王修植:《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年11月),盛档:044960。
⑪⑮⑰盛宣怀:《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盛宣怀:《愚斋存稿》第8卷,北平思补楼藏版,1939年,第31-34页。
⑫盛宣怀:《与盛宣怀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1902年9月17日),转引自许全胜编:《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7页;第31-34页;第31-34页。
⑬盛宣怀:《致汪凤藻函》(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盛档:044511-2。
⑭《吕景端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转引自王尔敏、吴伦霓霞辑:《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中),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61页。
⑯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第264页。
⑱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32页。
⑲张百熙:《致函盛宣怀》(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1903年2月11日),盛档:044179-1。
⑳盛宣怀:《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盛档:044179-2。
㉑盛宣怀:《开办高等商务学堂折》(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愚斋存稿》第9卷,第7页。
㉒盛宣怀:《准学务大臣咨奏南洋公学开办商务学堂一折奉旨依议札文》(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二日,1904年9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历史档案,档号:2326,卷名:《清代前工程部左堂盛关于开办商务学堂、聘请洋教员、筹划经费及派员赴日考察奏摺和照会》(1902-1904)。
㉓载振:《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九日,1904年10月27日),转引自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编盛宣怀档案萃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6页。
㉔㉖《商部奏请拟办实业学堂大概情形折》(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方杂志》第3期,1904年5月10日。
㉕《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1905年2月27日)。
㉗盛宣怀:《致载振函》(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1904年11月3日),盛档:044709-3。
(责任编辑 胡 岩)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in Private Education:Case of Nanyang College
OU Qijin
(Research Office of University History,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China)
The oncemost prominent Nanyang College(1896-1905)to which SHENG Xuan-huai devoted most of his efforts changed its name several times.Examining how and why the college changed its name helps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of modern education.From the outset,the gentry and merchants represented by SHENG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College in the name of Public School.This western-style College was then financed by the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mmunity.However,there was nomature and stabl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lass in China,while therewas awell-developed traditional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which made the education mode of Nanyang College less sustainable.After the reform in the Schoo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SHENG’smode gradually faded out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modernization led by the government.
SHENG Xuan-huai;Government Coordination;Nanyang College;change
10.16382/j.cnki.1000-5560.2015.0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