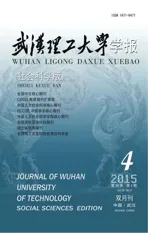能指的狂欢与创生:当前文学产业写作的意趣延宕与意义生产*
2015-03-18王慧菊
王慧菊
(铁道警察学院 公共基础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53)
由于文学产业的受众群体并不以文学阅读为教育、认知的机会,而是以之为娱乐、放松的方式,所以,在产业机制下的文学写作中,能指的狂欢成为当前文学产业写作最为突出的表征,并成为当前文学产业写作意义创生的方式。
一、能指的狂欢与意趣延宕
(一)能指的狂欢:文学产业写作的制度特征
2004年,王一川教授以文学语言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进为线索,勾勒当代文学写作的轮廓为:20世纪70年代末,能指与所指高度统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能指已经开始溢出所指,取得与所指脱离的独立表现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能指的扩张、剩余、狂欢场面随处可见。他把能指与所指分离后能指的扩张、剩余与狂欢称为“能指盛宴”。依照王一川教授的分析,无论是就先锋语言在通俗文学中的大量播散而言,还是就市民口语的通俗、直白对严肃文学的冲击来说,能指的盛宴与狂欢在写作风格上都表现为通俗。[1]
以严肃的、纯文学的眼光来观察,无论是表象的通俗,还是内在的狂欢,都是对文学趣味的破坏与解构,因而,基于纯文学视角的文学批评,往往会要求在文学写作中消除狂欢与通俗,返回纯文学中能指与所指一体的“纯净”状态。然而,10年过去后,根据我们的观察,通俗仍是文学产业写作减少阅读障碍、保持阅读的畅快感的主要手段。无论是网媒文学还是纸媒文学,在市场上取得不俗表现的作品,尽管在语言特色上表现出温婉、柔和、恬淡、刚健、激情、热血、幽默、痞气等不同风格,但在言语选择上却都呈现出通俗的特点。比如,在文学期刊市场哀鸿一片的环境下,《故事会》《读者》等以通俗为特点的期刊却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营销业绩,成为期刊界的奇迹。四大名著在文学、文化产业语境中的传播所借助的主要力量便是通俗化的改编。当然,对四大名著的通俗化改变并不局限于言语,但言语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对比原作人物对白与影视改编或各种现代改编版本的人物对白,我们便可以轻松地发现这一点。起点中文网编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说明文学产业写作中通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们(即读者)要的,只是一个顺滑的故事,一些可以满足他们一点小小幻想的角色,甚至是脸谱化角色也行。基本上直白的没有修饰的文字他们就能满足了。找遍世界,你也找不到如此容易满足,要求如此简单的读者了。”[2]“直白的没有修饰的文字他们就能满足了”,这是网媒文学受众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产业对文学写作最重要的规制。即,文学产业写作言语选择的通俗化,不仅是读者整体文化素质所要求的结果,而且也是写作的产业机制所规制的产物。这表明,在文学产业写作中,能指的盛宴与狂欢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已经成为当下文学产业写作的制度性特征。
(二)白日梦:文学产业写作与阅读的意趣
1.作为能指狂欢结果的白日梦。狂欢这一为现代文学理论所熟知的术语是巴赫金从拉伯雷小说言语行为中大量出现的脏话、极度夸张的数目字、怪诞形象(在当前的中国文学产业写作中,这些现象乃是常态)中发明、提炼出来的。在巴赫金的阐释与建构中,狂欢意味着“正面肯定物质-肉体的存在本性”[3]32,在能指的狂欢里,“世界因此而肉体化;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全在时间的双重性之中丧失了色情意味和恐惧感”[3]33。
文学产业机制下的写作,如玄幻小说、架空小说、穿越小说、青春小说等等,通过能指的狂欢,表现出对物质丰盈、富饶的创造与占有,构建出或大尺度的、或永恒化的宇宙与世界,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实现克服、消解、超越“性”与“死”两大基本畅销元素[4]在现实人生中所引发的哀伤与恐惧。当代中国文学产业写作中的能指的狂欢这一特质不仅表现于对物质的肯定和对“性”与“死”的色情意味与恐惧感的消解与超越,而且表现出对言语狂欢的至高意蕴的认同与践履,即“揭示生存的另一重境域”[3]30。所谓“生存的另一重境域”指与基督教化的、严肃的、沉闷的世界观相区别的非宗教化的、欢笑的、怪诞的宇宙观念。在当前的文学产业语境下中,它意味着写作的非现实化和趣味化,意味着对欢乐情绪的绝对化的追求,意味着对内心深处的成功梦的营造。
无论以何种风格的语言来写作,主人公总能够从各种艰难险阻中脱困而出,攀登上作品世界的最高峰,获得人生的成功。在现实中,即便不能说这些现象不可能发生,也得实事求是地把它们划到小概率事件的范畴中去,文学产业机制下生产的作品中,这些现象简直是必备的“神器”。读者泰然自若、习以为常地阅读、欣赏,热烈地追捧中意的作品和作者,作者殚精竭虑于如何使所有的事件在一种顺畅的言语之流中拥有看起来合理的或合乎作品设定规则的原因和结果,在读者与作者的共谋中,一件件“伟大的”历险梦幻般地从无到有,构筑出主人公的世界、生命与人格。
这些“白日梦”式的文本常常遭受评论者的批评,如,有论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以‘中国作家富豪榜’为例,像蔡骏、沧月、李西闽、江南、桐华等上榜作家,他们不但敢于涉足盗墓恐怖、历史宫闱、穿越幻情、颓废边缘、黑道江湖这样一些明显带有猎奇色彩的领域,而且还赢得了网络受众的普遍喝彩。”[5]这些评论揭示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涉足带有猎奇色彩的领域,二是居然赢得受众的普遍喝彩。前者是基于传统的、严肃的、纯文学的立场的价值判断,后者是对在价值判断中处于边缘甚至负面的作品居然赢得普遍喝彩的不满与不解。在传统文学理论中,二者的组合不合逻辑,也不应该发生。因而,真正的问题是,二者之间的组合究竟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
2.文学产业写作与阅读的意趣。文学产业主要受众群体年龄处于18~39岁之间①。在现代生活的流水线上,这个年龄区间的人们普遍地生活在席勒所言的断片式生存之中,尚未达到“不惑”的生活境界,距离社会价值标准所界定的幸福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不满足是他们的普遍的感受,当然,这也是当代社会发展与进步所需要的心理驱动力。然而,问题在于,当不满足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常态时,现实生活将不可能以愿望实现的方式满足个体的需求,这会对个体产生强大压力,形成焦虑、郁闷、无聊等种种负面情绪。此时,唯有艺术与文学能够作为现实替代品,使人在幻境中获得暂时的愿望满足和情绪宣泄。因而,相较于严肃文学的清醒与现实批判精神,白日梦式的文学文本更容易受到受众的欢迎与追捧。
现实中存在这样的作家,“声誉不那么高,却拥有最广泛、最热忱的男女读者。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一个重要的特点不能不打动我们: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作为兴趣中心的主角,作家试图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赢得我们对这主角的同情,他似乎还把这主角置于一个特殊的神的保护之下。如果在我的故事的某一章末尾,我让主角失去知觉,而且严重受伤,血流不止,我可以肯定在下一章开始时他得到了仔细的护理,正在渐渐复原。如果在第一卷结束时他所乘的船在海上的暴风雨中沉没,我可以肯定,在第二卷开始时会读到他奇迹般地遇救;没有这一遇救情节,故事就无法再讲下去。我带着一种安全感,跟随主角经历他那可怕的冒险;这种安全感,就像现实生活中一个英雄跳进水里去救一个快淹死的人,或在敌人的炮火下为了进行一次猛袭而挺身出来时的感觉一样。这是一种真正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由一个出色的作家用一句无与伦比的话表达了出来:‘我不会出事情的!’然而在我看来,通过这种启示性的特性或不会受伤害的性质,我们立即可以认出‘自我陛下’,他是每一场白日梦和每一篇故事的主角。”[6]根据弗洛伊德的解析,我们可以辨识出,文学产业写作在构筑白日梦时遵循的逻辑是潜意识欲望的满足。
白日梦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困境、不满足、不如意与人类的深层心理机制合谋的结果,也是民间文学、快餐文学、不入流的文学在文学领域中始终顽强地存在着的土壤与逻辑,更是当前文学产业写作与阅读的意趣所在——人们在这里获得对生活中的不如意的遗忘与超越。我们可以批评它的简单、粗俗、重复及其幻觉式的快感,但却无法阻止它的存在。
(三)意趣延宕:能指盛宴的享受
在文学产业写作中,虽然成功与快乐是绝对的价值追求与故事终点,但困难甚至磨难等生存困境、喜怒哀乐爱恶惧等情绪却是梦境与故事的主体。
从叙事逻辑看,批评者视之为负面的“盗墓恐怖、历史宫闱、穿越幻情、颓废边缘、黑道江湖这样一些明显带有猎奇色彩的领域”并不存在什么实际的所指,“作家不再悉心致力于能指与所指的准确匹配,而是有意识地追求和享受能指本身的狂欢化效果”[1]。对能指的浮夸与狂欢的享受,使得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创造出的“延宕”现象在文学产业写作中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被再造出来,并成为当代文学阅读的典型症候。
哈姆雷特的延宕源于对最终的残忍真相的恐惧感,而当前文学产业写作中的延宕却源于对成功、快乐终将结束的不满感,当然,其中也不能排除作者以长度计费的利益驱动。于是,当年的人文主义者的高贵的精神延宕,在能指狂欢与白日梦的共同作用下,演化为普通民众的通俗的幻觉式延宕。其作用是为主人公的最终成功设置能量蓄积、缓冲环节,是为了延长阅读者的快乐时间,是一种为了享受快乐的“延宕”。
二、能指的创生与文学意义的生产
能指的狂欢不仅创造出了现代读者阅读意趣的延宕,而且还意味着能指的自由游戏与创生能力,在能指的自由创生中,文学产业写作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消解“性”与“死”的紧张感、色情意味和恐惧感,创造出生存的另一重境域——欢乐与趣味,营造出瑰丽的梦境。
(一)幻境:能指创生的想象力盛宴
文学产业机制下,能指的以通俗为表征的狂欢不仅能完美地实现其无障碍传播的目的,而且能够使作者以更快的速度、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产业的本质职能——虚构故事上去。虚构,即构造非现实的世界。它不是从文学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意义上截出一个高于现实的非现实世界,以便对人生、社会进行深度认知和批判,并以高度的教益价值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事实上,“从现代产业化的角度观察,与虚构性小说相比,已经垄断学术体系话语权的严肃小说大多并不适合小说产业化的要求”[4]。当前文学批评中对文学产业机制下的文学作品脱离现实的抱怨与批评没有注意到,普通读者、疲劳于日常生活的读者在放松、休闲、娱乐的时候需要遗忘、脱离日常生活以获得一种情感上的短暂的满足与愉悦。因而,要求这些作品具备传统文学理论所要求的高度与深度与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并无二致,难免言不及义。虚构,从语言学角度来观察,指作品中的言语在整体上呈现出能指与现实所指的疏离,甚至能指通过对作品世界的建构为自身构造出仅存在于作品之中的想象性的所指。夏烈在“类型文学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上曾说:“无论是写实的作品还是幻想的作品,类型文学的作者们都有意识地构架出一套作品主题、题材所需要的知识体系,比如宫廷典章制度,比如中医中药,比如宇宙学物理学,比如盗墓史考古技术,比如职场规则,比如金融期货,比如人情世故,等等。”[7]这里的“知识体系”就是言语在作品中为自身虚构出的所指。当然,作品架构出来的,或者说言语在能指游戏中为自己架构出来的所指,并不仅仅限制于夏烈所指出的这些,它的范围要远远大于“知识体系”的限定,从宇宙、世界、历史、社会组织与制度、文化、风物、物种、器具、技术、人种……无不在言语为自己构造出的所指范围内。
在文学产业机制下的写作中,言语的能指从现实的能指与所指的牢固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灵动的、飞舞的符号,能指在想象力的驱使下构造形象、价值、意义,成为言语生产能力的源泉。在现实生活的言语与纯文学的言语中,这种现象作为古典神话、巫术思维的遗留偶有发生,但既不必然(因其不合逻辑),也非必然(因其不合实际)。因而,与以所指为意义核心的普通言语表达相比较,文学产业写作中的言语呈现出以能指为意义生产核心的特点。
(二)梦想秀:文学产业写作的意义生产
白日梦书写是当前文学产业写作意义生产的主要途径与方式,它不但拥有所有的白日梦文本的特点,而且还有着时代的风格与特征,表现出与黄粱一梦、弗洛伊德的白日梦不同的意义指向。
1.与黄粱一梦文本的意义区别。中国古代的黄粱一梦式的仙、幻文学通过对现实的否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否定而宣示、强调、强化纯精神式存在的价值,严肃的如《红楼梦》也难以逃脱这样的意识的笼罩。在当前的白日梦文本中,价值取向却与传统梦幻文学的截然有别:物质现实和人的生存价值获得了极高程度的肯定。一般来说,这种肯定是极度夸张的,主人公“不会出事的”自不待言,其生命的长度也绝非现实生活的几十年,动辄以万年为单位的生命长度,永恒与超脱轮回也屡见不鲜,物质世界被极大丰富为一个奇幻的世界,而主人公的使命之一就是引导、拥有这个世界。与黄粱一梦相比,当前的白日梦文本在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上都完全地现代化、现实化了,它深刻地拥抱着现代世界的质的规定性——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人的生命质量的极大提高。
2.与弗洛伊德式白日梦的意义区别。在弗洛伊德看来,白日梦“很自然地分成两大类。或者是野心的欲望,或者要想出人头地;或者是性欲的愿望。在年轻的女人身上,性欲的愿望占极大优势,几乎排除其他一切愿望,因为她们的野心一般都被性欲的倾向所压倒。在年轻的男人身上,利己的和野心的愿望十分明显地与性欲的愿望并行时,是很惹人注意的。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强调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对立,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事实:它们常常结合在一起”[6]。在当前中国文学产业文本的白日梦中,虽然权利与性是重要的因素,并常常为批评家观察到并施以大量的批评,但是人类的道德品质、认知欲望与把握未来的愿望乃是潜藏于表象之下的结构性因素。在相当多的白日梦文本中,人类命运、社会发展方式、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些传统的严肃文学思考的课题都获得了通俗的、夸张的、长久的思考与描述。以国族的复兴与崛起为目标的文本,更是直接超越了个体的白日梦层面,直接沉浸到了集体无意识之中。因而,与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单纯以性为核心的个体的白日梦不同,当代中国文学产业文本中的白日梦又带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国族意识、集体意识、道德意识。
当代中国文学白日梦文本的另一意义构造是,其中的主人公,大都遵循着这样的身份设定——孤儿或离家追求梦想的少年。他们以朋友为创业、奋斗、战斗的核心伙伴,父母、家族在主人公的履历中没有什么作用,相反,父母和家族的力量一般而言是主人公的对手、作品中的反派的标准配置。这里既显示出主人公的草根属性,显示出主人公孤独与独立的生存状态,又显示出草根式主人公与啃老族、靠老族之间的对立。这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或主动、或被动的草根一族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展演,是现实对梦想的规训,是一场盛大的梦想秀童话剧。
因此,当代中国文学产业中文本所书写的悲欢离合、是非成败、情爱欢愉、无双霸业、星空探索、精神超越、历史改写不仅是极富时代精神与中国文化特色的“白日梦”,而且是当代作者与读者共同营造的一场承载着意义与趣味的“梦想秀”。
注释:
① 参见2010年中南大学文学院蒋金玲的硕士学位论文《网络文学阅读研究》第21页。这里的统计数据是根据网络文学阅读的调查做出的,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产业以小说为主要体裁,其中网络小说市场又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势,结合我们在生活中对文学阅读的观察,我们认为以18-39岁年龄段为文学产业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合适的。
[1]王一川.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J].文艺争鸣,2004(2):15-17.
[2]网络商业写作新手指南之大纲设定[EB/OL].[2014-12-03].http:∥forum.qidian.com/ThreadDetail.aspx?threadid= 90000025.
[3]周军伟.在独白与虚无之间:巴赫金的生存美学[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4.
[4]樊 柯.小说产业化的动力及其影响[J].中州学刊,2013(7):163-167.
[5]彭松乔.品牌榜单里的中国文学问题:以“中国作家富豪榜”为例[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6):28-33.
[6]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M]//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林骧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18-319.
[7]刘莉娜.类型文学:不只是娱乐和消费[J].上海采风,2013(9):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