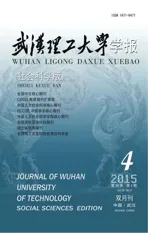由“小众”到“大众”:《圣天门口》从小说到电视剧之变*
2015-03-18沈嘉达
沈嘉达
(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48集电视连续剧《圣天门口》是基于著名作家刘醒龙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圣天门口》而改编。这部“本来获奖呼声很高”[1],只是在“七进五”最后关头落选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在2005年12月13日于北京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称赞。
对电视连续剧《圣天门口》而言,其导演是曾导演过《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多部作品的知名导演张黎,其编剧是以“解构主义的反讽特色”作为“金字品牌”的知名编剧邹静之,其参演演员则汇聚了王庆祥、马少骅、宋佳、段奕宏、黄志忠、柯蓝等著名演员。显而易见,该电视连续剧打造的总体阵容不可谓不强大,不可谓不豪华。然而,电视剧《圣天门口》却遭遇到现实的冷遇。“据央视索福瑞调查公司公布的数据,《圣天门口》的收视率没有达到60%,连同时段电视剧收视率前五都没有进,被《加油妈妈》、《新女婿时代》等家庭剧打得无招架之力。”[2]诸如此类的吐槽比比皆是,让这部费时五年、号称投资5000万元的“大制作”处境尴尬暗淡。
一、小说的《圣天门口》:新历史观下的现实主义抒写与史诗气象
我们先从原著说起。据刘醒龙自己交代,一百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圣天门口》始作于1999年10月,成稿于2005年元月,其间三易其稿,光废弃的文字就将近20万字。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六年间作者反复磨练,写垮了三台电脑。
《圣天门口》一经面世,便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巨大反响。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炯认为《圣天门口》是“民族文化的精品,堪比《白鹿原》,有史诗性气象”;著名评论家何西来称之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里程碑式著作”[3]。如此高的评价,直指“史诗”。那什么样的作品能堪称“史诗”呢?
著名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在我看来,真正的史诗绝不是宏大的历史事件与复杂时空的叙事拼凑,它必须立足于创作主体丰沛深邃的思想,立足于创作主体诗性气质的提炼,立足于作家内心卓尔不群的精神品格和艺术胸襟。……这部作品的确超越了某些既定的历史经验,超越了某些共识性的价值判断,在承续民族叙事的优秀传统中,既渗透了作家对历史的拷问深度,又彰显了许多具有飞翔姿态的叙事细节。也就是说,它既有‘史’的深层考量,又有‘诗’的审美韵致。同时,它还非常清晰地凸现了作家立足于仁爱和善与人性救赎的文学信念。”[4]评论家施战军也毫不吝啬地认定《圣天门口》是“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圣天门口》是值得称道的一部。”[5]
《圣天门口》这部小说值得我们关注,并不在于其一百万言的巨大篇幅和50余个人物、70余年的历史跨度叙写,也不在于同样运用了雪杭两个家族的恩爱情仇模式来进行历史叙事,更不在于作者掺杂其中的鄂东方言的点缀,甚至我们把作者取材于《黑暗传》并由说书人董重里陆续说出的中华民族历史,都可以看作是一种附加注释……那么,《圣天门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难以释怀呢?我们认为,是作者的历史观以及在这种历史观指导下的人物刻画与描写。王春林指出:“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在处理历史事实时一个值得充分肯定之处,则正在于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种外在的意识形态的规限与控制。相对于‘革命历史小说’而言,在更大程度上尽可能地逼近了历史的本相。”[6]而这种对于“历史本相”的“逼近”,当然离不开小说人物的全新塑造。
譬如梅外婆。那么,“梅外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用小说中在汉口花楼街德国人开的医院里当过护士长的梅外婆最著名的一句话来加以诠释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梅外婆说:“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7]63在梅外婆看来,认定“福音”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境界——不只是与人便利是“福音”,受人侮辱如能消解他人的暴力天性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福音”(基督教义的引入)。例如,同样主张非暴力的梅外公被施暴者杀死在街道上,书中写道:“梅外婆凄美地低头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福音’到了!她将这话作为横批写在那副白色挽联上。”[7]67“梅外婆要(外甥女)雪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杀死梅外公的人,是他们用灵魂作了铺路石,垫在梅外公的脚下,送梅外公上了天堂。”[7]68小说写到,即便是棺材铺老板林大雨有意将梅外婆反锁在家致使梅外婆被偷袭的日本人集体践踏,梅外婆也在事后反对众人去找出这个祸害自己的人,自身忍受奇耻大辱,坚定地活下去,并将她的“福音”哲学实施开来。深受其影响的外甥女雪柠,同样以慈悲为怀。当驴子狼成群而来不肯离去之时,雪柠主动将自己爷爷——雪大爹的尸体抛给驴子狼,以换取天门口的宁静和天门口人的幸福。其实,雪氏一门女性从爱栀到雪柠,再到雪荭、雪蓝,都是梅外婆精神的传续载体。小说就是以梅外婆(雪氏一门)的慈悲、宽容与杭氏一门(从杭大爹到杭氏四兄弟)形成鲜明的对比。[8]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逻辑?
显然,刘醒龙是一位有“思想”的作家。抛开刚入道时的现代派小说集《异香》不论,刘醒龙始终以现实主义为怀,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入的思考,譬如新现实主义作品《分享艰难》(积极介入当下),譬如“问天”之作《弥天》(揭露乔家寨修水库弥天大谎事件),譬如《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对“生命”本质的拷问,譬如《女性的战争》对战争年代的诡异和生命的脆弱无常的审视,譬如《威风凛凛》对“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深切同情和对流氓无产者的无比痛恶等。可以说,《圣天门口》作为刘醒龙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其思想精髓的集大成者。
刘醒龙曾夫子自道:“我用一百万字写了各种各样的争斗,却没有使用描写那段历史一贯使用的一个词:敌人!一个民族间的内战,不管是正义或者非正义,都不应该再由后人来继续互相称呼为敌人。这种时候,写作者的立场,应该是儿女们面对父母间纠纷时的立场。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其实是让人心里有一种耻辱感。在这种至关重要的细节上,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圣天门口》是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在小说中,我所写的是人物,而不是阶级;是对和谐社会和和平崛起的渴望,而不是历史进程中的暴力血腥和族群仇恨。”[9]无独有偶,刘醒龙在《母语写作的宿命——〈圣天门口〉未完的话》中再次强调:“于我最关心的还是作品中‘敌人’一词。如果说《圣天门口》有出众之处,其百万字所描写的近代中华山河破碎、血雨纷飞、生灵涂炭,却没有一次使用‘敌人’一词。当我意识到作为后人,我们不可能再将先辈同胞间的乱战与争斗用‘敌人’相称,心里就有了此番写作的分量。”尽管他严于自责——“在初版的《圣天门口》中,有些文字在编辑过程中被重新用‘敌人’来表述与形容。这样的失误,当然是我的不主动沟通造成的,我应当在编辑之初,就将自己的思考告知责编。”[10]但其对出版社肆意篡改自己意图的不满已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这显然与刘醒龙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有关。刘醒龙说:“对史诗的写作历来都是每个作家的梦想。在当下,更是成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的责任。因为有了《红楼梦》,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眼中,被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阉割过的历史,才有了迷人的才情。一部好小说,理所当然是那个时代民间的心灵史。做到这一点,才是有灵魂的作家。我写《圣天门口》,是要给后来者指一条通往历史心灵的途径。……我写历史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认识现实。”[11]诚然,《圣天门口》是刘醒龙的天门口,从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这70年的风云变化,作者并没有循规蹈矩,沿袭既有的写作路径走一条平坦的大道,而更愿意从新历史视角,从民间角度来解读这个大千世界。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小说中独特地呈示了神性附身的梅外婆及其一家,真实表现了“不坚定”的革命者董重里,还原了草莽英雄杭九枫和将双胞胎女儿分别嫁给共产党杭九枫与国民党马鹞子的“两面派”段三国形象,推出了兽性加人性兼具的日本人小岛北等。从叙事效果看,“我们在作品中读到的,就不是革命(暴动)必然要发生的历史逻辑,而是已经发生了的革命,如何改变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过程。这就避免了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演绎历史事件,而是让历史事件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酵母。毕竟,日常生活是历史的常态,芸芸众生是日常生活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回到了‘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本位。”[12]
二、电视剧的《圣天门口》:传播策略下的草莽英雄革命历史传奇
现在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分析一下48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圣天门口》了。
包新宇在《改编的“三重天”——评电视剧〈圣天门口〉的改编特点》一文中指出:电视剧与小说原著“精神内蕴契合”,“原著站在什么样的历史立场和价值角度诠释人物和历史,主创者就不能偏离这个基点。在这一点上,《圣天门口》的主创们读懂并尊重了原著作者的历史观点,借助影视的艺术手法,还原了原著中的历史精神,其核心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圣天门口》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与一些‘改编作品’最大不同即在于,它没有为迎合观众尚需提升的观赏心理而任意篡改原著的基调。”[13]
真的如此么?我们有理由怀疑包新宇根本置原著精神的内蕴不顾而信口雌黄!笔者想问:电视连续剧《圣天门口》的主创们真的读懂并尊重了原著作者的历史观吗?电视剧真的还原了小说的“历史精神”吗?原著的核心果真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电视剧真的“没有为迎合观众尚需提升的观赏心理而任意篡改原著的基调”吗?
就笔者看来,除了显在层面(情节等)的“改变”外,电视剧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创作主旨与原著的南辕北辙,泾渭分明。说白了,就是化“神奇”为“腐朽”,将原著作者的“思想”放逐到剧集之外。正如前面所言,作为刘醒龙最重要的思想集大成之作的原著,凸显出了作者非同寻常、有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个人历史观。他的对于革命、暴力、社会前进动力、革命效应等的“思想”的彰显,正是他的作为“有灵魂的作家”之“责任”所在——“是为了更有效地认识现实”,“给后来者指一条通往历史心灵的途径”。
而电视剧导演张黎显然明白这一点,因之“除了不能拍的都拍了”——什么东西能拍?什么东西不能拍?什么东西好拍?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样一个并不深奥的现实问题。
电视剧《圣天门口》先验性地在理念上进行了“位移”。电视剧完全改变了原著对于“革命”、“暴力”等的思考,而演变成了符合意识形态诉求的寻常的革命历史电视剧。可以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一部关于草莽英雄杭九枫在“革命导师”傅朗西教导之下不断“成长”的革命故事。我们暂且列举一例:以《国际歌》作结的电视剧获得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从朝鲜战场上返回的杭九枫终成正果,与傅朗西、阿彩等人一起,享受着革命胜利后的喜悦,以此证实革命道路的成功和暴力推翻旧制度的功德圆满。而小说结尾则是,“文革”时期正在被红卫兵批斗的杭九枫,在数十年的“草莽”冲撞之后已经接受了雪家精神的浸润——小说“曲终奏雅”写道:
雪柠于是对杭九枫说,就像当年杭家人刁难雪家人的那幅对联,“谁最先被历史所杀”只是上联,还有下联,在历史中谁是最后一个被杀死的?杭九枫想也不想就说,只要雪柠同意,他愿意成为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雪柠觉得杭九枫说反了,她才愿意成为自己想到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后来,他俩异口同声地说,最想成为这个答案的人是梅外婆。[7]1197
显然,这个结尾除了再一次张扬梅外婆的基督哲学、表达对未来的忧虑之外,还暗示着代表暴力、血腥、邪恶的杭九枫向代表着隐忍、宽容、慈悲的雪家的回归。较之小说与电视剧,虽曰同名,却天上地下,实则不可以道里计。
在《国际歌》声里,电视剧中的董重里同样享受着生死的喜悦,而小说则颇有意味——从前的革命者、指路人,当然也是以历史说事(说书)的董重里,竟然在革命成功之后,“和(曾是妓女的)圆表妹真的跑到香港去了”[7]1188。书中写道:“他在寻找进一步去法国的时机”。法国曾经是暴力革命的发源地,巴黎公社等就是革命的样板。可是,革了一圈命的董重里需要重新分辨革命之路——他在怀疑自己和自己曾经的“革命”。这真是耐人寻味!
小说中,“革命导师”傅朗西是如何死的?他死在了“文革”的批斗会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对着他哭喊:“老傅哇老傅,没有你时,我家日子是很苦。可是,自从你来了,我们家的日子反而更苦!”[7]1184此时的傅朗西非常激动,说了三次“惭愧”,反思“这么多年,自己实在是错误地运用着理想,错误地编织着梦想,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紫玉离家之前说的那一番话真是太好了,革命可以是做文章,可以雅做,可以温良恭俭让,可以不用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7]1185最终,众人一齐踩过傅朗西的身体。
可以肯定的是,刘醒龙主张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或然”。可是,这些内容导演能拍吗?不能。那么,导演张黎和刘淼淼又是如何规避这些内容的呢?很简单,其一,将电视剧的起止时间厘定在1927年到抗美援朝结束,这样,就有效地回避了大跃进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运动,从而使得悲剧性的故事变成了喜剧式的表达;其二,将刘醒龙所谓(当然也是他所追求的)“民间的心灵史”改弦更张为革命历史传奇。当然,故事情节、人物冲突乃至细节安排等随之作了取舍。我们看到,本来“原生态”的革命、伴生式的家族恩仇、原欲式的破坏(暴动)等深层次的探索,统统归于传统的“党的领导”、“革命青年成长”模式,这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路径。只不过,革命领路人由卢嘉川、江华、林红变成了傅朗西、董重里等。在电视剧中,“共产党”、“革命”、“为穷人”、“翻身”、“入党宣誓”等不断呈现,强化着受众的神经感受。本来在小说中“爱情”源于情欲,一开始,八岁的杭九枫就发誓要娶因癞痢头而被雪茄抛弃的广西女子阿彩,其后,杭九枫与阿彩的分分合合也都离不开这种原始情欲。但是,在电视剧中,“爱情”成了革命的伴生物——阿彩与杭九枫的分离、与老资历的共产党员王巡视员的结合等,都与革命有关,而不只是自然产物。为了强化这一点,电视剧还设置了傅朗西与麦香这一对革命伴侣(小说中,麦香形象模糊),加入了第三者林大雨。林大雨挚爱麦香,但他作为“契卡”(埋伏的地下党),成全了傅朗西与麦香而牺牲了自己。实际上,在小说中,麦香就是一小酒店主,林大雨更是残害梅外婆的“坏人”。更可笑的是,本来在小说中,雪家第三代雪柠留恋的是浪漫的气象学家柳子墨,“24朵白云”是雪柠理想的纯洁象征,但在改编后的电视剧里,雪柠却变成了坚定的女革命者,爱上了职业革命家傅朗西,并有意骗取了自卫队马鹞子和吕团长的军费,从而导致国民党军队溃败,雪柠自身也壮烈地死在了冯旅长的枪下而成就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孙百卉称电视剧“对人物形象及情节进行了较大调整,提炼了主题思想,使之更符合当下大众传播的内容要求”是切中肯綮之言。现在看来,最不能容忍的是,电视剧去掉了小说中的神性人物梅外婆,而梅子(小说中的爱栀)却缺乏梅外婆身上的光辉与神韵。其道理在哪里呢?导演刘淼淼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按原小说去拍是绝对无法通过审查的。”[14]为了获得认可,就必须符合“规范”;为了获得观众,就必须制造传奇。我们知道,雪茄在小说中几乎是隐形人物,且在大革命刚刚到来之时,就作为暴力的祭祀品自甘与爱栀一起被天雷殛死,从而显示“革命”对百姓的摧残;电视剧中雪茄却成了“后发”志士——当日本人使用细菌战并打入天门口之时,雪茄竟然连带自己一起,用细菌将气象小组六人全部毒死(这中间只有一人被设置成间谍,其余的都是无辜者)。董重里在小说中就是一介新质,是作者对暴力革命的反思产物(退出暴力),电视剧中却让其秉承一贯的革命激进特质,在性格上与傅朗西多有重合,多多少少消弭了自身存在的属性。再如,小说中,杭老大形象近无,定位飘忽(强化的是老四杭九枫),电视剧中杭老大却成了独立大队大队长,并为保护常守义、麦香等人不受王巡视员之死牵连,而承担责任自甘被革命者所杀!黄水强在小说中只是普通的独立队员,电视剧中先是向冯旅长假投降,后来又真投降,最后成了日本人的间谍等。所有这一切设置,说到底,就是为了获得“大众传播效果”,吸引眼球,如此而已。这已经完全不是小说的主旨和意蕴了。是谍战迷雾,是谜案追踪……谁又能说不是呢?
三、《圣天门口》的小说之“得”与电视剧之“失”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无疑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其“要义”一直延续到21世纪。然而,曾经作为“新现实主义”代表的刘醒龙有着自身的现实思考。在与汪政的文学对话中,刘醒龙认定:“小说与绘画不一样,小说从来就不是活在沙龙里,小说是仰仗民间而生存的。……现实主义文学如同我们的家父家母,谁都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们,实际上,许多人连父母的基本生活习惯都不清楚,直到他们告别人世了,才后悔得哭天抢地。中国的现实主义需要在课堂上彻底正名,只有摒弃对现实主义文学鱼目混珠的解读,恢复现实主义的尊重与尊严,文学才能真正地融入当下社会生活。”“我曾经有过历史是主观的早期写作阶段。随着文学能力的成熟,主观的我依然还在,其成分早已全部换成了在民间中广为流传的客观细节。当客观细节真实到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时,就会自动变化成伟大的主观。”[9]在刘醒龙看来:第一,我们过去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功利化;第二,现实主义存在于民间,至少民间现实更真实;第三,现实主义离不开“细节”的真实。
不可否认,本质上作为案头文学的“小说”(不是“故事”)与讲求大众传播效果的电视剧是有根本区别的。毋庸讳言,在当今社会,电视剧尤其是电视连续剧,上有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有制片人的收视要求,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之下,电视剧作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张黎等选择《圣天门口》作为题材蓝本,本身就有“讨巧”的嫌疑。我们一点也不想否认导演所作出的艰辛努力,譬如摄影出身的张黎(像张艺谋一样)对影视成像的唯美追求,将人物的心理活动采用影像化表达,多视角事件闪回等,确实给电视剧带来了“文艺”效果,然而,就笔者看来,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根本就不适合拍摄成电视剧,因为小说的“离经叛道”式的主旨,对历史事件的民间表述,对情欲的原生态呈现等,都不适宜用电视剧这种大众媒介显现。如果一定要改编成大众“读物”,当然就要既符合意识形态诉求又切合普通民众尤其是家庭妇女等的欣赏习惯,这样,“文艺”、“思想”常常就变成了一堆“脂肪”,吃力不讨好。从这个角度讲,电视剧《圣天门口》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而可以说,它要么为文艺而死于“小众”,要么为“大众”而死于文艺。
著名学者陈思和认为:“民间世界自身并不生长知识分子的品质,只有当知识者将主体精神投诸民间时,民间才可能产生出与权力意志以及在其控制下的生活之流相抗衡的现实力量……给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的解释方法,但这‘另一种’的解释既然还是由知识分子来进行的,它仍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的某种思考特点。也唯有如此区别,才能使九十年代民间文化的意义不与传统的民间文化等同起来。”[15]即,“民间”的意义并不直接存在于民间本身,“民间”只有获得知识分子的精神投注才会被激活,从而获得“另一种”样态及其价值。
刘醒龙的意义即在于此。《圣天门口》正是在刘醒龙作为知识分子所发散出的批判性,附丽于从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七十年中国现代历史本身之时,才获得了不一样的意义。反观电视剧,作为“知识分子”的导演与编剧,却主动迎合了大众需求,直接的后果便是电视剧《圣天门口》为求得“收视效果”(制造传奇)而导致的“硬伤”比比皆是:本来,小说中异常沉重的大别山革命老区错误的清党事件,电视剧中却变成了对上级派来的王巡视员之死调查案例,长达四集之多!严肃的历史悲剧幻化成了通俗的案件调查。小曹、管团长的身份置换,给人以神出鬼没之感,犹如谍战剧。
小说中写到了山中的地洞,可以躲避日本人,而在电视剧中,地道竟然藏在了教堂及杭家与雪家的地下,绵长宽大,却无旁人知晓。更可笑的是,日本人投下手榴弹让近在咫尺的林大雨、阿彩等人毫发无伤,却能炸通段三国家地洞与大地洞的连接,从而让林大雨等人从容逃出,日本人只会干瞪眼!
虽然电视剧中也承认在中国腹地大别山里,20世纪30年代的自行车是稀罕物,可是独立大队竟然能组成自行车突击队,突入天门口镇抢粮,并基本上全身而退,比电视剧《还珠格格》还要传奇,真是不可思议!
还有,子虚乌有的日本飞机被打下,天门口人竟捉住了日本飞行员,而这个日本飞行员还是国民党军统争取过来的“反战分子”!第37集中,杭九枫竟能从冯旅长处只身偷来一门迫击炮,打退国民党军!当自首的杭九枫要被已经联合抗日的冯旅长枪毙时,执行枪决任务的阿彩对随行的国民党军官说:“给我一刻钟,我要给他留一个孩子。”就是说,要在卡车上与杭九枫行房,而车外就是成群的行刑士兵!日本鬼子为寻找被捉住的飞行员,占领了天门口镇,冯旅长受伤被隐藏在雪家地道内。由于黄水强的告密,日本鬼子包围了雪家,临近分娩的阿彩顶替为冯旅长包扎急救的梅子而被日本人识破,阿彩差不多就在日本人的面前生下了孩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无意抹杀电视剧制作者的努力,也无意否认电视剧本身的艺术属性与小说的区别,而只是想说,这是一部与原著没有精神关联的电视连续剧,不过是张黎、刘淼淼导演的一部革命历史传奇而已。
[1]王春林.位卑未敢忘忧国[N].中国教育报,2011-08-28(04).
[2]《圣天门口》遭遇“滑铁卢”[N].齐鲁晚报,2012-11-08(A21).
[3]湖北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文学“双冠”的乡土情怀[EB/OL].(2011-08)[2014-07-20].http://news.cnhubei.com/hbrb/hbrbsglk/hbrb04/ 201108/t18058 02.shtml.
[4]洪治纲.“史诗”信念与民族文化的深层传达: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J].当代作家评论,2006(6):140-147.
[5]施战军.人文魅性与现代革命交缠的史诗[J].文艺争鸣,2007(4):51-54.
[6]王春林.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J].小说评论,2005(6):49-55.
[7]刘醒龙.圣天门口:第1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周 毅,刘醒龙.觉悟:关于《圣天门口》的通信[J].上海文学,2006(8):62-71.
[9]恢复“现实主义”的尊严:汪政、刘醒龙对话《圣天门口》[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2):81-83.
[10]刘醒龙.母语写作的宿命:《圣天门口》未完的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2.
[11]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N].新京报,2005-07-10(A20)
[12]於可训.读《圣天门口》(修订版)断想[J].南方文坛,2008(4):72-75.
[13]包新宇.改编的“三重天”:评电视剧《圣天门口》的改编特点[J].中国电视,2012(12):44-46.
[14]《圣天门口》导演刘淼淼:国产剧需要更多类型[EB/OL].(2012-10-26)[2014-07-20].http://yule.sohu.com/ 20121026/n 355762458.shtml.
[15]陈思和.犬耕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