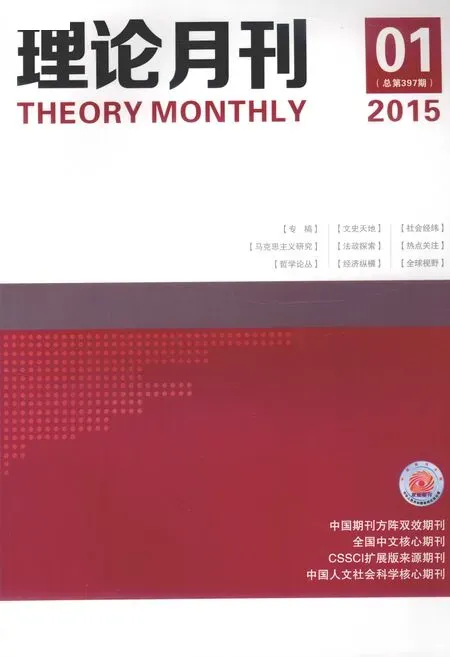卢前《八股文小史》的学术史意义
2015-03-17李鸿渊
□李鸿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卢前《八股文小史》的学术史意义
□李鸿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卢前的《八股文小史》强调八股文为明代文学之胜,主张其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观点,代表了20世纪反八股思潮下的另一种声音。该书第一次对八股文的渊源、结构、演变、衰微及各时期的主要特点等,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和附录的资料,亦很丰富,对于八股文的进一步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该书虽然篇幅不大,但是最早用现代方法专论八股文的著作,在科举学史上具有开山之功。
卢前;八股文小史;科举
卢前(1905-1951),字冀野,一生多才多艺,著述丰硕。其《八股文小史》,约5万字,原是1932年在暨南大学的讲稿,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国学小丛书”印行。1996年,东方出版社列入“民国学术经典文库”,附于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之后。2006年,中华书局编印“冀野文钞”,该著列入第二辑《卢前文史论稿》。2011年,岳麓书社将其附于《明清戏曲史》之后,列入“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印行。全书共七章:帖括经义之变体、八股文章之结构、正嘉以前之演进、隆万以后之作风、清初八股名作家、八股文体之就衰、关于八股之文献。本书不仅介绍了八股文的渊源与作文方法、历史衍变及特点,还收录了大量有关八股文的文献。作为第一部八股文史专著,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开山之功不容忽视。
1 强调八股文为明代文学之胜,主张其在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八股文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集众体之长,别具一格,“是中国各种文学技巧的结晶和集大成者”。[1]江国霖在《制义丛话》序文中指出:“制义者,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2]卢前在“牟言”中提及:“传奇与八股文为明代文体上两大创作,既别作《戏曲史》,复草此七章。”显然,他继承了业师吴梅的观点:“有明一代,止有八比之时文,与四十出之传奇,为别创之格。其他各学,非惟不能胜过前人,且远不如前代,无论其他。”[3]
八股文被废止后的最初十余年,很少有人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八股文作为旧文化的象征之一,遭到猛烈抨击。不过,1923年恽代英在《八股》一文中认为:“若干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4]进入1930年代,人们开始以比较平和、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它。1930年5月,周作人在《骆驼草》上发表《论八股文》,提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5]以他作为文学家的敏锐眼力,指出了八股文特有的价值。1934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中更是认为:“明初八股文渐盛,乃能与骈体、诗赋合流,能融入诗词的丽语,能袭来戏曲的神情,集众美,兼众长,实为最高希的文体。”[6]钱基博的《明代文学》,专设第四章“八股文”,认为治明文学者,不可不顾八股文:“自科举废而八股成绝响,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明贤抉发理奥,洞明世故,往往以古文为时文,借题发挥,三百年之人文系焉”。关于编写此章的目的,作者明言:“遂为明其流变,著其名家,以俟成学治国闻者有考焉。”[7]陈柱《中国散文史》中,将明清散文置于八股文的大背景下,强调了八股对散文创作的影响:“明之文学,诗与文多不外因袭前人,不特不能过之,且远不相及。惟传奇、八股,为其所创造,而八股尤为普遍。降至清代,取士仍用八股。故明清两代,实可谓为以八股为文化之时代焉。此时代之古文,实受八股之影响不少;盖无人不浸渍于八股之中,自不能不受其陶化也。”[8]可见,作为一种极端化的形式主义文体,八股文自有其艺术性。正如黄霖所言:“八股,作为一种表现形式,也有它的美的内核。用这种形式,也能写出富有个性和独特见解的文章。……毛病是出在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而竭力将它绝对化,从而使它僵化。”[9]
卢前对八股文在文学史上乃至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给予了明确肯定,“弁言”中说:“八股文有五百年历史,在文学史上自应占有相当之地位,治文学史者固不能以一时之好恶而抹杀之也。”又在第一章中指出:“顾八股文为学所践已久,科举废后以至于今,垂四十年,此体弃置,已无人道,惟自通识观之,盖不平之甚者也。造文学史者,故应还其应得之地位。”针对当时对八股文的全盘否定,他引述了刘鉴泉《四书文论》中的观点:“制义之足为知言论世之资,固同于策论、齐于诗词,其尤且足上拟诸子,远非律诗、律赋、四六之所能及。今反谓为不足与于立言之伦,岂为平乎?”并认为其论述“最为知言,其通论部分,至精核,可作八股文之价值论观”。而后进一步引申道:“是以治八股文者,不独须谙其体制,因其内容,且可知当时之学术,非特为文学史料已也。”又在第三章的开篇,引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五中“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以为“以八股文代表明代文学,其论允且当”。显然,“这在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中,可谓是慧眼独具了”。[10]
八股文作为风靡明清时代的一种应试文体,自科举制度崩溃后便迅速衰绝,成了令人不甚了解,乃至深恶痛绝的文体。在长期而普遍的冷落、鄙弃中,卢前此作就显得格外难得了。他意在通过对这种特殊文体的介绍,唤起国人对其形式上、技巧上的注意,正如他在“牟言”之末尾所希望的:“近日士夫,渐稍稍注视于此道,知他日必有一部完备之《八股文史》,然则兹编,其嚆矢耳。”现在看来,“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是第一部八股文史,在那个时代敢于为八股文‘树碑立传',是需要有一点学术胆识的”。[11]
2 第一次对八股文的发展历程及特点,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
第一章,作者探讨了八股文的起源,指出其为帖括经义之变体。
第二章介绍了八股文的结构,细致剖析了八股文是如何写成的。而该著重点,是突出“史”的线索,对数百年八股文的演变,按时代顺序进行了整体描述,既有时代风格之宏观把握,又有代表性作家作品之评述。
第三章中,作者指出明代正、嘉以前的制艺“标清真雅正为宗”。“制义开科,自洪武三年始。而科举条格,备见于元年之诏”,“士既无不出身于科举,即无不能为制艺”,“明初之制艺,其体犹未备,但求平淡,能自圆其说”,“当时之以经义取士,命题但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乎人伦治道者,以求真才,非欲以难士子也”;而至“嘉靖一朝之作者,大率在八股文外,亦有所表见,如唐荆川、归震川、茅鹿门,以至王元美,皆卓有声名于文学史者”。引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云:“明人制艺,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谨守绳墨,尺寸不渝。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作者总结道:“八股文演进至成、弘而体备,至正、嘉而登峰造极,不可谓非最盛之时期。”
第四章开篇,作者引录《明史·选举志》曰:“论者以明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而后引用王景盘《制艺章稿》中的观点,“论隆庆、万历后以至明末之八股文,以为有五特色:一曰认题之细。文之精美者,必先察题,以期其不蔓不支,俾详察周虑,以见其精神。二曰意测经旨。文既细密,于经文乃尽心力以深究之,揣摩语调,仿佛口气,务期克尽代圣立言之义。三曰无施不可。虽然,制艺有一定程式,有对仗,有犯上侵下之律,而作者未尝因此自限,每能于言外逞其辞锋也。四曰遣词之美。格律最严之文体,往往有绝佳之作品;前者谓从心思上出奇,此则指以文字炫美者言也。五曰不着边际。八股文既以代圣人立言为归,所陈述皆哲理抽象之言;作者每渲染适如其分之辞,出语则面面可通,为敷衍成篇之诀。聊以造句上技巧,为引人注目之具。于无可如何中,为此出奇求售之计,用心诚良苦矣!其结果遂使举国之人,养成一种不求甚解之恶习,以似是而非之说相标示,少彻底之思想,无分析之能力,其影响于后来者不小,是固八股文之弊也”。到启、祯时期,明代八股文趋于没落,而场屋外之八股文和民间选本异常繁荣,官方权威受到挑战。作者引录郑灝若的观点:“大抵天启之文深入而失于太格,崇祯之文畅发而失于太浮。”
至清代,八股文体式虽已定型,但仍有自己的风格,即以义理取胜,注重学术考证。清代八股文的发展,以乾隆中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五章开篇,作者指出:“八股文至明末,臻无施不可之境,在技巧上殆蔑以加矣。入清以后,因圣祖好学术,知制艺之足以羁縻人士,乃益倡导;文章虽不足以超越前明,而在义理上实有进步;其演为考证之学,启朴学之风,讫乾隆朝之中叶而大振。盖所求者在于经,八股文与之同也。举国之人,皆以穷经为制艺,则不复效明代之以新奇耀试官之目,而影响于学术者甚深。及其后,禁学者之博览,以《朱注》为之准绳,其风始渐杀。以是就八股文体言之,明人已造其峰极,而以内容关系学术者,则清人之八股文然也。”此足以概括此时八股文风的整体状况。以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的勃然兴起,不可避免地浸染着科举考试。作者引录林畅园的话:“任钓台先生深于经学,发而为制艺,虽小题亦必用考据之法行之。”于此可见乾嘉考据之风对八股文影响之巨。
第六章开篇指出,清代八股文与明代有六点不同——“一曰在义理之求胜。如韩菼《寒碧集》、方舟《自知集》等,识力透到,往往足补传注之不及”;“二曰识字与正义。如阎若璩将明名家制义中错解题、误用事者,标为一帙”,就是将清人的考据之长用于八股,纠正明人的错误;“三曰人文一致。管世铭曰:‘前人以传注解经,终是离而二之,惟制义代言,宜与圣贤为一,不得不逼入深细。谓朱子之前已有时文,其精审更当不止于是也。'如徐用锡之《知者乐水章》文、陈鹏年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文,皆品节存诸文章,表里相符之作也”;“四曰搜奇。制义既以经说为骨干,而学者以读书之富,不限于群经正史,乃演为辑逸书、诸子书,以逮小学、校雠、金石、版本。……虽有功于学术,而制艺之文体隳矣”;“五曰旁务。陈用光曰:‘近人作时艺,每以包罗史实为长,而词句遂搀杂后世史迹,恐非所以代圣人立言之意。'弃经而之史者,实为一大枝派,如崔述、赵翼、章学诚、俞正燮,其著者也。此风在乾隆中叶以后而日盛”;“六曰言辨。一题入手,巧用心思,一义数篇,篇各一旨。其中标尚独特,匪夷所思。于是心灵浚沦,竞立一说,所谓能翻新出异者矣”。最后总结道:“凡此六端,多在内容。且当时古文之风已炽,学者或引而治其专业,或更肆力于古文,而八股文日趋于巧薄,亦稍稍衰矣。”
道光以后,文道衰落。作者引“吴瞿安先生序先太史(讳崟,字云谷)《石寿山房集》”的话:“清乾嘉间,登上第、占巍科者,咸正大弘畅,有扬鸾和铃之度;迨光绪之季,放纵以露才,渔猎以炫博,而国势乃日益不振。”同治朝已觉察此弊,谓“近年以来科场或抄袭肤词,或抄录旧文,于士习文风大有关系”;为正文体,于同治十一年明谕考官:“衡文务当认真校阅,以‘清真雅正'为宗。”[12]考官衡文选士虽仍以“清真雅正”为基本准绳,但已无法遏制颓靡之风。为求文章能在千篇一律之中博得青睐,士子们应试竞尚丽辞,以耀试官之目。作者认为晚清八股之弊,约而有四,即“一曰尤王派之弊。尤侗、王广心以辞藻为制义,所以竞求售也”;“二曰雷同之弊”;“三曰文陋之弊。士不读书,以滥调轻而易举,籍以博科名”;“四为截搭题之弊。截搭题本以防熟记陈文,以《四书五经》之文有限,出题已殆遍及,非经倒置,不得出新;于是强为割裂,勉合为一语。作此题者,亦牵强附合以完篇,文乃日益恶劣”。最后指出,“凡此四弊,使八股文仅能存一躯壳,虽欲不亡,其可得邪?神之不充,貌亦难寄,一切文体皆然,又不独八股文如是也”。
3 引用的文献和附录的史料,颇具参考价值
在“牟言”中,作者有感于“八股文经三四十年之摧残,在今日已有文献不足之叹,是篇聊述大凡,不能详尽也”。所以该书的写作,大量引录各时代经典的八股文作品及相关评论,“让自己的观点通过丰富的材料表现出来”。[13]不足的是,所引评论大都没有注明出处,且行文中引录作品或评论过于频繁,以致其间没有多少作者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缺失。无怪乎有研究者批评它“只将《制义丛话》中的一些资料,按书中所列历朝八股文名家名单,加以连缀而成,毫无新意”。[14]
作者不仅在文中大量引述前人或同时代人关于八股文的评说,而且第七章专门述列清代各种别集中有关八股文的序跋文章,篇目达数百种之多。作者指出:“凡此文字,皆足以补益八股文之史料,果加以钩稽,厘分子目,使成专编,亦文坛应有之事也。虽然,是非此书所能尽已!”可见作者十分重视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应用,这也是当时治文史的一个传统。无疑,“这对于八股文的进一步研究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15]
总之,卢著并非要为八股文翻案,而是抱着尊重、清理历史的态度,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文体,审视其确切之地位与作用。这种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确如作者在第一章中引章学诚《叶鹤涂文集序》所言:“二十年来,举及时艺,辄鄙弃之为不足道矣。夫万物之情,各有其至,苟有得于意之所谓诚然而不为世俗毁誉所入,则学问文章,无今无古,皆立言者所不废也。”作者赞同“此论可谓明且清矣。言之有物与否,固不在于体制”。该书“虽然篇幅不多,但是最早一本用现代方法专论八股文的著作,在科举学史上具有先导价值”[16]。可惜此后,长期少见有同类著作之出现。成书于1986年的王凯符《八股文概说》,对八股文作了较全面的描述,但对其态度还是否定的。直到1990年代,启功、张中行、金克木等老一辈学者陆续发表长篇论文《说八股》、《〈说八股〉补微》、《八股新说》,才开始逐渐转变人们对八股文的看法。
[1]邱江宁.八股文“技法”与明清戏曲、小说艺术[J].文艺研究,2009,(5):82.
[2]江国霖.制义丛话序[A].梁章钜.制义丛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吴梅.顾曲麈谈[A].王卫民.吴梅戏曲论文集[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97.
[4]恽代英.八股[A].恽代英文集: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9-390.
[5]陈为民.周作人文集[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77.
[6]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7]钱基博.明代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109.
[8]陈柱.中国散文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79.
[9]黄霖.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A].章培恒,王靖宇.中国文学评点研究论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45.
[10]高明扬等.二十世纪以来八股文研究述评——从激情的批判到理性的思考[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5):103-104.
[11]董乃斌等.中国文学史学史(3)[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559.
[12]崑冈等.清会典事例(5)[C].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1.305.
[13]苏永延.复旦大学文学史传统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97.
[14]龚笃清.明代八股文史探[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681.
[15]宁俊红.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26.
[16]刘海峰.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J].社会科学战线,2013,(7):215.
责任编辑 段君峰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11
I209=6
A
1004-0544(2015)01-0056-04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YBB091)。
李鸿渊(1964-),男,湖南东安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