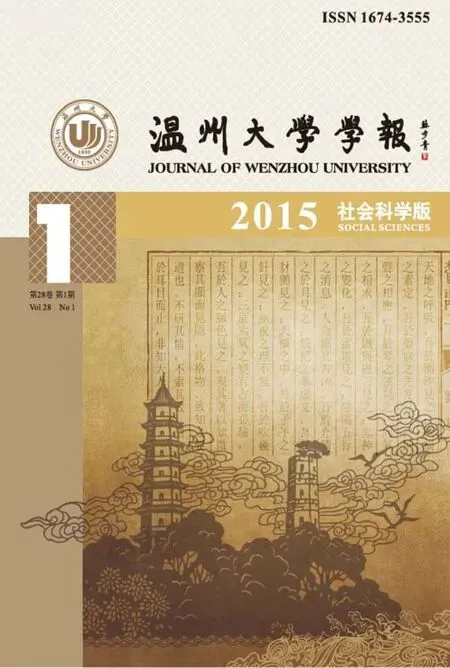欧洲近代史学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
2015-03-17张峰
张 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 710069)
欧洲近代史学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
张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欧洲近代史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于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至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欧洲近代史学东传的过程中,傅斯年穿针引线,对欧洲近代史学的引介不遗余力,贡献尤著。尤其是,他对巴克尔史学的借鉴、兰克治史理念的宣扬,以及德国“种族-文化”观念的运用,不仅成为其取得重要史学成就的学术渊源,而且为转型期的中国史学创辟了一条新路径。同时,欧洲近代史学经由傅斯年输入国内,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取得国际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欧洲近代史学;傅斯年;巴克尔;兰克;“种族-文化”观念;中国现代史学
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方面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厚土壤,另一方面则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引介密切牵涉。20世纪初期,伴随着梁启超《新史学》的发表,在中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破旧立新的“史界革命”。针对传统史学的弊端,中国学者奉西学为圭臬,借道日本引介了欧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希冀借助他山之石构建中国的新史学。“五四”以后,欧美史学经由留学生径自输入国内,对中国史学界的浸染更为深刻。在西方史学东传的过程中,傅斯年对欧洲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贡献尤著,特别是对巴克尔的治史方法、兰克的治史理念以及德国“种族-文化”观念等新学理的宣扬与吸纳,不遗余力。欧洲近代史学经由傅斯年输入国内,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一、借鉴巴克尔的治史方法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 – 1862年)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两卷本的未竟之作《英国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是其代表作。其史学观点经德国史家伯伦汉、美国史家鲁滨逊的发扬,以及中国学者梁启超、陈黻宸、朱谦之等人的评介,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界曾风靡一时[1]。1913至1919年,傅斯年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与本科国文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对于西方史学的传入有着敏锐的洞察,此时的他对于巴克尔史学已有所认知。大学毕业后,傅氏旋即留学英国。在留英期间,他虽醉心于自然科学,但对于文史之学始终关注与爱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即购于留英时期,这反映了他当时在学术研究上的偏好。
巴克尔之史学对于傅斯年的影响,不仅在于傅斯年购买了《英国文明史》,还在于他曾着手翻译该书,这从1935年傅氏致函丁文江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可以得到明示。他在信中提及欠钱未还之事,并叙述1934至1935年,历经结婚、生子、捐款等事,开销甚大,希望出售书稿用来还账。傅氏“旧稿将定”而欲出版者主要有:(一)《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二)《战国子家叙录》,(三)Buckle前五章之译文,附弟之《地理的史观》“Geo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①参见: 傅斯年档案(Ⅱ: 610)[R].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据此来看,傅氏非对《英国文明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不能作出翻译此书的决定。傅斯年于留学欧洲时期购买了大量外文图书,内容涉及心理学、数学、历史学、比较语言学、物理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在诸多外文论著中,傅氏急于译介巴克尔之《英国文明史》,体现出此书观点对其治史的影响。根据笔者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西文书库所见《英国文明史》来看,傅氏在此书中用横线作了大量标识,折射了他对该书内容的谙熟与观点的青睐。
《英国文明史》是巴克尔试图运用自然科学构建历史学的一次努力与尝试,他在该书首章“历史研究底方法”下说道:“研究历史之方法及人类活动规律性之证明的叙述,这些活动本为思想定律及自然定律所支配,故两部分之定律皆须研究,且不恃自然科学,历史亦不能成立。”[2]1巴克尔所言的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统计学。他冀图运用统计学的知识与方法,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现象作出统计,如他在前几章所探讨的统计学对于人类犯罪行为的重要性,统计学在自杀率、结婚率、性别出生的比例等方面的应用等,均是借助统计学的方法进而探讨人类历史演进的“定律”。傅斯年在留欧期间即对统计学表现出兴趣,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讲授“统计学方法导论”[3]61。1924年,他写信给顾颉刚,谈到丁文江运用统计学探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给他的刺激:“这篇文章我非常的爱读,当时即连着看了好几遍。我信这篇文章实在很有刺激性,就是说,很刺激我们从些在欧洲虽已是经常,而在中国却尚未尝有人去切实的弄过的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4]可见,傅斯年对统计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极为欣赏,对于巴克尔在历史学中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感同身受,这也是他以后在历史著述中运用统计、归纳的一个重要导因。
在探讨地理与历史的关系方面,傅斯年同样受到巴克尔史学方法的影响。在《英国文明史》中,巴克尔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对人类历史所发生的影响,主要有四大类:气候、食料、土壤及自然之一般现状[2]23。傅斯年受其影响,撰写了《地理的史观》附于自己的译文之后。在一份“傅斯年档案”中有一份杂记,从标目来看,似乎是傅斯年编纂中国通史的拟纲,其中有几项专讲方法论,如“历史界说”“地理与历史”“中华民国各人种”与“中国史之形态”等②参见: 傅斯年档案(Ⅰ: 808)[R].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窥知“地理与历史”一目中傅氏的撰写内容,但从当时学界史学研究法类的著作,以及傅斯年自己的历史地理涵养来看,当不出巴克尔所言历史与地理关系的范围③在20世纪初期史学研究法一类的论著中, 大多设有“历史与地理”一目, 如日本学者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设有“历史与地理”一章, 专门讨论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反映的大体是巴克尔的史学观点”. 而梁启超在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地理与文明的关系》“系译自浮田氏《史学原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 仅在文字上略作修改, 对当时学界影响至深, 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讨论地理与文明关系的文章大致不出该文的范围”. 可知巴克尔地理史观对东方史学界的深远影响. 参见: 李孝迁. 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J]. 史学月刊, 2004, (8): 85-94.。傅斯年在史学论著中很重视地理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他的未刊稿“由部落到帝国”①参见: 傅斯年档案(Ⅱ: 609)[R].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的提纲来看,首重“地理的导引”,反映出地理因素在傅斯年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傅氏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指出:“历史凭借地理而生……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5]181可见贯穿该文的主线便是着重阐发地理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对上古史作出新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撰写《夷夏东西说》的同时,亦在翻译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两者相辅并行,时间正相吻合,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所倡言的治史方法与巴克尔人文地理史观之间的渊源关系。
实质上,以地理的视角作为探讨历史研究之途径,在傅斯年的大学时期便对此有所认识。他说:“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6]33换而言之,历史学之研究,实为种族变迁与地理环境双重交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可以通过“种族”与“地理”作为切入点,进而探讨中国历史之进程。而巴克尔在《英国文明史》中对地理的重视,无疑会进一步对其历史研究予以刺激,只是“他从未如此僵硬地套用”[7]而已。
二、宣扬兰克的治史主张
在19世纪欧洲史学发展史上,兰克史学曾居于主导地位,其学术辐射力不仅波及欧洲各国,而且对整个西方史学演进的路径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西方近代史学家对后世影响之大,无过于兰克者。”[8]兰克史学在惠泽西方史学发展的同时,也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回响。“在现代中国史学界,为引入德国兰克及其学派的史学、进而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更大贡献的当数傅斯年。”[9]
在大陆学术界,无论是研究傅斯年的学者,亦或研究兰克的学者,均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兰克史学相互联系进行探讨。原因在于兰克强调史学的实证、客观,强调史料,而傅斯年曾留学德国,回国后标榜“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10]。为获取史料,傅氏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10]。基于此,很多学者将兰克与傅斯年之史学主张相互比照,进而将傅氏这一思想之渊源追溯至兰克史学②参见: 张致远. 兰克的生平与著作[J]. 自由中国, 1952, (12): 382-387 ; 张广智. 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J].安徽史学, 2004, (2): 13-21; 李泉. 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132. 侯云灏. 傅斯年与朗克学派[C] //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 傅斯年.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 1991: 125-133. 易兰. 兰克史学研究[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278-325.。
观之傅斯年的言行与实践,他对兰克的治史主张及其成就深为服膺。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傅斯年已初识兰克史学。1915年,留德博士徐子明在北大讲授德国语文与历史,而徐氏乃为民国学术界最早通读兰克主要著作的学者,傅斯年曾是他班上的学生[11]22。1926年,傅斯年留学回国后,先于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继在中央研究院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之创办史语所,笼络大批学术人才,实“要建设中国的朗克学派”[12]。对于傅斯年的这一理想,从张致远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旁证。抗战前夕,傅氏告知张致远:“史语所的研究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13]可见史语所的创办及规划均与兰克的史学主张有所关联。当年轻的周一良于1936至1937年在史语所工作时,傅斯年叮嘱其将来可以学习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的原著”[14]。在1945年史语所出版的《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傅氏亦明确表示:“本所同人之治学,不以空洞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15]这些言论均明示傅斯年对于兰克史学的推崇。
问题在于,尽管傅斯年对兰克史学在中国学术界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张扬,但其推许的兰克史学并非源于兰克的著述。台湾学者王汎森曾指出,“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的兰克学派,但是在傅斯年的藏书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兰克的著作”[16]。王晴佳也从治学旨趣与研究倾向上辨析了傅斯年与兰克的差异,他指出[17]:
傅斯年对实物、考古史料的热衷和对“通史”著述的厌恶,都无法归之于兰克的影响。因为兰克一生,虽然重视原始史料的爬梳,但却没有参与任何考古工作;他所研究的重点,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史,所以也大致上不需要考古史料。其次,兰克虽然强调批判史料,但其目的是为了著史,亦即用叙述的手段,交待历史的演化。……兰克对“著史”的兴趣和对写作“通史”的热忱,显然是傅斯年所无法认同的。由此看来,我们若把傅斯年视为、或奉为兰克史学在中文学界的代言人,显然也是有所偏颇的。
实际上,强调对于史料的批判只是兰克史学的一个要点,而非兰克史学的全部。兰克对于著史的重视,对于实证背后精神力量的推崇,以及对于自然科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均与傅斯年的主张大相径庭。
从20世纪20年代国际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傅斯年留学德国时期,兰克史学适逢低潮,傅氏极有可能未曾阅读兰克的著作。同时,一个人购书的爱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学术兴趣,傅斯年于留学时期不曾购买兰克的史著,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阅读兴趣并未达于兰克的原著。兰克一生,门徒众多,再传弟子与三传弟子遍布学林,其学术思想早已被后辈学人吸收、消化于个人的著述之中,而傅斯年所认识的“兰克形象”或受到兰克史学的影响,即源于后人对兰克治史理念的阐发。
傅斯年的藏书中虽未收藏兰克之著,但他却购买、批阅了不少受兰克学术影响的史著,其中,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即为重要之一种。伯伦汉于治史理念方面承袭了兰克的衣钵,在德国学术界极富盛名,《史学方法论》是代表作之一。在版图设计上,该书共分为“史学之概念及本质”“方法论”“史料学”“考证”“综观”“叙述”六章,作者直言其史学方法,多源于兰克的著述,“探讨解释、结合、综观及叙述等方面之反求作用,兰克氏亦曾致力于其形成,其工作殊不易以数语了之,著者惟有承认本书中有关此之诸篇,其中大部分之知识及规例,均系得之兰克氏之实例及启发者”[18]。伯伦汉强调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并可经由史料批判方法获致,以及方法论可以驾驭史家的想象,使史著达到高度的客观性。兰克所言的客观与史料,经过伯伦汉的发扬与发挥,“被约化为史学方法论”[11]28。傅斯年对兰克治史主张的认识,多半源于伯伦汉的倡导。在中文世界里,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中文本出版于1937年,在此之前,傅斯年曾反复阅读过该书的德文版,以致书损不得不重新装订[3]51。究其所自,“这本书是当时有意跨入史学门槛,接受新史学者的重要读物”[19]。核质以傅斯年对于史学的理解,以及他所宣称的兰克史学,可以看出主要源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
再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成为傅斯年对于兰克史学认识与宣扬的又一来源。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虽与兰克未有师承渊源,但在著史思想上却并秉承了兰克的治史主张。《史学原论》重点探讨了“搜索史料”“史料之类分整理”“校雠考证与校雠考证家”“事实之汇聚分组”等内容,尤其是在上篇第一章开篇即言:“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在此等人类思想与行为之中,所留遗可见之陈迹,实至微少。且此等陈迹,极易遇意外而磨灭。凡一切思想行为,有未尝留遗直接或间接之陈迹,或其陈迹之可见者皆已亡失;则历史中亦无从记载,正如未尝有兹事之存在者然。以缺乏史料之故,人类社会过去无量时期之历史,每成为不可知晓,盖以彼毫无史料之供给故:无史料斯无历史矣。”[20]这一表述,可视为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另一种说法。
以此来看,傅斯年所认识的兰克形象及其史学,乃间接取自后兰克时代史家之总结,而非直接源于兰克的著作。但无论傅斯年采取何种途径认识了兰克及其史学,不容否认的是,经其倡导,推动了兰克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扩大了兰克史学的影响①参见: 杜维运. 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J]. 台大历史学报, 1976, (3): 409-440. 张广智. 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J].史学理论研究, 1996, (1): 92-105. 易兰. 兰克史学之东传及其中国回向[J]. 学术月刊, 2005, (2): 76-82. 易兰. 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J].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8, (6): 305-324. 李长林, 倪学德:.兰克史学在中国的早期流传[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 (1): 136-140. 李孝迁. 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J]. 东南学术, 2006, (3): 150-159.,尽管他所宣传与认识的兰克形象与真实的兰克未必吻合。
三、推崇“种族–文化”的治史观念
傅斯年留学欧洲多年,学术视野聚焦于“西方学术整体发展的情形”[7]344-345,虽然他对兰克史学的认识并未达于兰克的经典著作,但是他仍然受到了积淀甚深的德国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德国“种族–文化”观念对其治史灵感的激发。
从18世纪末期以来,德国学者特别重视从文化史视角思考政治与民族(种族)的关系。从赫德到兰克,以致其后的日耳曼学者,无不偏重种族和文化问题,因而在当时的学术界形成深厚的传统积淀。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学术界承其遗风”,仍然“以种族和文化论述历史”[19]。以“种族”为视角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在傅斯年的大学时期即有认识。他在评价日人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时,指出[6]30-31:
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陈亡隋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
此时的他已明显意识到“种族”之升降、变化对于历史研究的关键作用,遂提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6]33的深刻见解。可以说,傅斯年“有此民族史观,则在德国接触德国史学中的民族史观,自然两相契合,以致将德国特殊的学术角度,转化为治中国历史的方法”[21]。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在他的一本笔记中曾有撰写《赤符论》的计划,内容之一便是“论封建之中国在民族和文化上不是一元”②参见: 傅斯年档案(Ⅴ: 117)[R].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从另一份“傅斯年档案”——“北京大学中国通史纲要讲义”的内容来看,对中国史之分期,他仍以“民族迁动”作为标准,并以此将中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世——周秦汉魏晋南朝;(二)中世——后魏后周隋唐五代宋;(三)近世——元明清。并主张按照这种划分标准来“叙说中国史上制度、文化、社会组织、人民生活之变动,及外来影响之结果”①参见: 傅斯年档案(Ⅱ: 625)[R].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史语所曾有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计划[22]。对于历史教科书该如何编纂,傅斯年于1935年在《教与学》杂志上发表《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倡言其编纂中国史的理念。他认为中国史的编纂应重视政治、社会、文物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以此呈现“文化演进的阶段,民族形态的述状”[23]。在这几部欲写而未完成的著述计划中,傅斯年都不约而同地将“种族–文化”观念作为一种观察中国历史的工具,足见这一观念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傅斯年所受“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对王国维治学特色的评价。他说:“十六年(1927年)八月,始于上海买王静庵君之《观堂集林》读之,知国内以族类及地理分别之历史的研究,已有如《鬼方猃狁考》等之丰长发展者。然此一线上之题目正多。”[24]142言下之意,他见到以“种族”观念治史在欧洲司空见惯,至读王国维之论著,始知国内学者亦有以此观念研治古史者。但他认为,秉持此种治史理念可以获得的“题目正多”,这预示着他将以此为视角展开内容更为丰富的研究。
二是在傅斯年致陈寅恪的一封讨论治学的私人信件中,也曾言及“种族–文化”观念对于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文云②参见: 傅斯年档案(Ⅰ: 1692)[R].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自尔朱乱魏,梁武诸子兄弟阋墙、外不御侮之后,南北之土客合成社会,顿然瓦解,于是新起之统治者,如高齐、如宇文周、如杨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类之一流,塞上杂胡,冒为汉姓,以异族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时代皆此等人闹,当有其时势的原因,亦当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独立的政治结合力之表现。
傅斯年言及高齐、宇文周、杨隋以及李唐等皇朝在种族上皆为“塞上杂胡”,“以异族之个人,入文化之方域”,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这种从种族、文化角度对历史的认识,实与陈寅恪的治史理念不谋而合。
三是从学术研究实践的层面来看,“种族–文化”观念实为一条主轴贯穿于傅斯年的上古史研究之中。他的《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殷周之际政治集团与文化之间的变动,指出:“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25]在《夷夏东西说》中,傅斯年认为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5]181-182。可以看出,“种族–文化”学说对傅斯年学术研究的影响。同样,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傅斯年强调:“凡是一个野蛮民族,一经感觉到某种文化高明,他们奔赶的力量,远比原有这文化的人猛得多。这是一个公例。王季、文王、武王的强调殷商化,并用一个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讨殷商或殷商治下诸侯的女儿做老婆。这是野蛮人的文化系统的大道。”[24]135诸如此类的观念,在《周东封与殷遗民》《论所谓五等爵》等论文中亦不乏见。陈其泰教授据此将傅斯年借用“种族–文化”观念治史所关注的重点,总结为三个方面,对于我们理解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尤具启示意义:“1.重视研究分处于中心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或种族)在政治、文化上既对峙又互相影响、渗透的关系,由于这种互动关系引起中心与周边民族(或种族)集团文化特征上的变化和政治势力之消长,导致全局性历史的盛衰变化;2.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包括其风俗、信仰等)是影响历史演进的很重要的因素,处于中心地区的民族与边境地区民族(或称‘蛮族’)文化上的高下并不是绝对不变的,由于有原先处于后进地位的周边民族的‘骠悍’、‘质朴’的文化成分加入到昔日先进而后来已衰颓的中心地区民族的实际中,会有助于恢复其活力,演出历史的新场面;3.民族的先进和落后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原先落后的民族(或称‘蛮族’)因吸收了先进的文化因素而居于先进地位,原先先进的民族(或其一部分)也可因周围环境影响而退居落后地位。甚至民族(或种族)界限也非绝对不变,而是会发生双向的‘同化’现象,并给予历史演进以很大的影响。”[26]
总之,傅斯年将欧洲近代史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的实践,进一步促进了中西史学的交融,为转型期的中国史学创辟了一条新路径;同时扩大了欧洲近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传播与影响,大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取得国际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俞旦初.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J]. 史学史研究, 1982, (3): 54-67.
[2] 巴克尔. 英国文化史[M]. 胡肇椿,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3] 王汎森, 杜正胜.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M]. 台北: 台湾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 1995.
[4] 傅斯年. 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一.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425.
[5] 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三.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6] 傅斯年.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一.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7] 王汎森.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331.
[8] 孙秉莹. 欧洲近代史学史[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167.
[9] 张广智. 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J]. 史学理论研究, 1996, (1): 92-105.
[10]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8, (1): 3-10.
[11] 汪荣祖. 史学九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12] 岳玉玺, 李泉, 马亮宽. 傅斯年: 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135.
[13] 张致远. 兰克的生平与著作[J]. 自由中国, 1952, (12): 382-387.
[14] 周一良. 史语所一年[C] // 杜正胜, 王汎森. 新学术之路.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8: 557.
[15] 傅斯年. 《史料与史学》发刊词[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三.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335.
[16] Wang Fan-sen.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2.
[17] 王晴佳. 科学史学乎?“科学古学”乎?——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思想渊源新探[J]. 史学史研究, 2007, (4): 28-36.
[18] 伯伦汉. 史学方法论[M]. 陈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82.
[19] 周樑楷. 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历史观点: 从西方学术背景所作的讨论(1880-1930)[J]. 台大历史学报, 1996, (20): 101-127.
[20] 朗格诺瓦, 瑟诺博司. 史学原论[M]. 李思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3: 1.
[21] 许倬云. 傅先生的史学观念及其渊源[J]. 大陆杂志, 1998, (5): 1-8.
[22] 傅斯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一年度报告[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六.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389.
[23] 傅斯年. 闲谈历史教科书[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五.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55.
[24] 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三.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25] 傅斯年.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C] // 傅斯年. 傅斯年全集: 三.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62.
[26] 陈其泰. “民族-文化”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 (1): 129-133.
(编辑:朱青海)
European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Academic Ideas of Fu Sinian
ZHANG Feng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China710069)
Abstract:As imported goods, European modern historiograp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evelopment from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o modern trans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European modern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Fu Sinian, acting as go-between, spared no effort to introducing Eueopean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With reference to Buckle’s historiography, advocation of Ranke’s historiography concept and utilization of German Race-Culture ideas, he got great achievements and opened up a new path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ransition period. Meanwhile, as the result of his introducing, European modern historiography broadens Chinese scholars’international vision. In a word, Fu Sinian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given it a louder voic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Key words:European Modern Historiography;Fu Sinian;Buckle;Ranke;Race-culture Concept;Chinese Modern Historiography
作者简介:张峰(1981- ),男,安徽淮北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资助项目(13JK0048);西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1NW40)
收稿日期:2014-06-1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1.003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1-0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