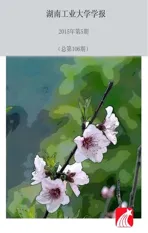经典与模型——试论《断头台》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
2015-03-17龙其林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龙其林(1.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2.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经典与模型
——试论《断头台》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
龙其林1,2
(1.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2.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 要]对于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狼叙事寓意的由来,研究者一般将其归因于作家经历、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把比较视野纳入到中国生态小说中的狼叙事研究中来,将前苏联文学经典《断头台》与之进行对照阐释,可以发现中国生态小说狼叙事中的母性美与狞厉美与《断头台》存在着相互呼应的关系。比较视野的运用,将突破以往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为生态文学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和思路。
[关键词]生态小说;《断头台》;狼叙事;母性美;狞厉美
人类文明进入现代之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践行的工具理性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不断高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不断地对自然进行掠夺,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断裂。生态危机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为棘手也最为艰巨的生存考验,生态文学中的狼叙事以特殊的关注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聚焦。作家试图通过对于狼的生存状况的揭示、对于人与狼关系的变化来反思人类面对自然、动物时陷入的误区,同时揭露人类对于狼的捕杀、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的内在关系,从而对当代人的狭隘的伦理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进行批判和反思,这将“有助于克服‘人性的分裂’(指理性与感性的分裂),避免人变成‘单面人’(马尔库塞语),有助于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树立万物平等的意识,培养健全的人格”。[1]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郭雪波的《大漠狼孩》、雪漠的《猪肚井里的狼祸》和姜戎的《狼图腾》与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似点,这不仅体现在这些小说中都出现了以狼为中心表现对象,关注人与狼、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在小说结构、叙事手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
钦吉斯·托列库罗维奇·艾特玛托夫(1928—2008)是前苏联和吉尔吉斯斯坦富于盛名的当代作家,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获得了前苏联的许多奖项,还获得过意大利“橄榄枝”奖、德国“吕克特”奖、奥地利的“国家文学奖”等重要奖项。在前苏联作家中,艾特玛托夫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家,王蒙将其列为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四个外国作家之一,甚至认为艾特玛托夫的影响超过了卡夫卡、海明威和马尔克斯。
从生态文学的角度来看,《断头台》(又译为《死刑台》)也是艾特玛托夫最富意义的一部作品。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善于描写大地、海洋和动物的作家,他的作品如《断头台》《风雪小站》等洋溢着鲜明的生态意识。在《断头台》这部小说中,作家通过母狼阿克巴拉及其家族遭遇的一系列苦难向人类发出了生态预警: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最终只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从而给自己带来深重的灾难。1986年,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分3期连载于前苏联的《新世界》文学杂志上。小说刊载之后不到半年,前苏联《图书评论报》曾举行过一次读者民意测验选出四部1986年国内的最佳文学作品,出炉不久的《断头台》便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向人们昭示了小说的独特魅力。随后,《断头台》被翻译成各国文字,获得了世界性声誉。在中国《断头台》也掀起了一股译介和传播的热潮。1987年10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李桅翻译的《断头台》,这是国内第一部翻译的该小说的译本。之后,外国文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重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断头台》的翻译全本或节选,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作家和读者熟悉了这部经典作品。
艾特玛托夫是长期以来极少数被选入中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中专节介绍的苏联当代作家,在有的外国文学教材中同时在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中对艾特玛托夫进行专门介绍。在中国,艾特玛托夫也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之交,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只言片语,都会成为中国学界的报道内容”,“他无疑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20世纪下半期俄语作家中的一个”[2]。前苏联解体之后,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文化圈内的影响有所下降。即便如此,中国文学界对他仍然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苏联解体之后,艾特玛托夫再次成了中国读者最为追捧的对象之一,他的作品几乎都被译成了汉语,读者为数众多。对于前苏联解体之后艾特玛托夫仍然受到追捧的现象,有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艾特马托夫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首先当然得益于他的‘东方身份’,他是吉尔吉斯族人,所谓的‘吉尔吉斯人’(Kirghiz),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柯尔克孜人’,而且,艾特马托夫的母亲还是与中国人有着更近血缘关系的鞑靼人,艾特马托夫若是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是没有人会把他当作外国人的。其次,艾特马托夫所描写的‘群山和草原’,就在天山的那一边,中亚的风土人情通过我国新疆的文化接力,对于我们而言已然具有了某种天然的亲近感,艾特马托夫作品所具有的‘东方风格’(善恶对立的二元模式、相对明晰的结构、浪漫清新的笔触和体现东方智慧的神话传说等等),能在中国读者处赢得更多的共鸣。最后,艾特马托夫在中国的流行,对于读者而言,或许是其‘中庸’的风格更易于接受,他的作品既新颖独特,又不至于现代、后现代到让人读起来感到吃力的地步;而他在中国作家中赢得了较多的认可,恐怕还在于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为尽量体现创作个性、努力突破模式局限而付出的种种努力。”[2]虽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经历过曲折,但是对于他的文学成就人们还是有着普遍的认可,作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的地位应无人提出质疑。
二
艾特玛托夫在中国作家中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与中国许多作家一样都是来自乡村社会,对于大地上的草木和乡村发生的变化了如指掌,由此而发展成他们创作中对于大地的热爱,在自然描写中传达对于大地的诚挚感情。艾特玛托夫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的舍克尔山村,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春时光。幼年时祖母讲述的民族神话、民间传说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熏陶,使他对故乡的这片土地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艾特玛托夫曾说:“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点,有一个自己的、与土地相连的连结点”,“舍克尔山村就是我创作的源泉”[3]。对故土的熟稔,对故乡文化传统的热爱,使艾特玛托夫意识到了故乡与民族、自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他的创作中,自然的母性情怀主题贯穿于始终。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已经具有了与生态美学非常相似的观点和立场,即“它不是孤立地从人的生命现象本身去寻求审美体验,而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围绕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去探索,体现对人类命运的美学关怀。”[4]在艾特玛托夫看来,人类来源、生活于大地之上,大地以自己的无私和宽容哺育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成为万物生存和延续的母亲。因此,人类应该亲近自然,聆听来自大地的呼唤。在《白轮船》这篇小说中,艾特玛托夫所表达的主旨即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承担与义务,这是人类对于哺育自己生命的大地母亲的神圣责任。在《断头台》中,这种大地的母性形象主要是通过母狼阿克巴拉体现的。阿克巴拉和她的家庭经历了不少坎坷,先后遭遇了围猎、火燹、被猎人端窝、配偶殒命等不幸事件,虽然在被逼上绝路之后曾对人们实施了残酷的报复,但就其本质而言并不让人感觉冷酷。在阿克巴拉身上,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母性的坚忍和博大。阿克巴拉和塔什柴纳尔结成配偶后,在莫云库姆草原上过着其乐融融的生活,尽职尽责地哺育着自己的孩子。当官方为了边区的利益而对发现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行大肆捕杀时,大地与母狼一样默默地承担着巨大的痛苦:在大地上,连绵不断的射击声、刺耳的马达声、直升飞机的轰鸣声以及羚羊临死前的哀吟声交织在一起;阿克巴拉一家的三只狼崽命丧围猎之中,只有母狼和公狼侥幸逃出。此时,大地与母狼一样忍受着丧失生灵的痛苦,以坚强的毅力默默地承受。阿克巴拉和塔什柴纳尔迁移到阿尔达什岸边芦苇丛中,又生下了五只小狼崽。但是,它们和苦难的大地母亲一样再一次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由于战后在这一带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稀有金属矿,人们又要将芦苇丛夷为平地。大地母亲在这次人为的劫难中再一次饱尝苦难,阿尔达什沿岸地区仿佛堕入了末日世界,一群群鸟儿在湖泊上空飞来飞去,到处都是它们凄厉的叫声;所有长期生活在芦苇丛中的动物陷入极端的惊慌之中,全都在四散奔逃。与大地母亲的遭遇相似,阿克巴拉再一次品尝到了丧失爱子的痛苦。在大火将阿克巴拉一家包围时,为了泅渡获救,母狼和公狼狠心将三只狼崽扔在火里不管,嘴里叼着另外两只游过湖湾。尽管它们非常小心地叼着狼崽,最后还是发现它们被湖水呛死。绝望中的阿克巴拉和塔什柴纳尔走到伊塞克湖畔盆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并繁殖出最后四只狼崽。但是这一次,游手好闲的牧人巴扎尔拜端掉了狼窝,将全部狼崽卖掉换酒喝。痛失狼崽的阿克巴拉在深夜里发出撕裂心肺的哀嗥。当她看到小肯杰什时,阿克巴拉的母性力量使她对小孩产生了怜爱之情。当小肯杰什伸出手摸摸这只和善的“狗”脑袋时,痛苦不堪的阿克巴拉怦然心动了,它不由自主走上前去舔了舔小孩的脖子。小家伙也把狼的脖子一把搂住,此刻的阿克巴拉骨头都酥了,伏倒在他脚下。此时此刻,母狼已经将自己全部温情都倾注到孩子上,陶醉于小肯杰什的儿童气息中。与人们之前所熟知的狼外婆、中山狼等故事不同,小说中的阿克巴拉非但没有让人感觉到凶狠、可恶,反而让人产生怜悯与同情之心。母狼阿克巴拉身上所体现的母性,与大地母亲所呈现的母性具有同一性:阿克巴拉家庭经历的危机实际反映的正是大地(自然界)的危机。一方面,人们毫无约束地肆意屠杀野生动物,导致了动物数量的急剧减少和生态链条的断裂,由此必将产生更为深远的生态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类文明不断地向着自然界纵深挺进,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极大地缩减了生物的存活空间。不难看出,母狼的遭遇与自然界(大地)的遭遇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母狼阿克巴拉一家的生活遭遇具有深刻的批判锋芒,它将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人类对于大地母亲的恩将仇报联系起来。作品借此警告人类,只有保持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发展,大地母亲才能真正得到保护。
这种对于自然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美的发现与书写,在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和雪漠的《猪肚井里的狼祸》中得到了延续。与《断头台》相似,郭雪波在《大漠狼孩》中也十分注意刻画母狼身上的母性美内涵。当母狼偷偷来到苏克家,看到母亲给小龙喂奶的场面时内心充满了母性的柔情,这一情节与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的设置极其相似。当母狼看到小龙时眼神变得很奇特,它仿佛停顿在了这个时刻,眼神中充满了柔情慈意。母狼微眯上眼睛后,似乎找到了往日自己喂养狼崽的幸福。当母狼接近小龙后其母性情怀得到彻底释放,小龙伸出手摩挲打“狗”的脖子和嘴鼻,而“大狗”也伸出红红的长舌舔他的脸、吐出的奶汁、露肉的双脚以及开裆裤后的光屁股。母狼的这种母性情怀在小说结尾处发挥到了极致,狼孩冬日河边饮水时不慎掉入水中,母狼奋不顾身地营救狼孩。当母狼看见小龙落水的一幕,它似乎浑身充满了神奇力量,勇猛地扑过去,纵身一跃扑进了冰窟窿,力图救出自己的狼孩。正是母狼与狼孩之间这种相互依存、难以弃舍的情感,向人们昭示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并对造成母狼与狼孩悲剧的罪魁祸首们发出了强烈的控诉。这祸首固然是胡喇嘛、金宝等人,但同样也包括了那些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肆意掠杀动物、压缩野生动物生存资源的人们。他们在欲望的驱使下,一味地向自然攫取,而忽略了生态平衡与人类行为之间的隐秘关联。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心理的存在,即便在胡喇嘛、金宝之后人们仍然在毁坏环境,最后造成狼兽绝迹兔鸟烹尽的生态恶果。这不仅是狼类的悲剧,同样是大地的悲剧。在雪漠的《猪肚井里的狼祸》中,母狼灰儿的母性色彩在与残疾小狼崽瞎瞎之间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同人之母亲最疼残废儿子一样,母狼灰儿最疼爱看不见东西的瞎瞎。当其它狼崽争抢着喝奶时,母狼就将其它狼崽扔到一边,让瞎瞎单独吃食。瞎瞎吮吸奶头时很温柔,那抽丝似的快感令灰儿产生了异样的温柔。母狼总是幻想着自己能够用舌头舔开瞎瞎紧闭的双眼,从此幼儿便可看见世界的模样,为此灰儿坚持着,“开不开是天的事,舔不舔是妈的心。尽了妈的心,就随它瞎眼的天吧。”[5]而到瞎瞎为猛子当作黄羊误杀之后,灰儿总觉得风里似乎有瞎瞎的声音在长嚎。母狼不相信瞎瞎死了,只是枪响后的那声嚎叫回荡在心头。夜晚灰儿到旷野里嚎哭,“那声音,悲凉,悠长,把天地都戳通了,表达着一个母亲的悲哀。”[5]母狼觉得瞎瞎还会憨憨地走来,在自己的腹下滚寻找属于自己的奶头,母狼还决定那奶头不叫其它狼崽吃,只是给瞎瞎留着。在《猪肚井里的狼祸》中,狼一方面扮演着嗜血的角色,闯羊圈,啃牛肚,另一方面则又洋溢着慈祥的母性气息。如此强烈的反差,根源就在于人类对动物生存权力的践踏、对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由此必然导致充满母性色彩的灰儿与人类为敌。究其根源,“狼祸”实为人之祸、欲望之祸。
三
以《断头台》为代表的狼文学的兴起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它既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疏离自然的一次反叛,又有着振奋民族精神的寓意。生态文学中狼叙事的兴起是对于现代文明的一次反拨,它通过回归自然、再现生态环境中的狼的生存境况,对于陷入庸常趣味、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叙事表达了强烈的反动。
事实上,若追溯这种生态性反动的典型代表则应归属于自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表现了狼叙事题材的独特魅力,它以罕见的狞厉、原始之美向长期处于物质叙事中的文学进行了强有力的冲击。狼自身具有的凶狠、锐利和生存竞争中的残忍在狼叙事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并由此而产生一种罕有的狞厉美,予人以极大的惊愕感、惶恐感。艾特玛托夫并不回避狼的狡黠、智慧和愤怒后的嗜杀、狰狞,反而对这些厮杀、捕食的残酷场面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从而给予读者以精神上的不寒而栗和灵魂深处的惊悸。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促使读者深思:造成人与狼之间的对立根源在何处?狼是否与人类势不两立?如若不是,则狼与人愈演愈烈的冲突因何而起?通过对作品的阅读不难发现,母狼阿克巴拉之对人类的敌意与报复,根源在于人类为了追求经济、政治利益而无视自然生态和动物的生命价值。母狼的三窝狼崽不是丧命于人类的围猎,就是在人为的火燹中殒命,甚至是在人类的偷猎中被变卖换酒。屡屡丧失爱子的阿克巴拉终于向处于强势地位的人类发动了进攻,这时它们对于可能遭到的危险完全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陷于向人类复仇狂热的母狼和公狼,永久地告别了老窝,从此不再来此过夜,而是开始了到处游荡、伺机报复的行程。它们的复仇行动不仅不加隐蔽,而且特别大胆,愤怒已使它们不再防备人类的袭击。陷入绝望和悲痛中的母狼,向人类和羊舍发动进攻。在大白天围攻一个拖拉机手、一个牧羊少年之后,两只狼又对一群怀崽母羊实行了一场真正的屠戮。十五只怀崽母羊被两只狼咬破了喉管,但是狼并不乘机饱餐一顿,而只是从嗜杀中获得一种隐隐的快感,这场杀戮的目的只在于为杀戮而杀戮。这种狞厉美的产生向人们昭示了动物与自然强有力的报复,并由此对践踏生命的行径进行了鲜明的批判。
同时,狼文学中的狞厉美也和题材本身的特点相关。由于题材原因,作家在描写狼时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写到它们的生存环境,而这些生存环境又大致属于人烟罕至、原始荒芜的地区。于是,在这样一种荒蛮之地进行的生存博弈自然具有了狞厉之美。读者在感受狞厉美的同时,也可以由此而体验到返回大自然的粗粝、蛮荒与野趣,并由此而获得一种久远疏荒野后的心理代偿。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代生态小说中在表达狼叙事的时候常常喜欢追求这种狞厉之美。狼文学的神话传说或者争斗、杀戮等情节,虽然可能比较粗糙,却依然禀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在姜戎的《狼图腾》中,我们经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狞厉之美。在狼群袭击军马这一情节中,可以充分感受到狼群袭击马群时的灵魂惊悸和由此带来的思想震撼,同时这一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向我们揭示了自然力量的强大和生态平衡破坏之后的恶劣影响。在狼群突袭军马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幅恐怖的生态图景:马群被狼群咬破侧肋侧胸鲜血喷溅、皮肉横飞,大屠杀的血腥使陷于疯狂的狼群异常亢奋而残忍,它们顾不上吞吃已经到嘴的鲜活血肉,而是不顾一切地撕咬和屠杀。狼群一次又一次地往马群冲击,狼王和头狼更是疯狂残暴,它们蹿上大马之后咬住马皮马肉,盘腿弓腰,用脚掌死死抵住马身,猛地全身发力,将连带着马毛的皮肉活活地撕拽下来。狼群如此循环,将狼族遗留在血管中的嗜杀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彻底消灭军马,狼群不惜采用自杀式的袭击方式,那些丧子的母狼疯狂地纵身跃起咬透马身侧肋后面最薄的肚皮,以不惜牺牲自己作为代价,力图置马群于死地。无论对于狼还是对于马而言,这都是它们见到的最为残酷和血腥的死亡方式。一头被马蹄踢破腹部、下了马的公狼,蜷缩在雪地上嗥叫,仍然拼命地用两条前腿挣扎着爬向倒地未死的马,撕咬生吞那匹囫囵个的大马。至于被猎杀的马群,其惨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马肚皮一旦被狼牙豁开,胃包和马肠就会一下滑坠到雪地上,仍在飞奔的马腿就会踏破了自己的胃囊和肚肠,刹那间胃包崩裂,柔肠寸断。惊吓过度的马仍在奔跑,甚至可能将胸腔中的气管心脏肺叶也一起踩拽出来,胆破致死、心碎而死、窒息而亡。在如此惨烈的狼马之争中,读者自然会因此而受到灵魂的震撼,并对造成此类现象的深层原因进行思考,从而揭示出草原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
这种狞厉之美,在《猪肚井里的狼祸》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当母狼灰儿失去最疼爱的小狼崽瞎瞎后,嗅到羊圈中瞎瞎味道后的灰儿和瘸狼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当瘸狼和灰儿扑入羊圈后发现了瞎瞎葬身于羊腹,于是它们开始一场真正的杀戮。这不是为了生存而来的猎杀,而是为了复仇进行的残酷杀戮。因为是复仇,灰儿和瘸狼便要叫仇家感到灵魂深处的剧疼,它们咬断羊的喉管后便扔一旁,再咬再扔。很显然,作家之所以大量地描绘狼的复仇与自然的教训,目的正在于向现代人发出生态预警,对违反生态规律的滥杀行径和欲望膨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号召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界的生态规律,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实现人与狼、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
《断头台》代表了前苏联生态小说乃至生态文学的思想、艺术高标,展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发展具有启示意义的经典作品,其中体现出的深厚的道德责任感、强烈的忧患精神和自觉的生态意识,为中国生态小说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苏俄文学传统中强烈的道德诉求和心理主义,对于矫正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存在着的意义浅薄、侧重纪事的缺点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参考文献:
[1]陈松青.生态诗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学功用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3(1):67-71.
[2]刘文飞.别了,艾特马托夫![N].中华读书报,2008-07-30(05).
[3]史锦秀.艾特玛托夫在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107.
[4]吴景明.生态论与新世纪美学的兴起[J].文艺争鸣,2010(21):20-23.
[5]雪 漠.猪肚井里的狼祸[J].中国作家,2004(2):4-110.
责任编辑:黄声波
The Classic And The Model
——On Guillotine and the Wolf Narrativ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Novels
LONG Qil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iterary Thought,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Department of Chines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wolf narrativ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novels is full of implied meanings,which researchers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the writers’experi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If included in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literary classic Guillotine interpretation,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n echo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uillotine and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novels in the motherhood beauty and ferocious beauty.The use of comparative vision will exceed the certain mindse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past and it can explore new spaces and ideas in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ecological novel;Guillotine;wolf narrative;motherhood beauty;ferocious beauty
作者简介: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生态中国:文学呈现与跨文化研究”(13FZW051);广州市教育系统创新学术团队“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研究”(13C05);广州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博士学术团队项目“生态灾害与中国当代文学书写”(201404XSTD)
收稿日期:2014-08-05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5.013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70-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