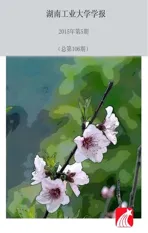特别累犯:扩展抑或限缩
2015-03-17仝其宪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仝其宪(1.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2.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特别累犯:扩展抑或限缩
仝其宪1,2
(1.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山西忻州034000;2.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 要]新近有不少学者认为,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应继续扩展,但是支持这些见解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特别累犯扩展论不仅缺乏足够的法理正当性,而且完全不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今后对特别累犯的立法取向应保持限缩。
[关键词]特别累犯;刑事政策;扩展论;限缩论
长期以来,有不少学者主张特别累犯过于逼仄,应扩大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随着2011年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扩展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此为契机,新近又有不少学者的见解认为,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应继续扩展。与此相对,还有学者呼吁要警惕特别累犯裂变式增加,特别累犯未来发展应限缩。[1]那么,我国特别累犯未来发展趋势究竟应择期扩展路径还是信守限缩政策?换言之,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究竟是扩展,抑或限缩?以及如何看待《刑法修正案(八)》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扩展?这些问题确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并且能够深化对特别累犯的认识,廓清特别累犯的未来立法取向,这对于特别累犯的日臻完善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 特别累犯扩展论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特别累犯立法经历了从反革命罪特别累犯,到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再到危害国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的发展轨迹。相应地,学界关于特别累犯扩展论的主张,自1979年《刑法》设立反革命罪特别累犯崭露头角,到1997年《刑法》改设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势头渐长,再到《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以来,特别累犯继续扩展论呼声强劲。以特别累犯的发展轨迹为参照系,笔者试图将特别累犯扩展论划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旧刑法、新刑法及刑法修正案八为参照点,笔者将特别累犯扩展论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旧刑法阶段的特别累犯扩展论、新刑法阶段的特别累犯扩展论和“刑八”后的特别累犯继续扩展论)。这期间,支持特别累犯扩展论的论据各有不同,有必要对之一一检视。
(一)“旧刑法”阶段的特别累犯扩展论
“旧刑法”阶段一般认为是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行到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期间。这一阶段的特别累犯扩展论主要集中在我国应设立何种类型的特别累犯上。反观世界各国对特别累犯的立法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规定前后罪为某一或某类特定之罪的特别累犯,另一种是规定前后罪性质或种类相同的特别累犯。我国对特别累犯立法模式属于前者,其适用范围较后者狭窄。因而,在这一阶段持特别累犯扩展论的学者认为,我国特别累犯的立法应该不局限于具体的种类和性质,而只规定前后犯同一罪的特别累犯。对此笔者不予认同。我国对累犯立法之所以在一般累犯之外又设立特别累犯,主要是因为对于某些特殊犯罪有其自身的特质,如果拘泥于一般累犯的较为严苛的条件论处根本体现不出予以集中打击与预防此类犯罪的目的,有必要对此类累犯规定较宽泛的构成条件以显示对其从严处罚的立法取向。但是,如果特别累犯在构成条件上过于宽松,并且适用范围上不断扩张,即如此双管齐下,并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与预防此类犯罪的滋生,也与特别累犯设立的目的与初衷相悖。因此,我国刑法既然对特别累犯的刑度与时间等构成条件不作限定,显然设立过于宽泛,就应当对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予以限制与紧缩。如此这样一张一弛,合理界定特别累犯的范围,方能发挥特别累犯的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的立法目的。所以,主张特别累犯为前后犯同一罪的立法模式基本上已经淡出学界,设立前后罪为同一性质或种类的特别累犯,这在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
(二)“新刑法”阶段的特别累犯扩展论
“新刑法”阶段在此指的从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到2011年颁行《刑法修正案(八)》期间。1997年《刑法》改设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以来,特别累犯扩展论日渐扩大,并认为继续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仅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已不合时宜[2]。对此笔者予以认同。
毋容置疑,相对于1979年《刑法》规定的反革命罪特别累犯,1997年《刑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适应了当前国内外社会发展情势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了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国家治理日趋稳定。在这种社会境况之下,由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仅仅涵盖12个具体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很低,加之在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极少发生,致使我国的特别累犯制度即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几近虚置,成了一种“叫好不叫座”的安排[3]。显而易见,这种专设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犯罪的做法,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其实际意义都很有限。
(三)“刑八”后的特别累犯继续扩展论
“刑八”后阶段指的是从2011年颁行《刑法修正案(八)》以来到现在期间。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别累犯,自此,特别累犯继续扩展论的主张再次高涨,势头迅猛。根据笔者现有的材料,通观持特别累犯继续扩展论的主张,举其要者,支持其论点的论据大致有:其一,特别累犯扩展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果;其二,继续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不合时宜;其三,特别累犯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严重的犯罪客观危害、高重犯率应成为纳入其范围的重要标准,可以予以增设生产、销售伪商品类犯罪、走私类犯罪、侵犯财产类犯罪和淫秽物品犯罪的特别累犯。这些论据大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一,关于“特别累犯扩展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果”的论据,笔者认为,这是对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误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为了更加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提出的贯彻于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乃至刑事执行全过程的基本刑事政策,它是对以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发展与完善[4]。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学界的解读大同小异,根据较为权威的观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是指: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5]。那么,《刑法修正案(八)》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扩展,可以说是适应了国内外社会发展形势和犯罪发展态势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果。正如赵秉志教授所言:《刑法修正案(八)》扩大了特别累犯的范围符合惩治严重犯罪的实际需要,符合累犯制度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设立目的,同时也符合国际刑事法治的发展趋势[6]。如果说《刑法修正案(八)》对特别累犯的扩展较为适宜的话,那么,有学者仍然主张还应对特别累犯继续扩展,对此笔者坚决予以反对。我们知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精髓在于“以宽济严”,在“宽”与“严”之间,重点侧重于“宽”。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精神和内容的把握,必须对刑罚目的、刑罚效果、刑法谦抑性以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予以考虑,才能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符合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7]。如果对特别累犯不合时宜地继续扩展,这不仅违背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切不可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名,行刑法扩张之实。
第二,关于“继续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上不合时宜”的论据,笔者予以认同。
毋庸违言,刑法根植于动态的社会生活,而刑法修正也应尽可能及时地反映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因而,刑法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发展的变迁,不断满足国家对犯罪进行惩治和预防的需要[6]。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迅速发展的特殊时期,犯罪发展态势呈现新的特征:一方面,国内外形势与环境相对较为宽松缓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较少发生,在司法实践中仅仅起到宣示式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近年来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却非常猖獗,犯罪分子组织、策划、指挥或实施了多起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和长期的潜在威胁,同时也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和平。然而,囿于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使得上述这些再犯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从严惩罚。显而易见,长期以来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上已经不合时宜,现有的特别累犯制度已经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司法实践中惩治和预防犯罪的需要。鉴于此,为了实现对特定法益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扩展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较为适宜。
第三,关于“特别累犯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严重的犯罪客观危害、高重犯率应成为纳入其范围的重要标准”[8]的论据。笔者对此不予认同。
早有不少论者认为,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出发,应适当扩大特别累犯的范围,将那些客观危害性较严重、复发性较高、犯罪后果扩散性强的犯罪纳入到特别累犯的范围,予以重点打击和惩治。[9]这些如出一辙的观点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就不攻自破。其一,如果将那些犯罪客观危害性强、高重犯率的犯罪均纳入特别累犯范围,充塞其中的内容如此庞杂,使得特别累犯不堪重负,以致会撑破特别累犯的意义边界。大量的犯罪从严处罚,极不利于对犯罪者的教育改造和再社会化,亦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二,对犯罪客观危害性强、高重复犯率的犯罪仅依靠特别累犯制度从严处罚,不仅不可能凑效,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走向重新犯罪的另一极端;其三,不能因为某一类或某一种犯罪在某一时期凸显或猖獗,就想当然地将其纳入特别累犯之中,这是不了解刑法立法科学规律的盲目建言。其实,刑法是宽容的,而不是万能的,特别累犯有其适用的特定边界,切不能漫无边际地扩张,比较明智的方式乃是理性地去研究此类或此种犯罪滋生的原因,如何规制与治理此类犯罪,而不是一味地给予从重处罚。
还有学者主张应增设生产、销售伪商品类犯罪、走私类犯罪、侵犯财产类犯罪和淫秽物品犯罪的特别累犯[10]。这种机械地、僵硬地增加刑罚当量,笔者更不予以认同。一方面,上述这些犯罪已经依据刑法所预定的法定刑施予定罪量刑了,这种规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限制或阻截了刑法再扩大处罚范围的危险;另一方面,按照论者的逻辑,特别累犯还要将大片新地圈入自己的疆域,这彰显的是刑法容忍度急剧下降的境遇,由此导致特别累犯再次大幅度裂变式的扩充。如此这样,刑法的惩罚之网急剧扩张,必然使我国刑罚又陷入重刑主义的泥淖,同时也与世界刑罚轻缓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二 特别累犯扩展论缺乏足够的法理正当性
(一)特别累犯自身特质昭示不宜扩展
累犯制度的设立是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刑罚个别化原则”的产物,与崇尚报应主义的刑事古典学派所关注的犯罪行为及客观危害不同,以预防主义为归依的刑事实证学派更关注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并以此作为罪责轻重的评价基点。一般而论,对特别累犯从重处罚是有其正当根据的,行为人在犯一定之罪接受一定的刑罚处罚后又犯一定之罪,呈现“刑罚迟钝型人格”[11]说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因而,设立特别累犯制度的目的与初衷就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和预防那些主观恶性深重而人身危险性较大的重新犯罪者。然而,这一目的与初衷虽属良善之举,但绝不能使特别累犯泛化。
由于特别累犯自身的特质,要求前后罪必须为同一性质之罪或同类性质之罪,其适用的范围相对狭窄。所以,特别累犯制的立法模式日趋式微,当今世界采用特别累犯制的国家并不是很多。加罗法洛早在1885年就反对当时构成特别累犯的理论[12],到现在,对特别累犯予以非难的学者也为数不少。主要是因为对犯罪人之后罪刑罚处罚的意义,与其说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同样之罪,倒不如是为了使犯罪人弃恶从善,不再重新犯罪。譬如说初犯诈骗罪者再犯此罪,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予以构成累犯从严处罚;而初犯诈骗罪者再犯谋杀罪或其他罪,反而不能构成累犯,从而不能适用累犯从严处罚的规定,这显然有“挂一漏万”之嫌,与情与理不符[13]。这是特别累犯制度自身无法消解的致命硬伤,这一致命硬伤预示了特别累犯制度不宜扩展,特别累犯越是泛化,这一硬伤就越凸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累犯圈的大小并不是立法者随心所欲地划定的,它不仅取决于社会发展情势的需要,而且还取决于累犯类型和成立条件的设立模式。不同的累犯制度模式不仅左右着不同的累犯理论,同时也决定着实践中累犯问题得以解决的实际效果。如果累犯圈划地过宽,刑罚从重处罚泛化,刑罚触角延伸过长必然导致“刑罚法规的肥大症”[14],其后果必然是重刑主义盛行。
我国采累犯制度模式为混合累犯制,它是在吸取了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各自长处的基础上的一种折中,即以一般累犯为常态、特别累犯为补充的累犯立法格局[15]。这一立法格局暗含了这样一种状态:一般累犯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而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较为狭窄,特别累犯只能在其适度的边界内运行,只能作为一般累犯的辅助,并且其前后罪为同一或同类罪。如此这样,对特别累犯的设置才符合惩罚的理性,体现刑罚的人道与谦抑。一旦特别累犯丧失其个性时,它便趋于消亡。要保持特别累犯这一立法特质,就要时刻警惕特别累犯的扩展。
(二)配刑原理预示特别累犯扩展易呈现“过剩”刑罚
对于任何犯罪,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都必须依据刑法中规定的刑种或刑度施予犯罪者判处刑罚,即对于一定的不法行为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如果不严格遵循刑法的配刑规则,就随意突破所犯之罪的法定刑幅度以处罚犯罪者,显而易见,这就极大地违反了法定刑配置根据和量刑原理,也与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即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经典表述。它贯穿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不仅是定罪量刑时应当遵循的铁则,而且还是法定刑配置的铁则。随着历史的变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已逐步从以报应主义刑罚观为基础的传统罪刑相适应原则转换为以预防主义刑罚观为根基的修正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原则可以被解读为,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既注重刑罚与已然的犯罪行为相适应,又注重刑罚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也就是说,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予犯罪者的处罚不仅要和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而且要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还应当结合犯罪者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来确定其刑事责任的程度,适用轻重相应的刑罚。立法者就是依据这一观念以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大小来配置法定刑的。然而,在法定刑配置上,立法者所面对的是抽象的、一般的类型化行为,是对事而不对人的情况下将罪刑关系以刑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这就意味着,抽象的、一般的类型化行为的法定刑区间的配置,主要取决于这一类型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16]。行为人虽然所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一,其人身危险性也各不相同,但只要属于某一类型化行为,则其应当判处的刑罚肯定在其所对应的类型化行为的刑种与刑度之内。至于具体行为的某些法定或酌定量刑情节,也只能在所属该类型化行为的法定刑区间内而上下浮动,并不能使该具体行为所对应的刑罚超出所属该类型化行为的法定刑区间。
又根据行为刑法原理和罪刑法定原则,能够作为刑罚处罚基底的具有可罚性的不法行为只能在立法者所预定的法定刑区间内裁量刑罚,而且立法者是根据这种违法有责行为类型的刑事责任的大小而配置法定刑区间的,并尽力做到重罪法定刑则重,罪轻则法定刑则轻。并且“犯罪者应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尺度”[17]。然而,以特别累犯扩展论的逻辑并非如此,特别累犯扩展论将导致大量的犯罪者被纳入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强行地增加刑罚当量,这种做法必然呈现“刑罚过剩”。鉴于特别累犯是一种法定的从严量刑情节,这就意味着许多犯罪者都要在其对应的法定刑区间内从重处罚,还有可能突破该罪的法定最高刑的界域,在其所犯之罪的法定刑幅度之上予以处罚。这势必导致如下令人担忧的景象:
第一,以特别累犯扩展论的逻辑,必然违背特别累犯设立的目的与初衷。特别累犯者的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虽然较大,但这都是相对于初犯而言的,并不是必然如此。况且,特别累犯的设立,绝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更不是为了从重处罚特别累犯者,而是为了促进特别累犯者的教育改造和自新向善。如果使特别累犯不断扩展乃至泛化,那么,许多犯罪者本来就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加之又构成“特别累犯”的污名化效果,这种“标签化”和“污名化”使得犯罪者在耻辱感和道德非难上压力重重,极有可能导致对犯罪者处罚的“立法过剩”。这不但不利于对此类犯罪者的教育改造,而且会发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二,以特别累犯扩展论的逻辑,一方面,特别累犯的立法模式将逐步失去其应有的特质,最终将与一般累犯的区隔微乎其微,特别累犯也将丧失其存在的特定价值,沦为“悲哀的玩具”;另一方面,许多再次犯罪者都将构成特别累犯,并且在应判处原有刑罚的基准上予以从重处罚,势必导致刑罚触须干预过度,极有可能出现过度扩大打击面甚至侵犯人权的风险。
三 特别累犯扩展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
如果说特别累犯扩展论在刑事法理上欠缺正当性的话,那么,它也完全不具有刑事政策上的必要性。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社会刑法的发展趋势,它不仅意味着刑事政策诉求的立法化,而且意味着刑事政策诉求的司法化,因为刑事政策是根据社会发展形势与犯罪发展态势而有效合理地作出的对犯罪的反应。我国在2006年以来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基本刑事政策,其时代精神在于以宽济严,主要彰显的“宽”的一面。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该“意见”第14条规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这些描述均显示了我国司法运用刑事政策限缩甚至搁置刑法条文适用、缩减定罪处刑适用范围的价值取向。
但是,以特别累犯扩展论的理论践履,极易导致特别累犯从重处罚泛化,这与当前我国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同时也意味着从重处罚的刑罚负担会延伸到更多的刑法罪名,对许多犯罪行为以从重处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论这种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性质如何,也不论这种犯罪行为的情节、手段以及是否既遂或未遂如何。在犯罪现象产生或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或司法者甚至公众只想到容易但引起错觉的补救办法,想到刑法典或新的镇压性法令[18]。其实,刑罚并不是像公众舆论想象的那样,是抗制犯罪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它对犯罪的威慑力很有限。并且累犯的涌现是复杂的个人因素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累犯者经过教育改造后势必要重新回归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实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表征,这种冲突仅仅通过惩罚难以完全解决,在对付累犯、防卫社会上刑罚的功能十分有限,必须建立一定的动态机制予以缓和抚平,即通过社会化过程使犯罪者被社会所接纳,在社会正常生活中得到教育改造。正如菲利所言:“一个真正文明的立法者,可以不过多地依赖刑法典,而是通过社会生活和立法中潜在的救治措施来减少犯罪的祸患。”[19]这与李斯特提出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此,无论立法者还是司法者,一方面,要以审慎的态度,遏制住随意启动扩展特别累犯圈的冲动,刑罚本来就不是对所有利益进行面面俱到予以保护的刑罚法则,刑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刑法保护的不完整性和不全面性。[20]并且在刑法领域应遵循人只能是法律的目的而不是手段,惩罚绝对不能因为一般预防的需要而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21],让犯罪人承受一种不必要的“恶”。借用边沁的的话所言,如果适用刑罚成为“滥用之刑”“无效之刑”“过分之刑”和“昂贵之刑”时[22],就不能扩展特别累犯圈。
另一方面,要明智地看待这样一种现象:现代社会中对犯罪的治理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司法资源短缺而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治理成本投入过大而效率过低这一刑法结构性矛盾。如果立法者和司法者无视这一凸显性矛盾,武断地采特别累犯扩展论,使刑罚干预的触须不断地扩张,甚至可能使大量惯常发生的而侵害法益不甚严重的犯罪都成为特别累犯从重处罚的对象。这不仅可能导致现代法治社会无法容忍的重刑主义、泛刑法主义的倾向,而且还使这一负面印象无端地给人提供攻击我国刑法依然追求重刑主义刑法的口实。简言之,以特别累犯扩展论而导致特别累犯泛化的结果,根本达不到有效保护法益的刑事政策目的,势必造成压制国民自由的危险。
幸运地是,不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总是现实的,并未走向特别累犯扩展论的泛化倾向。一个明智的、审慎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平衡刑法干预这一刑事政策的必要性与谦抑性,刑罚之适用应该避免刑罚过度或滥用,尽可能地节省刑罚资源,以最小代价而获取最大效益[23]。特别累犯扩展论势必导致国家更多的刑罚资源的投入,而国家的刑罚资源是一种稀缺性的社会资源,故合理配置国家的刑罚资源以发挥其最大效益便成为刑罚运行的价值取向[24]。而且刑罚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就要求合理划定特别累犯圈,合理限定特别累犯的边际。根据现代刑法的辅助性法益保护机能原理,基于实践理性使有限的司法资源配置效益化和最优化。一方面,要坚守特别累犯适用范围的界域,有选择性的、合目的性地将侵害重大法益的那些严重犯罪纳入其麾下,策略性地放弃有背刑事政策必要性的方法与手段,作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刑罚是维持人类社会适度和平与秩序所必要的恶,但刑罚必须有其特定的适用领域与边界,不适当的惩罚或过度的惩罚都是对刑法的莫大的损害。
当今世界文明各国无不以人权保障、法治国家为建设目标,也无不以体现人权保障精神的罪刑法定为刑法的根基[25]。这就意味着,刑法作为补充法、保障法在国家刑罚权的启动或延伸上必须遵循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这已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显然,特别累犯扩展论有偏离应然航向的风险,而特别累犯限缩论的提倡却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搏。
特别累犯限缩论的提倡能够体现这一累犯立法模式的功能与张力。一方面,它能够保持特别累犯所具有的特质,与一般累犯一起信守各自应有的边际效应,彼此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它能够使刑罚干预的触须伸缩有度,保持一定的张力,坚守刑法扩张的基本底线。
但是,特别累犯限缩论的提倡并不是把特别累犯看成是自足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适度的特别累犯圈。特别累犯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根据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犯罪态势、治安状况、刑事政策的走向以及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的变迁而适时地作出相应的调适。一般而言,在犯罪态势严峻、治安状况恶化、重刑主义盛行以及刑罚泛化观的主导下,极有可能会扩展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反之,则会限缩特别累犯的适用界域。如上所述,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扩展,正是这一特别累犯圈适度调适的合理运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而仍然是限缩的。笔者认为,当我国重新犯罪态势发生了如下变化时立法者方可以考虑扩展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其一,该犯罪侵犯了国家、社会或不特定个人的重大法益;其二,该重大法益引起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恐慌;其三,是刑法合目的性的追求。否则,特别累犯的适用界域将始终保持限缩。
参考文献:
[1]王强军.特殊累犯裂变式增加的理性应对[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8):80-86.
[2]赵秉志,苏彩霞.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以及立法完善[N].法制日报,2003-04-24.
[3]韩 轶.我国累犯制度立法之完善[J].法商研究,2006 (3):26-31.
[4]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117-122.
[5]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J].人民检察,2006 (10):15-18.
[6]赵秉志,杜 邈.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特殊累犯规定的解读[N]法制日报,2011-05-04(012).
[7]储槐植,闫 雨.刑事一体化践行[J].中国法学,2013 (2):139-146.
[8]董文辉.突破与困窘:累犯制度修正辨析[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1(6):75-79.
[9]谢应霞.论我国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67-69.
[10]孟庆华.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及立法重构问题探讨[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5-6):177-183.
[11]陈金林.累犯的前提:犯罪还是刑罚?——对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的解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5):21-26.
[12]加罗法洛.犯罪学[M].耿 伟,王 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90.
[1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69.
[14]卢勤忠.《刑法修正案(六)》与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思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79-87.
[15]季理华.累犯制度研究—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累犯制度一体化构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67.
[16]苏彩霞.累犯法律后果比较研究—兼论我国累犯刑事处遇之检讨[J].法学评论,2003(3):31-40.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1.
[18]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70.
[19]恩里科·菲利.实证派犯罪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43.
[20]车 浩.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J].法学研究,
2010(2):136-155.
[21]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4.
[22]吉米·边沁.立法理论[M].李贵方,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73-374.
[23]梁根林.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J].中国法学,2011(2):156-176.
[24]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87.
[25]刘艳红.“风险刑法”理论不能动摇刑法谦抑主义[J].法商研究,2011(4):26-29.
责任编辑:黄声波
TONG Qixian1,2
(1.Department of Law,Xin Zhou Normal College,Xinzhou,Shanxi 034000,China;2.School of Law,An 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bstract:Recently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e scope of special recidivist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But the reasons supporting these viewpoints were not convincing.The expansion theory of special recidivist does not only lack enough legal legitimacy,but also lack the necessity of criminal policy.The legislation tendence of special recidivist should be restricted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pecial recidivist;criminal policy;expansion theory;restriction theory
作者简介:仝其宪(1974-),男,河南濮阳人,忻州师范学院讲师,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收稿日期:2015-01-01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5.010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55-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924.13
Special Recidivist:Expanding or Restric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