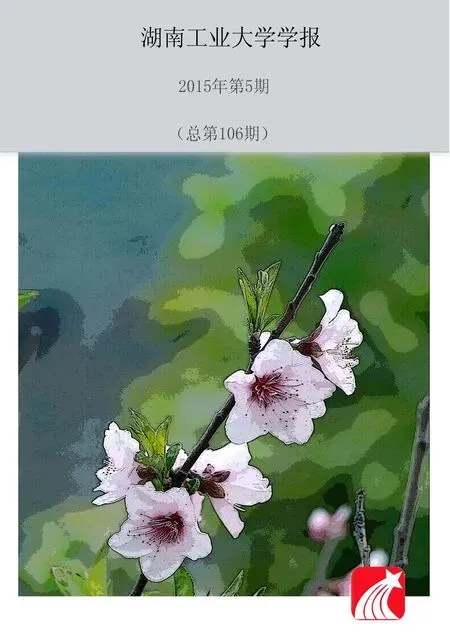郑小驴论
2015-03-17乔宏智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乔宏智,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郑小驴论
乔宏智,张丽军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郑小驴是出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作家,身为代际划分法中的“80后”新生代文坛力量,其与市场化的“青春写作”截然不同,给我们带来了接续文学传统的新希望。郑小驴的小说以80年代生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为创作资源,既有青少年期的成长与创伤,又有当下社会青年人的生存困境;既有以家族、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化写作,又有充满隐喻的寓言故事。无论是何种题材,都共同表达了80后一代人独有的生命体验。郑小驴的小说在讲述同代人的故事背后,呈现了一代人的反思和批判。
[关键词]郑小驴;现实题材;家族历史;“80后”;生命体验
张丽军(1972-),男,山东莒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山东省
作协特邀文学评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郑小驴是“80后”文坛新势力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其小说既关注湘西的乡土世界,又充满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反思,在传承文学史的同时,呈现其特有的生存经验和精神立场。郑小驴超越年龄的成熟、老道的小说创作近几年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过去的“80后”写作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市场孵化·轻写作·伪忧伤·恋物”[1]等等一系列负面的阅读感受,以郑小驴为代表的新生代“80后”作家的渐次出场,逐渐改变了人们对“80后”作家的成见,看到了新生代作家们对文学史传承的努力。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读过郑小驴的小说后评价道:“他的文字功力和叙事才能让我难以忘记。他改变了我对80后这代人不应有的判断。”[2]作家温亚军也曾这样评价道:“感觉小驴不像80后写作者,他的叙述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没有他那个年龄段写作者的狂放恣意。”[3]具体到郑小驴的小说创作,《1921年的童谣》《1966年的一盏马灯》等历史题材小说和《痒》《飞利浦牌剃须刀》等关注现代社会的作品,同样出自这位“80后”作家之手,关注当下社会,回忆历史故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小说创作在郑小驴这里是统一的。将一位作家的作品大卸八块,进行“条块化”的处理往往会导致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对郑小驴而言,现实题材的小说和历史题材的小说同样也是“貌离”而“神合”的。沿着这两条郑小驴小说创作的路径,我们一起去探寻郑小驴小说核心地带的精神秘密。
一 关注现实:随“80后”一代人的成长阵痛而颤栗
尽管当前学界对按照作家出生年龄来划分作家创作群体的“代际划分法”存在颇多争议,许多作家自己也并不同意简单地将其归入某一创作代际阵营中。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不同时代的人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性,即便是同时代的人身份认同也是多元和自相矛盾的,代际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存在。”[4]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和社会文化思潮对其生活的影响等往往成为一个作家最直接和重要的创作资源。亲历者的身份赋予言说者一种天然的合法性。较早成名的“80后”作家们便是借书写自己的“正青春”而引起人们的关注的。郑小驴也自然选择了书写同代人的故事这一天然的创作源泉,他毫不避讳自己“80后”作家的身份,还经常在作品中直接调侃“80后”一代人。如《大罪》中事业不顺利的小马和一群年轻的教师在一起喝酒的时候直呼:“我们80后没法活了!”[5]121又如《像人》中郑小驴借警察之口自嘲道:“你们80后是什么也不知道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唉!”[5]170然而,郑小驴不是简单地轻松幽默,而是真实写出了“80后”一代人生存、成长的困境,表达了切肤的痛感。
1978年以后,我国正式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并将之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延续至今,“80后”一代人是最早与计划生育发生碰撞的一代人,尤其是在“重男轻女”思想更为普遍的乡村地区,计划生育的执行更加困难,也更加残酷。许多作家已将其纳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关注,如莫言的小说《蛙》等。郑小驴的长篇小说《西洲曲》、中短篇小说《鬼节》和《不存在的婴儿》关注的便是计划生育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西洲曲》将视角放在了南棉镇青花滩一个五口之家,以家中的小儿子——十几岁的少年罗成为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现计划生育制度下不同角色命运的云谲波诡。谭青的妻子北妹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却一直想生个儿子。便在罗家住下,躲避计划生育检查。一次躲避搜查的时候因为在地窖里时间太久导致缺氧,致使婴儿流产。不久北妹因为接受不了丧子之痛跳河自杀了。丈夫谭青从此性情大变,将这一笔血债记在了执行国策的罗副镇长身上,走上了复仇的道路。将罗副镇长的唯一的儿子——“我”的同学罗圭暗中杀害了。小说没有控诉计划生育制度的不合理,而是展现事件中个体的遭遇。通过罗圭之口,我们发现,貌似是主导这次悲剧的罗副镇长,也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只是因为妻子的不能生育而无法实现。中年丧子的罗副镇长,最终却收养了一个又聋又哑、不知从哪流浪过来的孩子,并喃喃自语:“孩子没了,老婆走了,他今后就是我的天,我的地,我的祖宗了……”[6]234八叔在此次北妹的悲剧中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较早察觉到了北妹在我家躲避计划生育,便以此相要挟,让“我”的姐姐左兰嫁给他的残疾儿子大方。从人情的角度来讲,这是不为人所耻的行径。然而谁又能想到,“在石门,大方是唯一一个独生子女。八叔那时其实大可再要一个,只是因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第二胎都有三四个月了,他将自己女人拉去了医院。”[6]69从执行政策的角度看,这反而是一个英雄。从这里我们看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杂性。从今天的社会现实看,关注“失独”家庭也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这些苦痛都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鬼节》和《西洲曲》在故事结构上可看作姊妹篇,将躲避计划生育放在了七月十五过鬼节的背景下,凸现了悲凉的成分。短篇小说《不存在的婴儿》则从未出生也不可能出生的腹中胎儿的视角,讲述他的离去给自己和一家人带来的痛苦。
展现少年时代成长期的孤独、苦闷和青年一代80后蚁族生存、奋斗的艰辛也是郑小驴现实题材小说中的重要关注点。这种经验也是郑小驴同时代人所共有的体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直接导致了许多少年青春期时的孤独、苦闷无处发泄、无人诉说。《西洲曲》中的罗圭向好友罗成直接倾诉道:“我很孤独,我家就我一个孩子,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让别人超生孩子,却忽略了我的孤独。”[6]24有时,这种孤独甚至会造成心理的扭曲和创伤。《我略知一二》中的初二小女孩李青梨便遭遇了这样的问题。她来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李青松。然而经过一系列侦查,根本找不到任何现场和证据。李青梨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哥哥,但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淹死了。李青梨曾经和一个叫林萧的男生谈过恋爱,后来也分手了。李青梨为什么要报假警呢?通过李青梨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我们了解了一点,李青梨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常年和聋哑的奶奶一起生活。李青梨是孤独,她曾试图向日记、向男朋友身上摆脱这种孤独,但都失败了。李青梨的母亲说道:“我知道她一直都想要个哥哥,她孤单,像只可怜的小鸟儿,从小没人陪她说话……”[7]116“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有所关注,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或许我们仅仅是略知一二的。郑小驴从切身的体验出发,为我们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感受。
作为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下的一代,没有了兄弟姐妹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伴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理应过上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没想到的是,等待这一代人的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文凭贬值和土地财政带来的高房价。知识不再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金光大道,社会阶层的固化日益明显,蚁族理所应当地出现了。《少儿不宜》中的少年游离,便在这样一种未知的茫然中游离着。他的好友溜子抱怨道:“我爸说今年考不上,明年再去复读,他说考大学才是我唯一的出路。妈的,你说现在大学生那么多,扫厕所的都有,我爸这人就是想不明白!”[7]10作为家里的成功案例,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的堂哥,却因为收入过低买不起房和女友吵架冲动跳楼。曾经被他人羡慕的伯伯竟这样感慨道:“早知道就不该送他念书,那花花城市,是他待得了的吗!”[7]18《七月流血事件》中的主人公蚁族小曾更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后精神崩溃挥刀向他人!这些都是属于“80后”一代人的独特体验,是郑小驴同代人的故事。
二 回溯历史:表达“80后”一代人的历史态度
李德南曾撰文分析“80后”写作中“去历史化”和“非历史化”的写作问题。他在文中分析道:“从生活环境上来讲,绝大多数的‘80后’,都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受反‘右’、‘文革’、‘上山下乡’这些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历史记忆相对稀薄。1990年以来开始愈演愈烈的商业意识和消费主义氛围,也使得这一代的作者乐于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地当中。”[8]对现代人而言,历史只存在于史料和想象之中,未曾亲历的心情体会到的更多只是他人的一段故事。故而历史叙事难免会成为“80后”作家们的软肋。郑小驴的几篇家族、历史叙事小说,如《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1966年的一盏马灯》《枪声》和《鬼子们》等,则成功表达了“80后”青年作家们眼中历史的模样和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尽管郑小驴本人曾表示过对这一部分历史小说的不满:“那时还在上学,视野有限。之所以有段时间偏执于年份为题目的小说,可能出自于自己的个人喜好吧。现在不这么取题目了。……比方说你现在对我小说的印象依然停留在年份与历史等为题材的层面。其实我就写了这么两三个,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我们依然不能忽视郑小驴对历史题材的成功实验和所引起的评论界的关注。对于未曾从那个年代走过的郑小驴,如何将历史题材处理得具有当下的真实感呢?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写出了当代人对历史的态度,二是对历史故事采取恰当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处理。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反右斗争扩大化等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都在郑小驴的笔下成为了他小说创作的内容。然而,面对同样一段历史,郑小驴小说中对历史的态度和看法,与老一辈作家们的书写是有着一种异质性因素存在的。小说《鬼子们》,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末期一批驻扎在“我们”村里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小说写出了侵略者的血腥、残暴,惨无人道,小说也写出了普通民众,如“我”的瞎眼老娘对侵略者的无所畏惧与抵抗。但小说还表现了侵略者们人性化的一面。得知日本遭到美国原子弹的轰炸后,他们会去寺庙里祈福、祷告,会常常拿着家里亲人的照片怀想,甚至还将“我”的瞎子娘当作家里老母亲的情感寄托给我们送猪肉和罐头吃。而在随时有着死亡威胁的“我”眼中:“说实话,我也不是很反感这些鬼子。要是他们不随便砍人脑壳,国军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去。”[10]86这种印象与我们传统的国民教育是磗格不入的。又比如小说《1921年的童谣》中,革命红军来到青花滩,将头号地主陈大膀子杀害时的一段:
陈大膀子挣扎着不服气,说,我哪该死了?你们把我们陈家祠堂也征用了,地契也没收了,饭也给你们煮了,还杀了一口猪给你们吃——我也是过年才杀得上猪啊!
湘西佬吐了几个眼圈,眯着眼睛说,这我知道,可今天必须要把你杀掉。
陈大膀子说,为啥呀?
湘西佬说,这是革命上的问题,给你说了,你也未必能明白,你懂了吗?
陈大膀子低着头,说,我不懂。
湘西佬说,还不懂?!不杀你我们杀谁去,谁让你是青花滩的头号地主,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
陈大膀子说,我富,也是靠自己一点一滴节俭出来的,我既不偷又不抢,凭啥杀我![10]9
不难看出,革命在青年一代作家眼中,不再只是一味地盲目狂热。“革命”的许多做法也并非完全经得住历史的推敲与审视。行刑前,“陈大膀子哑着嗓子边走边喊,难道富也有罪吗!?”表达的正是年轻一代作家对历史的反问和思索。对比当代文学中“十七年时期”的文艺作品,郑小驴的这种历史态度是具有代表性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文艺思潮与我国历史史实交融的结果。同时,这种历史观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代表了“80后”郑小驴同代人对历史的更加理性的理解和反思。
从小说技法来讲,郑小驴通过多种手段将虚构的历史小说赋予了相当真实的力量。首先,郑小驴从史书、史料和民间传说中去认识连自己的父辈都未曾亲历的故事。例如,郑小驴在《少年与蛇》文后写道:“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听说过有关这两个少年失踪的传说不下十余种。”[7]226将传说和历史记载进行想象和虚构,亦虚亦实。其次,郑小驴的历史题材作品往往采用家族修辞的手段,获得了一种类似自传般的真实感。其关注年份的几部作品尤为突出。《1921年的童谣》从祖父、祖母的童年写起,一直写到孙子辈的“我”。将郑家家族的命运放置在从抗战到文革的历史洪流中,以家族史的变迁管窥民族历史,获得历史真实感的同时,具备了史诗般的宏大品格。再次,小说中的鬼魅叙事增添了作品的色彩。各种怪力乱神往往是通过乡村的独特习俗和民间传说来粉墨登场的。比如《望天宫》中,爷爷对年幼生病的“我”传授经验:
万籁俱寂的深夜里,一阵清风徐徐而过,紧接着的便是幽幽袅袅的怪声,长时间地在那广袤幽暗的夜空里回荡着,恍惚中,你便能听到一个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好像是在喊你的名字。这时候,如果你未及细思,顺口就应了,那么大难很快就要降临到你的头上了。因为外间叫你名的是鬼,你应了一声,你的灵魂便脱离肉身,跟着它走了。爷爷的话总是让我夜里不敢一个人睡觉。他还说,夜里不能照镜子。
夜里照镜子,你会突然发现镜子里的人突然换了一副你陌生的面孔……夜里还不能梳头发和吹口哨,那样会让你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吹口哨会招来鬼……不能钻女人晾衣服的架子下面,也不能钻板凳和床,那样会长不高个子……[10]156
从今日科学的角度来看,许多民俗与传说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在那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这就是信仰的一种。时至今日,烧纸、祭祀等许多传统我们依然保留着。郑小驴的鬼魅叙事是对历史真实的一种再现。最后,郑小驴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平静地甚至于略显冷漠的叙事态度,无论是对暴力还是仇恨与战争,这与前文提到的现实题材作品的叙事态度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也是符合叙事真实的,因为毕竟对历史而言,我们都是旁观者。过于投入和激烈的感情反应反而显得技法痕迹太重了。
三 殊路同归:“80后”对社会、人生的追问与求索
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无论使用何种文体来表达,无论关注何种题材、虚构怎样的故事,他的作品中都必须要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能放弃一个作家所应承担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作家的责任和使命会随着时代发展、社会进步而发生改变,但关乎人类生存、发展、道德与良知的底线不会消亡。从郑小驴的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新生代“80后”作家对生命、对信仰、对爱情、对历史、对人生的感受和思考,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潜流在郑小驴小说写作的核心地带。对人自身的关注是每一代作家都要感受和思考的,郑小驴将他所感受到的同代人对人类价值和情感的追问用小说的形式传达了出来,作为“80后”一代人的时代经验传声筒,郑小驴正践行着一个作家的精神使命。郑小驴的多种类型题材的小说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反思和感叹。
《最后一个道士》表现了对传统文化后继乏人、衰落甚至消亡的惋惜。在石门的牯岭上,最后一户人家已经搬离,只剩下了蛇神庙里的老道士老铁。尽管庙宇并不大,但佛事、道场、巫术俱在,过去的人们不论何种重大事情都要请老铁做法事。老铁一生收了三个徒弟,子春是他的小徒弟,也是老铁寄予厚望欲传之衣钵的徒弟。子春悟性高,学习老铁的本领也最为精进,但是心不静。上牯岭两年后,老铁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子春报名当兵了。走的时候,子春答应复员后回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习,继承师父的衣钵。然而子春此一去,直至老铁病逝,都再没有登上蛇神庙。子春复员后宁肯去繁华的广州商场的门口作保安,也不愿意回去当道士。两年后,子春已是肥头大耳一副尘世人的模样,当过去的邮递员小楼来到广州见到子春,提起是否继承师父的几大箱衣钵的时候,子春笑了笑说:“都不干这行了,还留着干什么!你要吗?你要送给你好了。”[7]274子春眼里,这不过是个挣生活的行当。最后一个道士的死去,衣钵的无人传承,道士文化也永远停留在了史书的记载中。
《白虎之年》则是一篇反思人类文明的寓言故事。一只未进化完全的小人猿叫毛孩,他号称能看到传说中的白虎,并一直渴望有一天骑着白虎离开青花滩。大家都把他看成疯子。然而那一年的冬天开始,从旺家女人生下了一个死胎开始,各种各样的怪事发生在了青花滩。埋在山上的死婴不翼而飞,河里打捞上来长着人脚的会哭泣的鱼,人们开始忘记各种工具的使用方法,就连青花滩最聪明的教书匠郑源都不认识字了。情况继续恶化,人们忘记了怎样做饭,不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吃,饥饿笼罩了人间。直到最后父母子女之间互不相识,自相残杀。所有的文明印记在人类身上消失殆尽。毛孩一直等待着白虎出现,以为见到白虎这一切都会回到从前,然而白虎一直都没有出现,毛孩,作为青花滩最后一个人类,被一群野兽分食掉了。这是一篇醒世的寓言。人类进化到高级动物,产生了文明和道德。试想有一天,大自然将人类的文明一点点收回,人类终将退化成最原始的兽,今天的我们还会去做践踏道德、毁灭文明的兽行吗?!
《小驴回家》则是一篇关注现实、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兄弟的作品。“我”的家在偏远贫穷的大山沟里,不满22岁的“我”早早地就和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去了桃城做了一名水泥小工。生活艰辛、工作在城里备受歧视,孩子的教育无法保障,就连生病了都看不起。“他们这样的眼光我已经太熟悉了,我甚至不用抬头就能读懂他们眼神里所饱含的鄙夷和不屑,我已经习惯了甚至麻木了。二十年来,我去过好几个城市,所到之处,只要他们不驱赶我们就谢天谢地了。”[10]185即便如此,“我”一出生便死了娘的堂侄少斌依然跟我来到了城市打工。然而命运仿佛生来就不平等:“农村人的命贱,在城里做事,如遇天灾人祸,就如死了一只蚂蚁一样。”[10]192少斌在工地出事了,为了救其他工友,腰部以下被砸瘫痪。多年未回家的“我”,回家后却给少斌的爹带来了噩耗。为了不拖累少斌,少斌老爹喝农药自杀了。少斌仅仅得到了5万元赔偿款,后来疯了。我们自身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在农村,不管你怎样,只有读书,才是你步入城市的唯一出路。”[10]196然而仅仅依靠知识,在现在的社会想要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依然困难重重。但,其他已别无选择。《小驴回家》中展现的贫困农民生活是一种残酷的真相,从中我们也体味到了郑小驴一颗心忧大地的悲悯之心。
《和九月说再见》对纯洁的爱情和物质的爱情进行了思辨,并对人们普遍认同的爱情中的好男人形象进行了颠覆。《弥天》则对宗教信仰发出了思考。借小说中人物“信仰这什么狗屁东西,这世界还有什么值得信仰的吗?上帝给你房住给你饭吃给你钱花吗?”[7]79的反问,探寻信仰的终极力量。《1921年的童谣》,涉及一个家族三代人几十年的历史,最终要表达的不过是那首人人从小都会唱的童谣:“衣要遮体呃/饭要吃饱呃/苦难再多呃/活着就好呃”[10]4苦难再多,活着就好,这是一代青年作家对生存最本质的领悟。郑小驴通过对不同题材、不同角度对不同情感、价值的反思,为我们呈现了80后一代人“在路上”的成熟与思考。
“在新时期一个个文学浪潮中,一些作家被淘汰了,一些作家如贾平凹、莫言、张炜、铁凝、王安忆、迟子建、苏童、格非等新作不间断的推出,成为30年文坛的常青树,构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超稳定文坛格局。超稳定的文坛客观造成了作家群体代际更替的延宕。而对这一文学困境,80后作家另辟蹊径,彻底放弃了传统作家从期刊到出版的漫长、严苛的成长道路,而在新的市场经济和文化消费主义思潮之下,与出版、传媒、网络合作,直接走向文学终端市场,以造星的方式包装打造文学界的‘明星’。”[11]或许没有这一批文学明星耀眼的星光,80后一代作家的浮出历史地表还需要延后多年。幸运的是,明星耀眼光环的背后,郑小驴等一批继承文学史传统的作家没有错过登台的时机,在“80后”青春校园写作渐行渐远的时候,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继续前行的文坛新力量。郑小驴的作品依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缺憾,依然还是实验性的文本,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郑小驴小说中向大师致敬的影子,如《一九四五年的长河》相较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望天宫》中的蚩尤相较于《爸爸爸》中的丙崽,《坐在雪地上张开嘴》相较于莫言的《四十一炮》等,都是一些成功的尝试。通过郑小驴的小说,我们听到了80后一代人的故事,了解了“80后”作家在文学上的努力和尝试,看到了青年一代对文学的继承和对责任的担当。“80后”一代人的故事,更精彩的篇章在等着我们。
参考文献:
[1]张丽军.市场孵化·轻写作·伪忧伤·恋物——关于“80后”文学精神性缺失与困境的讨论[J].艺术广角,2010(5):14-20.
[2]郑小驴.此行西去[J].美文,2010(1):4-8.
[3]《民族论坛》编辑部.来自大地的书写——湖南省青年文学奖获得者周伟、郑小驴评论的摘录[J].民族论坛,2012(5):63-65.
[4]郭 艳.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12.
[5]郑小驴.痒[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
[6]郑小驴.西洲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7]郑小驴.少儿不宜[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8]李德南.为什么历史在“80后”写作中缺席[N].北京日报,2012-05-24(018).
[9]姚常伟.对话青年作家郑小驴[J].创作与评论,2012 (10):9-11.
[10]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11]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2):65-77.
责任编辑:黄声波
On Zheng Xiaolv
QIAO Hongzhi,ZHANG Li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250014 China)
Abstract:Zheng Xiaolv is a young writer born in the 1980's.As a new generation writer of post-80’s according to the generational dividing method,his writing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rketized“youth writing”,and has brought us a new hop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iterary tradition.The creative resources of Zheng Xiaolv’s novels are mainly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people born in 1980s,including the growth and trauma in adolescence,and the living predicament of the young peopl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His novels not only have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both family and history,but also full of many fables of metaphor.No matter what subject matter it is,they all express the uniqu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Behind the stories,Zheng Xiaolv's novels present the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an entire generation.
Key words:Zheng Xiaolv;realistic theme;family history;post-80’s;life experience
作者简介:乔宏智(1989-),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2-28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5.003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14-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