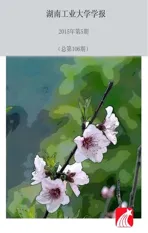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家族叙事——评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
2015-03-17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熊 辉(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家族叙事
——评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
熊 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关键词]《1921年的童谣》;新历史主义;家族叙事;述史立场
[摘 要]新历史主义从解构的立场上去重新书写历史,意欲发掘在主流意识形态遮蔽下的真实现实。据此观念出发,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通过“边缘”的家族叙事,从历史、革命、女性和日常生活等四个维度去解构了“大历史”的权威性和唯一性,进而揭示出鲜为人知的历史本相,也传递出作者鲜明的述史立场和历史观念。
新历史主义随着西方后现代解构思潮而兴起于文学批评界,成为20世纪后半期冲破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乃至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的文论巨擘之一,它注重从生活碎片中去寻找建构历史的文化符号,从而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叙史立场的解构,达到重新书写和建构文学史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郑小驴的小说《1921年的童谣》,我们就会发现其通过家族叙事的方式对历史、革命、女性和日常生活的观照具有较多的文化意涵。
一
新历史主义的总体精神“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整体性、未来乌托邦、历史决定论、历史命运说和历史终结说做出自己的否定判词上。因而,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和中断论,否定历史的乌托邦而坚持历史的现实斗争,排斥非历史决定论而张扬主体的反抗颠覆论,成为其流派的标志。”[1]156因此,历史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历史的非连续性和生命的变化无常在《1921年的童谣》的家族叙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部小说以“祖父”那辈人的生活经历为叙述时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合理或不合理的斗争与反抗构成了家族发展的主要的内容。从青花滩郑家和陈家的家族发展历史来看,曾占据上风的陈家并没有一直延续祖上的威望,他们族里的领头人陈大膀子碰到红军的武装力量时,在不由分说且毫无辩驳机会的情况下,被湘西佬的大刀砍去了脑袋。红军接着烧掉陈家的地契并分发其粮食,让陈家几辈人积累的基业瞬间荡然无存,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在青花滩的荣威。与此同时,郑家在红军路过青花滩这一偶然事件中,不花费任何力气便取得了与陈家竞争的胜利。加之当时郑家有七个儿子,家族人丁兴旺,毫无争议地称为青花滩的名门显族。但恰如美国新历史主义学者格林布拉特所言,历史具有非连续性和非乌托邦色彩,总是充满了断裂性和矛盾斗争,[1]160家族的发展同样如此。郑家在陈家衰败后,也没有一直占据青花滩的主导地位,曾经兴旺的人丁在各种“革命”和“斗争”中纷纷离世,衰败之势不可阻挡。为躲避抓壮丁的老五一直下落不明,为维持生计当土匪的老四被斩首示众,婚姻不幸的老大被火药枪走火打死,心灵手巧的老二被疾病折磨致死,快要成亲的老六在修路时被钢材击中身亡,懒惰成性的老三在灾荒年成中被饥饿夺去生命。最后只剩下游手好闲和爱寻花问柳的“祖父”,在极度向往自由而又不愿受家庭拖累的情况下,通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婚姻延续了郑家的血脉历史。陈家和郑家的家族遭遇不但说明了历史的偶然性和非连续性,而且说明了生命个体的发展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如郑家六兄弟的死亡都源于天灾人祸而非自然生卒。
历史不仅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历史的叙述者也不是主流的文化精英分子。《1921年的童谣》叙述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这不是“祖父”在芦花荡中唱童谣的天真年代,却是中国历史翻开新篇章的特殊时间,中国共产党在该年成立,中国的社会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因此,作者与其说是在家族叙事,毋宁说是在讲述一段历史;与其说是在讲述一段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家族发展历程来呈现一段历史。但郑小驴意欲讲述的这段历史,在时间维度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层人民革命并建立新社会的奋斗史重合,在内容维度上却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大历史”所讲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层人民革命并建立新社会的面貌有所差异。当然,作者在此并非想借助一部文学作品来解构1921年之后的中国历史,而是借助下层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家族兴衰的过程来更真实地呈现这段历史。“曾祖父”和“老外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叙述者,他们将红军进村后的各种举动看在心里,并与随后到来的国民党“正规军”的言行进行对比,不管两支部队进村后做了什么,但青花滩的人总认为国民党军当着众人的面,在红军的标语上“撒尿”是最不得体的行为,在普通村民看来就是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举动。“老外公”送粮给红军却得到“江西佬”按市面上的粮价返还的银两;反之,国民党军进村后,“北方佬”骂骂咧咧的要求给他的部队无偿地准备“猪牛羊鸡狗”之类的食物。在扩充兵力方面,红军靠行动吸引青年参军,脾气暴躁的郑家老四“蛮脑壳”自觉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想法;“正规军”靠抓壮丁补充兵力,村里的保长私下动员青壮年逃走,连一直想参军的“蛮脑壳”和老五郑能保也跟着逃丁的人群消失在夜色中。《1921年的童谣》除通过老百姓眼睛的观察比较了国军和红军外,也将日本部队的暴虐行为暴露无遗,“曾祖父”在日本人进村烧杀抢夺之后叹息道:“这哪是群军队,就是畜生嘛!军阀的部队虽然野蛮,可人家吃完饭也不会砸锅,更不会往里拉屎的,更不要谈那样对待老妇了!暴戾到如此的程度,气数也快到头了。”[2]
《1921年的童谣》无意于重新书写历史,其叙述的历史事件只是郑家人的经历和青花滩人的看法,他们世代关注的焦点就是“童谣”所唱的:“衣要遮体呃/饭要吃饱呃/苦难再多呃/活着就好呃”,他们是只知道吃饱穿暖的农民,社会变革和政治争斗对他们来说意义甚微,他们本就是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的“边缘人”,在宏大的历史书写中不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童谣》正是通过“底层”和“边缘”人群非历史意识的感官察觉和朴素的价值判断,建立起了红军的正面形象,比之意识形态的爱党教育和大历史对党光辉形象的刻写,郑家人的家族经历更为有效地突出了国共两党的优劣。让读者毫不犹豫地认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然会打败国民党军,帮助穷苦人民实现生活的温饱。难怪最后曾祖父长叹了口气说到:“我看红军还是会回来的。”[2]曾祖父意味深长的话实际上表明了大众的立场,他们从现实斗争中认清了红军代表的正义和阶级立场,从心底里希望红军回来解放大众。
大历史记载的“必然”事件往往祛除了血腥的场面和生命个体的感伤,从而让历史以客观和中性的角色展示在人们面前。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921年的童谣》通过家族叙事揭示出历史事件对其时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郑家老小的生活充斥着革命之后的运动热潮或自然灾害,从而演变成一出出悲壮的戏剧。红军来青花滩时,郑家“曾祖父”不知革命为何物而采取观望的姿态,他甚至阻止四儿子郑能崇参加红军,不想性格刚烈的郑家老四后来入了土匪窝,被镇压后尸首异处。日本人打到青花滩时,他们残暴地打死了“老妇人”,在村子里无恶不作,积累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无尽的仇恨。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祖母”的父亲、前夫和兄弟被划为地主成分处死,“和十几年前红军处决陈大膀子不同的是,他们都是吃枪子儿死去的,死之前还开了审判大会。”[2]这是种戏谑的表述方式,用枪打死和用大刀砍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充满了惊人的相似之处。“破四旧运动”开始之后,青花滩年久失修的破庵堂被一把火烧掉,不再允许和尚打道场,“祖父”的生活来源就此断掉。在这场看似积极先进的运动中,很多地方的民俗民风被封建迷信的大帽子压制得失传甚至消失,成为今天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最大惋惜。“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郑家老六被饥饿和疾病折磨致死,他是那个时期千千万万忍受饥饿并在饥饿中死去的中国人的缩影。“人定胜天”的豪情壮志面对自然的伟力显得如此惨白无力,人始终摆不脱造物主的作弄和“天”的安排。随之而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很多中国人卷入其中,“地主婆陈云青”除要忍受家人冷战的暴力和日渐严重的哮喘病外,“文革”中一直没有停止被批斗的厄运,残暴的体罚和让人失去尊严的批斗会最终让她不堪重负,童谣中“活着就好呃”的乡谚不得不让位于“死是最好的解脱”,于是“祖母”在1967年的春天投河自尽。“二叔”是典型的“进步”文革青年,他将不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母亲是地主婆,因此从心底里怨恨母亲,那个时代的政治热情高于骨肉亲情,造成很多父子或母子仇杀的悲剧。“二叔”是青花滩最有能力的知识青年,能背诵很多毛主席语录,能刷写出漂亮的标语,但却在一次武斗中被人装入麻袋沉到河底身亡,与曾经最怨恨的母亲一道魂归流水。
郑家人在历史的浪潮和大是大非的政治运动中相继离世,最后只剩下“祖父”和“父亲”,其他的都死于非命,这不能不让人思考历史的残酷性和生命的无常性。“如果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我们所不熟悉的事件,他必须使用比喻的语言而不是技术语言。……为了使数据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3]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叙事与历史叙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1921年的童谣》通过家族书写的方式,那些底层人的生活遭遇将中国社会革命和历史运动建构得有血有肉,至少从某种很少被人提及的侧面丰富了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而我们不再将历史置于某种社会学说中加以冷静分析,而是通过“考古”的方式发掘隐藏在大历史书写下的“碎片”,并借助这些“碎片”或偶然事件更真切地还原那个时代的生活现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赋予了文学文本更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小说创作不再是对日常生活的描摹和反映,小说家借助文学创作在小说文本中进一步生成了历史。郑小驴的《1921年的童谣》便具有这样的写作价值和意义,透过郑家老小在不同时代的命运和那首老百姓注重“吃”“穿”的民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至改革开放之际的中国历史便鲜活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
“1921年”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神圣的意义,而“童谣”则具有俚俗的特点,郑小驴将二者融合到创作中并将之作为小说的题名,其创作意图十分明显:用老百姓的生活经验来阐释严肃的历史。郑小驴的创作契合了新历史主义通过边缘人书写的“小历史”去重新审视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书写的“大历史”的文化观念,因此《1921年的童谣》这部小说呈现出的历史更为丰满。
二
《1921年的童谣》没有将红军英雄或领袖人物作为表现革命的对象,反倒是将青花滩郑家的传说和“祖父”的生活经历作为填充这段革命历史的素材,补充了正史之外的历史场景和边缘人对革命历史的认识。同时,小说透过日常生活事件再现了当年共产党革命的艰辛,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革命的目标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诉求,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
法国文论家福柯认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正在摆脱线性的时间或占据主导的宏大意识形态,从而将那些散落在时间深处的碎片和“物质事件”作为发掘真实历史现场的依据。在福柯看来,不仅是历史,就连“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4]在福柯观点的基础上,新历史主义“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伟叙事,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领袖人物)作为分析对象,看其人性的扭曲或人性的生长,看在权利和权威的历史网络中心灵是以怎样的姿态去拆解正统学术,以怎样的怀疑否定的眼光对现存社会秩序加以质疑”。[1]159《1921年的童谣》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家族叙事的方式来阐释中国社会革命的真实境况,即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之目的在于改变穷人的生活现状,建国后随之而起的各种运动都在于维护穷人阶层的利益。这种理念比较符合意大利社会学家马基雅维里的革命发生论:“人们因为希望改变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5]革命领导者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楚的思想指导,追随革命的人或被领导革命的人往往对革命缺乏宏观的认识,退而其次的广大农民就更难理解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最终目的。进步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和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产生了改变自身境遇的希望,在1921年组建了政党并拿起武器反抗统治者。
革命之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湘西佬”在面对陈大膀子质问为何要砍他的头时,只简单地回答道:“这是革命上的问题,给你说了,你也未必能明白”。这句话表明,要么红军将领湘西佬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人,要么陈大膀子听不明白革命的道理,总之是有人没明白什么叫革命,也总有人简单地把杀人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对郑家老小和青花滩的所有农民来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身边,但却与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他们关心的永远只有“吃饱”和“穿暖”两件事,谁当了皇帝谁作了统治者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青花滩的郑家“曾祖父”说:“这年头,管他们是红军还是国军呢,咱这些泥巴子能活着吃口饱饭就万幸了”,陈家坪的“老外公”等人的生活希望和目标就是“广积粮,多置田。”老一辈人尚且如此理解革命,那到了祖父这辈人呢?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湘西佬”实现诺言打回青花滩后与“祖父”的对话充满了反讽和哲思:“湘西佬”得意地对“祖父”说革命成功了,“祖父”顺势问以后世界会怎样;“湘西佬”说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且自由了,但“祖父”说:“我们做百姓的,这一辈子,人一个,卵一条,不为吃,为啥?你们的那些革命,太高深了,我们也明白不了,我们只关心每天有没有吃的,有吃的,就翻身了,这天下便太平了。”[2]这一席话让刚才还很神气得意的“湘西佬”摸了摸脸说:“这道刀疤,也算是革命的纪念品。要是为了你刚才的那席话,还真他娘的不值得。”[2]“湘西佬”光荣而伟大的革命经历被“祖父”的一席话瓦解得只剩下后悔二字。“祖父”从普通人维持生存的角度出发,认为革命与否或当官与否还不照样每天吃饭拉屎,到头来还不是挨不过阎王的那根索命索。所以,不仅革命不能改变人的日常所需,而且革命者也与普通人一样都是天地间匆匆的过客。事实上,“湘西佬”后来的结局更具讽刺意味,进一步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和重大价值。“湘西佬后来曾当过我们县的县长,大概五年不到就被批斗推翻了。他的一双腿被打残了,要靠轮椅才能行动”,他的处境让“祖父”强烈地意识到:“看来还是做个平民百姓好呐,上面整啥我们听啥,我们有口饭吃有件衣裳穿就够啦,湘西佬闹了大半辈子的革命,到最后还不是被人革了命么?”[2]
革命顺应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理想,就像青花滩的童谣唱到的那样,有吃有穿地活着就好。但同时,革命也冲击着人们固有的道德观念和行事准则,这反过来又会让人去追问革命的合理性。新历史主义力图通过被压抑的人性的生长来反思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的科学性,开掘出让底层人言说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广阔空间,进而揭示出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实际上,革命常常会出现有悖常理的地方,它必须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来成就另一部分人的政治诉求。《1921年的童谣》中有三个片段的描写突出了人们对革命的疑惑:第一个场景是红军第一次打到青花滩时绑杀陈大膀子,说他是青花滩的头号地主,平时鱼肉百姓看,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但陈大膀子说:“我富,也是靠自己一点一滴节俭出来的,我既不偷又不抢,凭啥杀我!”“难道富也有罪吗!?”[2]第二个场景是红军在陈家坪绑杀商人陈文祥,原因还是说他鱼肉百姓。第三个场景是解放后枪毙地主田世光,因为他是石门最有钱和地最广的人。但田世光却说:“我经营有方,那都是靠我的本事赚来的,我平时哪天吃过一点细粮?哪天就穿过一件绸缎了?我还不是靠自己辛勤节俭发的家!?”“你们这样做还有天理可讲吗!”[2]这三个场景无疑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出这样的道理:“做穷人最保险”,“财富有时也是挂在脖子上的一把刀”。但这样的道理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是极相矛盾的,省吃俭用或经营有方积攒下来的财富在一夜之间招来了杀生之祸,这除具有嫉富心理的人之外是谁也想不明白的道理。当然,共产党领导天下穷人革命的目的并非是消除财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勤劳致富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光荣追求。
即便革命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合情理的行动,也难见有人挺身而出维护真理,人们往往怀着自私的心理冷漠视之。首先就操持革命的人士来讲,“湘西佬”在砍杀陈大膀子之前,红军曾受到过陈大膀子的优待,不仅将陈家祠堂让给红军办公或休息,而且还杀猪招待红军。尽管陈大膀子被视为青花滩的首富,但他们一家老小也只会在过年的时候才杀猪吃肉,可见他对红军并无排斥之心。但因为革命的需要,因为团结民众的需要,他们还是杀了陈大膀子,烧了陈家的地契,分了陈家的粮食。在红军进陈家坪的时候,商人陈文祥放鞭炮拥护红军进村,并给红军递烟倒水,但还是没有逃脱被红军砍杀的命运。解放后要枪毙地主田世光的时候,他说:“红军当时也没说过要枪毙我,我家当时还请泰和裁缝店的田裁缝给红军做过一百顶军帽呢,钱都是我父亲出的,当时红军还说我家觉悟高!”[2]但时过境迁,如今的土地改革运动已经与当年的红军革命是两件事情了,田世光最后还是被枪毙了。对革命者或领导运动的人来讲,不管富人通过何种途径富裕起来,也不管富人对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砍杀或枪杀他们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但对于广大群众而言,他们支持处决富人的行动又是居于何种立场和需要呢?红军最初审问陈大膀子的时候,“四周围上了层层前来看热闹的人。陈大膀子瞅了瞅人群,脸上开始冒汗起来,人群中隐隐地散发着一股杀气。”[2]昔日的乡邻为什么此时会散发出杀气呢?红军到陈家坪的时候,“湘西佬”对陈文祥说:“看你表现不错,你今天上午赶紧找一百个穷人来保,如果一百个穷人都说你不该杀,我就放你一条生路。”[2]哪有那么多穷人,又哪有穷人为陈文祥说情呢?实际上陈文祥只有死路一条。“老外公”被枪毙也是村民的集体心愿,因为他们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会把家里所有值钱的家当放在晒谷坪上暴晒一天,这些家当足以让许多人暗地里垂涎三尺。田世光被审讯的时候就有人说:“石门就你最有钱,你的田最多,你的地最广,你开裁缝店,可我们却穷得没裤子穿,我们都给你当佃户,你靠剥削我们的血汗发家,为啥不能枪毙你!”[2]部分人终于找到了报复地主的机会,也有人喊道:“要穷大家一起穷,要富大家一块富,你先富了,你就是地主,是恶霸,就该杀!”[2]在这群围观的人看来,因为别人比自己富裕,或者因为自己不富裕,所以就坚决拥护枪杀地主的行动,暴露出人性中最灰暗的仇富心理。
在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进行光辉的革命斗争的同时,《1921年的童谣》这部小说还通过对边缘人和底层人生活的叙述,揭示出革命进程中的各种阻碍和些许不足。世上本无十全十美之物,有瑕疵的东西才会让人觉得更真实,《1921年的童谣》对“革命”的理解丰富并完善了共产党的革命史,从而让人们了解到一段更为真实的历史。
三
新历史主义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文化批评而诞生,这就决定了它与狭义的解构批评、女权主义批评乃至后殖民主义批评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历史主义批评关注在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被“大历史”所忽视的边缘人物和偶然事件,认为他们构成了鲜活而生动的社会意义。而中国女性数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压抑氛围中,挖掘她们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现实处境和心灵感受,必然会极大地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书写下的历史。《1921年的童谣》对家族女性的书写颇具功夫,不仅反映了中国女性本真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处境,而且演绎出中国近现代以来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和自我内部的发展演变史。作者在郑性家族中写到的第一位女性是“曾祖母”,按照时间推算应该是清末民初的女性,她至今被青花滩的老年们津津乐道的形象是:“曾祖母一到干活的时候,幼小的儿子们趴在祖母的背上饿了就哇哇大哭,曾祖母干活腾不出手脚来喂奶,于是掏出奶子往背后一抛,年幼的叔公们便一口含住使劲吸吮起来。”[2]这看似一桩奇闻异事,而且对“曾祖母”身体形象的描写似乎有些夸张和变形,但实际上对她生理部位的突出意在表明,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与她们的生理功能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她们担负着繁衍子嗣的生育角色。传统女性被赋予这样的社会责任后,生儿育女便成为她们神圣的使命,于是“曾祖父”的母亲生下九个儿子,“曾祖母”生下七个儿子,郑家的人口聚在一起便能体现出女性的“伟大”:“据说我的曾祖母的奶特别长,她有个外号叫长奶婆婆。曾祖父的七个儿子分别是能彬、能祯、能昌、能崇、能保、能泰叔公和祖父能安。郑家人口多,曾祖父九弟兄在青花滩虽然不算多,但是一家人口聚在一起,颇为壮观。”[2]
农村女性更是被置于男性社会的边缘和从属地位。《1921年的童谣》中家庭妇女的地位低于男性,她们除了生儿育女之外,还得担负起服侍丈夫和料理家务的重任。“天还未亮,郑家的妇女们已经早早地把早饭做好了”,但早起做饭的女性却并不能与男性同时吃饭,“妇女是不允许上桌的,要得男丁们吃完了,她们才能小心翼翼地端起碗来,蹲坐在灶前匆匆扒完碗里的饭。”[2]妇女不是家里的主人,而完全成了家里的佣人。在两性关系上,妇女也是处于从属地位,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总是向男性倾斜,一旦男女发生鸡鸣狗盗之事,错误一方肯定是女性。比如“祖父”私通了一个石门的妇女,“曾祖父”当面骂道:“你这婆娘还要不要脸,我儿子可还是没成过家的,你不要把他的名声毁了!”[2]没有结过婚的男人不能娶已婚女人,结过婚的男人则可以娶未婚女人,这对女性来说公平吗?而且在这件风流韵事上,是“祖父”主动追求漂亮的寡妇,为何“曾祖父”要怪罪于女性而不是男性呢?其中隐含的男权思想不言而喻。
《1921年的童谣》浓墨重彩刻写的女性是“祖母”陈云青,她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也是作者家族叙事中见证历史的女性。“祖母”与“曾祖母”是两个时代的女性,她身上体现出与旧时妇女迥异的特点:“祖母”上过正式的学堂,还走出陈家坪去到邵阳城里师范女子学校念书,她不再是待至闺中的小姐,而是一位性格开朗并乐于和男女同学交往的新女性。“祖母”不仅在新式学堂里吸纳新知,而且生性机敏过人,她会双手执笔写对联,青花滩的人至今都只能望其项背,包括那些受过私塾教育背过子曰诗云的男性都自愧不如。“祖母”的诗文写得非常漂亮,她是陈家四姊妹中最擅长吟诗作对的一个,虽然其中夹杂着她生活的不幸与感情的忧郁,但这丝毫不能掩饰她的才情,更不能抹灭她代表青花滩知识女性的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却并不比只是奶长的“曾祖母”生活得幸福,她一生结过两次婚,这在农村的婚姻观念中是不同寻常的经历,而且她的两次婚姻都以失败告终。“祖母”第一次嫁给了终日忙着做裁缝的不识字的田世光,没有感情的婚姻自然充满了痛苦和折磨。第一任丈夫被划为地主枪毙之后,成分不好的“地主婆”只能嫁给一个游手好闲的打道场的中年人,于是“祖母”在没有任何嫁妆的情况下和没有交付任何礼金的“祖父”结了婚。和大老粗田世光相比,“祖父”的缺点和对“祖母”的恶劣态度过之而无不及,导致“祖母”最后投河自尽。
为什么“祖母”作为有知识的大家闺秀会接连遭遇婚姻的不幸呢?这当然归咎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压,“祖母”反对没有感情的婚姻,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在老外公的逼迫下完成的,他为女儿选择对象的唯一条件就是将来有口饭吃和有身衣穿,而不过问当事人的择偶标准。但“祖母”的不幸也是现实社会造成的,因为在阶级上被划为地主婆,所以她的第二次婚姻更无条件可讲。更为严重的是,“祖母”在陷入第二次婚姻的困境之后,接踵而至的各种运动和批斗,让她在忍受家庭暴力的同时还得经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和皮肉之苦,而且落下了身体的顽疾,最终这个知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下选择了放弃生命。“祖母”沧桑一世,空负满腹经纶和满腔柔情,在知音难觅的愁绪中带着她的诗文和对这个世界无尽的伤痛投江而死。“祖母”的死暗示了人在现实社会中如同浮萍一样漂浮不定,也暗示了意欲与男性社会相搏的知识女性注定是一场悲剧的主角。“祖母”的凄凉身世并非被动的存在,它实际上生动地构成了历史的真实面目的,成为我们了解民国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女性在动荡社会中的生存现状,以及在这段历史中女性生活遭遇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本真面貌。
郑小驴的《1921年的童谣》是对家族历史的书写,贯穿着郑家人在革命和社会变迁中的压抑和抗争,所以亦是家族的心灵史。通过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去解读这部小说,我们会看到其中蕴含的潜在社会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在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历史乃至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纠葛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历史面貌,以及个体生命最本真的存在姿态:“饭能吃饱,衣能遮体,苦难再多,活着就好。”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2]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J].十月,2009(2):109-125.
[3]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M]//朱立元,李 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张京媛,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92-693.
[4]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 强,马 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
[5]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6.
责任编辑:黄声波
Family Narrativ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On Zheng Xiaolv’s The Nursery Rhymes in 1921
XIONG Hui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The new historicism wanted to re-write the history and reveal the true reality covered by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n the position of deconstruction.With the marginalized family narrative,the novel of The Nursery Rhymes in 1921 deconstructed the authority and uniqueness of the“History”by the dimension of history,revolution,women and daily life.Then the novel revealed some little-known history truths,and showed sharply the positon of historical narrating and history thought.
Key words:The Nursery Rhymes in 1921;New Historicism;family narrative;positon of historical narrating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5.05.002
作者简介:熊 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
收稿日期:2015-02-02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5-0008-06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