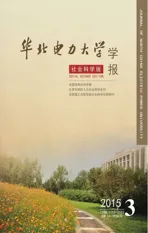从孟玉楼形象管窥晚明社会的市民文化精神
2015-03-17汪泽
汪 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从孟玉楼形象管窥晚明社会的市民文化精神
汪 泽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带动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市井生活中出现了一种异于传统儒家礼教的新型市民文化。小说《金瓶梅》于此时应运而生,在书中一个重要女性——孟玉楼的形象设计上,体现出重商逐利的价值追求,注重自我的主体意识以及呼唤公平的果报观念,三者皆属于晚明市民文化的范畴。分析这一人物形象,有利于把握16世纪中国的市民文化,透视晚明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
《金瓶梅》;孟玉楼;晚明;市民文化
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面临深刻的变革。随着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作为新兴社会力量迅速崛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导致社会心理变化。官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说教逐渐失去了号召力,意识形态领域涌动着富于近代人文色彩的启蒙主义思潮,市井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种异于传统儒家礼教、体现市民阶层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的新型文化。
约成书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突破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神魔小说的内容范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于人物、情节、风格各方面流露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市民文化气息。本文试图解读一个重要女性形象——孟玉楼,通过分析其心理性格与命运轨迹,把握晚明社会的市民文化精神。
一、重商逐利的价值追求
商业活动的高额利益颠覆了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诱使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经商热潮。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相适应,尚利好货的思想流行于市民阶层,甚至影响到整个晚明社会。据张瀚《松窗梦语·商贾纪》记载: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1]80
《金瓶梅》中孟玉楼于第七回首次出现,即表现出“财的利害”。张竹坡于回批中指出,“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来”[2]66-67。事实上,本回卷入改嫁风波的几个人物,无一不是贪财之人。西门庆自是看中了孟玉楼“手里有一份好钱”;杨姑娘“一力张主”,“爱的是钱财”;张四破婚,不过“要图留妇人东西”;薛嫂为说成亲事不辞劳苦、编造谎言,更是为了向西门庆索取财物,“典两间房儿住”。甚至孟玉楼本人,也是“爱嫁富家翁”——她不为“诗礼人家”的尚举人动心,而中意于西门庆。后者吸引她的,除了第一印象中“人物风流”[3]106-113的外表,恐怕还有那种善于聚敛财富、以金钱称霸一方的商人本质与商业魄力。
孟玉楼在作品中以布商杨宗锡未亡人的身份登场,后嫁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为妾;其弟孟锐作为专业商人往来于荆州川广各地。在当时,“商人凭借手中的财富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人生态度、生活追求、抑或是价值观点、价值取向,都与传统发生背离。”[4]71玉楼出入于富商之门,经商理念有意无意的引导,使其在人生选择上表现出明显的现实功利色彩。
但在求利的过程中,孟玉楼并没有陷入偏执与迷狂。张竹坡曾赞其为“高人”、“真正美人”,认为“写玉楼,是具立身处世之学问……教人处世入世之法”[2]68,甚至以玉楼为作者自喻。这种说法稍嫌武断,但也并非无稽之谈。张竹坡看到了孟玉楼立身处世方面的睿智与清醒,这种理性使她超越了《金瓶梅》的芸芸众生。在商业氛围中成长,见识过市场风波、物资流转及人事运筹,玉楼比其他女性多了一分沉着与机敏。更重要的,她身上体现出一种成熟商人特有的坚韧进取精神。孟玉楼的前半生充满了辛酸坎坷:青年守寡,孤苦无依,因媒误身,遇人不淑……但她从未灰心堕落,仅有的一次“抱恙含酸”[3]1060并不影响审度大局的冷静。被骗嫁西门府,屈身为妾又倍受冷淡,心中的愤悔之气可想而知,但玉楼始终以平和淡然的态度待人接物,对于西门庆及众妻妾都示之以礼又不卑不亢。潘金莲初来的“小意儿贴恋”[3]134掩饰不住内心的做作浅薄,李瓶儿一味的驯良懦弱使她最终难逃毁灭的命运,吴月娘的宽忍大度也未能在丈夫与婢妾间树立正妻的威信,而孟玉楼的乖巧柔顺却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空间。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3]245,对金、瓶施以马鞭,骂月娘不贤良,但未曾羞辱玉楼;吴月娘最终将众妾一一逐出,独不舍玉楼主动改嫁;潘金莲对其他妻妾虎视眈眈,却将玉楼视为盟友;李娇儿、孙雪娥亦不曾挑衅于她。同时,她还利用自己的经济头脑和充足财物在仆人中间赢得了慷慨使钱的声誉。孟玉楼的立足现实、乖觉圆滑使她能够上下周旋、游刃有余,这种保全自身的理性与机智,仍然可以看作求利观念的具体化——在勾心斗角、危机四伏的市侩之家,她所谋求的已经不是金钱财富,而是安身立命的生存资本。
二、注重自我的主体意识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在力量上不断壮大,思想也逐渐成熟,开始审视并关注自身的存在。“在这审视中,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看到了自己对社会的价值和具有的力量。”[5]85市民阶层在谋取基本生存权利的同时,重视自我个性的发展,肯定自身的需求与欲望;各种异端思想的流行,也对其主体意识的觉醒起到促进作用。
《礼记》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情爱之欲体现了人类本能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同作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分支,与“好利”价值观紧密联系的,是“好色”的社会心理。如颜山农所说,“人之贪财好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6]后集卷35。由“好色”而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是市民阶层主体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
孟玉楼在小说中以商妇身份出现。白乐天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行商的漫长旅程无可避免地造成商人夫妇两地分离,对于男女双方,尤其深锁空闺的女性而言,无疑是一种身心的折磨,她们往往比一般女性更渴望情爱慰藉与家庭温暖。唐宋诗词的某些篇目已经细腻深刻地反映出商妇的情感追求: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李益《江南曲》)
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任君逐利轻江海,莫把风涛似妾轻。
(刘得仁《贾妇怨》)
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
(江开《菩萨蛮》)
在情感表达方面,商妇似比一般封建女性更多一分真实与坦率。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通俗文学的发展,商贾小说逐渐萌发、形成规模。从宋元至明清,越来越多的以商人、商妇为主人公的作品,立足于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抛弃了三从四德、贞操守节之类的羁绊,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和自身的生存与发展”[4]116。
孟玉楼形象的塑造,在很大意义上是承袭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商妇传统而来。她有着对正常爱情与婚姻生活的渴望,“三揭红罗两画眉”[3]1336的婚恋历程正体现了一种带有近情色彩的人生选择。在她身上,封建道德与纲常礼教的约束相对弱化,不同于宦吏之家出身的吴月娘;而丰厚的个人财富与较高的社会地位亦使其思想境界与潘金莲、宋蕙莲等市井贫妇差别甚大。所谓“娇姿不失江梅态”[3]1336,孟玉楼于柔顺中保持独立,于多情中维护自尊。从“爱嫁李衙内”[3]1330的最终归宿来看,她追求的是灵肉和谐的爱情,以及男女双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婚姻关系。因此,玉楼既没有像月娘那样以刻板的贞节观念束缚自身,也不会如金莲、瓶儿、春梅等人一般沉沦于肉欲的宣泄。对贪淫无度的丈夫西门庆,她始终保持距离,既非百依百顺,也不放浪争宠;对恶意引诱的无赖陈敬济,更是不为所动、设计惩治,透出不容侵犯的凛然正气。
同时,她的婚姻选择也并未颠覆正常的伦理道德。“明代中叶以后,夫丧改嫁已一般为民间妇女所认同,社会舆论也持认可的态度……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离婚改嫁权以及经济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其法律地位较之前代有很大提高。”[7]110与娇、娥、金、瓶、梅等人不同,孟玉楼巧妙利用有利的时代氛围与宽松的礼教环境,在外界伦理规范许可的限度内追求幸福。如张竹坡评曰:“玉楼来西门家,合婚过礼,次视偷娶迎奸赴会,何啻天壤。其吉凶气象已自不同。其嫁衙内,则依然合婚,行茶过礼,月娘送亲,以视老鸨争论,夜随来旺,王婆领出,不垂别泪,其明晦气象,又自不同。”[2]32孟玉楼的人物设置体现出内在情爱之欲与外在社会规范、人伦法理的相对调和。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指出,明代的世俗小说“虽然还谈不上个性解放”,但已经“可窥见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在追求爱情与婚姻幸福的同时,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进而比较理性地寻求人生定位,是市民主体意识觉醒的另一个表现。“由于社会开始孕育着从封建母胎里的解怀,个人的际遇、遭逢、前途和命运逐渐失去独一无二的封建模式,也开始多样化和丰富化,各色人物都在为自己奋斗……”[8]190-191对于女性,家庭几乎是唯一合法的活动空间,纵然身处礼法松动的时代,她们依然缺乏展示才干的舞台,只能在治理家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孟玉楼善于圆滑行事、淡泊待人,但遇到关键问题,却并非一味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潘金莲私仆受辱,她委婉劝解,利用西门庆对月娘的信任,大事化小,既救助了潘金莲,又否定了自身随嫁僮仆的罪行;面对月娘与西门庆的冷战,娇、娥置若罔闻,潘金莲暗地挑拨,而玉楼却主动劝月娘“与爹笑开”[3]285;当李瓶儿轿至门首,无人理睬,独她请来月娘出面迎接,维护瓶儿的尊严;为春梅护短引起潘、吴二人争吵,又是她出面讲和,几句玩笑,尴尬立消。
不可否认,这些举动在收买人心之余也展示了孟玉楼的治家才干。在调停人际纷争、稳定家庭秩序方面,玉楼的能力超过了身为主妇的吴月娘。她本是杨宗锡的“正头娘子”[3]99,嫁入西门府之前,满心以填房自居;欲改适李衙内,更是详问其有无妻小。所谓“船多不碍路”,“若他家有大娘子,我情愿让他做姐姐”[3]113的一翻话,仅仅是面对张四破亲的“佯说”[3]113。与其认为孟玉楼是在刻意追求名份,宁勿说她不甘心做一个以色事人的小妾。于玉楼而言,尽管对欺骗自己的西门庆心怀憎恶,对淫欲横流、矛盾丛生的市侩家庭厌倦不已,但“当家立纪”[3]108的才能与愿望仍在不自觉间流露。
这也符合儒家道德为女性规定的持家职责和人生规范。无论孟玉楼自身,还是《金瓶梅》的作者,都没有摆脱封建文化传统的烙印。这体现出市民阶层在浸润启蒙思潮、彰显主体意识的同时,仍无法超越特定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局限。
三、呼唤公平的果报观念
“善恶报应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民众信仰由来已久……随着佛教的发展和佛教思想的不断传播……更是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它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宗教观念而存在,而是积淀为一种社会的,甚至民族的心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和处理日常生活的一个原则。”[5]109-110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使“公平”成为市民阶层的普遍要求,广大市民自由开放的生活观念亦使他们“较其他阶层更具有追求公平之心”,同时“在因果报应中找到了实现公平这一社会理想的便捷途径。”[5]112-114
《金瓶梅》一书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客观再现了晚明社会好利好色的时代风气,但作者主观上却有借财色之危害劝导世俗的强烈意图,在总体结构上昭示出善恶有报的观念。然而,这种报应思想并非是对佛教因果轮回教义的复制,它融入了市民阶层的公平理想与价值取向,以现世报应和市民道德为准则。
小说中的女性,因其“斗宠争强,迎奸卖俏”,大抵逃不过“尸横灯影,血染空房”[3]11-12的惨烈结局:潘金莲身首异处,暴尸街头;李瓶儿财匮儿丧,恶疾毙命;庞春梅风光占尽,纵欲而亡;孙雪娥沦落风尘,自缢身死…… “善良终有寿”[3]1336的孟玉楼和吴月娘是置身于死亡图谶之外的,但相比于严守礼教纲常、刻板造作以至于显现出“奸险好人”[2]33之相的吴月娘而言,孟玉楼的形象更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所以月娘虽保全性命,却不得不在夫死子散的孤苦空虚中了却残生;而玉楼却能再结良缘,夫妻偕老,尽享天伦。
孟玉楼之“善良”似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反衬金莲、瓶儿、春梅等人的“淫佚”[3]1336,谓其品行端正;另一方面则针对她未泯的道义与良知。书中写到玉楼磨镜周贫、为潘姥姥付轿钱,自是仗义之举。在家庭内部,如果说宋蕙莲事件中她对潘金莲的间接怂恿有借刀杀人之嫌,那么屡屡调停纷争、缓合矛盾,则不能不说是出自善意。很大程度上,以市民道德的是非标准做到利己而不损人,于相互倾轧的大家庭中已属难能可贵。孟玉楼利义结合的市民道义观,在她与潘金莲的关系中得到了集中展现。
张竹坡谓“作者特特为金莲下针砭,写出一玉楼”[2]77。刁泼凶悍、淫邪善妒的潘金莲,在为人处世上与孟玉楼态度迥异;如果按照传统道德的评判标准,更是“遗臭千年作话传”[3]1336,本应令其避而远之。但在西门府众多妻妾中,孟、潘二人却建立起最为融洽的私人关系。原因即在于孟玉楼看到了与潘金莲结盟的利益所在:共同对抗身居正室、敌视诸妾的吴月娘以及财色兼胜、最受宠爱的李瓶儿;排斥名存实亡却不忘搬弄是非的李娇儿、孙雪娥;另外,利用潘的外向泼辣、“有口无心”[3]1100为自己扫除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潘金莲亲密相处的过程中,孟玉楼虽时常与之议是论非、戏谑其他妻妾,甚至对潘的淫荡罪行包庇隐瞒,但在原则问题(如驯服狮猫害死官哥)上却未曾同流合污、助纣为虐——这体现出玉楼对道义的坚守,功利之心没有使其走向人格扭曲。潘金莲终因奸情被逐出府,尽失妇道尊严,又无利用价值,然玉楼对之毫不鄙弃,反而惺惺惜别,赠以衣饰,并在其死后为之真心一哭,与月娘的狠心绝情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淡化纲常礼教、倾情弱势的朴素民主倾向,虽不符合正统道德与法律准则,却体现出市民阶层的心理要求。
在笑笑生的安排下,孟玉楼离开了家反宅乱的西门府,于青春将逝之际,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机缘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归宿;其到老无灾、有子送终的幸运结局更被归结为“善有善报”。按照李泽厚的说法,“这里有对邪恶的唾骂和对美德的赞扬,然而同时也有对宿命的宣扬和对因果报应、逆来顺受的渲染。总之某种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性与腐朽庸俗的封建落后意识的渗透、交错与混合,是这种初兴市民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里没有远大的思想、深刻的内容,也没有具有真正雄伟抱负的主角形象和突出的个性、激昂的热情,他们是一些平淡无奇然而却比较真实和丰富的世俗或幻想的故事。”[8]191果报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玉楼谋求自身出路的主观努力,但却迎合了市民的公平理想与教化需求,一方面是作者受时代风习熏染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市民阶层作为通俗文学最大接受群体的阅读期待。
张竹坡给予玉楼“乖人”[2]33的评价,除乖觉、乖巧外,“乖”字有“违备”的本义。孟玉楼的存在,的确是对《金瓶梅》女性群像的违备。她是一位把握住自身命运并得到相对圆满结局的女性,这在《金瓶梅》中是唯一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亦是不多见的。如果说,金、瓶、梅一类放纵人欲而不见容于传统道德的淫娃劣女是小说作者主观批判的对象,以吴月娘为代表严守纲纪的节妇贤妻是古代中国客观真实的存在,那么孟玉楼则是特定文化背景与社会理想下的产物。对这一人物进行解读剖析,有利于把握16世纪中国的市民文化,透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
[1] 张瀚撰.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会评会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 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王言锋.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 王世贞.弇州史料[M].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7] 赵崔莉.明代妇女的法律地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1).
[8]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王 荻)
Look at the Spirit of Civil Culture in Later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Character Meng Yulou
WANG Ze
(Literature of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In mid-late Ming Dynas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aded to the changing of social psychology. A new kind of civil culture differented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al code grew in the chaotic street life.TheGoldenLotuswas born at the right moment. In design of its important character——MengYulou, we can realize the mercantilism values, self-awareness, fairness and comeuppance, which all belonged to civil culture in later Ming Dynasty. Analysing this figure can help us hold the civil culture in 16 century of China and inspect the social psychology and spirit of the time.
TheGoldenLotus; MengYulou; later Ming Dynasty; civil culture
2014-11-14
汪泽,女,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I207.419
A
1008-2603(2015)03-01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