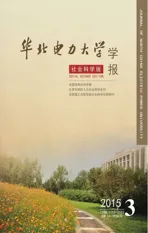核电公众接受性研究展望
2015-03-17陈润羊
陈润羊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 电力经济研究
核电公众接受性研究展望
陈润羊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高效安全地发展核电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核电的持续快速发展,公众接受性的研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类概述了国内关于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八个关键问题的研究现状:核电公众接受性的作用意义、对核电的影响、核电项目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公众核电风险的认知和决策、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现状特点和不足、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影响因素、国际经验借鉴、改善公众接受性的对策等,综述了目前核电公众接受性理论研究上呈现的特点、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当前蓬勃发展的核电实践提供指导。
核电;公众接受性;公众参与;文献综述;能源安全
在建设生态文明成为时代强音的今天,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核电在全球能源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我国核能利用的历史尽管起步较短,但核电发展迅速,核产业已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核电站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核能的利用,一直存在着公众疑惑等挑战,国外一些国家,如德国、瑞典等因为公众的反对而放弃利用核电。与国外相比,我国核电中公众接受性研究远不如核能技术本身的研究深入,我国核电的发展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的众多挑战。为此,以文献综述为切入视角,对我国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的综述和梳理,分析目前核电公众接受性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以解决核电发展的后顾之忧,并为推进核电产业的持续发展赢得更广泛的公众支持。
一、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学界对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角度、方法和重点有所不同,综合而言,国内关于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八个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上。
(一)核电公众接受性的作用意义
时振刚(2000)等认为,公众接受性研究是技术与公共管理科学的交叉研究课题,开展核电的公众接受性研究,可以缓解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可能冲突,并创造技术与社会的良性沟通环境[1]。陆玮等(2003)认为,公众接受是核电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核电发展初期,更多考虑的是技术性和经济性因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的意识也将不断增强,公众对核电政策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强[2]。孙晓琳(2012)认为,核电项目中的公众参与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减少核电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有利于核电项目决策的科学化[3]。曾志伟等(2013、2014)认为,公众的参与能够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化,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质量,提升公众参与度不仅能为核电发展的道德困境提供突破依据,更能提升公众对核电发展的接受度和支持度,公众的“核态度”,如同经济性和安全性,已成为核电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4] [5]。
(二)公众接受性对核电的影响
国外核能发展的实践表明,公众接受性对核电发展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分。一方面,由于公众接受性的变化或者降低使一些核能发展计划被迫搁置,如美国的尤卡山高放废物处置库就因公众的强烈反对而迟迟不能按计划实施、瑞典和德国因公众的抗议而不得不“弃核”等;另一方面,公众接受性还可能间接地影响核电的安全目标和管理。如三里岛事故后,为了恢复公众对核电的信任,美国核管会提高了核安全标准,加强了建设和运行阶段的监查(时振刚,2000、2002)[1] [6]。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核高潮,同时也促进了对核安全标准的提升。LI Chao-jun等(2013)认为,核安全目标与核电的公众接受性呈现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核安全目标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性,如良好的核安全记录对公众接受性具有积极影响,核事故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公众接受性也影响核安全目标的制定,如监管机构为恢复公众信心在兼顾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前提下,会不断调整核安全的目标[7]。
(三)核电项目环评中的公众参与
目前我国核电项目中的公众参与主要体现在核电厂从选址、建设、运行到竣工各个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方面,公众参与的形式主要有座谈会、听证会等,公众可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我国核电发展战略、核电发展规划以及核电项目决策环节上,基本没有设置征询公众意见的环节(曾志伟等,2013)[4]。核电项目具有规模大、工期长、影响范围广、涉及人员多等特点,为了让公众的合理需求得以提出,使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完善合理,公众参与应贯穿于整个环评阶段(裴娟等,2014)[8]。由此可见,公众参与如何从项目环评向战略环评延伸,不但是环评发挥优化决策的基本需要,也是提高核电公众接受性的重要体现。
(四)公众核电风险的认知、决策与控制
时振刚(2002)认为公众与专家在核电风险认知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公众对核电的风险决策与个人需要的满足、风险偏好、社会背景、监督机制和信任度等诸多因素有关。因此,只有在掌握公众的风险认知与决策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和公关等多种努力,才能解决核电公众接受性的问题[9]。方芗(2012)通过对风险社会建构范式下对核电风险的分析表明,科学研究数据和风险评估并不是大众了解核风险的主要依据,因此需要关注社会及文化对大众核风险意识的塑造和影响[10],她认为专家系统把大众排除在核风险的定义和处理系统之外,忽视了非专家知识,因此核风险的特殊性和科学的自反性是引发信任危机的关键[11]。杨波(2013)设计了一个公众对核电风险认知的概念性模型,认为公众对核电风险认知是一个复杂、动态以及主观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闭合的社会系统,如果系统出现了正反馈,核电的风险被各级放大出现循环,将使社会系统出现不平衡,并可能引发群体事件;如果在核电风险认知过程中,风险信息减弱,系统则会形成一个负反馈,并会逐渐达到平衡[12]。彭峰等(2014)以彭泽核电项目争议为例认为,从核电项目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公众参与程序的合理引入,不仅可以凭科学依据消除公众疑虑,也可权衡不同法益并预防对基本权利的侵害[13]。
(五)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现状特点及不足
一般意义上,核电公众接受性具有三个特点:事故发生率低而事故影响大、公众关注程度高、公众评价的主观性和非理性化(陆玮等,2003)[2]。有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公众对核电好处的认识、对政府和专家的信任和对现有运行核电厂风险的判断等对发展核电是相当有利的,但公众对核电的熟悉性和知识相对较弱(Changxin Liu 等,2008)[14]。陈钊等(2009)等以广东深圳为调研对象发现,公众对核电的认知程度非常低,甚至存在某些误解的情况[15]。王一龙和廖力等(2012)从对衡阳的调查得知,公众核电相关知识掌握不够[16]。全世文等(2012)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公众对核电知识的了解水平较低,但关注度和兴趣都比较高;公众对核电的感知价值、感知风险和接受意愿也比较高。公众对核电的感知价值对其接受意愿有促进作用,因此要提高公众对核电的信任度;而公众对核电的感知风险对其接受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要提高公众对核电的了解程度[17]。曾志伟等(2014)基于公众问卷调查发现:我国公众对于核电发展存在着“认知度与接受度的悖论”现象,具体表现在: 26-45岁的群体相对掌握了更多的核电方面的知识,但却更易夸大核电发展带来的威胁性;公众的学历越高,对核电的相关知识了解得越多,却也更不赞同将核电建在自己工作或生活区附近;虽然男性对核电的满意度高于女性,但男性对于“将核电站建在自身工作或生活区”的排斥度却更高[5]。陈方强等(2010)认为,当前我国公众核科学常识较为匮乏、核普及滞后、公众参与度低、核信息透明度不够、信息反馈机制缺乏[18]。也有学者基于实证调查及数据分析得出我国核电项目公众参与的不足有: 公众参与程度较低、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较低、参与有效性不高、参与工具利用不足、参与主体忠诚度不高(孙晓琳,2012[3]、曾志伟等,2013)[4]。
(六)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核电公众接受性有“四影响因素说”:熟悉性、可参与性、可控制性和信任度(陆玮等,2003)[2]。也有学者提出是另外的“四因素”:社会信任度、公平性、核事故和社会组织(袁丰鑫,邹树梁.2014)[19]。王一龙和廖力等(2012)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城乡及个人年收入都是公众核电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15]。田愉和胡志强(2012)认为影响公众核电风险认知有四个因素:核事故的发生是最重要的因素、媒体报道对公众核电风险认知有长久而持续的影响、时间的影响、对核电站的熟悉和了解程度[20]。孙晓琳(2012)的研究结果显示“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核电项目公众参与的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有负向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居住距离、居住时间这几个外在变量对公众参与的行为意向也有显著影响[3]。郭跃等(2012)研究发现,影响核电可接受度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技术特点因素、个体因素与制度环境因素,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出现差异不仅源于个体特点,也源于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差异[21]。
(七)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国际借鉴
法国是世界上核电比例最大的国家,这与公众对核电的高支持率密不可分。法国政府既告知公众核电的优点也告知风险,并把核安全、环境友好、放射性废物管理、公众接受作为核电政策的四大关键要素(Chuanwang Sun等,2014)[22]。法国的公众策略值得借鉴:独立监察以及透明度、全面沟通策略、社会与经济计划、跨区域合作等(贾峰,2014)[23]。日本作为经历过核战争和核事故的国家,日本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帮助公众全面理解核电对促进能源安全和区域发展的意义:建立更有效的监察体系以避免再次发生数据伪造或掩饰等情况,加强教育和信息公开以赢得公众对核电项目的更大接受性(Chuanwang Sun等,2014)[22]。俄罗斯是世界上发生过首次大规模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国家,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启示有:对公众意见进行跟踪监控,要考虑到不同特殊群体的利益和反对意见,对不同目标团体区别对待;批判性地理解和针对性地利用专业化信息部门工作中的集体性经验;考虑到实际辐射风险,要形成统一的科学观点;大力促进科学发展和知识传播,让公众了解核电站的作用;提高公众关于辐射性方面的知识,向公众系统性告知核电安全性和放射性废物处理方面的最新成就;大量出版通俗的核电百科丛书;取消一切无根据的保密限制;提高放射生物学和放射生态学的教育水平等(丁志萍,2014)[24]。
(八)改善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对策
为促进和增强公众对核电的认知、理解、信任和接受,必须把公众接受作为一项长期的、动态的核电公关战略,具体采取的策略有:树立主动公关意识,多渠道广泛宣传;加强核电企业形象建设;建立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陆玮等,2003)[2]。也有仅仅从核电公众宣传角度提出增强公众接受性的对策的,如:实现核电公众宣传再认识、整合核电公众宣传资源、加强涉核信息公开透明、完善传播方式和途径、加强核电公众宣传对标交流和深化核电公众宣传研究等(田桂红,2011)[25]。潘自强(2012)认为,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沟通和生物效应研究是提高核电的可接受性的有效措施[26]。郭跃等(2012)提出,政治家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弥补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核能接受度的“鸿沟”:增强技术特点因素对公众的影响,扩大公众对核能技术认知中的理性成分;在缺乏技术了解时,应通过信息公开、决策程序等制度安排应对公众的疑虑[21]。曾志伟等(2013)提出,要结合核电发展决策链——核电发展战略制定、核电项目规划和核电站项目运行,来构建公众参与的有效平台:拓展核电发展战略的公众认知度、提升核电发展规划的公众参与度、设置核电项目运行的公众参与环节,并在立项申请、建设、运行和退役等阶段全过程开展公众参与活动[4]。陈润羊(2013)提出要构建“五位一体”公众参与体系:科普教育是基础,法律制度是保障,信息公开是前提,公众宣传是关键,参与机制是核心[27]。Guizhen He 等(2013)以海阳核电厂为例的研究表明,在核电的决策上由政府机构、核电企业、科研机构组成的“铁核三角”为主,而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没有参与,建议应加强核电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28]。Chuanwang Sun等(2014)的研究表明,全面的信息会降低核电的公众认知风险,增加对核电政策的公众支持,认为应该更加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励核能决策的公众参与[22]。曾志伟等(2014)针对核电发展中存在公众“认知度与接受度的悖论”,认为要提升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不能简单地依靠核电知识宣传和普及,而要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将科普宣传、现场体验和必要的利益补偿机制结合起来[5]。黄维娜(2014)建议核电企业应改变以往将信息沟通当作单纯地“信息公开、披露”义务的消极态度,将“利益相关者参与”视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沟通过程持续运作的动力机制[29]。彭峰等(2014)认为在核电项目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中,应突出核电知识的普及教育并提高风险沟通能力,尽可能提前公众参与的时间节点,增强公众参与的透明度,但公众参与方式需一定的限制[13]。
二、评价与展望
以研究我国核电公众接受性的中英文成果为对象,放眼国际学术前沿,总结归纳目前的研究进展、特点不足和研究趋势,无疑对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研究现状评述
综合而言,我国核电公众接受性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有:(1)在研究主题上,我国核电公众接受性与核电公众参与问题紧密相连,相关研究已经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已形成一定的共识。以环境影响评价领域的公众参与为代表,在法律法规、技术程序、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等层面都已形成了一套体系,但针对核电整个决策链的全过程参与上,我国与国外相比尚有较大距离;(2)不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偏好和特长基于不同的视角所开展的研究,既有相互验证的一面,也存在对同样问题的不同认识;(3)中文文献研究主要针对的区域和对象涵盖了已建核电站的广东大亚湾、湖南衡阳等地的学生、科学家、核电站周边居民等,外文主要是英文文献有的也涵盖了对全国重点群体的分层抽样调查等;(4)我国核电建设历史较晚以及政治体制的不同,核电公众接受性研究起步也较晚。从研究成果的发表时间看,自1998年郭裕中、李昌举和卢同发表了西方公众对核电站安全的忧虑的文献综述以来[30],针对本土的研究一直较少,但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视角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日益丰富,这与国际上针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是一致的[31] [32];(5)与国外相比,我国核电公众接受性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学科交融度低,核电公众接受的理论模型研究和理论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如除少部分研究用复合模型(Changxin Liu等,2008)[13]、支付意愿(Chuanwang Sun等,2014)[22]等相对更能反映现实的方法进行研究外,大部分定量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都是是否支持核电等单一性的问题居多,描述性、列举性的分析较多,但在理论根据的规范性、量化研究的科学性、反映现实的可靠性等方面都颇显不足;(6)研究机构和学者研究成果的集中度不高,使该领域研究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受到限制,这与日本等国学者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如我国除时振刚[1] [6] [9]、曾志伟[4] [5]等有连续和系列性的研究外,其他鲜有学者在较长期集中关注此问题,而日本的T. Ohnishi等学者则有系列成果发表[33][34][35]。总体而论,虽然我国核电利用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目前也是世界上核电建设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核电公众接受性和公众参与的量化和系统研究颇显不足,公众核电接受度的系统性地调查尚没有深入开展,对于核电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中公众参与模式的研究更是极其缺乏,这种相对滞后的研究现状与我国核电快速发展的实践形势不相适应。
(二)研究趋势展望
针对核电公众参与性的研究现状和不足,该领域的有关研究预期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和深入:(1)需要把核电公众接受性和核电公众参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需要重视有关公众接受性和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如构建核能风险认知和决策理论,公众接受的心理学、社会学基础,核电舆情和新闻传播理论、公众权益和核能伦理理论等;(2)任何单一学科难以反映复杂的现实问题,因此,在核能科学技术、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交融互动中寻求该领域研究的突破,无疑是研究的基本趋势;(3)在针对公众接受性的研究上,要区分不同的公众类型,并深入分析核能接受度的影响因素,以寻求适宜于不同群体特点的对策方略;(4)向国际学术前沿看齐,既要仔细分析国外理论对我国核电和公众理论解释的适应性,也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研究的规范性水平,以适应同类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并增强对我国核电实践的指导性;(5)增强问题导向意识,针对核电领域的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回答核电“邻避现象”的理论原理和应对策略、构建核电舆情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干预机制、设计核电公众参与的有效模式和响应机制、关注外国反核浪潮对我国的长远影响、注重信息和网络时代的民意引导、开展核电接受性的舆论形成集合模式的研究、关注媒体对公众接受性的影响等等;(6)随着核能在国家能源战略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公众民主权益意识的不断高涨,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在我国已引起相关学者的广泛重视,并有望成为核电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三、主要结论
从现实情况而言,世界范围内的拥核派、反核派一直在争论,我国也深受其影响,国内拥核派以核工业系统内的专家和官员为主,反核的有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也有网络上的意见领袖。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核电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低碳型等方面,也有对政策程序中没有设置或者公众参与的机制不完善的质疑。所以要在制度上保障公众的参与权,并落实在具体操作程序上;同时,也要形成建设性辩论、争议、质疑的学术氛围,不能压制质疑的声音,可以理性地进行学术争辩,这样在各种声音的交汇中以形成最大的社会共识,同时也有利于公众分辨是非、厘清纷繁、看清真相。
当然,我国和西方政治体制毕竟存在较大差异,在发展核电上如何倾听民意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公众的声音、质疑和疑惑。当核电发展不能与公众参与同步时,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加之长期核能科普和宣教的缺位,有可能导致公众非理性的、激烈的甚至是群体性的对抗,并掺杂其他复杂的对社会或某些政策的不满,借助偶发的事件,或者一些导火索而爆发出来,将造成政府、社会的对立,造成不信任的加剧,不仅不利于核电的有序发展,也最终危害整个社会的治理基础。诚然,尽管大部分公众有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意见形成中随所谓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的观点而舞,并随波逐流。因此需要培育一支中坚的拥核力量,从大学生开始的教育,社会团体的扶持、面向社区居民的宣教等细微的工作着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微博、微信等,进而构建信息公开、宣传教育、法律保障、利益协调等多策并举的有机体系,推进核电领域的公众参与,并不断提高核电的公众接受性,将为发展核电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支持。唯此,核电才能在持续、和谐发展中更好地支撑国家的能源安全战略。
[1] 时振刚,张作义,薛澜,等. 核电的公众接受性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0(8).
[2] 陆玮,唐炎钊,杨维志,等. 核电的公众接受性诊断及对策研究:广东核电公众接受度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9).
[3] 孙晓琳.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我国核电项目公众参与影响因素研究[D].衡阳: 南华大学,2012.
[4] 曾志伟,邓欣蓉,孙晓琳.试析我国核电发展中的公众参与现状及其提升对策[J].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2).
[5] 曾志伟,蒋辉,张继艳. 后福岛时代我国核电可持续发展的公众接受度实证研究[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
[6] 时振刚,张作义,陈飞.日本核能接受度的变化[J].核科学与工程,2002(2).
[7] LI Chao-jun,ZHANG Chun-ming,CHEN Yan,ect. The Study on Safety Goals and Public Acceptance of Nuclear Power[J].EnergyProcedia,2013(39).
[8] 裴娟,杜风雷,黄晓冬. 核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对象选择及建议[J]. 江西化工,2014(2).
[9] 时振刚,张作义,薛 澜.核能风险接受性研究[J].核科学与工程,2002(3).
[10] 方芗.风险社会理论与广东核能发展的契机与困局[J].广东社会科学,2012(6).
[11] 方芗.我国大众在核电发展中的“不信任”:基于两个分析框架的案例研究[J]. 科学与社会,2012(4).
[12] 杨波.公众核电风险的认知过程及对公众核电宣传的启示[J]. 核安全,2013(1).
[13] 彭峰,翟晨阳.核电复兴、风险控制与公众参与——彭泽核电项目争议之政策与法律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14] Changxin Liu,Zuoyi Zhang,Steve Kidd.EstablishingAnObjectiveSystemfortheAssessmentofPublicAcceptanceofNuclearPowerInChina[J].NuclearEngineeringandDesign,2008(10).
[15] 陈钊,孔吉宏,耿明奎. 广东省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09(S1).
[16] 王一龙,廖力,何煦,等.衡阳市公众核电认知水平分析[J].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3).
[17] 全世文,曾寅初,黄波. 北京市居民对核电的认知与接受意愿——基于日本核泄漏事故背景下的调查[J].北京社会科学,2012(5).
[18] 陈方强,王青松,王承智.我国核电公众态度和参与现状及对策[J].能源研究与信息,2014(1).
[19] 袁丰鑫,邹树梁. 后福岛时代的核电公众接受度分析[J]. 中国集体经济,2014(4).
[20] 田愉,胡志强.核事故、公众态度与风险沟通[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7).
[21] 郭跃,汝鹏,苏竣. 科学家与公众对核能技术接受度的比较分析——以日本福岛核泄露事故为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2).
[22] Chuanwang Sun,Xiting Zhu.Evaluating the Public Perceptions of Nuclear Power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Contingent Valuation Survey[J].EnergyPolicy,2014(6).
[23] 贾峰.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法国核电公司的公众策略分享[J].世界环境,2014(3).
[24] 丁志萍.1986—2012 年俄罗斯核电公众接受度研究[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4(2).
[25] 田桂红.浅析加强和改进核电公众宣传[J].中国核工业,2011(11).
[26] 潘自强.如何提高核能可接受性[J].中国核工业,2012(6).
[27] 陈润羊.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核安全文化走向成熟[J].环境保护,2013(5).
[28] Guizhen He,Arthur P.J. Mol,Lei Zhang,ec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in China[J].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2013(7).
[29] 黄维娜.我国核电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沟通策略选择——以中广核“公众沟通”为例[J].财政监督,2014(5).
[30] 郭裕中,李昌举,卢同.西方公众对核电站安全的忧虑(文献综述)[J]. 辐射防护通讯,1998(1).
[31] Younghwan Kim,Minki Kim,Wonjoon Kim.EffectoftheFukushimaNuclearDisasteronGlobalPublicAcceptanceofNuclearEnergy[J].EnergyPolicy,2013(10).
[32] Michael Siegrist,Bernadette Sütterlin,Carmen Keller.WhyHaveSomePeopleChangedTheirAttitudesTowardNuclearPowerAftertheAccidentinFukushima? [J].EnergyPolicy,2014(6).
[33] T. Ohnishi. vA Cellular Automaton Model for the Change of Public Attitude Regarding Nuclear Energy [J].NuclearEnergy,1991(3).
[34] T. Ohnishi. A Collective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An Application to Nuclear Public Acceptance [J].MathematicalandComputerModeling,1994,19 (11).
[35] T. Ohnishi.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Activities for Public Acceptance and the Resultant Reaction of the Public: An Application to the Nuclear Problem [J].MathematicalandComputerModeling,1995(5).
(责任编辑:李潇雨)
Research on Public Acceptance of the Nuclear Power
CHEN Run-yang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Gansu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Saf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the nuclear powe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ergy strategy in China. With sustainable and quick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public acceptance research has caught wide attention.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used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acceptance in China’ nuclear power.Eight key issues has been classified,inclu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ublic acceptance in nuclear power,the impact on nuclear power,public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nuclear power project,public awareness and decision-making risks of nuclear power,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acceptance in nuclear power,factors affecting the public perception of nuclear power,international experience,measures to improve public accept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hortage of theory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public acceptance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hina’s nuclear power,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future has been prospected.
nuclear power;public acceptance;public participation;literature review;energy security
2015-04-28
放射性地质与勘探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我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公众参与机制研究”(项目编号:RGET1303);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招标项目“基于产业链视角的甘肃省核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GSSL2012-006)。
陈润羊,男,兰州财经大学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副教授。
F407.61
A
1008-2603(2015)03-00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