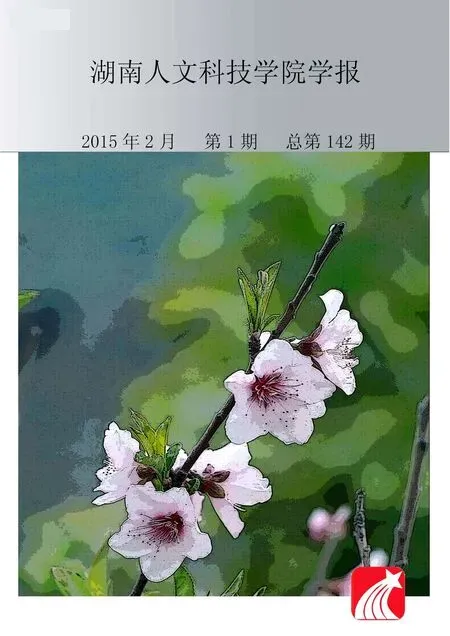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受虐心理分析
2015-03-17周紫薇
周紫薇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在众多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中,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残酷的天才”(俄评论家米哈伊洛夫斯基首次提出)这一称号几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融为一体,甚至说他是一位写变态的专家也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凶杀、癫痫、幻觉、双重人格、歇斯底里等边缘状态在他的作品中一应俱全。在这些病态心理中,受虐心理几乎贯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便注视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遭遇压迫与残害,肉体和精神都处于备受摧残的状态,仿佛随时就会步入疯狂或死亡。《罪与罚》中的马尔美拉陀夫、《白痴》中的纳斯塔西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丽兹等人物,都带着身体和灵魂的创伤痛苦地挣扎。现有的研究大都从外部入手,分析他们遭受苦难的原因,然而深入思考后不难发现,那些悲惨的人们在承受痛苦的同时却也享受着痛苦。本文以受虐心理作为切入点,从人性与心理的角度试探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思想的深层内涵。
一 受虐与施虐的共生关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受虐与施虐是一对双生花,同时栽种在人物性格里。《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承受着生活重压的弱者,在精神上从始至终都处于一种自虐与受虐的极端状态,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杀人犯,展现出狂暴的施虐特征。
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里,涅利的外公史密斯,一个逆来顺受的穷老头,“不仅不敢得罪任何人,而且他自己也明白,他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人家像个叫花子似的赶出去”[1]9,但他却以最残酷的冷漠与无视对待自己穷途末路的亲身女儿,使她深陷痛苦的深渊。弗洛伊德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具有施虐与受虐的双重心理:“在小事上他是个虐待别人的虐待狂,在大事上他是个虐待自己的虐待狂,实际上则是个受虐狂。”[2]由此可见,受虐心理作为一种普遍的人性特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往往与施虐心理相伴相随。
受虐与施虐这一组看似对立的状态为何联系的如此紧密?或许这要从生命伊始说起。子宫作为生命起源之地,意味着婴孩与母体从一开始就结成了牢固的纽带,而被动与母体分离则成为生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脐带剪断的那刻起,婴孩被迫宣告自由,从属关系带来的安全感顿失,孤独的焦虑如约而至。交友、结婚、聚居、血脉认同,都可以看作是人对孤独体验的拒绝与回避,而施虐与受虐心理显然也出于同样的动机。“惊恐的个人寻求某人或某物,将自己与之相连,他再也无法忍受他自己的个人自我,企图疯狂地除掉它,通过除掉这个负担,重新感到安全。”[3]于是,受虐者将个人的自由交给施虐者以求得安宁,施虐者则在统治受虐者的快感中忘记渺小个体的无能为力。他们都不愿面对自我孤独的处境,而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受虐或施虐)企图与他人达成生命的联系,伪装成生命的最初形态,剔除自由,用以抵御孤独感的侵袭。“我不是一个人”,这是多么难以抗拒的诱惑。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著名章节《宗教大法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宗教大法官之口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重要的不是他们的心作出的自由判断,也不是爱,而是他们必须盲目服从甚至违心地服从的秘密。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纠正了你的作为,把它们建立在奇迹、秘密、权威之上。人们大为高兴,因为他们又被当作羊群领着走了,而且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可怕禀赋终于从他们心上解除了。”[3]在红衣主教与耶稣对峙之时,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孱弱的人类将自己双手奉上,甘愿臣服于教会的统治与权威,自动放弃了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他们换来的彻底醒悟与绝对自由。作为逃避的方式,人们必将有意无意地反复进行精神或肉体上的施虐与受虐,用以忘记自由与孤独,也许这就是所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吧。至于施虐与受虐体现出抛弃生命的趋死倾向,我们将放在后面深入探析。
二 受虐心理的深层剖析
(一)绝望的反抗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受虐心理体现最明显的往往是那些受伤最深的人,“许多受到命运折磨并意识到命运对自己不公平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都有这种存心加剧自己痛苦并引以为乐的心态”[1]292,这着实令人费解。在小说《白痴》中,纳斯塔西亚一生受尽屈辱,她明知罗戈任的危险和疯狂,却不顾梅什金公爵的劝阻,三番五次地回到他身边,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刺杀的结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故事与其如出一辙,小女孩涅莉出生失去母亲,以乞讨为生,险些被卖入淫窝,被好心人救出并收留后,她却将他们拒之千里,仍然坚持拖着病体去街上乞讨;《罪与罚》中马尔美拉陀夫深知家境窘迫,妻子积劳成疾、疯疯癫癫,长女索尼娅被迫卖淫,却一次又一次将家中所剩无几的积蓄拿去酗酒,无法自拔。通过深入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人生的悲剧根源竟是他们自己。当外部的恶劣境况将他们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时,人性本能使他们倾向于反抗,而在改变现实处境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种反抗就会内化为心理层面的抵触,内心的抗拒随着外界的压迫逐步加深,最终演化成对整个世界的强烈敌意和全盘否定。外界伸出援手、给予帮助,亦或有改善现状的选项,他们都没有欣然接受,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直接拒绝,这样做无疑将自己推向深渊。这种自杀式的抗争是他们对抗世界的最后办法,是弱者得以一跃成为主宰者的唯一途径,纵使这样做对于他们本已经潦倒的生活百害而无一利。在这种疯狂的受虐背后是对整个世界的报复性反抗,在虐待自己的同时获得了藐视一切的权威感、一种特殊的道德优越感、一种残酷的快感,这是绝望中的绝望,是困兽的最后反击。
这样的心理现象与行为动机并不是孤立的,半个多世纪后,中国的鲁迅同样也窥见了弱者的受虐倾向与绝望反抗。诚然,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阿Q的形象,主旨在于鞭挞国民之劣根性,“引起疗救的注意”[5]。但在残酷又令人绝望的现实处境下,“精神胜利法”会成为一种合理选择,以肉身的受苦换取精神的安慰,从而找到藐视世界的借口,在虚幻的优越感中觅得存活于这残酷世间的微弱自信。因此我们看到,鲁迅的“阿Q精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受虐倾向有着相似之处,区别在于鲁迅站在局外冷静地戏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5],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身临其境,歇斯底里地呐喊。
(二)“罪”与“罚”
俄国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度,东正教(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被广泛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而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思想交火最激烈的时代,1861年,俄国实施农奴制改革,俄国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发展,对俄罗斯民族影响深远。传统的东正教“认为没有经历苦难砺炼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贫穷和苦难才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原初所具有的神性”[6]。然而当时正蓬勃发展的俄国资产阶级相信的是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与资本积累,现实完全不是圣经描述的样子,上帝的预兆似乎也没有实现的可能。面对信仰与现实的差距,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焦虑,“还没有一个世上凡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打开过深渊裂口的宽度,他是信徒中最虔诚的信徒,又是精神中最极端的无神论者”[7]。他被撕裂了,一方面他在感性层面始终坚持着东正教的正统教义,相信上帝存在,相信博爱拯救世人;另一方面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却一次又一次有力地证实着人性最极致的残酷与冷漠。作为教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在赎罪的路上,“罪”的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作为怀疑者,他看遍了世间惨象,不禁对上帝产生怀疑,对人性彻底失望,而这种对宗教的背叛是他内心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他怀疑上帝的那一刻起,无休止的“罚”便萦绕着他。左边是赎罪,右边是愧疚,受虐在此,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定信仰的必经之路,又是对背弃上帝的自我惩罚,这种分裂的深层内涵,导致了他作品中无休无止的矛盾与癫狂。他塑造的人物非常鲜明地体现出精神受虐的这一深层原因。《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秉持的“超人”哲学致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而基督信仰却使他最终跪倒在良心与博爱的感召之下;《白痴》中梅什金公爵尝试用基督的思想来忍受苦难、拯救他人,但无力改变现实;《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质问耶稣的剧本洋洋洒洒、天衣无缝,却在父亲被杀后备受良心折磨,精神崩溃。他们在信仰与怀疑的夹缝中虐待自己,苦求心灵的平静而不得。
鲁迅先生曾表示:“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8]这种精神受虐的产生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和当时的社会情境之间的矛盾分歧,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有些难以理解,但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向灵魂与上帝的“罪”与“罚”。
(三)死亡本能
弗洛伊德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食色本能(生命本能)常欲将生命的物质集会而成为较大的整体,而死亡本能则反对这个趋势,主要将生命的物质重返于无机的状态。这两种本能势力的协作与反抗产生了生命的现象,到死为止。”[9]死亡本能带有攻击性、毁灭性,若指向外部,则会形成破坏、侵略等施虐的行为,若这一过程受阻,死亡本能则会针对自身,造成自我伤害等自虐与受虐的行为。虐待自己和虐待别人的最终目标都是毁灭生命,本质上都是死亡本能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陀式作品中出现的大量病态心理与反常行为,最终都指向这个唯一的终点——死亡。随着情节推进,人物内心逐渐失衡,理智再无用武之地,死亡事件在作品中频繁发生便是预料之中的了。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罪与罚》),涅莉的母亲在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中过早离世(《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罗戈任刺死纳斯塔西亚(《白痴》),斯麦尔佳科夫弑父(《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情节都暴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命消逝的着迷。其作品中常展示出人物受尽折磨直至生命终结的情节线索,带给读者或心惊肉跳,或涕泗横流,或慷慨悲壮的感受,却从来没有苟延残喘和委屈求全。虽然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活着的人们,但在这一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凿出一股强力,它超越短暂的生命,超越俗世,超越痛苦,直抵真理与永恒,给人们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与阅读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虐心理指向死亡本能,而死亡本能却能激发出强烈的精神能量。尼采的理论恰好可以用来解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酒神精神”,它与“日神精神”一起构成了尼采对世界的二元诠释。“酒神的本质”在于“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10]。生命从无至有再至无,死亡实则是一种回归,而生存则是孤独的暂居。个体生命宣告消亡,却获得了融入自然、融入万物的入场券,如同亚当与夏娃重返伊甸园,与万能的上帝、永恒的宇宙再次走到一起。尼采从“酒神精神”的亢奋状态中获得了面向死亡的强力意志,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将自我逼向死亡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原初的答案,超越了转瞬即逝的表象世界,触到了终极存在的本质。从短暂的存在一跃而与永恒并存,他们都感受到向死而生的能量与幸福,这种接近极限的人类生命体验将他们塑造成了真正的“超人”。
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的作品中同样以受虐的形式不断体验着死亡,他的作品很好地诠释了弗洛伊德所谓爱欲本能(即生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相关论述在李遇春的《拂不去的阴霾——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死亡心理分析》中有较全面的阐释。张贤亮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将死而复生的经历,现实经验使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都将“死亡”作为写作主题之一。但由于历史情境的差异,张贤亮的作品在受虐与死亡的体验中包含着对历史的反思与追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对宗教信仰的痛苦领悟中,完成了对受虐与死亡的形而上的探析。
除了上述的阐释与分析,也应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经历与东正教教义对于陀式受虐特征形成的影响与作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而被捕入狱并被判死刑,在处决当天又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死亡如此逼近的经历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之后的生活中不断强化这段痛苦的回忆,最终使它们成为陀式作品特有的深刻主题之一,以不同的情节、不同的叙述形式表达出来。经受过死亡的折磨,受虐行为即可视为作者对这段经历的强制性重复,陀思妥耶夫斯基“残酷”的风格也就有了强大的心理承受力作为坚强后盾。另一方面,东正教作为俄罗斯人民长期信仰的传统宗教,其教义本身就包含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忍受苦难。因此,俄罗斯人民面对严苛的生活,并不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而是听从上帝的指导,选择忍耐和宽容,这一点无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然而人毕竟不是神,长期的压抑与顺从必然导致人们心理失衡,甚而造成心理扭曲与心理变态,信仰的教导既帮助人们更加顽强地面对生活也迫使人们承担更加沉重的精神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即在忍耐与反抗中走向分裂与疯狂,最终,苦难于他,已从被迫的忍从转化为主动的接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开掘之深鲜有人企及,而更可贵的是他始终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孜孜不倦地鞭挞自我、拷问灵魂,从而开启了20世纪反理性思潮的大门,为现代主义文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弗洛伊德、弗洛姆、尼采、茨威格、普鲁斯特、鲁迅等文化巨匠都或多或少地从陀式这里汲取了珍贵资源,在思维领域继续开拓出各自的道路。单就受虐心理这一点,即能从他非理性的写作状态中窥见其天才的洞见与智慧的哲思。
[1]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M].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弗洛伊德.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弑亲[J].顾闻,侯国良,译.文艺理论研究,1984(4):91-99.
[3]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308.
[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5]鲁迅.坟·摩罗诗力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0.
[6]刘锟.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思想中的东正教文化内涵[J].国外文学,2009(3):120-126.
[7]茨威格.三大师[M].申文林,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35.
[8]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2.
[9]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4.
[10]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