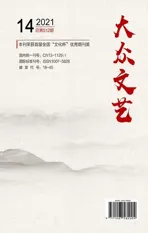信仰的形象·陶瓷佛教造像之语义——东汉至辽陶瓷佛教造像
2015-03-12欧阳昱伶四川美术学院404100
欧阳昱伶 (四川美术学院 404100)
信仰的形象·陶瓷佛教造像之语义
——东汉至辽陶瓷佛教造像
欧阳昱伶 (四川美术学院 404100)
造像之于人的信仰,如同精神之于人的生命。而陶瓷为佛教造像的这个神祇世界增添了新的可能和创造,依靠它的材料,它的技、艺和釉药,依靠无形之火将有形之态转化,取得恒久性和使命形象,在陶瓷中建造了一种神圣。在一个本身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观想了悟的造像的概念中,这些用于观想的造像通过演化和发展,产生了各个朝代范式、造像状貌。
佛教造像;东汉至辽代;陶瓷语言;朝代范式
陶瓷佛教造像不仅是像美观的艺术品那样被解读:它是相当积极的,而且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直接的弘法方式。它对这样一个事实提供语境,即造像安抚众生、接引众生的菩提因缘进入了人们的意识,就在人们观想佛像种种相好(这个过程是佛法介入过程;要暂时关上思维的门窗,不被世间的喧嚣和争斗所打扰)、在成千上万这样的过程之中,感受佛法智慧,认识自性的本来面目——直指佛性——这就是佛教造像的目的。它是感化者、心灵教化、安宁、解脱的救度者:没有观想触动,何来开悟,何来度脱,何来喜乐,何来静观,何来当下。
东汉以后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日渐深广。从云南昭通东汉三维圆雕佛像和四川彭山东汉灰陶摇钱树座上的佛像来看,信仰的形象是通过对印度早期佛像模仿并成为一种形式,从而在观想与精神之间建立了深度的纽带。形象的模仿是由来源所决定的选择,是把仪轨特征、共识符号与必要的神圣和正统联系在一起的模仿学习,这是“学徒期”的一种训练。佛像的造型在承载和传递神圣的那个形状中完成。这里与其说是符号性的模仿,毋宁说是知识汲取性的模仿。
三国、两晋时期陶瓷佛教造像主要见于“人神杂陈”的明器魂瓶(谷仓罐)上。汉晋时期的佛教被认为是神仙方术,此时的贴塑佛像依附于中国固有的神仙思想,这些多有肉髻、项光、结跏趺坐、手结禅定印的模制佛像连同有明显本土特征的各路仙人和祥禽瑞兽,组成了当时的神仙体系。在东神西佛、杂糅混血的混合中,这些非完全佛教意义的佛像把佛教引向了日常生活的风俗之中,甚至把人们引向了它希望无限延续的修行和成佛的精神乐土。魂瓶流通使佛像在其最大限度的地域内得以存在和传播,佛教在它们所构成的空间中酝酿即将来临的兴盛。魂瓶贴塑佛像生产两种意义:作为新颖的商品噱头和介入中国本土丧葬活动——升仙与外神、商品与异教的这种混合标志着其特点。正是在外神的普及中,人们接受了佛教及伴随而来的佛教的发展。人们信佛,是因为那些佛法似乎大慈悲、普度众生,能给人们永久的安慰。对于“佛教的用途何在”这个问题,答案可以是:致力于树立西方乐土的实相、抛弃为了攫取利益而需要殚精竭虑和烦乱心志的所有那些苦的,除了佛教,还会是别的吗?
由于东晋及南北朝完备和规范了佛教教义和礼仪制度,由于确立了佛教的尊崇地位,佛像便在开窟立寺中一跃而成了那些宏大独立的偶像。这种宏大更使人们易于观想佛法宏大。陶瓷佛像被意识到无疑不应该再以装饰性和附属性形式制造,加之陶瓷类佛像的发展还缺乏工艺、技巧或应用,因此此期陶瓷佛像罕见。
唐代陶佛造像就是在逐渐上升的工艺技术的推动下信仰把信仰形象作为充满活力的现世映像加以反映。造像在这个上升中通过审美到艺术的层面而得以精美化,尤其是泥质无釉陶佛像,就好象造像必然在同时期石窟寺的泥或石的精美造像中寻求模式一样。三彩天王作为此期活跃的神祗,呈现贯穿唐三彩的那种视觉强度:由于夸张的复合造型和釉彩绚丽灿烂把天王威严和气势定义为一种超现实的概念——一种对神性的实现,所以,我们看到那种强度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促成了神话的生产。相对于装饰和附属在一个器物之上的佛像它由于本身独立于过去的形象而具有一种充足的清晰性——一种佛教意义的清晰性,这种清晰性,被聚合在造像之内,既是从前没有见过的又是经过过去出来的。其审美效果、艺术水平已非唐代以前陶瓷佛像可比。唐代正值烧造高峰期的邛窑,烧造了不少陶瓷佛像,既有三彩佛像,又有绿釉、黄绿釉佛像,还有灰绿釉褐彩、青釉褐彩佛像,在造像活动中传递的神圣借助釉药在结果中提升它的影响,釉药使佛造像符号在色彩中层层套嵌:轮廓层次凸显、大衣层叠显隐有致。我们完全可以说造像是一项因地制宜的生产:它毕竟要由环境和资源的获得决定。邛窑陶瓷佛像以当地特色的釉药介入造像,这样,佛像就深入了当地——是以服从于实际状况的匠人的技艺的形式,是以资源上的条件或当地的趣味的形式。
在瓷艺得到空前发展的宋代,瓷佛造像在几乎没有人不感到有必要通过一种更优质的瓷进行造像来丰富佛像这个概念中亮相。这也许就是仁爱的观音身上那种慈祥的起源:她脸上特有的优雅,一种母性的亲和,和由高贵控制的姿态;她通过占有一种准存在而保持可能的最大意义。这里,我们看到观音的理想化身是如何在不断创造的连续基础上得以生成的;形象是如何根据对观音的理解而得以完善的;以及构成观音意义的那些选择又是如何在匠人头脑中联系的。出土于广东潮州窑的四尊瓷塑坐佛,一起充当了祈愿的教条形象,它们是祈愿与赐福之间的中介。这祈愿中相同的形象,相似的铭文深刻地揭示了佛教文化普及的方式,并简化了人与天、祈愿与赐福的程序。铭文的行为既是本能的,也是瓷塑所预先设定的,其由佛像的送福功能所生发,是有能量的祷文。
辽代三彩不同于唐代三彩的差异是理解与时代的差异,以至于与它不同的东西最终是其最神话的内容之一,这就是深郁,界定为本身携带的生命内在的深郁。辽代三彩罗汉像足够写实、与现实人物充分融合的对生命的关注,在一种精神真实的悲悯中包含对世间人的仁爱。神情、内在恰恰被置于写实当中的真实之中,然而,神情显然不是世俗的:深切的悲悯就如同佛教的深刻一样,变成精神存在,由其传播,由其扩张。并且,当直觉被卷入这种内在张力时,自我就让位于自觉的和无思的精神体验。深切的悲悯是罗汉像的特征,它同时往返于形貌与精神之间,将其相互联系起来,把后者置于前者当中,使罗汉像达到形貌与精神的一种真正共存。
从东汉至辽代,陶瓷佛教造像逐步成为拜赞之要物,即成为供养、礼佛、参悟或祈愿的媒介,它们被观瞻和礼拜,又被以人为取向的物化成为各朝各代的传播面貌。造像不是一个纯粹的重复、相同情况的重复;而是在其中不断生产新的东西,在精神中生产新的东西,并出于时代的原因呈现差异。
[1]何志国,李莎.从昭通东汉佛像看中国早期佛像的来源.艺术考古,2008.04.
[2]李杨.《外来佛教本土化的滥觞——吴地魂瓶上的佛像、胡人形象》.广西艺术学院学报,2007.8,第21卷,第3期.
[3]吴明娣.《中国古代陶瓷佛教造像考》.理论研究,2002(2).
[4]葛雾莲.《易县北部山洞中的八个辽代三彩罗汉》.新美术,19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