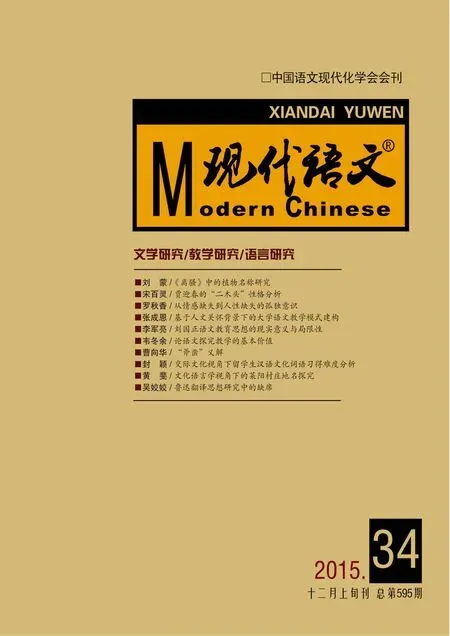《文心雕龙》“术”的范式意义——与论文之“法”的内在关联
2015-03-09任小青
○任小青
《文心雕龙》“术”的范式意义——与论文之“法”的内在关联
○任小青
摘要:《文心雕龙》无疑是我国文论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文艺理论著作,也代表了文艺的第一次觉醒所标示的成果。而其中关于“文术”的卓见,更是与后世大行于世的“法“有着密切的关联,特别是与清代翁方纲的“肌理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翁氏亦可看作是深识文理的重要一人。
关键词:《文心雕龙》术法
《文心雕龙》几乎全篇覆盖了对“术”的精微推阐,特别是通过文体论部分的文类源流考与创作论部分的写作要术指导以及全方位的“术”之理论内涵的鉴定与殊致多方的阐发,我们不难发现“术”在刘勰这里其实是一个统摄范围相当宽泛的概念,而最为深刻的是,他所建立的“术”论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既有技术层面的推进之方,又不失理论上的观照与总结。这一点,詹锳讲得很明白,他说:“我感到《文心雕龙》主要是一部讲写作的书,……但这部书的特点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文章作法和修辞学,而作者的文艺理论又是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和对各体文章代表作家作品的评论当中总结出来的。”杨明也说:“纵观全书,我们感到刘勰努力把有关文章写作的一切前人论述都网罗无遗,并加以自己的亲切体会、深入细致地分析,再按自己的意图,组织成体系。”的确,刘勰正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总结与艺术手段积累的提炼来建构理想之文的。特别是对于“文术”的推阐与后世大行于世的“法”存在着很大的关联,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诚如骆鸿凯在《文选学》中所指出的,“唐以前论文之篇,自刘彦和《文心》而外,简要精切,未有过于士衡《文赋》者。顾彦和之作,意在益后生;士衡之作,意在述先藻。故彦和以论为体,故略细明钜,辞约旨隐。要之言文之用心莫深于《文赋》,陈文之法式莫备于《文心》。”由此可见,《文心雕龙》在文法的研讨方面确实是开唐以前集文论之精华的典范之作,具有承前启后的范式意义。
翁方纲在将自己的“肌理”说与传统的诗法论贯通起来的过程中,曾经提出:
文成而法立。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原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杜云:“法自儒家有”,此法之立本者也;又曰“佳句法如何”,此法之尽变者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原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达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
我们知道,翁方纲谈“肌理”包含了内容层面的“义理”和形式技巧层面的“文理”。而“义理”大体指向了上文所说的“正本探原之法”;“文理”则相应地指“穷形尽变之法”。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翁方纲的“肌理”是在研究《文心》的基础上赋以诗学的含义,并以考据作为外壳。也就是翁氏所标举的“肌理”,其渊源竟是承续《文心》的“术”论而来。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发现《文心》在文体论部分“原始表末,敷理举统”的正本探源中直寻的恰恰是儒家之学的内在理路,特别是对以“宗经”为枢辖的范式体系的建构。总的说来,刘勰正是利用人们“法古”的思维习惯,先将自己的“术”论溯源到圣人那里,为其理想之文的建构寻得立论的渊薮,然后再分条缕析地对圣人经典展开精神脉络的深刻剖析,而在这个过程中,“文之枢纽”明显充当了纲与首的范式作用,“创作论”则是接续其旨并作为支撑文章骨骼活络的细密文法而存在。这样一来,刘勰的“术”论架构就有了兼具法之先后的贯中效应。而更具实践意义的则是对于包括了“附会”“章句”“通变”等细密精微之“术”的具体发挥。
至此,“术”与“法”就存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涵容性。既然“法”在刘勰这里也兼具了“正本探源”与“穷形尽变”的内涵,那么,这就牵涉到了寻“法”的问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谈“术”与“法”的关联,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完全等同。实际上同样作为文学规范性的准则,两者的出现与内涵所指是有着差别性界定的不同场域,尤其是随着江西诗派的兴起,“法”更具权威性与普适性,这就不得不迫使我们去探究从“术”到“法”在中国文论史上的纠结与绾合问题。关于此,笔者将另辟专文加以探讨,此处暂时不论。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同理,“法”在这里不是玄虚飘渺的东西,根本上来讲还是要以法则示人的。于是,刘勰从圣人那里寻得一套规范与成法,而关键是运用这套规范能够造出不同的风格。换言之,这套法不是我的独创,乃是从古人那里寻来的,但是运用的对象不同创作出的风格自然不同。这就是翁氏所说的:“诗文之赖法以定也审矣。忘筌忘蹄,非无筌蹄也。律之还宫,必起于审度,度即法也。顾其用之也无定方,而其所以用之,实有立乎法之先而运乎法之中者。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可见,“法”在这里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约束力的“范式”,处于形而上的“法”没有固定的形态可言,但一旦形之于文则就会产生“体变万殊”的效果。我们刚刚提到了“体”的不同,刘勰专列《体性》篇探讨“八体”的问题,并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这其实与吕本中强调的“活法”“变化不测”所致的“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是相通的。
然而,无论是翁氏、吕氏还是刘氏,三人在肯定“活法”的同时,都并不否认“学养”功夫的积累。“胸中无千百卷书,如商贾乏资,本不能致奇货”“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理。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妙处”“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考编他诗,自然功夫度越过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大约如此。联系上文,可知他们所主张的“法”,都含有从有法可循,到不为法所拘的精神,也就是黄庭坚所申张的“两步走”战略,即从“法度布置”到“不烦绳销而自合”。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与准备,后者是前者的提升与内核。于是,对“定法”的追讨与研探就成为初学者的入门之阶和必经之途,而这部分也是刘勰研究的重心所在。之所以这样,在于不变之法,也就是自然律,是有迹可求的,也是易于入手的,尤其是对于“才童”而言。朱光潜曾就“创造与格律的关系”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古今大艺术家都是从格律入手。艺术须寓整齐于变化。由整齐入变化易,由变化入整齐难。从整齐入手,创造的本能和特别情境的需要会使作者在整齐之中求变化以避免单调。从变化入手,则变化之上不能再有变化,本来是求新奇而结果却仍还于单调。”又说:“古今大艺术家大半后来都做到脱化格律的境界。他们都能从束缚中挣扎得自由,从整齐中酝酿出变化。格律是死方法,全赖人来活用。善用格律者好比打网球,打到娴熟时虽无心于球规而自合于球规,在不识球规者看,球手好像纵横如意,略无牵就规范的痕迹;在识球者看,他却处处循规蹈矩。”朱氏的言论很通彻也很明了,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二者的关联。紧接着在论及“创造与摹仿”的命题时,他再次肯定了摹仿于创造的重要性,没有摹仿的功夫创造就失却了始基。并坦言“要学一门艺术,就要先学它的特殊的筋肉技巧。”也就是说,“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故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无匠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摹仿。匠人虽比诗人身份低,但亦绝不可少。”这也就是刘勰所说的“摹体定习,因性练才”的道理。
据此,我们于刘勰对“法”(或称“术”)的重视可见一斑。其实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在这一理论的背后所呈现的正是刘勰对“天才”与“学力”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天赋与性灵本是先天的,生性使然,而法则确实可从后天的研习中获得。关于二者的关系,主“性灵”的袁枚明确指出:“无诗转为读书忙”“读书久觉诗思涩”,显然是将“诗”与“书”“学”对立起来,表现出重天才、轻学问的倾向。不过,在刘勰看来两者并不是天然的对立关系,他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又言:“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承认天资的条件下,刘勰充分认识到了学习对于“入门”“立志”的正道的导引作用,于是强调“习亦凝真,功沿渐靡”的深刻意义。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他的立论基点和针对的受众群体主要是初学者,至于天才虽言及不多,但从他对“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的判断来看,我们大胆揣测刘勰的意图则是天才自有运法帷幄的道理在其中,也就是说,“格律不能来束缚天才,也不能把庸手提拔到艺术家的地位。如果真是诗人,格律会受他奴使;如果不是诗人,有格律他的诗固然腐滥,无格律它也还是腐滥。”而这也正是刘勰大量阅读与躬身创作的经验与心得,借用清人李家瑞的话就是,“刘彦和著《文心雕龙》可谓殫心淬志,实能道出文人甘苦疾徐之故;谓有益于词章则可,谓有益于经训则未能也。”(《停云阁话诗》)
现在看来,刘勰就“术”这一范畴的提出以及将其通过文之枢纽、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探究贯彻到全文的论述中,揭橥着他“术有恒数,循势而成,动不失正”的文学观的根本宗旨。更具有影响意义的是,他在主张博学识理的同时,又指出了“精一”“随势”“因革”的突破性意见,这就为后世“学古而赝”与“师心而妄”的文学病症,开辟了一条相对慎妥的切中肯綮的创作道路,同时亦是深契当时“弃术任心”的弊端的有为而发。很清楚,他对创作原理及方法论体系的体会与抉发也更加幽微深入,绝非“体大虑周”所能概括,而兼具“思深意远”的特点。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整部《文心》的体系建构与内容构成即是一个大“术”,缀联着的仍是其一以贯之的条贯首尾的整一性原则,也正是沿着这条思路,刘勰在研术而以驭群篇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诚如贺拉斯自序:“我将起磨刀石的作用,使刀刃锋利,尽管磨刀石本身不能切东西。即使我自己什么也没写,但我会告诉诗人,他的职责和义务是什么,从哪里找材料,什么能够滋养和塑造他的诗歌才能,用这些资源,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正确的道路引导他到什么地方,错误的道路又会引导他到什么地方”,的确,刘勰虽未有诗文创作留传于世,但无疑其宏阔幽邃的理论建构却最恰当地诠释了其“为文用心”最深刻之处。这一点是我们论“术”必须格外观照的。因为他的“术”论的稳固性与权威性得益于他为文的确立以及文的展开与形成从本质上寻到了法理依据,更是“龙学”研究能够经久不衰的根由,全赖于《文心》的广延性与深刻性。依着他的养术之道,其理想之文的孕成最终要达到的审美效果是覆盖了各类审美嗅觉的鸣凤之章,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这足以反映刘勰在追求“沉思翰藻“的同时,不忘从读者的层面来观照文章具有“悦目娱心之适,咏叹抑扬之致”的审美愉悦功能。实际地讲,一篇优秀的文章应该是法度严密,扬敛束放自如,而又富于变化,合规矩又能自成一家的“活法”之“术”的产物,这显然是深得文理的掷地有声之论。

表1:“文术”之“术”在《文心雕龙》中的出处与内涵统计一览表
说明:纵观《文心雕龙》,“驭文之法”(《附会》)确实是“术”的同义项词。此后其中虽有提及“文法”(《奏启》:“秦之御史,职主文法”。)一词,但此处明显指“法令、条文”而言,故而与后世所论驭文之“法”显然在意思上不相一致,不过我们不难想见后世之“文法”也是“法令”意义上的延伸,表征着文法的约束力与规范性的形成与确立。而我们这里列表讨论的“术”也是专就“文术”之“术”而论,与文中出现的“诡术”(《正纬》、“经术”(《辩骚》)、“心术”(《乐府》)、“方士之术”(《祝盟》)、“智术”(《序志》、“杂术”“政术”(《诸子》)、“道术”(《才略》)、“文武之术”(《程器》)等诸篇什,皆就具体领域的的“学术”“道理”来讲,干系不大。不过,我们对“术”的罗列也并不能止步于以“术”的出现来表象的统计,因为其中有些词汇术语的运用,与我们所指的“术”是息息相关的,如“楷式”(《祝盟》)、“体要”(《杂文》)、“大略”(《诏策》)、“纲领”(《诸子》)、“大体”(《哀悼》)、“明范”(《议对》)、“典型”“风轨”(《奏启》)、“制”“旨”“通矩”“范式(《事类》)、“经范”“准的”(《才略》)、“矩矱”(《序志》),等等不一而足,这一点我们是绝必不能忽视的。至于从“术”的内涵指向来讲,我们则不难发现它包含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要求,也就是“义理”与“文理”的意义。典型的例子,如:“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议对》)于此,刘勰从“文理”“义理”两方面立法的用心可见一端。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09).
[2]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朱光潜.谈美[M].北京:中华书局,2010,(08).
[4]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
(任小青山西太原山西大学文学院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