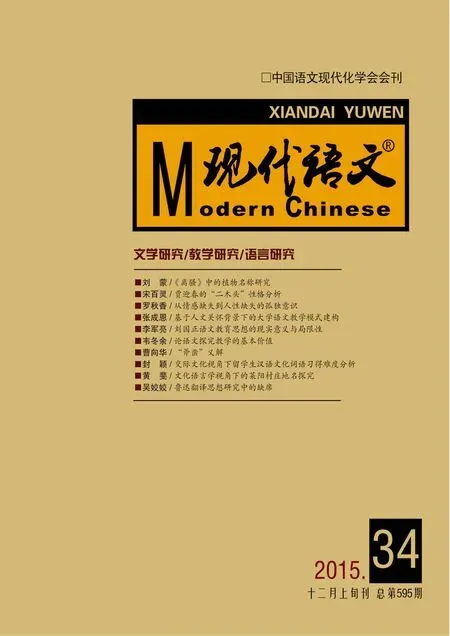译介学视野下张爱玲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特色的比较
2015-02-28柳青青
○柳青青
译介学视野下张爱玲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特色的比较
○柳青青
摘要: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出现了近20个不同的译本,小说家张爱玲与诗人余光中都曾翻译过这部作品。由于他们的身份、创作风格和面对的文化语境不同,其译作也在不同方面有着较大差别。文章试图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视野出发,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的主体视域及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从译者身份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比较分析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2010年版)在感情色彩、语言风格和文化传译方面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感情色彩语言风格文化传译译者身份文化语境
自古以来,文学就是联系全世界人类的重要纽带,文学交流则是促进民族间相互交往、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进行文学交流的前提是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无疑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随着“世界文学”时代的逐步走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文学关系日益密切,文学翻译面对着具有极大语言差异的异质文化体系,难度大大增加,翻译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领域。一部优秀的作品之所以享有长久的世界性声誉,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译作是分不开的,通过对这些不同译作的比较研究,我们能够看出一部作品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接受及产生影响的情况,及其所折射出的不同译者的不同身份、风格和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日本比较文学家野田丰一郎说:“作为比较文学家的工作之一,是存在着对同一作品的两种以上翻译的对比研究。根据这个方法,我们能够理解同一作家产生的几种微妙的印象。这样说来,同时也能够理解到那个作家对于外国影响的质量和范围的变迁。”[1](P87)由此可见,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并不是对译作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而是重在关注不同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种文学研究。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比较文学译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翻译理论不断更新,出现了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说、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等,与此相应,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成果也日益繁荣。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获得评价最高、最集中地体现了海明威写作风格的一部小说。《老人与海》于1952年9月发表于美国《生活》杂志,1953年即获普利策奖,1954年又帮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迅速被译为多种语言,风行世界各地。它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诠释不尽的象征意义以及主人公表现出的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普通读者及文学研究者,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在我国,《老人与海》同样受到广泛欢迎,五十年代至今已出现了近20个不同的译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海观、吴劳、李锡胤、黄源深等译本。而事实上,中国最早的译本是1952年12月由香港中一出版社出版的署名范思平、实为张爱玲翻译的《老人与海》[2],以及1952年12月1日至1953年1月23日在台湾台北市《大华晚报》上连载的余光中翻译的《老人与大海》。这两种译本虽在原著发表的同年即在港台面世,但大陆地区正式出版则分别在2012年和2010年。与大陆读者见面时,张爱玲译本并未有太大改动,余光中译本则经过了他本人的大力修正,全书所改在一千处以上[3](P4)。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独具特色也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余光中则是享誉两岸的著名诗人,二人同为读者所熟悉和喜爱。然而,他们的身份、创作风格和所处的文化语境却差异很大,因此,他们的译作也在不同方面有着较大差别。文章试图结合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视域、文化学派等翻译理论,分析研究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与余光中《老人与海》译本(2010年版)在感情色彩、语言风格和文化传译方面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
一、感情色彩:女性的细腻与男性的粗犷
海明威被称为“硬汉”作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有着铮铮铁骨和不屈灵魂、面对重压依然表现出优雅风度的男子汉,甚至有学者评价其小说世界中“只有男人,没有女人”[4]。《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也不例外,他孤独一人在无边的大海上与大鱼、鲨鱼惊心动魄的搏斗与毫无畏惧的勇气,使他成为永远打不败的“硬汉子”的典型代表而铭刻在读者心中。这样一部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作品在女性译者和男性译者笔下,必然会展示出不同的感情色彩。
(一)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彰显 女性情感的流露
由于曾经就读于女校以及亲人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对女性有深切的关怀。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在作品中始终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她塑造了多个感人至深的女性形象,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们都是男性话语社会中的受害者,她们的不幸代表着那个时代千万女性的不幸。张爱玲通过描绘她们的命运,表现出也控诉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压抑的现实。同时,与其他女性作家一样,张爱玲也试图颠覆那种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她将范柳原、姜季泽等都塑造成了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苟且之辈。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是一位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
同样,张爱玲在其作品的自译及其他译作中,也采用了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女性译者有时会在序言中解释自己选择原作的初衷以及采用的翻译策略来彰显自己的女性身份。芭芭拉·戈达尔德认为序言是译者“积极参与原文,参与意义生成的重要工具”[5]。张爱玲在1954年11月为《老人与海》写的译者序中表达了她对这部作品的喜爱:“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热爱的一本……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愧色。”[6](P4)这篇简短的序言并没有对原作者以及作品内容做过多的介绍,也没有像大多数译者一样对作品的意义进行深层的挖掘,而是充满了她对海明威和这部作品的敏锐而细腻的女性感情:“……我觉得这两句话非常沉痛,仿佛是海明威在说他自己。……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6](P4)这篇序言显然传达出了张爱玲作为一位女性读者、一位女性译者的独特感受。
除序言外,张爱玲在具体的翻译中也采用了一些女性主义的干涉策略,如“劫持”。女性主义译者认为她们有权利“操纵”政治上不正确的文本,纠正原文当中的男性话语,其翻译策略中的“劫持”即对不具有女性主义意图的文本进行操控[7]。《老人与海》中有大量男性化的词语,以强调主人公的男子汉气概,张爱玲将其中的一些译成无标记词汇,以回避强烈的男性特征。如以下两例:
原文:It is what a man must do.[3](P126)
译文:【余光中】男子汉应该这样。[3](P16)
【张爱玲】活总是要干的。[6](P16)
原文:And pain does not matter to a man.[3](P186)
译文:【余光中】男子汉不在乎吃苦。[3](P66)
【张爱玲】疼痛是不碍事的,并不伤人。[6](P53)
man一词既可指男性、男子汉,又可指不限男女的人、人类。为了凸显海明威原作中的硬汉气质,余光中等大多数男性译者在以上两处都将man译作“男子汉”以突出主题,而张爱玲则故意模糊该词的性别界限,将其虚化或译作笼统的“人”,显示出她的女性意识。
另外,张爱玲在译文中同样传达出了她作为女性对原作中人物情感的细腻把握与强烈共鸣。《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不仅是一位不屈的硬汉,同时是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老人,他爱生活,爱大海,爱海里的种种生物,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与男孩诺曼林之间的深厚感情。张爱玲以一颗女性的敏感的心把握和传达着这些感情,也传达着她本人对人物的喜爱。与其他男性译者相比,她在译文中注入了更多自己的感情,使人物形象更为柔和,感情也更加丰沛。如在一些动作的描述上,张爱玲不自觉地选择了女性特有的词汇或句式,具有更丰富的感情色彩。如以下几例:
原文:He took hold of one foot gently and held it until the boy woke and turned and looked at him.[3](P125)
译文:【余光中】他轻轻地握住一只脚不放,直到男孩醒来,转身望他。[3](P16)
【张爱玲】他温柔地握住一只脚,一直握着它,直到那孩子醒过来,翻过身来向他望着。[6](P16)
张爱玲将gently译为“温柔地”,相比“轻轻地”显然更具有女性特色。另外,她在此处采用的句式虽然不如余光中的译法简洁,但使人物的动作显得更加自然流畅,突出了老人对男孩的关爱。
此外,张爱玲在一些形容词等修饰词的翻译上,也用女性特有的敏锐加入了更细腻的感情色彩:
原文:…and sail desperately over thesurface.[3](P133)
译文:【余光中】在水面拼命飞行。[3](P22)
【张爱玲】绝望地在水面上掠过。[6](P20)
原文:…and then swinging them wildly and ineffectually as he followed the flying fish.[3](P134)
译文:【余光中】接着又猛烈地、吃力地拍动双翼,追赶飞鱼。[3](P23)
【张爱玲】然后他狂乱地徒然地扇着翅膀,追赶着飞鱼。[6](P21)
绝望、狂乱、徒然这几个词的使用,赋予了鸟儿和鱼以人类的感情,体现出老人、作者和译者将鸟和鱼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对于他们有着深切的同情。类似于这种细节词语的感情处理,或许女性译者比男性译者更为敏感。
(二)余光中:粗犷之中有温情的硬汉气质
与张爱玲在译文中流露出的鲜明的女性意识与女性情感不同,余光中作为一位男性译者,更加侧重于在译文中表达出海明威原文所具有的强烈的男性气概,在感情的处理上也更加男性化。首先从序言来看,无论是1957年还是2010年的译序,他注重的都是对作品意义的阐释,以及对语言风格的客观评价,如将《老人与海》与《白鲸》的象征意义做比较,或对英文语法转换为中文语法的讨论,而较少个人感情的流露。张爱玲担忧的是“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而余光中则说年轻的自己“译得太文……像是白手套,戴在老渔夫粗犷的手上”[3](P3)。一人关注的是悲哀的意境,一人关注的是粗犷的风格,显示出男性译者与女性译者在翻译原作时侧重点的不同。
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余光中在译文中大量使用“男子汉”“汉子”等具有强烈男性特征的词语,以突出原文的阳刚之气。海明威本人热衷于在作品中描写战争、斗牛、打猎、捕鱼等以男性为主导的活动,更乐于塑造刚强不屈的男性英雄,甚至连余光中都感到他“作品中主角的男性实在是强调得过分了一点”[3](P7)。但想要使译文忠实地传达出原作的硬汉气质,则必须采用海明威式的男性词语。此外,男性译者一般很难如张爱玲一样自觉意识到这类词语所带有的男性主导色彩,在翻译时自然也就不会采取回避的态度。为了更加强烈地突出主题,余光中有时不按字面翻译,而是直接译出词语的关联意义。例如:He took the bite like a male.[3](149)余光中译为:它吞食钓饵,像个汉子。[3](P35)其他译者大多将male按照字面意思译为雄鱼、公鱼,但“汉子”则更能淋漓尽致地体现原作整体的男子汉气概,不仅忠实传达了该词的原义,也应和了全文的主题。
在感情色彩方面,余光中很好地把握了原著中老人温情的一面,如他与男孩的对话中体现出的对于男孩的关爱,独自在海上漂流时对男孩的想念。在他的译文中,阳刚、粗犷的男性化语言与老人身上这种普通人的温情形成张力,使读者能够体会到在老人硬汉气质的背后,有一颗感情丰富的灵魂。当然,如前举例,余光中在一些细节词语的处理上没有张爱玲那样细腻,在老人对海中生物的感情方面也没有张爱玲那样敏锐(如他将大鱼的代词him译为“它”,似乎对老人将大鱼视为同类、朋友、兄弟的感情有所削弱),但依然忠实地传达出了原著的感情层次,很好地展示了老人粗犷之中有着温情的硬汉气质。
二、语言风格:小说语言与诗情译笔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海明威更是以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他“一生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老人与海》的语言简洁有力,行文干净利落,尽量少用修饰词而只用动词,删去了一切冗言赘语,是海明威“新闻体”风格的集中展现。而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翻译中必然会留下自己的痕迹。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有一千个译者也会产生一千种不同的译本。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视域,而翻译主体具有怎样的视域势必会决定翻译的具体结果[8]。构成译者视域的重要成分是译者身份与翻译环境。
从译者身份来看,张爱玲与余光中同为作家,在文学修养与文字表达能力上自然无可指摘,他们也都具有深厚的外语功底,对英文原著的理解相当透彻。然而,二人一为小说家,一为诗人,身份不同,写作风格迥异。张爱玲作为极具特色的小说家,语言风格亦中亦洋,大俗大雅,精致的用词背后是无边的苍凉感。余光中则是一位风格多变的诗人,其诗中既有壮阔铿锵的远大理想,也有细腻缠绵的浓浓乡愁。他们笔下的《老人与海》自然会染上小说家和诗人的不同风格色彩。另外,二人所处的翻译环境也不同。1952年的香港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习惯都受西方影响,也易于接受欧化表达方式;而2010年余光中对译文进行修改再版时,新中国文学已发展数十年,汉语的使用形成稳定规则,翻译策略大多采取归化原则,以适应读者阅读习惯。这也是造成二人译文风格不同的重要原因。
(一)张爱玲:中西结合的小说语言
张爱玲出生在传统的封建大家族,自幼受私塾教育,酷爱古典文学,《红楼梦》更是对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同时,张爱玲曾出洋留学的母亲又使她接触到西方文明,再加上在学校受到西式教育,后长期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使她无论个人气质还是文学创作中都同时交织着中西特色。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既有古典遗风,又有通俗色彩,还有西方情调。同样,在张爱玲译的《老人与海》中,既有大量地道的汉语流水句,又带有欧化语言的特征。例如:
原文:He was asleep in a short time and he dreamed of Africa when he was a boy and the long golden beaches and the white beaches, so white they hurt your eyes,and the high capes and the great brown mountains. He lived along that coast now every night and in his dreams he heard the surf roar and saw the native boats come riding through it. He smelled the tar and oakum of the deck as he slept and he smelled the smell of Africa that the land breeze brought at morning.[3](P124)
译文:他很快就睡熟了,他梦见非洲,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还有些长长的金色的海滩,和那白色的海滩,白得耀眼,和那崇高的海岬,和棕色的大山。他现在天天晚上住在那海岸上,在他的梦里他听见海涛的吼声,看见土人的小船破浪而来。他睡梦中嗅到甲板上焦油和碎绳的气味,他也嗅到非洲的气味,早晨陆地上吹来的风带来的。[6](P15)
原文基本都是由and连接的几个简单句构成的并列句,张爱玲将其译成汉语口语常用的流水句,没有严密的语法结构,而是靠句子间的意义关联,一句句娓娓道来。其中一些显然不符合汉语语法而是照搬原文语序,表现出欧化特征。这样的译法还能较好地传达出原文中老人梦境的零乱与不连贯感。
张爱玲的用词也较为简单和口语化,多用描述性的话语而很少用书面词汇,例如:
原文:The clouds over the land now rose like mountains and the coast was only a long green line with the gray blue hills behind it.[3](P134)
译文:【张爱玲】陆地上的云气现在堆得像山一样高,海岸只是一条长长的绿线,背后是灰蓝色的山。[6](P21)
【余光中】这时,陆上的云像群山一般涌起,海岸只余下一痕绿色的长线,背后隐现淡蓝色的山丘。[3](P23)
相比而言,张爱玲采用的几乎是最为通俗易懂的口语化的表达方式。类似之处还有很多,她在翻译中尽量使用最简单的汉语词汇和句法,把小说变成了故事,而她则是讲故事的人。这是她作为小说家在创作和翻译中惯于使用的方式。
(二)余光中:凝练而悠长的诗意
一般而言,由于文体特点和篇幅限制,诗歌语言比散文语言更为凝练,也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20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进行了几十年诗歌创作的余光中,在运用文字时自然惯于精心锤炼,力求用较少的文字表达丰富的涵义。余光中对海明威的文体风格有着清醒的认识,说“他的文体习于冷眼旁观。简洁而紧凑,句子不长,段落也较短”[3](P2),另外,语言要对应主人公的身份,“不可使用太长、太花、太深的字眼或成语”。可见,余光中在翻译时“力求贴近原文风格”,向读者传达出海明威极简单、极客观的“电报式”特色。然而,由于英文与中文句法结构和语言习惯的巨大差异,单纯照搬原文句式不符合汉语语法和阅读习惯,正是“贴得太近,也会吃力不讨好”[3](P4)。余光中将原文的许多较短的简单句凝练为四字短语,既符合原文简洁的风格,又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如上文中所举例子,余光中的译文如下:
不久他便睡去,梦见少年时去过的非洲,梦见漫长的金色海岸和白得刺眼的海岸,还有高耸的海岬、褐色的大山。如今他夜夜重回那岸旁,在梦中听见波涛拍岸,又看见土人的小舟来去乘潮。他嗅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绳的气味,还有清晨陆上微风送来的非洲气息。[3](P15)
相比张爱玲的译法,余光中所译更加简洁,更符合汉语语法。“波涛拍岸”“来去乘潮”等词语的使用也使译文具有了诗的节奏感与韵律感,使人读后回味深长。余光中在多处都采用这种中文特有的格式整齐的四字词语,如原文中:He could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lowing noise the male made and the sighing blow of the female.[3](P148)余光中译为:他能够分辨雄鲸喷水,声音喧嚣,雌鲸喷水,有如叹息[3](P34)。既形成排比,又富有诗的悠长韵律,充分发挥了汉语形美、音美、意美的优势。
同时,余光中选用的词语常有多重意味,可以使长期浸润在汉语环境中的读者联想到词语的深层隐含意义。如全篇的第一句话:
原文: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3](P105)
译文: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3](P1)
英语是重形式的语言,汉语则重意义。余光中将原文的一个长句拆分成几个汉语短句,但无一赘词,简洁而清晰。“独驾轻舟”短短四字如同一幅简笔勾勒的水墨画,既传神地勾勒出老人的状态,又带有诗情画意,引发了读者关于孤独与坚持的内涵的联想。可见,与张爱玲在语言风格上更侧重异化相比,余光中更侧重于归化。
此外,余光中在序言中提到:“原文中有许多代名词,旧译本无力化解,常予保留。后来经验丰富,已能参透英语文法,新译本知所取舍,读来就顺畅多了。”[3](P4)以上例分析,原文中代词he出现两次,冠词a(an)出现三次,但余光中的译文中没有任何多余的成分,增一字嫌多减一字嫌少,可见几十年的经验与锤炼也是其译文能达到既凝练又富诗情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传译:归化与异化
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所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变化方面,更突出地表现在翻译过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形成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包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等。他们的研究重点从翻译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如勒菲弗尔认为,翻译主要受到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种因素的操纵,译者的翻译行为或隐或显无不受到这三因素的制约。
一部作品中最具文化意味、最能体现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的是文化词汇,即那些具有一定文化负荷的词语,这些词语“受文化制约,从它们身上可映射出不同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9]。《老人与海》中既有富于宗教色彩的基督教文化词汇,也有直接从西班牙语引进的词汇。这些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色彩和异域风味,并且与中国文化有着巨大差异。在翻译时如何充分传达并使读者理解其中的文化信息,不仅与译者个人的策略有关,更受到译者所面对的翻译环境,即当时整体文化语境的影响。张爱玲和余光中在翻译这些文化词汇时,所面对的是不同的文化语境,因此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宗教意味:
《老人与海》是一部充满象征意义的作品,许多人尤其是西方读者从中解读出了基督教的象征意义,如老人与鲨鱼的搏斗象征了耶稣受难。原文中也有多处出现基督教词语,具有宗教意味。由于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张爱玲和余光中在翻译这些宗教词语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张爱玲侧重于异化,余光中侧重于归化。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中立于政治上尖锐对立的大陆与台湾,此时又有大量内地学者移居香港,因此形成了文化多元的环境,香港居民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较为熟悉,也容易接受。同时,由于美苏冷战的世界环境,当时的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及新中国政府,在香港大力宣传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大量发行美国作品的中文译作。1952年张爱玲翻译《老人与海》时,正受雇于美国新闻处设立的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这种受雇人身份使她必须配合当时的美式文化宣传,按照赞助人的意志宣扬美国主流价值观。操纵学派认为,赞助人“是能促进或阻挠文学的阅读、书写和改写的权力(人士、建制)之类的东西”[10]。赞助人对张爱玲的影响表现在译文中,就是宗教意味的彰显,她将许多宗教词语按照原义忠实地翻译出来。而余光中的译作2010年再版发表时,没有赞助人的特殊要求,所面对的读者群体是较少有宗教信仰的大陆读者,整个文化语境也较为宽容开放,没有必要特意突出原作的宗教意味,一些宗教词语只需表现出其包涵的感情色彩即可。如以下几例:
原文:God help him to take it.[3](P142)
译文:【张爱玲】上帝帮助他吞饵。[6](P26)
【余光中】天哪,让它吃吧。[3](P30)
原文:Christ knows he can’t have gone.[3](P142)
译文:【张爱玲】耶稣知道他不会走的。[6](P26)
【余光中】天晓得,它不会走的。[3](P30)
原文:Thank God he is travelling and not going down.[3](145)
译文:【张爱玲】幸而他只是航行,并没有往下面去——感谢上帝。[6](P28)
【余光中】谢天谢地,它一直向前游,没向下沉。[3](P32)
这里的God,Christ都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词语,张爱玲将其直译为上帝、耶稣等宗教名词,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宗教意味。而余光中则侧重于传达感叹语气,将其翻译为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天哪”“天晓得”,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
(二)异质文化
《老人与海》的主角圣地亚哥是一位古巴老渔民,他所说的语言应是西班牙语。为了符合他的身份和地理背景,海明威在小说中直接引用了不少西班牙语词汇,不仅使老人的形象更加生动可感,也为原文增添了一份异质文化的气息。对于这些西班牙语词汇的翻译,张爱玲几乎全做归化处理,而余光中则偏向于异化。原文中有23处西班牙语词汇,张爱玲或直接意译为汉语,或干脆略去不译,并且没有一处解释说明的注释。余光中则保留4处西班牙语原文并加以注释,有些音译为汉语之处也做了注释说明。例如,原文中的西班牙语la mer和el mer,在张爱玲笔下被译为“海娘子”和“海郎”,具有了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容易为中国读者接受,但通过译文完全看不到原文所体现的异质文化。余光中则将这两处西班牙语直接移植,然后加以注释“la是阴性冠词,mar是海。”“el为阳性冠词。”[3](P19)这样,使原文的异质文化色彩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受美国新闻社的委托,张爱玲要将原文翻译得通俗易懂,从而利于更多读者的广泛接受,而如果音译或移植原文中的西班牙语,显然会打断读者阅读的流畅过程,拉长阅读时间。如前文中的例子,如果张爱玲也采取移植并加注的翻译策略,可能会影响到当时不熟悉外语中的词性、冠词的普通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从《老人与海》在美国首次发表到张爱玲译本的出版发表,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之前并无其他译本可做参考和对比,因此张爱玲将文中的西班牙语词汇归化翻译或许是出自个人的爱好和感受。而余光中面对的则是翻译文学已占据很大一部分文学市场的新世纪,《老人与海》已成为许多读者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此前的多个译本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他自然会对翻译策略谨慎思考和选择。对这些西班牙语词汇进行异化翻译既能很好地保留原著带有的异域风情,也能更加直观地向读者传达异质文化信息。
张爱玲与余光中在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同时,他们在文学翻译领域也有不可忽视的贡献。由于二人身份、风格和所处文化环境的不同,《老人与海》这部作品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张爱玲的译本充满着女性意识与细腻的女性感情,采用的是她创作小说时常用的中西结合、又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同时由于特殊的赞助人影响而彰显了宗教意味。余光中的译本体现出原著粗犷的硬汉气质,语言凝练而富有悠长的诗意,同时传达出异质文化的色彩。文章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的主体视域及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从译者身份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比较分析了这两种译本在感情色彩、语言风格和文化传译方面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产生的原因。张爱玲和余光中以作家身份进行文学翻译,本身就具有独特的价值,虽然其中也有些许不完美之处,但作为《老人与海》在中国的最早译本依然值得关注。文章对两种译本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优劣高下的价值判断,而是试图从比较文学译介学的角度,对不同的译者身份、文化语境对译作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以期对更深层的研究做一些铺垫。
注释:
[1]野田丰一郎:《比较文学论要》,《比较文学译文选》,长沙:湖南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陈子善:《范思平,还是张爱玲?——张爱玲译<老人与海>新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1期。
[3]余光中:《老人与海》,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4]夏志清等:《文学的前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版。
[5]转引自:李思乐,王娟:《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特色研究》,安徽文学,2012年,第12期。
[6]张爱玲:《老人与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
[7]李思乐:《张爱玲译<老人与海>中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研究》,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8]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 月版,第112页。
[9]转引自:汤洁:《<老人与海>中文化词汇翻译的认知解读及翻译策略——以张爱玲和吴劳的汉译本为例》,常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0期。
[10]李思乐,王娟:《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特色研究》,安徽文学,2012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1]余光中.老人与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张爱玲.老人与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3]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2.
[4]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6]杨大亮,邵玲,袁健兰.海明威作品研究:冰山的优美[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7]张韬.张爱玲译《老人与海》的特色研究——以海观、吴劳译本为参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8]查晓丽.多元系统论观照下的《老人与海》译本对比研究[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1).
(柳青青山西大学文学院03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