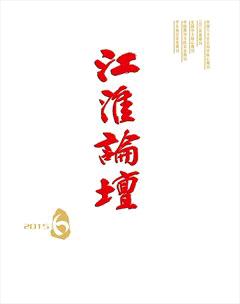心性论视域下朱熹“致知”理境探析*
2015-03-09郭文李凯
郭 文 李 凯
心性论视域下朱熹“致知”理境探析*
郭文李凯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江西上饶334001)
朱熹的“致知”说在发挥人之本心先天本具的灵昭明觉之知的知觉之能的同时,通过推极心体本具的灵昭明觉之知,在穷理、尽心的工夫引导之下,臻于与物之理的一体贯通。从心性论的视角而言,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由于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意味着朱熹的“致知”理境并非纯粹停留在知性的知解层面,而是与德性修养的心性层面密切相关。这突显了灵明昭觉之知在致知的知解认识活动中显发其心性修养的德性意义和价值。在此一理境的照察下,人之心、性与天理通过“致知”的工夫一体贯通。
朱熹;致知论;心性论;贯通
在宋明理学诸家学说中,王阳明“致良知”一说最是受到后来学者的关注,而对于朱熹的“致知”说,学者们通常从“格物”与“致知”这一对概念的关系梳理中来界定和定位,尤为关注的乃是这一学说所显发出的知识论一面,如钱穆先生曾说,“致知”之论乃朱子论心学工夫最为关切的方面,指出:“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主要工夫,惟朱子一人。”[1]139意在表扬朱熹“致知”说于理学独辟知识论一途乃为一创举。然而,朱熹的“致知”说除了有追寻知识、探索物之理的知识论的一面,其学说的伦理本位意味着其“致知”说最终也是落在人之心性的德性修养层面。正是有见于此,本文尝试从心性论的角度对朱熹“致知”一说的理境作一探讨。
一、朱熹“致知”说的涵义
要论究朱熹的“致知”说,先有必要探讨一番朱熹对“良知”一词的看法。朱熹对“良知”的论说以及阐发是藉由注释、论说儒家先圣先贤的学说发展、推演出来的。“良知”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其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在《孟子集注》对“良知”之“良”作注时,用“本然之善”释之,并引伊川先生的话进一步论说:“程子曰:‘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2]430朱熹所注与孟子的原意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良知”乃是一种先天的本然之“知”,也即如孟子所谓不必思虑而能知觉之知。在《论语集注·述而》,朱熹在注释孔子“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段文字时,作如下之解读:“生而知之者,气质清明,义理昭著,不待学而知也。”[2]125-126这仍然是在用一种不必经过思虑的“本然之知”来解释孔子的“生而知之者”。同时,在朱熹那里,“良知”原是人生来即秉自于“天”的,是天所赋、天所贯注于人心而为人心所本具的知觉之能。因此,“良知”说在朱熹的语境中常常与人心自然而然地联在一起。朱熹在《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就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2]6-7在《大学或问》中也说:“人莫不有知。”[2]511这里所谓的“知”实从人心的角度来论说“良知”。同时,朱熹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对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作注时指出:“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2]425作为人心本具的先天知识原已涵括万物之理(众理),更准确地说,人心之知(知识论层面义)也即万物之理,唯如此才可能与万物之理相应,与众理一体。故朱熹认为:“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2]143内在本具的先天之知“具众理而应万物”,故能彻见精微义理,举一理而万理俱摄。故人之异于禽兽者在朱熹看来正在此一本具先天知识、洞彻万理之心知,也即良知。可见,朱熹之“良知”不仅具有先天的知识论色彩,且涵具此先天之“知”的心体亦具有知觉之能,这是朱熹对“良知”说诠释的独特之处,实已显出“致知”的倾向。正因如此,朱熹对“良知”之论说非简单着眼于义理阐释的层面,而直从人之与禽兽相区别的价值高度加以厘定。
由于朱熹在对“良知”含义的阐释上已经透显出“致知”的倾向,因此,在全面论说“致知”时,朱熹就直从“良知”的知觉之知(知识)与觉知之能(知觉)入手。《大学章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2]17可以看出,朱熹所谓“致知”并非是一种平常意义上的向外求索的实践功夫,实际上乃是吾人自身本具之知识的一个推极过程。因为此处所谓“知识”非由穷究外物所得“物之理”的积累而成,而是人心本具的先天本然之知识,故在朱熹看来只能言“推极”、“推展”,而不能言探求、索取。同时,朱熹所谓“致知”从来不是不涉外物的、孤立的、“反求诸己”的认识活动。朱熹认为,要推极此“知”,是离不开“格物”的。只不过,朱熹此处所谓“格物”乃“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3]2026。这一“体用一源”的立场表明朱熹所谓“先天本然之知”与“物之理”二者之间非是纯粹认识论意义上之架构,因为二者“元不相离”。因此,“致知”在朱熹看来,二者其实乃认识的同一个过程。只是朱熹认为:“格物,只是就事上理会;知至,便是此心透彻。”[3]297即谓二者意义不同而已。乐爱国教授认为:“在朱子看来,格物只是就事物和理而言,要求穷尽物之理;致知则是就我之知识而言,要求推极此知识;然而,穷究物理的过程就是推极我之知识的过程,而且,‘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4]实际上,就“格物与致知是同一过程而言,格物的过程,既是穷尽某一具体事物之理的过程,也是自己的知识不断扩展的致知过程”[4]。可见,朱熹的“致知”说更多的是一“我之知识”与“物之理”同时并进、一时并在的心理交融与贯通理境,而非纯粹知识论的探求过程。
如何推极此“知”?这就涉及一个知识的动力来源问题。朱熹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人莫不有知”,作为“知觉之体”也即认识主体的人心本身即本具先天本然之知,这是人之一切认识活动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推极吾之知识”之必备前提,此“知”实指人之本心先天本具的灵昭明觉之知(知觉之能),这是从体的一面讲。而从发生学的层面来看,作为人所本具先天本然之“知”,更有其“致知”之用的一面,就是说,此灵昭明觉之知有所谓“知觉之能”。如朱熹言:
本心知觉之体光明洞达,无所不照耳。
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2]534
本具灵明昭觉之“知”同时兼具“知觉之能”、知觉之用,是其所以能够“致知”、所以能够推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前提。必须注意的是,朱熹所谓的“致知”之用尽管有认识论的意味,且由于其讲“致知”多从“格物”,故其学具有本末兼备、内外贯通之实学本色。[5]然从心性的层面论,所谓“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则已更多地显发出德性色彩和善恶的价值判断。因为在儒家学者看来,对道德善恶的价值判断不是也不应该由知识进路,而应由个人心性进路。所以,其喜怒忧惧、妍媸俯仰作为明觉之知的觉知对象,也就不仅仅只是在认识论的知解意味上来说,而应从心性修养的德性意味上来说。
二、心性论与“致知”说的德性之维
朱熹论“致知”,常瞩目认识论背后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因其喜从心性论的立场来谈论此一问题。一旦涉及心性问题,又必与心性之德性修养连在一起讲,朱熹讲“致知”也同样是落到这一面上来发挥。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由于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意味着朱熹的“致知”说并非纯粹停留在知性的知解层面,而是与德性修养的心性层面密切相关。这突显了灵明昭觉之知在致知的知解认识活动中显发其心性修养的德性意义和价值。
前面已述,“致知”也即穷尽某一具体事物之理的过程,也是自己的知识不断推极过程。朱熹在《答潘文叔》中曾说:“《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穷得本来自然当然之理,而本心知觉之体光明洞达,无所不照耳。”[6]这一段话清晰地向我们描述了“格物致知”的具体情形:穷究事物本然之理的过程,实即本心本具之“知”的朗现(光明洞达)与物之理的照应过程。可以看出,朱熹所谓的“致知”似乎有一种明镜鉴物的映照意味,而非一理性的逻辑推理过程,亦不是对物之理的知解、探求过程,而是物之理在明镜般的自心之知的朗照下的自我显发。实际上,朱熹正是以此比喻来阐释其“致知”的具体开展过程。朱熹在《大学或问》论“正心”时指出:
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而喜怒忧惧,随感而应,妍媸俯仰,因物赋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无者也。[2]534
朱熹在这里分别从体、用两个方面来论说“人心”:从本体的一面来讲,“人心”本体、本真的一面如明鉴一般纯净虚明,不染一物;又如衡器一般公平公正,不著私意。但在发用的一面,“人心”则不能不因外物“喜怒忧惧”、“妍媸俯仰”表现出“随感而应”、“因物赋形”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从朱熹对“人心”体用两个方面的阐发不难看出,“人心”不仅是知觉的主体,且作为知觉主体的“人心”本身具有德性色彩和善恶判断。陈来教授指出,朱熹所谓“心”、“人心”不仅能知觉,而且有善恶,他说:“知觉之心不仅指能知能觉的精神,也指具体的知觉活动,具体的思维和情感。心千思万虑,出入无时,其中合理者为善,不合理者为恶。因此‘心有善恶,性无不善’(《语类》五,甘节录)。”[7]由于朱熹的“人心”在发用一面既已体现为善恶两方面的道德属性,所以,由心性论的视角来观照朱熹的“致知”说,则朱熹所谓“致知”便从单纯之认识的知解色彩转进成显明之心性修养色彩。或者进一步来说,从心性的视角来审视朱熹的”致知”说,则对于人之认识而言并非一纯粹的认知论问题和知性问题,而是心性修养的德性问题。
即谓心性修养的德性问题,就存在着如何在“致知”的过程中持守“良知”,保证本心灵觉之知能够“无所不照”的问题,也即保持其“光明洞达”、“湛然虚明”。朱熹从心性修养的立场认为,要如此,关键是灵昭明觉的本心(人心)能够不为外物所蔽。朱熹认为,“人有是心,莫非全体”,即为全体,则必有人心所不能照顾的地方,必有不能穷极事物之理的时候。究其所以,人心之“知”被遮蔽,而不能时常地穷究事物之理:“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尽,故其心之所发,必不能纯于义理,而无杂乎物欲之私。”[2]527故,人心尽管本具灵明昭觉之知,而一旦被私意、私欲所遮蔽,不仅会干扰乃至阻碍“致知”的进一步推进,也会对“存心”、养性带来直接的危害。朱熹认为,人心一旦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即说这全然不是一个靠自身的知解努力所能达成的认识过程,阻碍认识活动难以继续推进的非是人自身之知识能力缺乏的问题,而是认识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
那么,致知之要,如何去蔽,如何复其本心之虚明,使“致知”不至为私意、私欲所累和遮蔽?朱熹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存心,也即其常说的要操存、涵泳、持敬、守静;一为为学,即通过读书实践以求得心性的涵泳与义理的畅达。就前者,朱熹说: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2]35-36
是以平居静处,虚明洞达,固无毫发疑虑存于胸中;至于事至物来,则虽举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尝接于耳目思虑之间者,亦无不判然迎刃而解。[2]994
盖欲应事,先须穷理;而欲穷理,又须养得心地本原虚静明澈,方能察见几微,剖析烦乱,而无所差错。[8]
就后者,朱熹说:
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徳,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知,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2]527—52
由“存心”几段话看,朱熹“致知”说的心性修养色彩不言而喻,更显发出在朱熹的语境中,德性的修养对于知解认识活动而言所具有的究竟意义。由“为学之方”一段话看,朱熹”致知”说的认识论、知识论色彩鲜明,然究其极,知识论的诉求最终还是落在心体的证成上。当知觉之心体“虚明洞达”,面对纷繁复杂的外在事物时(格物之际),知觉之心的“迎刃而解”则不过就是此心体的“发而中节”,如朱熹所谓:“及其感物之际,而所应者,又皆中节,则其鉴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滞,正大光明,是乃所以为天下达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2]534显然,这一段话绝非知识论层面的阐述,而是德性价值层面的心性显发。
尽管朱熹在阐述”致知”说时时常与“格物”联系起来论说,但是其所谓“致知”定然不能单纯从知解的认识论入手来加以体认。通过对人心本具灵明昭觉之知的揭橥,朱熹详细阐明了“致知”与心性修养的紧密关系,突显了灵明昭觉之知在格物穷理的知解认识活动中显发其心性修养的德性意义和价值。而藉由“致知”的推极理路与心性论诠释,我们更可得以一窥朱熹如何在论究天-理(性)-人(心)的内在架构过程中贯通天人以及天道与人道。
三“致知”说的心性贯通理境
由于人心本具灵昭明觉之知,同时又具众理而能应万物,而心所具之理谓之性(朱熹言),理之所自,乃“无不本于天而备于人”(《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故天、理(性)、人(心)原本浑然一致,而心、理、性又为天所统摄。朱熹认为,对于此浑然一致之天人关系的体认,必须依赖“致知”的工夫。也可以说,对于天人关系的体认原是“致知”的理境与价值诉求所在。朱熹注道: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者,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2]425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朱熹谓天、理(性)、人(心)原为浑然一致,故致知其一,则全体该摄。所谓“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意在表明,尽心与穷理致知与体认天理天道原是一并显发的。只要尽得此心之全,亦即意味着对“物之理”的穷极无余。“物之理”原不过天理的显发与天道的下落,故穷得“物之理”同时即可体认到“物之理”所由以生发的天道本源。在这里,朱熹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其理(性)、人(心)与天(道)的贯通、合一的意味。
朱熹又谓,对于全体涵具的“人心”,要尽得此心,必须“穷理”、“致知”。唯如是,才能通过格物以了达“物之理”,透显涵具灵昭明觉之知的本心,并上达性天,最终实现天人以及天道与人道的贯通。实际上,朱熹此一态度乃是排斥内外、物我分立的立场,基于一体涵具、内外交融的致思理路,从弥合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的视角来说。如钱穆先生言:
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专务于外,从物穷理,则心不尽。物不尽,心不尽,皆是理不尽。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即理之境界,始是豁然贯通之境界。[1]150
就是说,朱熹所谓致知之贯通理境全然以心物内外之交融为归趣。朱熹说:
必其表里精粗无所不尽,而又益推其类以通之,至于一日脱然而贯通焉,则于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义理精微之所极,而吾之聪明睿智,亦皆有以极其心之本体而无不尽矣。[2]528
其贯通之意正是在一体交融的理境上言说的。当为学致知进至脱然贯通境界,知觉之心知与物之理则一体契合。故本心所具之灵昭明觉之知不仅能够究极天下之物之精微义理,也能够究极此心体之量。
是以圣人设教,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本;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2]528
其“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而至豁然贯通之后,则“无内外精粗之可言”,可见其“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即理之境界”的交融贯通之理境显见无疑。但此交融贯通之理境是知觉之心体在穷理、致知“真积力久”之后心、理合一的证成,不是心性自我显发、扩充之后的境界。此或正是朱熹与孟子所不同的地方,牟宗三也正是以此而批评朱熹一系乃歧出孟子以来的儒家正统一途的真正原因。
四、结语
牟宗三先生曾说:“孟子从道德的本心说性,其将存有问题之性提升至超越面而由道德的本心以言之,是即将存有问题摄于实践问题解决之,亦即等于摄‘存有’于‘活动’(摄实体性的存有于本心之活动)。如是,则本心即性,心与性为一也。至此,性之问题始全部明朗,而自此以后……中国永不会走上如西方以外的、知解的形上学中之存有论。”[9]28并由是批评从知觉的心体说性的朱熹为歧出。但是,朱熹的“致知”说原本或许就可以由多维度进入,而不必纯以扩充、显发为一途,也不必纯以心性的契合为依归。故牟宗三对朱熹的“歧出”判释未免有所谓“矫枉过正”之嫌。由于朱熹的“致知”说常与格物穷理一体来说,故除去心性的显发与契证以外,心性与义理的贯通以及对知识的追寻与穷究未始不能成为朱熹“致知”说的重要方面,至少钱穆先生就是如此认为的。钱穆视“致知”为朱子论心学工夫最要着意所在,“欲求致知,则在格物。就理学家一般意见言,心属内,为本,物属外,为末。理学家所重之理,尤在心性方面。心性之理,则贵反求自得。朱子不然,认为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俱到,统体兼尽。此为朱子之伟大识见所在。故朱子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实欲以此开出理学之新趋”[1]139。钱穆先生的立场就是批评理学家专从心性方面言理,尤其批评从自身本心本性的角度来体认和探求心性之理,这就不可避免会有忽视外在一面的嫌疑。因此,在钱穆先生看来,朱熹的学说理境原本精粗俱到、统体兼尽,此也正是朱熹别开生面的伟大之处。当然,钱穆此说虽不免有所拔高,但就朱熹“致知”一说而言还是较符合其题中之义的。此一立场也即意味着探讨朱熹的“致知”说,最好能够将其追寻知识的知性理境与心性修养的德性理境圆融地贯通起来,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或许不失公允。
[1]钱穆.朱子新学案(第一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朱子全书(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3]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乐爱国.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10:146.
[5]沈娟.“物理”还是“道理”——作为实学的朱子“格物”论》[J].朱子学刊(第24辑):53.
[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答潘文叔(一).
[7]陈来.朱子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2.
[8]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三)·答彭子寿(一).
[9]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心体与性体上(卷五)[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责任编辑吴勇)
B244.7
A
1001-862X(2015)06-0121-0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www.jhlt.net.cn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2014年招标课题(JD14123)
郭文(1982—),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儒学、佛学、儒佛道三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