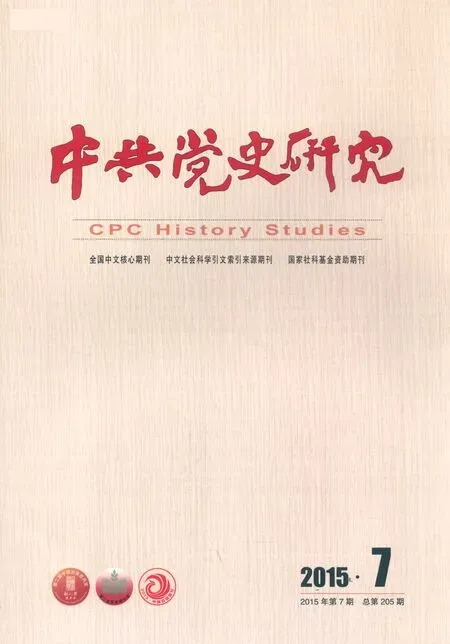革命、党争与上海罢工:一九四八年申九“二二”工潮起因研究*
2015-03-03贺江枫
贺 江 枫
革命、党争与上海罢工:一九四八年申九“二二”工潮起因研究*
贺 江 枫
1948年申九“二二”工潮的爆发是工人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斗争和中共城市革命三重因素互相叠加、彼此作用的结果。工潮首先缘于工人对厂方迟迟难以发放配给物品的不满,其次则是申九工会新旧干部争夺领导权和三青团与工人福利委员会矛盾斗争的产物,同时中共以不同政治面貌出现,充分利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发动城市革命,以申九工潮掀起全市年奖斗争。通过对申九工潮起因多重面相的呈现,亦可窥知战后上海工人运动所具有的复杂性与挑战。
申新九厂;派系斗争;中共革命;上海罢工
1948年2月2日,上海申新九厂7000工人罢工3天后,与军警发生冲突,3名女工受伤殒命,30余人受伤,300余人遭国民党当局扣押①《申新九厂工潮剧变》,《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在此之前,1月29日上海爆发同济学潮,市长被学生殴伤;1月31日又发生舞女捣毁社会局的事件。一时之间,舆论惊恐不已,《大公报》感叹“我们生活在这苦难的日子里,既在忧深思远,而且时时受着刺激,人们是被笼罩在远近大小的纷乱气氛中”②《社评:纷乱中需要祥和》,《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哀叹局势混乱已达极点,“最近军心民心动摇已极,无人无地无不表现其失败主义之情绪”,“情势愈急,险象万状”③蒋介石日记(1948年2月3日),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申九“二二”工潮的爆发极大地破坏了国民政府的统治秩序,因此,1948年7月李立三在中共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上,特别强调申九工潮“表现了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英勇传统至今是仍然保持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第369页。。
申九“二二”工潮作为战后上海最为惨烈的大规模工人运动,始终是内战工运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大陆学者郑庆声强调工人的生活困境是罢工得以实现的首要因素,中共曾积极组织罢工,但有“左”倾冒险倾向;台湾《中国劳工运动史》将申九工潮视作中共运动工人的结果;法国学者鲁林(Alain ROUX)强调罢工由国民党派系斗争所引发;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认为申九罢工标志着工厂女工的组织以及她们的意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女工开始出现革命精神和阶级意识*代表性论著包括: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台北)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59年;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郑庆声:《论一九四八年初上海申新九厂大罢工》,《史林》1996年第2期;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Alain ROUX, Chine 1945—1949: la classe ouvrière dans une révolution à l’envers. Cahiers d’histoire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n°28 1987, pp.8-44, 48.。然而无论是经济压迫论、中共策动论、派系纠纷论抑或性别论均有失片面,罢工的实现可谓是多重因素互相促进、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即利用多方档案与口述史料,重新考察工潮爆发的多重原因,集中呈现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纠葛、中共革命在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俾使今人对于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杂性有更深层次的体认。
一、经济诉求与申九罢工
作为上海知名的民营纺织企业,申新九厂产业规模可谓各纺织厂之佼佼者,1948年已拥有纱锭13万、布机850余台,“蔚然为产业界之巨擘”。申九劳资关系处理得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上海10万纺织工人稳定的大局。上海市社会局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强调申九“治乱动静足以反映本市产业界之安危”。为稳定生产秩序、调和劳资关系,申九资方早在战前就对工人福利设施多有经营,开沪上纱厂之先例,创建工人宿舍、厨房、眷属住宅、合作社、医院等设施。抗战胜利后,上海房荒严重,“各厂在恢复期间,工人大量由乡区集中都市,居住大成难题,有蹴居盈尺铺位之地即须付出重大代价者”。申九资方为解决工人住宿问题,先后建设四区暨242间女工宿舍,均为公寓式钢筋水泥建筑,“无论外观与内容,堪与大规模之学府宿舍或公寓比美”,共容纳3184名工人,解决了近半数工人的住宿问题。*《上海各工厂福利设施概况》,《社会月刊》1948年第3期。1948年记者道克(Doak)的观察也能提供几分印证:“近年劳工已经开始运用他们讨价还价的权利,为自身争取利益,工作情况和战前相比,已有明显改善。”*Barnett, A.Doak,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London : Thames & Hudson, 1963, p.79.
战后上海工人运动因紊乱的经济社会秩序,呈现再次复兴的趋势,国民政府被迫转变劳工政策。1946年2月6日,蒋介石召开会议,商讨应对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案,*蒋介石日记(1946年2月6日、7日)。并手谕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要求劳工运动以“维持工人最低生活”为原则*《劳工事务》,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55000-0002。。即如福瑞泽(Frazier)所言:“为防止劳工怠工,处于战时经济的国民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来强迫企业向工人提供住房和其他基本的生活需求。”*Mark W.Frazier,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workplace: state, revolution, and labor management,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9.当时,最严峻的问题,无疑是国统区急剧恶化的通货膨胀。为此,国民政府通过在上海各行业全面推行工人生活费指数制度,使得工人生活有所保障。“所谓生活费指数,是为了要测量生活费变迁的一种科学化的统计数字。举凡衣服、食品、房租、燃料、交通、教育、娱乐、水电等等费用,都包括在内。”*邵心石等编:《民国三十七年上海市劳工年鉴》,1948年,第71页。尽管存在指数偏低、计算方法不尽合理等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工人生活“曾一度得到很大的改善,大部分工人家庭除能还清战时的债务外,还能添置一些新衣和有积蓄”*《上海工人的生活费指数斗争(初稿)》,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4年第3辑。。
就申新九厂而言,该厂工人1937年8月每日工作12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每日最低工资0.24元,最高工资1.1元,平均每日工资0.45元。每月以30天计算,实际工作时间为26天,每月收入最高28.6元,最低6.24元,平均工资为11.7元。1948年1月,申九工人每日工作时间缩短至10小时,工资依据政府每月公布的生活费指数,按照基薪折扣的方式发放。工人每月底薪在30元以下者,依照生活费指数十足发给;底薪在30元至100元之间者,除30元照指数发给外,其余部分以10元为一级,逐级递减10%。*《上海市工资调整暂行办法》,《社会月刊》1947年第6期。1948年1月生活费指数为95200倍,但零售物价指数为188300倍,故而计算工人收入仍须考虑生活费指数偏低的影响。综合言之,1948年1月申九工人收入按照1936年币值计算,最高24.93元,最低11.27元。具体状况则如表一。与1937年8月相比,1948年1月的最高收入有所降低,为战前最高收入的87%;最低收入则有较大涨幅,为战前最低收入的180%,已接近1937年8月申九工人的平均工资。由此而言,除少数高薪工人实际所得有所降低之外,大部分工人的收入反较1937年8月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表一:1948年1月申九工人薪资
表格数据来源于《申新九厂工人人数与工资(1948)》,上海社科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卷号20-004。1948年1月工人每月实际所得(按照1936年币值)的计算公式为:工人每日基本工资×26天×基薪折扣×95200/188300。
此外,1948年的申九工人与战前相比,还享有部分福利。“以每月基本工资总额(包括升工在内)为100%,则其中每月的津贴:年奖是6.53%,考勤奖是0.67%,蓝布制服是0.94%,膳米贴是16.67%,加点工资是0.07%,总计每月津贴为月基本工资的24.88%。”*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38页。同时,“住外工人因在膳食方面所得较少,故另有所谓代办米,每人每周可得一斗”*《上海各工厂福利设施概况》,《社会月刊》1948年第3期。。
申九工人无论薪资水平抑或衣食、住宿、医疗等均有所保障,与此相反,上海资本家大多对现状忧虑不堪,认为1948年1月生活费指数“暴涨比例,允称空前,而物价与指数,互为因果,呈角逐之势,经济状况至此,诚不堪设想耳”*上海市档案馆编:《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91页。。申九资方更是自感“年来纺织业处于原料荒、电力荒、材料、燃料无不恐慌之时代,加以高工资、低限价等重重困难,环境日趋恶劣”*《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下),第745页。。若就劳资双方所处客观经济环境而言,工人必定安分守己,缘何仍心生不满,倾向于罢工之举,这又与战后通货膨胀阴影下的工人收入体制有较大关系。
首先,根据《工厂法》的规定:“工厂每营业年度结算,如有盈余除提股息公积金外,对于全年工作并无过失之工人,应给以奖金或分配盈余。”1947年年奖“最先处理同时也是最难处理的便是棉纺业”*沈讱:《三十六年度年赏问题》,《社会月刊》1948年第1期。,当年棉纺织工业“已由顺境转入逆境,黄金时代业已消失”*《一年来的上海工商业》,《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8日。,故而年奖谈判艰难异常,“最初资方表示分十天、十二天半、十五天三种等级,其后又增加为十天、十五天、二十天三级,最后则增加到三十五年的四十天、五十天、六十天对折。在劳方则坚持不得少于去年,两方所坚持的数字相差过远,最后经调解,结果采用双方自行协议的方式,照三十五年八折计算。好容易总算大前提解决,而指数所依存之月份、发放的时间以及等级之重行拟定,又耗了不少时间与精神”*沈讱:《三十六年度年赏问题》,《社会月刊》1948年第1期。。申九资方要求年奖依据1947年12月份生活费指数发放。由于1947年12月生活费指数为68200倍,而1948年1月已至95200倍,上涨幅度达39.59%。若年奖全部依照1947年12月指数发放,则工人年奖实际所得将受到严重侵蚀。故而申九工人坚决反对,主张1947年年奖必须六成照1947年12月份生活费指数发放,四成照1948年1月份生活费指数发放。申九劳资双方因年奖计算所依存的月份指数及发放时间,发生争议,双方难以达成协议。
其次,194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有条件解冻生活费指数后,鉴于生活费指数仍旧持续上涨,“其中实以米价高涨为最大因素,乃遵照市政府、粮食部之指示,实施调解,办理配售”*吴开先:《一年来物价管制与物资配售》,《社会月刊》1947年第11—12期。,成立民食调配委员会,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形式,向上海产业工人配售食米。民食调配委员会试图通过实物配给制度,减缓生活费指数的上涨速度,降低资本家对该制度的不满*张处德:《民食调配之意义及其开展》,《社会月刊》1947年第7—8期。。随后,上海市政府进一步推广实物配给制度,1947年8月16日颁布《上海市产业工人配售煤球实施办法》,向产业工人配给煤球,“每人配售一担,每担收回成本两万八千元”*吴开先:《一年来物价管制与物资配售》,《社会月刊》1947年第11—12期。。根据规定,1948年1月政府将向产业工人提供第二期配给煤球,但配给煤球迟迟未予兑现,直至1月30日上海市社会局方才决定“本市职工工人第二期配给煤球已经制成十万担,即日起配售,凡按生活指数计算的各业职工即可向配售会申请核配”*《民食会昨日开会》,《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30日。。然而,1948年1月下旬上海恰逢奇寒,1月26日气温低至零下八度三,除1943年上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十度外,实是多年不遇*《冷风砭骨昨日奇寒》,《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7日。。配给煤球作为生活燃料对于工人生活自属不可或缺,而奇寒天气更凸显了它的重要性,政府发放配给煤球行为迟缓,无疑加剧了工人的不满情绪,乃至多年后中共地下党员仍认为申九罢工“直接的导火线是工人为了争取别厂兄弟已经到手的配给米、配给煤球”*申九二·二斗争史编写小组:《申新九厂二·二斗争纪要》,中国政协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4页。,“这给其他已经领到配给品的棉纺厂的响应工作带来困难,以致申九罢工孤军突出”*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第227页。。
无论是年奖六成照1947年12月份生活费指数、四成照1948年1月份生活费指数计算的主张,还是争取配给煤球的发放,均为申九工人经济诉求的具体表现。客观而言,经济诉求难以实现,无疑将促使劳资矛盾趋于激化,但是否一定引发大规模的罢工行为,却又未必尽然。根据上海市社会局统计,1945年8月至1948年7月上海各业工人因经济诉求与资方共发生争议案件5688起,但罢工停业案件仅为561起,占劳资争议总数的9.86%*相关数字依据上海市社会局劳资争议统计整理所得,可参见贺江枫:《革命、党争与社会控制:1945至1949年上海工人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3年,第314页。。换言之,仅有约1/10的劳资争议最终演化为严重的罢工停业案件。至少当时在上海社会各界看来,“申九资方仍被视作良好的雇主,在最近两年之内并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劳资冲突”*“Labour report No.6: The labour situation in Shanghai”,February 9, 1948, FO371/6959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若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资方压迫愈严重,工人反抗愈激烈,似乎申九出现大规模工潮的概率要小的多,此类罢工更应发生于工人待遇更差、资方剥削更为残酷的企业。申九资方事后就曾感慨“二二”罢工事发突然、猝不及防,“事前微有所闻,自审绝无足以引起罢工之口实,故亦仅能嘱各部职员严加防范,绝不料其行动如此迅速”*《申九厂长吴士槐呈吴国桢的呈文》(1948年2月2日),上海社科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卷号20-004。。此种现象看似悖论,实则又与申新九厂内部的政治生态密切相关。即如社会学家西德蒙·塔罗的分析:“客观机遇并不一定导致持续的社会运动,因为社会运动过程需要挑战者用已知的斗争手法,动态地构建他们的运动宗旨,获得或创建统一的动员结构。”*Sidney G.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pp.81-82.事实上,当时愈演愈烈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与中共城市革命为工潮的实现充当了必要的挑战者。
二、派系斗争与申九罢工
战后国民党诸多派系均试图染指上海工运,不仅陆京士的工人福利委员会掌握部分工会领导权,而且三青团上海支团、中统背景的劳工协进社均跃跃欲试,结果使得彼此互相争权夺利、冲突时起。工人福利委员会就曾感慨“中统、青年团亦从事领导工运工作,且各自为政,不特难收合作之效,且易发生重复相歧之势,自相纷扰”*《上海市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31-306。。申九纱厂可谓最典型的案例,国民党各派工运势力均曾涉足其间,申九工会的领导权主要由工人福利委员会的范才骙与章祝三把持;而战前即在沪纺织业从事工运的陆荫初,依靠王仲良的一六二兄弟会,得以控制该厂大部分男工;此外还有三青团的何锡龄亦积极拓展工人组织,冲突自然在所难免*《上海申新纺织厂二二斗争被捕名单及报纸登出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28。。上海市社会局认为申九工潮的部分原因正是“陆荫初掌握大部分工人,而章祝三仅掌握工会权,两人为争取工人之领导权暗斗甚烈,因此失去领导作用”*《上海申新纺织厂二二斗争被捕名单及报纸登出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28。。
1946年6月,上海工运党团指导委员会成立,对外称为工人福利委员会,并分设沪东、沪西、沪中、沪南、沪北办事处及浦东、吴淞联络站,陆京士任主任委员。申新九厂所处的沪西办事处由陆荫初担任主任,章祝三为副主任。*《上海市工福会职员名册》,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31-144。同时,陆京士“为加强领导力量,并彻底推行党团决策起见,特以性质相同之工会分为若干业别,综合领导,以求统一”,指派范才骙与章祝三担任棉纺业召集人,其中章祝三负责沪西区棉纺业工会,范才骙则以沪东区棉纺业为主*《上海市工福会训令、各行业工会的名册等》,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31-325。。
范才骙、章祝三均是战后初期国民党内利用上海混乱的经济秩序而兴起的新派工运干部。章祝三1909年出生,1933年进入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服务,“组织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售票员司机员工互助会”;抗战期间“奉令再度来沪,担任上海市工团团委,上海市工运指挥部行动组组长”,*《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工界人物志》,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7-1-126。此时,章祝三在上海纺织业内部并无力量可言。然而,待至抗战胜利,“日资纱厂停工,由经济部接管,其时工人失业,徬徨失措,遂酝酿团结,而有组织之雏形”,“初因领导乏人,情形混乱,社会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乃征得经济部之同意,遣派同志分赴各厂,争取群众,促成合法组织,而由范才骙、章祝三总其成,经三四月之努力,至三十五年春国营、民营各厂工人均在本党领导下成立正式工会”*《中纺第三纺织厂工人反对黄色工会进行罢工事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8-114。。章祝三由此一跃成为国民党在上海棉纺织业内的重要工运干部。为巩固个人势力,章祝三在沪西各棉纺厂积极安插人员,“有的是实际担任职务,有的是名义上的职务,但主要都是搞工人运动的情报工作,或者担任黄色工会的指导员来控制工人运动。这些人有上棉一厂的杨宽海、上棉二厂的陆锡山、上棉三厂的□□□、上棉四厂的邹春芳……申新二厂的章祝康和申新九厂的我(王剑冲),还有嵇金龙等人”*《王剑冲谈范才骙、章祝三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1946年3月29日,申九工会在范才骙、章祝三的推动下成立,石璞初始为工会理事长,因申九“一般工人不能谅解,故有种种责问”,随后以身体原因辞职,申九“好像仍无工会状态”*《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产业工会成立大会和各次会议记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8。。1947年申九工会理事长遂由茅玉庭出任,王剑冲则以指导员名义控制了工会领导权,并担任工人福利委员会护工队第四大队大队长。
陆荫初抗战前即在沪西从事工运,“在大小棉纺厂都有他的基础,如申新一厂翁喜和,申新九厂的王仲良、陈鳌郎、毛和林等,统益纱厂的费祖培等”*《王剑冲谈解放前国民党在沪西各种特务组织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抗战爆发后,陆荫初留沪参加敌后抗日工作,一度被捕,出狱后在童行白所办垦立女中任教,虽按月从国民党市党部领取津贴,但对上海敌后工作“每以环境不佳为托词,未曾参加任何工作,反暗中与伪方工运人员张升等往返甚密”,1940年5月14日吴绍澍曾密电重庆,“为保障市部工作安全,拟予制裁”,此后陆荫初转变立场,撤往后方*《上海党务概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档案号301-01-06-172。。抗战胜利后,陆荫初返回上海,试图重新领导工运事务,但是“这些厂已经由范才骙、章祝三夺去了领导权,他只有申新一、八厂和上纺五、七厂仍由他领导”,“他和范、章斗争、争夺权力的事不断发生”*《王剑冲谈解放前国民党在沪西各种特务组织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如1946年章祝三对中纺一厂赵往义不满,缘于赵某是“陆荫初关系的老工会的人,当时是在争夺工会的领导权,这事大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姓赵的就不听到说起了,后来中纺一厂由范小凤主持,杨宽海领导了;在同一时期统益纱厂也有类似的争执,结果是陆荫初关系的□□□改做厂里的门卫,不再接工会事”。陆京士对于各工会国民党新旧工运干部的内部矛盾,也曾试图解决,“按照原来领导这些工会的和新领导这些工会的,由陆京士安排,双方力量大小作为主要根据,能合并即合并,有争论的强制指定领导人,但争端并未终止”。*《王剑冲谈范才骙、章祝三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陆荫初领导的申新九厂王仲良、陈鳌郎等旧派工运干部,为获取工人支持,“利用工人群众优秀分子的向上性,利用了工人群众野心份子的领袖欲,来把握群众、煽动群众,正因劳资双方的不健全,他们极容易找到机会,造成纠纷,纠纷即起,他们又用一些技巧,使工人得到一些小惠”,“或者另一部分与他们同阶层的力量将动摇他们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往往再来发动一次纠纷”*樊振邦:《本市劳资纠纷之解剖与处理》,《社会月刊》1948年第1期。。1946年1月12日,申九工人1000余名发生怠工,工人代表王仲良、陈鳌郎、毛和林等50余名向资方要求年终红利预先公布;饭菜改为两荤两素一汤,饭碗由厂方供给;发给每人恐慌补助金15000元等六项条件。调解后,厂方答允工人部分要求,如饭菜决定随即改善,年终赏金比照国营各厂履行,工人一律增加工资一成等。“至于要求发给士林布及恐慌金两项虽未予采纳,但工人已认为满意”。然而,1月13日,工人又复怠工,声称对于资方答允条件表示不满,“该厂工人代表王仲良肆言:如厂方对于前提之六项条件如不能完全接受,渠等可使沪西各工厂一律怠工,以为援助”。尽管罢工最终由陆京士出面解决,但申九工会新旧干部冲突持续恶化,1946年4月开始演变为大规模的武斗。4月11日上海市警察局普陀分局报告:“申新九厂工人内部分新旧两派,新派工人代表为石阿春等,系社会局专员范才骙所掌握,旧派工人代表为陈鳌郎、毛和林等,亦系社会局专员陆荫初所掌握,该两派代表各分门户,勾心斗角,近更摩擦激烈,时在厂外殴斗,昨日下午六时该厂两派代表复在厂内互施暴力,大打出手,并由厂方依照工厂法规处分,现新派代表已接受处分,惟旧派代表仍蕴蓄不平,复在厂内鼓动工人怠工,冀图恢复代表地位。”*《上海警察局普陀分局呈报市警局申九统益信和新生纱厂工人罢工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44-2-21。事后,双方经陆京士、范才骙、章祝三、陆荫初等多次协商,“决定王仲良等人写了悔过书,表示以后不再过问工会事务”*《王剑冲谈范才骙、章祝三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在陆京士压力之下,此次武斗虽以陆荫初领导的王仲良系工运干部退让宣告结束,但申九工会新旧二派的矛盾并未因此化解,反而为1948年“二二”工潮埋下了祸根。
根据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显示,上海各纺织厂工人内部,“男工十之七八都参加了青洪帮,拜有老头子”,各种类型的弟兄会更是层出不穷。王仲良虽因1946年申九工会新旧二派冲突被迫让步,不再干预工会事务,但其“主要地盘在布厂”*《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下),第746页。。男工大多聚集于布厂。申九布厂下设准备、整理、织布、保全四科,因工种分配的缘故,尤其是整理科几乎全部由男工组成。王仲良为东山再起,在布厂男工内部组织了一六二兄弟会。
恰逢申九工人对王剑冲控制的工会日趋不满,“认为王剑冲与资方勾结,并贪污工会会费”。王仲良组织的一六二兄弟会看到时机成熟,积极筹划,“试图制造更多的工人诉求,以便尽力夺取工会的领导权”。*“Labour report No.6: The labour situation in Shanghai”,February 9, 1948, FO371/69592, The National Archives, UK.为夺取工会领导权,王仲良提出了煤球配给问题,声称“厂方吞吃了工友的配给物品”,“别的厂家有配给煤球,我们九厂为什么没有?这当然是厂方所吞吃!”*季勉君:《申新九厂工潮经过》,《纺织周刊》1948年第9期。劳资双方围绕配给煤球发放所产生的争议,在王仲良一六二兄弟会的鼓动下,迅即向工潮演化。王剑冲上世纪80年代回忆时即认为,“1948年2月2日的大罢工的起因就是王仲良等不甘心失败,结合了162人结拜兄弟,由陆荫初派了□□□在内当老大,替陆荫初指导他们夺取工会领导权,这162人中分子复杂,有中统、三青团分子,也有中共地下党人(如毛和林、杨光明等)”*《王剑冲谈范才骙、章祝三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申九“二二”工潮除工会新旧二派之争的缘故,更掺杂着三青团与工人福利委员会的矛盾。中共地下党员杨光明曾明确指出申九工潮的部分原因,正是由于申九厂内的三青团干部“在伪工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也想乘机夺取领导地位”*《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1950年5月4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战后三青团上海支团不仅注重在学界发展势力,并将工人群体作为拓展目标。他们认为工潮之所以频发,主要缘于工人内部缺乏强有力组织,“一般工会之领导,似未能顾及工人整个生活,诸如补习教育、休闲活动,以及团体生活之适应,均须通过更严密之组织关系加以指导。半年来本市工潮之空前紧张,是一反证”。因此,三青团决定“为求改善工人生活、共谋社会福利,结集工人力量、贡献国家建设,计划设立工人分团”。*《三青团上海支团部组织组工作报告备忘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29-1-1。1946年吴绍澍被免去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后,仍担任三青团上海支团的干事长。他更注重三青团向工界渗透,指定“陈公达、何锡玲、范锡品等专事组织工厂分团职业分团”*《上海市政府关于工人运动等问题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7-56。。三青团对工人运动的介入,“打乱了吴开先、陆京士在反动工运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双方争权夺利的冲突不断发生,至1947年夏甚至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范锡品:《上海舞潮案亲历记》,中国政协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3页。。
三青团通过同乡观念、帮会组织等传统形式吸纳工人,甚或煽动工潮迫使资方提高工人待遇,进而获得工人支持。沪西区工人团务由何锡玲负责,“何锡玲就住在三区机器业工会中,先在该会发展团员,再向外发展”。据王剑冲回忆,“王伯椿是分队长,申新九厂杠棒间工人,杨长富、杨光明等都参加,发展了很多人,这是以同乡关系来发展的,王、杨都是安庆人,杠棒工人极大多数是安庆人,这个组织成立后在国民党内党团矛盾中起了很大作用”*《王剑冲谈解放前国民党在沪西各种特务组织情况》(1982年7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1947年9月,国民党宣布实施党团合并,但此举“不但没有达到消灭派系纷争的目的,相反导致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和斗争的尖锐化。全国范围如此,上海亦如此”*姜梦麟、毛子佩:《抗战胜利后上海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国政协上海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84页。。三青团上海支团仍旧自成体系,如1947年11月3日,三青团派人到沪东纱厂发展团员,宣称“国民党老大了,没有用了,今后一切责任应该由我们去担任起来”,并告知工人党团合并“是没有的事”*《派员进入各工厂拉工人入团》,《立报》1947年11月4日。。申九工潮爆发后,何锡龄辩称“自去年中央决定党团统一组织以后,即行遵令停止一切团务活动,听后进行合并”,“再则该厂工人共有七千余人而团员仅一分队,共为十五人,且早已受党工领导”,*《关于申新九厂二二罢工问题与社会局等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7-49。但事实上,在上海市政府拟定的包含78人的《申新九厂工潮主要分子名单》中,三青团团员毛和林、徐富民、杨长敏、杨光明等六人名列其中,杨光明更是罢工工人总代表。申九惨案发生后,三青团工运组织的成员多有愤怒之情,三青团主办的《正言报》亦在报道中流露出对申九资方和工会的不满与嘲讽,称申九“一切都似重症后的病人。唯有职员俱乐部大厦管理处、庶务处,以及大门口的产业工会,还是如先前那样灯火通明,布置的很是整齐,四菜一汤的端进去”*《劫后申新巡礼》,《正言报》1948年2月4日。。
申九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对申新工潮背后所隐现的国民党派系纠葛,并非毫不知悉,但却讳疾忌医,认为“甚至有人信以为真,殊可怪也”*蒋介石日记(1948年2月3日)。。国民党派系斗争不仅困扰其高层政治运作,更深入党国体制肌理,以不同形式呈现于基层政治,对其统治秩序造成极大破坏,申九工潮可谓最生动的说明。正如上海市警察局的分析所言,“上海历次工潮均与领导工会及争取领导权者,有甚微妙之关系”,“平时在上海工人中有关系者均在勾心斗角,而工厂工会又多处置失当”,“故只须遇到机会,工潮、学潮良无已时”*《上海申新纺织厂二二斗争被捕名单及报纸登出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28。。
三、中共的城市革命
1946年4月,中共中央就上海工运对敌斗争发出指示,“须研究了解K每一派别之背景活动姿态、方式、力量及其内部之矛盾”;“必须打进它内部去,上层分子亦可必要时加入K”,“无论如何要做到迷惑K,以各种不同面目、姿态出现,在战略上并可应用游击战术,闪避主力”*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65—367页。。据此,上海中共地下党强调,“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努力渗透进入国民党的工运组织,“凡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去活动,利用当时一切合法的可能去进行非法的活动”*毛齐华:《略谈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工运史研究组编:《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据1948年2月美国上海领事馆的情报分析,“工人群体中,中共已经在百货业、公用事业、纺织和烟草业获得了稳定的力量”,“30%的上海工人或被中共所主导、或有高度的怀疑是受中共的影响而完全的反对国民党”*“The Consul General Shanghai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4, FRUS 1948 Volume VII, The Far East: China, p.92.。
就纺织业而言,即便到1948年10月,中共自称“假使把一年的得失对比一下,那么损失是大的,得到的很少”,但中共力量仍旧不容忽视,“领导着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力量”*《最近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1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中共在申九纱厂长期经营,积极向国民党工会内部渗透,“基本上掌握了工会的领导权,十七个工会理监事及候补理监事中,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八人,中间偏左一人”*《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746页。, “到1947年底,厂里已有三十名党员,建立了甲班、乙班和男工三个支部,形成了一支有一定群众基础和战斗力的队伍”*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工运史编写组:《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尽管“申九党组织人员新,斗争经验不足,但党员和工会干部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毛和林、许泉福和杨光明还打入了162弟兄会”*上海二十二厂厂史编写组:《申九“二·二”斗争》,上海纺织工运史编写组:《上海纺织工运史资料》第1辑,第50页。。而毛和林、杨光明不仅是王仲良一六二兄弟会的成员,更是三青团的团员。
中共以部分党员加入一六二兄弟会的方式,在男工中发挥着较大影响力。但申九女工人数超过6000,如何有效动员女工呢?上海市社会局认为:“本次罢工工人大部分为女工所操纵,该厂有夜校一所,大部分女工均就读该校,该校系女青年会所操纵,与民盟确属有关。”*《上海申新纺织厂二二斗争被捕名单及报纸登出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28。实际上,民盟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活动的。申九工人夜校全称申九劳工补习夜校,教职员16人,共分两级,第一级为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第二级为初中一二年级程度之补习班兼授纺织知识。1948年1月各级学生共有509人,每周授课6小时,夜校教职员除少数聘自厂外,多数为本厂人员兼任,并且该校学费全免*《申新九厂福利概况》(1948年2月),上海社科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卷号20-004。。申九工人夜校自1946年开办之后,共产党员唐孝纯和沃贤清先后担任夜校教务主任,并聘请民主人士俞庆棠为夜校顾问。中共要求唐孝纯“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办好申九工人夜校,以此进行进步思想的宣传,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提高学生的觉悟和文化水平,掩护工厂地下党同志,帮助进步师生在夜校开展党的工作”。*唐孝纯:《申新九厂工人夜校的开办》,《上海纺织工运史资料》第6辑,第24—25页。
确如上海市社会局所言,“当时在很多工厂的斗争中,夜校的学生往往是骨干与积极分子,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明显”,申九“二二”工潮“夜校学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前上海的工人夜校工作》,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D1-1-1884。。夜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有计划的招生,“尽可能的吸收预定的工厂的工人和预定的培养对象入学”;第二,通过教学及各种文娱活动,对学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从而启发工人意识到工人阶级在反动统治下的悲惨地位;第三,动员学生积极参加本厂的各项斗争和社会上的群众运动;第四,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的组织来教育培养和组织积极分子,其中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拜兄弟或拜姐妹,“这种组织最初往往是由学生中的骨干团结较好的学生组成,结拜以后,由于经常往来,感情密切,彼此有了了解,心腹话就好谈了”*《解放前上海的工人夜校工作》,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D1-1-1884。。戚怀琼1946年进入申九做办事员,后来又做夜校教师,“这样戚通过夜校等阵地,在厂里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一个总支,纱厂布厂各设有支部”*《周小鼎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10月31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权试图通过压制资方、满足工人部分利益诉求,换取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共认为,国民党此举正为其城市革命提供难得机会,“因而就来一个顺水推舟的做法”,通过掀起经济斗争,一方面让工人获得生活的些微改善,一方面逼国民党把这种做法继续下去,“国民党原以为吐出一点,可以缓和一下,那晓得前口气还未喘过来,还要吐出另一份来。这样就使国民党用来做防御的改良主义失掉了效力”,“迫使敌人高筑债台,最后逼使敌人死在这债台下”。中共反复强调,经济斗争“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是最实际的办法”。*刘长胜:《论蒋管区职工运动新动向》(1948年2月1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1953年第3辑,第54—55页。
当1947年全国各类反政府学潮此起彼伏时,工人运动未对学潮形成有力配合。中共上海工委认为,“富通事件以后工人情绪都打消了,比较低落了”,现在“考虑要放手发动群众,使工人运动跟上去”*《张祺谈话记录》(1980年4月),转引自郑庆声:《1948年上海申新九厂大罢工真相》,《世纪》2004年第1期。。因此,随着1947年棉纺业黄金时代走向终结,资方和国民政府被迫降低工人年奖数额,中共即试图重新点燃工人的革命激情,“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可以与上海学生正在进行的救饥救寒斗争相呼应,改变富通事件后工人运动一度比较沉寂的局面,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故而,当1947年12月18日“棉纺业同业公会向全市各厂和外埠大型厂发出通知:本年度工人年赏……按照上年旧例以八折计算,发给奖金分两期,引起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时,中共上海工委“决定提出年奖不打折扣,按当月生活费指数发放的口号,发动全市棉纺业工人进行反击”,“由申九带头罢工,反对年奖打折扣和分两期发放,其他棉纺厂积极响应”。*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226—227页。
1948年1月17日和24日,中共沪西民纱工委先后召集男工支部、女工支部开会,进行罢工动员,要求1月底之前发动罢工。在召开男工党员支部会议时,“毛和林有些顾虑,也有道理,主要是怕失败,怕镇压,这是中年人的思想;青年人有青年人的想法,没有顾虑,许泉福同意搞”*《周小鼎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10月31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最终沪西民纱工委“指定徐毓秀与上级联络,罢工后由杨光明利用合法身份公开出面领导,在党内由许泉福负责指挥,毛和林担任二线”*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工运史编写组:《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无论是公开领导罢工的杨光明抑或负责党内指挥的许泉福、毛和林,均为王仲良一六二兄弟会成员。中共明确指示罢工“要利用162弟兄会的势力,以及他们同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同资方之间的矛盾,必要时可以让王仲良出面”*上海第二十二棉纺织厂工运史编写组:《申九二·二斗争》,《上海工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2期。。国民党在申新九厂的派系纷争,不仅使得工会“会务已临停顿状态”*《申新九厂工会理监事及代表会员名册、运转工作法则》,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6-417。,更为中共城市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机遇。中共“这时一方面在工人群众中酝酿罢工,一方面挑拨与利用他们之内部矛盾来进行斗争”*《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1950年5月4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最终,以国民党派系斗争掀起之罢工,外界观察到工潮领导分子自然是王仲良的一六二兄弟会,无怪乎警察局感叹“每次工潮均谓系奸匪发动,而被捕获人犯后甚难取具实证”*《上海申新纺织厂二二斗争被捕名单及报纸登出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28。。
申九罢工发动之前,中共特别制定如下斗争方针:(1)虽然在原伪工会(王剑冲领导的工会)中,我们也有一部分同志,但在斗争中要推翻伪工会,另行组织新工会,以另外一个我们能掌握的走狗(王仲良的一六二兄弟会)来代替原有的反动分子(王剑冲领导的工会),来达到我们完全控制这个工会;(2)坚持罢工,等待其他兄弟工厂之支援;(3)万一国民党、三青团内部打起来,我们要利用大的打击小的,利用他们内部矛盾来削弱他们自己;(4)发动罢工时,因王剑冲主要地盘在保全部,王仲良主要地盘在布厂,故而中共上海工委决定将铜匠间、布机间作为主要力量,万一反动派(国民党政权)逮捕工人,布厂作为后备力量。对于敌人可能的镇压,则不要恐惧而坚决英勇的斗争。*《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下),第746页;《上海职工斗争情况简单介绍(从抗日时期到上海解放,1937—1949年)》(1950年5月4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1948年1月28日,地下党员毛和林就煤球发放问题有意识地在布厂车弄旁,当着很多工人的面责问布厂主任陶宗唐,“女工们很关心这个问题,纷纷围上去探听消息,于是许多布机都停了下来”,“这样就形成了一次试探性的关车”*上海二十二厂厂史编写组:《申九“二·二”斗争》,《上海纺织工运史资料》第1辑,第50页。。最终,上海工委决定罢工自1月30日12时30分由修理部突然开始,具体由杨光明指挥铜匠间首先关车;*《申九厂长吴士槐呈吴国桢的呈文》(1948年2月2日),上海社科院中国企业史资料中心藏,卷号20-004。随后“铜厂内杠棒间工人及铜匠间工人来到打包间,主使停止工作”;细纱间工人“正在工作时,有本厂内不相识之工人十数人进来将车关停,并不准工作”;女工面对关车时,采取了“别人都不做,我也不能做”或者“我们看他们停止了,我们亦停止”的态度*《上海市警察局江宁分局第二股关于申新九厂工潮被捕工人审讯笔录和关押人名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43-2-401。。至12时45分,全厂停车,申九罢工由此展开。
四、余 论
1948年1月30日,申新九厂7000工人宣布全面罢工,并向资方提出政府配给煤球、米、糖,没有发的要照发;年奖六成照1947年12月份的生活指数发,四成照1948年1月份的生活指数发等七项复工条件*《茂新、福新、申新系统荣家企业史料》(下),第747页。。若揆诸工人所提各项复工条件,似乎罢工更多缘于申九工人争取各项经济诉求的实现,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诉求背后所隐含的国民党派系纠葛与中共城市革命,同样是工潮发生的必要条件。通过对申九工潮起因多重面相的呈现,亦可窥知战后上海工人运动所具有的复杂性与挑战。
首先,就申九“二二”工潮而言,工人经济诉求、国民党派系纠葛与中共城市革命三者缺一不可。若仅重视经济诉求的作用,就难以解释待遇较有保障的申新九厂因何爆发大规模罢工这一吊诡现象。即便就经济诉求而言,学界过往研究往往重在强调工人遭遇的资方压迫及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忽略了国民政府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渗透及其对劳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战后国民政府为防止工潮,通过生活费指数制度的全面实施,逐步实现了对劳工薪资计算方法、生活物品选购的操控,政府权力开始全面介入劳资争议。资方对工人的各项经济诉求,可以转圜的余地极为有限,如申九工人要求及早发放煤球等配给物品,但煤球由政府统一拨配,申九“人数太多,每人一担,需六千多担,我们一个厂的配量,要抵十多个小厂,所以小厂便占了先”,资方“为了此事,奔走交涉”,社会局则行敷衍应付之事,告知厂方“煤球绝不会少,仅是时间问题”*季勉君:《申新九厂工潮经过》,《纺织周刊》1948年第9期。。工人在焦急等待中最终选择罢工。
其次,中共对战后上海工人运动确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甚或在一定程度上领导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及走向,然而包含申九工潮在内的上海三大风潮并非中共有计划策动的系列运动。学潮、舞潮、工潮三大风潮的接连爆发,更多是时间的巧合。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张祺承认,“在这场斗争中,当时工委与其他各委互相间并没通气,‘三潮并发’不是有计划的统一行动”*张祺:《上海工运纪事》,第231页。。实际上舞潮案更多是国民党党团矛盾的结果,“青年团藉禁舞声中争取群众,极力主持工会,并利用种种方法暗中鼓动。舞业从业员中,青年团团员甚多,如百乐门领班唐宗杰等均系范锡品之门徒”,*《上海市社会局关于上海舞业从业人员捣毁该局及范锡品在舞场之门徒名单》,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6-32-24。中共对舞女风潮的影响极为有限。中共上海工委的斗争策略极为理性,重在巧妙利用国民党内部不断恶化的派系纠葛,因势利导,发动罢工,甚或促使罢工向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转化。1948年10月,中共在总结上海工运斗争经验时,就特别强调“过去一年的斗争也是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下发展起来的,曾经利用了敌人矛盾击破敌人的压制,也利用了敌人的矛盾击退敌人的反攻,更利用了敌人的矛盾助长了斗争的声势”,“在运用敌人矛盾中不管某些人有任何的阴谋与欺骗作用,只要成为真正群众运动时,果实是属于我们的”*《总结报告》(1948年10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
此外,裴宜理提出上海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8页。。若观察申九工潮,裴宜理之结论有待商榷,申九工人在工潮中已经克服地域局限与技术隔膜,开始采取一致的抗议活动。申九工潮68名罢工领导者,来自皮棍间2人、精保间4人、粗保间5人、细保间16人、整理部9人、打线间4人、试验科1人、燃保间3人、精梳科2人、摇纱间1人、细纱间5人、腾纱间2人、杠棒间2人、铜管间2人、布厂4人、打包间3人等*《关于申新九厂二二罢工问题与社会局等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7-49。。罢工过程中工人打破技术差别的限制,开始趋于同一性。同样,被上海当局起诉的38名申九工潮领导者,属于苏南籍的工人19人,苏北12人、浙江2人、上海1人、广东1人、湖北2人*《上海申新纺织厂二二斗争被捕名单及报纸登出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93-4-28。,不同地域的工人亦采取统一的抗议行动,超越了地域的局限。若从性别的角度而言,虽然女工已成为罢工的重要参与者,但主导力量仍是包含中共地下党员、王仲良系及三青团工会干部的一六二兄弟会,并非韩起澜所言罢工主要是妇女领导的,更未有上海舞女支持申九女工之说*〔美〕艾米莉·洪尼格著,韩慈译:《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女工,1919—1949》, 第227—231页。,反抗政治更多与男性紧密相连。概而言之,申九工潮超越了技术差别与地域局限。当然,这种超越也是有限度的,当时工人在多种党派政治力量渗透影响下,因政治观念及组织的差异而难以实现统合,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当时中共亦承认“上海职工组织,也还存在着许多缺点,需要继续来克服,比如: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少的职工尚在组织之外,某些职工政治上、思想上还未能作应有的提高;有些工会内部生活不民主,因而不能发挥群众力量;职工队伍中工贼走狗的活动,尚未争取他自觉或肃清出去;同时自己内部团结不够,还发生脚碰脚的打架”*《论上海的工会组织》(1947年5月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D2-0-817-36。。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组织和思想的整合,待至1949年上海解放后,方得以逐步实现。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 汪文庆)
Revolution, Factionalism and Shanghai Strike: Study on the Cause of Shenjiu “February Second” Strike in 1948
He Jiangfeng
Shenjiu “February Second” Strike in 1948 was the result of the triple factors of workers’economic demands, factionalism of the KMT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of the CPC, which superimposed on and affected each other. The strike was first due to the workers’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factory delay to release rationing goods, and then the product of the struggle for leadership between old and new cadres of Shenjiu worker’s union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Youth League of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and Workers’Welfare Committee. Simultaneously, the CPC appeared as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identity, made full use of the KMT factions struggle to launch the urban revolution, and set off the city’s annual prize fight through Shenjiu strik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Shenjiu strike tide causes, the complexity and challenges of Shanghai workers movemen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can be known.
*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共内战时期民众运动研究(1945—1949)”(15CZS040)的阶段性成果。
D231;K266.9
A
1003-3815(2015)-07-00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