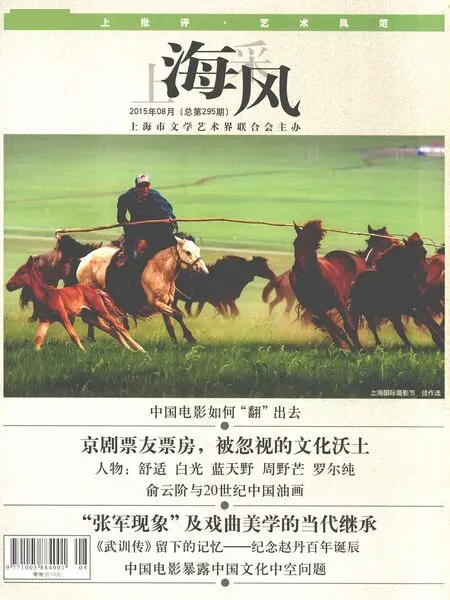周野芒:演员应该演“活生生”的人
2015-03-03曾钇榕
文/曾钇榕
周野芒:演员应该演“活生生”的人
文/曾钇榕
于娜被雷带进了一间杂乱的办公室,然后两人开始谈话,但显然气氛并不对,两人说得有些语无伦次,呼吸急促,而雷显然更加拘谨,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充满戒备……
当“雷”走下独幕话剧《黑鸟》舞台,换下白色长袖衬衣、条纹领带、黑色西裤、皮鞋,换上休闲T恤、中裤、凉拖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国家一级演员“周野芒”又出现了,拘束而不自然的肢体动作忽然变得洒脱而自如,紧张而低沉的声音忽然变得爽朗而有些高亢,而刚才的“雷”的怯懦、惶恐更是一扫而光,整个形象硬朗起来,嘴唇上方、下巴处一排胡子让他的脸显得更有棱角;颇有光泽的头顶以及不时挂在嘴边的自嘲的笑,让他颇有几分“痞气”。
如此快速得”变身“,不由让人暗暗惊讶,不过熟悉周野芒的观众都知道,他是个”千面人“。几个月前,我看了话剧《老大》,周野芒饰演的执拗的、对大海充满感情的船老大形象让我印象深刻;待到看话剧《长恨歌》时,竟一时没有认出性格软弱、身不由己的康明逊也是周野芒扮演的。再看银屏,从早期老版《水浒传》中生性耿直的豹子头林冲,到新版《红楼梦》中禀性恬淡、优哉游哉的甄士隐,再到去年播出的《我心灿烂》中懦弱敏感、欺软怕硬的叶文祥,形象实在多变。
戏中的周野芒非常投入,悲伤或激动时,经常热泪盈眶;而接受我的专访时,周野芒也很投入,思维活跃,谈起来滔滔不绝,他的手不时比划着,表情不时配合着做一下示范,使得恰巧路过的上海话剧中心艺术总监吕凉忍不住笑着“提醒”我:“不要被他吓到了,他聊戏时就是这样。”
演员的一生都在准备
如今作为“上话”的资深演员,周野芒是制作人争抢的香饽饽,但他坦言,刚从上戏表演系毕业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时,他并不受待见。剧院里的资深演员太多了,哪轮到上初出茅庐的青年。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年轻演员就有了混日子的心态。但是,周野芒并不甘心,对自己又有要求。那该怎么办?“我是热爱戏剧的,我就时刻准备着,我就不信一个机会都没有,但凡有合适的时机,可能就会发光。”
为何周野芒有这样平和的心态?这跟他父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周野芒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上海人艺的演员。在周野芒三个月大时,就被演出繁忙的父母放在了后台,哭了,就这个叔叔哄哄,那个阿姨抱抱。
“我从小在剧院长大,看他们排戏演出。那时一个戏,一个角色要安排三到四人演,分ABCD组,至少两组,一是为了培养年轻人,二是当时剧目非常多,忙不过来。有时导演对A组的人不满意,就让B组的人上。我妈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她是B组的,只是在旁边跟着学,一直轮不到上台排练、走台。都快演出了,A组的人状态还是不好,导演就对我妈说,‘你上去走一遍,我看看’。结果,台词全拿下来了,调度、地位清清楚楚,人物感觉又好,导演就说,‘好,明天首演你演’。立刻把A组的人换了。当时我六七岁,在旁边都看傻了。作为B组,很可能排了两三个月,根本没机会上舞台,但是我妈就有这样的自觉性,在家里还跟我父亲一起背台词,排戏。”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周野芒也像父母一样,时刻准备着。他经常去健身房锻炼,一练一个下午,练出了比较完美的体型,终于引起了一个香港导演的注意,让他演一个重要角色。不过周野芒没高兴多久就发现,原来是让他演话剧《马》中的马,没有台词,只有简单的小小的舞步,观众是看不见脸的。周野芒把剧本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加强了对戏的理解。有一场戏,男孩子跟马有一段对话,周野芒演的马轻微地摆了摆头,用马蹄搭了他一下,形态很鲜活。因为投入了真情,即便假扮的马都是有生命的。演完后,导演激动地对他说,“野芒,我真的很感谢你,所有的演员中,你是进步最大的。”
“我不会因为观众看不见我的脸而瞎对付,而领悟是把自己投入进去。演戏的时候是要安静的,把所有的杂念排除掉,沉浸下来,找里面最细微的感觉,再一点点释放出来,这是很有味道的。这也是为何西方观众看戏像看小说一样,会上瘾。”
刚进剧院的五六年,周野芒一直在跑龙套,却也跑得乐此不疲。“我认为不管怎样的戏,归根到底就是塑造人物,哪怕人物上台只有两秒钟,给观众留下印象了,就成功了。”周野芒还发现了跑龙套的好处,“2个月时间,主演只能演一个角色,而跑龙套就可能演5个角色,我就得到了更多锻炼机会。”
1987年,剧院要排话剧《中国梦》,当时定的主演因为在外面排戏来不了了,换了一个演员,导演不满意,这时有人提议找周野芒试试。一试,周野芒获得了主演的机会。不过,挑战也不小,一个人要表现五个人。“之前我都没演过主要角色,但我演过各种类型的普通角色,这个戏里面我就发挥了平时我在演龙套时候的感受,我不把他看成主要角色,而是踏踏实实一个个人物演。我可以一瞬间从一个人物换到另一个人物,大家就服了。”后来,周野芒凭《中国梦》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所以青年演员跑龙套不要怨,这是你的机会,这是非常好的准备的机会。演员永远要准备,演员的一生都在准备。”周野芒总结道。
上世纪80年代末,有部中外合拍电影《花轿泪》在找演员,姜文、秦怡等已确定主演,还缺个角色,全程台词都是英语。这对很多演员来说,颇有难度,剧组一时找不到人。这时有人说,上海人艺有个演员叫周野芒,听说他在自学英语,找来试试?那时,周野芒的英语还说得磕磕碰碰,但毕竟有基础,剧组觉得可以,马上与他签了约。“薪酬好几千啊,高兴死了,那时剧院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这个戏拍完7年以后,我在加拿大时,有人跑来跟我鞠躬,并对我说,‘你是电影明星’,我忙说,‘我不是,你搞错了’。‘是的,我刚看过你演的电影’。”
喜欢自由的周野芒外表看起来很随性,有时甚至有些吊儿郎当,但排戏时,他绝对是严肃而较真的。接了一个外国戏,他会把英文本子找来,对照着看,他觉得,虽然翻译家翻译的是准确的,但也许不太清楚时下的思考和交流,或者不一定适合口语,可能对观众的理解造成一定障碍。此外,拿到剧本后,他还要看全部的人物,思考人物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戏告诉观众的是某个瞬间、某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时间段前后的事情,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要通过演员准确的表演告诉观众。”
除了在舞台上积累经验,周野芒还非常注重文学素养、文化素养的准备。“我们这代人在最需要读书、最需要打根基的时候,碰到了‘文革’,十年没读书,全部荒废掉了,等于是个文盲。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后,我看了大量小说,也看了很多哲理类、艺术类、人文类,包括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书。毕业后进了人艺,看书的劲头也一直延续了下来。”周野芒感叹道,“现在大部分的年轻人一碰到问题,马上上网查,查完就忘了。OK,网络是个好东西,但不要有依赖性。从事艺术的人最要紧的是自由,倒不是行为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有了思想的自由,灵魂才能打开。”
流淌在血液里的是对戏剧的热爱而不是金钱
周野芒有记忆的时候,舞台就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小时候,周野芒并没有想到当演员,他想要当的是司机,那时候车不多,他就觉得司机太了不起了。这个念头一直保留到十五六岁。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演员这个行当不被人看好,没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周野芒的父母告诫他,千万不要当演员。于是,周野芒去当了工人,一周三班倒,身体严重透支,他就一直盘算着如何脱离这个“苦海”。“文革”快结束时,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成立了个话剧队,周野芒瞒着父母偷偷跑去报名。因为普通话很标准,被顺利录取了。周野芒就乐颠颠地跑去跟厂领导请假,说去参加市工人文化宫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厂领导觉得这可是件光荣的事,欣然应允,由此周野芒逃离了三班倒的苦闷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招生了,趁着父母去外地巡回演出,周野芒跟市文化宫的队友一起去应考。“招生的老师觉得我有些舞台经验,不错,但好像形象不太好,后来一想,‘反正这一类型也需要’,就把我招进去了。”周野芒带着调侃的口味回忆道,“从此我就知道我演不了英雄了。我父母都长得很漂亮,演的大都是正面人物,可是不知怎的我没有遗传到他们外貌上的优点。那时,在学院,很帅的角色都没我的份,我经常演那些灰色的、有弱点的人物,比如《雷雨》里的周萍,《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奥赛罗》里演引诱奥赛罗去犯错的伊阿古等,毕业后,刚进上海人艺的一段时间,我往往是个‘边角料’,演个土匪啊,挨打的人什么的。”
初当演员时,周野芒希望形象好,画眼线、画眼影,把眉毛画得很粗,但都无济于事,那些“英雄”角色总轮不上他,于是他干脆安心地钻研起 “灰色人物”。之后他慢慢领悟到,一个演员如果永远只想演正面人物的话,就会束缚住自己。“所谓正面人物,往往是领导或作家,把人拎到一定高度,把他树立成道德的楷模,没有瑕疵。但生活中的人是会犯错误的,错误大到一定极限就是罪恶,小的错误即小小的缺点,演员应该演这样的人。好剧本中的人物,好人也好,坏人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情力量。真正的痛苦点总是埋在人们心底的,我们做戏就要把这个点挖掘出来,展示给大家。”
在周野芒眼中,演戏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到心里,这个过程让他感到兴奋与刺激。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越来越了解人性的复杂与真实。在他看来,《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是浮士德人性中的另一面。因此,周野芒在演《浮士德》中的魔鬼时,没有刻意去演一个坏人,没有演得张牙舞爪。“其实他还是一个人,只是这个人有七情六欲,这些欲望会超强地压住那些道德的、法规的或者伦理的东西,他经常走一些不受管束的路。所以我演魔鬼的时候,只是把人的恶的一面、欲望的一面演出来了。”周野芒也凭借魔鬼一角获得第十九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配角奖,并获2010年全国戏剧文化奖话剧金狮奖优秀表演奖。
周野芒挑选角色,并不考虑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他在意的是:演的是否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的开放观念让他的戏路越来越宽,创作方法越来越多,也让他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角色。
1996年,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导演张绍林邀请周野芒饰演林冲。当时很多人不认可,出品方中央台里不少人也都质疑,连周野芒自身也不太自信。但张绍林有信心,之前在一部戏中他请周野芒配过音,觉得这个演员懂戏。当时周野芒一点武功都不会,但导演觉得“要看的不是他的功夫,是他内在的感觉”,在据理力争之下,最终说服了大家。周野芒也不负所望,演绎了一个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林冲”。
无论是话剧还是影视剧,周野芒演过非常多的人物,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他如何在表演时防止千人一面呢?“首先要抓住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人物是有自身节奏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很多人印象中林冲是绿林好汉,会拔刀相助。概念!林冲是个懦弱的人,善于听从命运,是官僚体制下的儒将,没有旧时代草莽的气息,应变能力很差,他的结局是性格悲剧。《老大》中的渔民,很倔,因为一次失误背上了‘十字架’,一生都在为此付出,执拗,坚定。”周野芒解释道,边说边示范了起来,“那么,性格是通过台词、说话节奏以及人物的外貌、外部动作表现出来的,比如《万尼亚舅舅》中的医生,很潇洒,很自由,有想法,说话没有遮拦,拿得起放得下,他的外表、动作就很随意。《黑鸟》中的‘雷’因为有虐童的前科,出狱后是隐姓埋名过来的,所以胆小谨慎,我演这个人物时就不太动。而《长恨歌》中的康明逊,也胆小,想表达又不敢表达,但这个人压力没有‘雷’那么大,所以有些捣糨糊的态度,但他心底是喜欢王琦瑶的,所以表情是真诚的。”
有的演员形象很好,之后就“躺”在自己形象上;有的演员有些小聪明,一个好戏撞巧让他红了,他就认为这是他的才华了,不再努力。而周野芒不同,永远在准备,永远在感悟。有空闲时,他就去旅游,去伦敦、纽约看戏,看国外的戏剧潮流,研究人家的表演方式,再反观自己的表演方式。周野芒的太太王之夏是知名影视演员,开平时也会跟周野芒交流,看完戏后会提出不少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了对这个职业的尊重感、敬畏感,你可能就会跟别人不一样。流淌在血液里的是你对戏剧的热爱,而不是金钱。”周野芒说道。也正是这份热爱,使得他本人以及他塑造的角色带有一种野性而蓬勃的生命力。
记者:已经演过那么多戏了,最近出演《黑鸟》,对你而言还有什么难度吗?
周野芒:由于剧本结构的关系,演这个戏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以前的角色都是有逻辑的,台词是有逻辑的,行为也有逻辑,内心坚持也是有逻辑贯穿的。但《黑鸟》不同,你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有一大段时间是不一致的,说的具体的内容和背后的欲望是不一样的。作为演员,要找内在的联系,这是要花点时间的。说一句良心话,《黑鸟》是我从艺到现在,演得最过瘾的一个角色,没有之一。
记者:为何是“最过瘾”的?
周野芒:男主角“雷”这个人物表面和外在的反差是那样大,人物的隐藏性是那样的强烈,所以演起来特别过瘾。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制造很多的假象,但又不是凭空捏造的,是完全有依据可循的。善恶丑陋都集中这个角色身上,但是你不会立刻看到,只会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看到他的变化。两个人的戏,必须每分每秒给观众递出信息,让观众琢磨演员在干嘛,让观众看到我,并从我的感觉上看到她(女主角)。观众、她、我三者是互动的。有一段戏,女主角有18分钟的独白,我一句台词也没有,怎么填满这个时间,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千万不能游离,要找到适合这个角色的状态。
记者:很多观众是抱着娱乐的心态进剧场的,这类需要思考的戏,是否比较挑观众?
周野芒:这个戏就是挑观众的。长期以来,很多观众习惯于灌输性的戏。但这个戏,是需要观众去思考的,看见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因此观众看的时候,可能会游离一下,想想背后的东西。比如戏中,雷对于娜说,我真的是喜欢过你,是唯一一个,再也没有了。但结尾,啪,一个小女孩出现,戏中并没有说明雷是否喜欢这个小女孩,只是说在照顾她和她的母亲,可是观众会有疑点,因为他有前科。这个剧本真好,是开放式的。
记者:一些观众认为,《黑鸟》中的人物灰暗,破坏了他们心中美好的想象。你为何愿意演那些负能量的角色?为何愿意倾力演绎人性之恶?
周野芒:人性是不完美的,人的恶和丑陋是天生的,之所以跟畜类有区别,是因为接受了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给人看完美的一面,如果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丑陋的,一直封闭着,一旦有一个机会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丑恶的东西就先出来了,人们可能就架不住了。因此我们要提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样是因为有昨天那样,或者说,我们当下这样是因为有前后左右出现的那样。所以我很乐意阐释丑陋给人看,告诉大家这是客观存在。演员要善于解剖自己,要善于把内心打开来,让人去了解。戏剧的宗旨是给人思考的,我们要把在创造人物过程中的思考、获得的感触,结合于角色,传达给观众。
记者:用戏剧来剖析人性之恶,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周野芒:法律是控制人的,文艺是熏陶人的。戏剧给大众提供的是一种养料。一些真理,用戏剧的理解方式来传颂的话,用一些辩证的手段来传颂的话,说不定说服力更强一些,戏剧是一种说服力。
记者:你怎么看待现在国内舞台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肢体剧?
周野芒:肢体性很强的戏,倒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挑战。更换表现手段能吸引观众,但是注意要合理,不能脱离演员基本的情感传达、感受,否则会让人觉得突兀、哗众取宠,在卖弄肌肉。我在国外看过一些肢体剧,非常震撼,用得恰到好处,为何这样,说得出道理来。以前国内话剧里就有很多肢体的部分,但如今一些戏剧人觉得当时的就是土的,现在的才是牛的,或者认为国外的才是先进的。其实方法是一个方法,并非国外的东西就是新的,经过检验的。我们不信任自己的根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给人信任的可能性,就是你以为给人家最好的东西,但因为你造诣不够,给的东西使人大失所望,一批观众就觉得被欺骗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记者:演话剧之余,你也会接拍
一些影视剧,但不多,你是如何考虑的?
周野芒:演电视剧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点,而且挣得钱比话剧多,我不会排斥。前一阵,我在电视剧《少林涅槃》中饰演一个方丈。导演傅东育以演员表演为第一动力,善于挖掘演员内心,他经常跟演员谈戏、抠戏,用话剧的方式拍电视,周期很长,对演员来讲很有帮助。话剧演员遇到这样的导演是福气!但是电视剧的拍摄毕竟不可能达到像话剧排练那样一遍遍排练,演员与演员间、与导演间彻彻底底的朝夕沟通,所以作为创作来讲,比较过瘾的还是话剧。近些年有一些成熟的好的话剧剧本,这是比较难得的,拿到了以后就觉得很珍贵,我就希望好好去创作。
记者:结合你自己的从艺经历,对于后辈有些怎样的建议?
周野芒:端正态度,不要老想着出人头地,踏踏实实演戏,演你权且来说热爱的东西。今天这个社会不会让你饿死的。当时我们考进戏剧学院,第一节大课上,老师就教我们如何一门心思做演员。后来有了这阿片天地,可以好好演戏了,开心啊,至于获得名气啊,级别啊,钱啊,都没想过。但是现在有些家长、老师教小孩:长大当明星去哦,有粉丝。什么叫粉丝?当年也有追星族,《日出》上演时,观众就冲着白杨买票去的,她成为所谓的“星”,是用血汗一步步累积起来的。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一上来就说要做明星,在戏剧学院才念到大二大三,就跑出去拍影视剧了,说是实践,怎么不到舞台上来实践?好莱坞那么牛逼的演员,隔三差五还要回到伦敦西区演出,《纸牌屋》的主演凯文·史派西是话剧演员出身,演了多少话剧,才得了影帝。如今,一些明星也来演戏了,可惜演得非常烂,观众也觉得好,但那是艺术吗?那是一种现象,是风暴,但不是艺术。
记者:现在不少青年人一进剧团就能主演话剧了,机会比你们当时多得多吧?
周野芒:是的,现在有那么好的机会,那么多的剧本,当然有些剧本是成熟的,也有些是不成熟的,但我不认为“文革”之前的剧本个个都是成熟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在里面发挥一下作为演员的作用,想办法丰富它,帮助这个作品产生,这很锻炼人的。可惜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锻炼自己,喜欢谈吃谈喝,排练时还拿着手机,还在玩。你来干嘛的啊?让他们出出点子,没有点子,没有主人翁精神。开演之前,从来不摸戏,你跟他说,你的节奏不对再想想,他就觉得麻烦,这样就行啦。回顾老一辈的演员,他们有努力奋斗的目标,演员能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不停地沟通,而沟通是基于对这个事业共同的热爱。
记者:这其中的变化,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周野芒:“文革”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了盲目服从的习惯,产生了惰性,“文革”结束后,重新恢复了,但心态坏了,余毒一直到现在。有些年轻人选择话剧只是为了挂靠一个单位,留在上海,这是很势利很实际的,他们的方向目标并不明确。当然,有些年轻人是很认真演戏的,但为数不多就形成不了风气,没有艺术氛围,这是很可怕的。表面上风风火火,大家都在做戏,但为什么产生的尖子和有影响力的人少之又少,我觉得这是原因。那么多的演员上台,但真正压得住阵的还是老演员,焦晃、娄际成等,但他们年纪大了不上台了,牌子就没有了,怎么办?一年那么多戏,不能水一样淌过去了,底下还要有一块岿然不动的礁石,而这不仅需要演员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形成一个好的艺术氛围,就是好的习惯的蔚然成风,好的表演观的蔚然成风,很严肃地对待艺术表演,没有功利地对待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