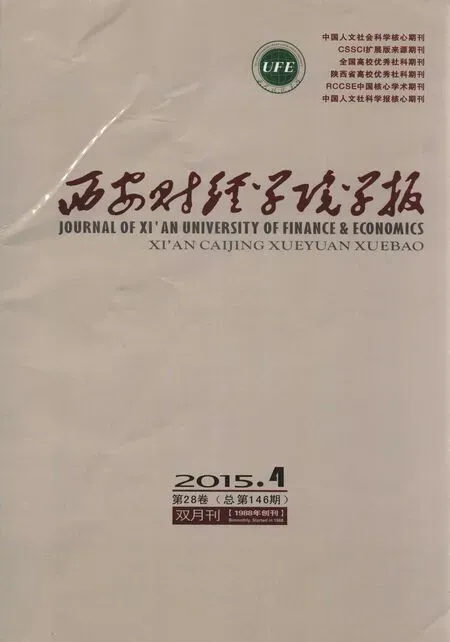陕北神木石峁遗址即“不周山”——对石峁遗址的若干考古文化学探想
2015-03-02胡义成曾文芳
胡义成,曾文芳,赵 东
(1.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2.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3.陕西省委党校,陕西 西安 710061)
继西安在泾渭两河汇合处惊现杨官寨遗址[1]后,近年陕北在考古方面也屡有惊人发现,其中神木县石峁遗址就令人震惊。
201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宣布,由来自各国的190位考古专家反复筛选,中国石峁遗址与浙江良渚遗址共同入选10项“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2]。此前,石峁已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内专家即用“石破天惊”形容它,因为它不见诸包括《史记》在内的任何文字记载[3],但却是“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2]。
学界有论者断其为“黄帝族裔遗址”,甚或其他。面对陕北这个出人预料的最大城址,笔者则猜想它即毛泽东主席诗句“不周山下红旗乱”之“不周山”,应加强识别。
石峁遗址相关发掘与研究都还只是开始。胡适先生曾讲过,历史研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故本文从考古文化研究层面对它展开了大胆猜想。借用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一句话,石峁遗址研究“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塌毁”[4]148,故本文从考古文化学出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也仅属抛砖引玉,借以活跃陕西近年在考古方面屡有惊人发现的研究和思考。
一、神木石峁遗址简介
(一)略况
石峁遗址位于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北距长城10公里,东离黄河20多公里。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及“马面”、“角楼”等组成。最早的“皇城台”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晚于被笔者视为“黄帝都邑”的西安杨官寨遗址千年左右);包围它的内城墙体残长2千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经碳14测定,遗址距今4000—4300年,寿命超过300年,在规模上大于西安杨官寨遗址,也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山西南部襄汾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等,故仅从规模上看,就很值得注目。
石峁遗址的文化特征,体现在它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石筑城”并出土了大量玉器。
(二)发现过程
遗址被发现,纯属偶然。其中玉器的大量出土,可上溯至20世纪20-30年代。当时出土的巨量精美玉器已大量散失海外,被大英博物馆、科隆远东博物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世界著名博物馆收藏,使“石峁玉器”声名远扬。在网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研究员估计,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专攻玉器研究的陕西元阳文化博物馆馆长高玉书先生还亲口告诉笔者,估计国外有遗址玉器两三千件,国内有两千多件,包括神木县私人收藏家胡文皋先生手中就可能有数百件。此外,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神木县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均有“石峁玉器”收藏。
在“石峁玉器”出名半个多世纪后,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戴应新教授从民间听到信息后,到神木石峁考察,才揭开了对它进行科学发掘的序幕。2006年,它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地区文物部门联合组队,发掘出埋在石峁石墙里的完整玉器,证明“石峁玉器”不虚,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被“正名”。对石峁玉器的年代断定已有龙山说、夏代说、商代说等不同观点。也有考古学家提出,石峁玉器极有可能是商代玉器的重要渊源之一。2012年10月,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博物馆的40余位考古专家经考察认定,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国内对石峁遗址的研究简况
石峁距司马迁家乡韩城并不远,同处黄河晋陕峡谷沿岸,《史记》开头就写了比石峁更早的黄帝时期,但对石峁不着一笔,匪夷所思。目前,国外和国内对石峁遗址的研究已经或正在展开,见解很多,争论难免。
(一)石峁玉器显示出中国特有的“玉文化”、“玉教信仰”及其中待破的史前奥秘
叶舒宪先生以石峁玉器为主据,提出中国古代存在“玉教信仰”和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分量重于“丝绸之路”的“西玉东输之路”[5]。此见颇新颖。如果它确立,其中会不会潜藏着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重大奥秘呢?
石峁所在的黄河河套地区,特别是银川附近的水洞沟一带,曾出土中国首个旧石器时代遗址,且其遗物显示出与欧洲旧石器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被视为欧洲旧石器文化传播的最东端。由此人们当然可以猜想,石峁出土的大量玉器,可能与史前陕北所在河套地区存在“西玉东输之路”甚或与“河套—欧洲通道”相关。联系宋耀良先生关于宁夏贺兰山及银川一带史前“人面岩画”的研究结论[6],以及宋先生关于沿中国东海岸和赤峰—银川一线传播的人面岩画后来还传到北美洲西海岸,并成为北美玛雅文明源自中国的证据的看法,同时鉴于银川一带这些岩画与石峁遗址均处黄河河套地区,该地区在考古上存在着史前“阿善—白泥窰子纵剖面”及“岱海遗址群”[7]166-167,已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史前文化类型,且其中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又是中国青铜文化之源[7]170。那么,石峁显示的“玉文化”和“西玉东输之路”甚或“河套—欧洲通道”,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如何?石峁遗址出土的玉石人头像和壁画,与银川一带人面岩画应有某种一致性,究竟两者关系如何?石峁是否展示着中国“西玉东输之路”甚或“河套—欧洲通道”上的一种溢出《史记》视野的“石筑文化”?笔者注意到,石峁玉器代表着的中国“玉教信仰”,当时在中国国内各地均有表现,不仅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玉器颇丰,而且在此前黄帝族从银川迁徙到关中途经的陇东崆峒山一带也出土了良渚式玉琮[8]。这就意味着石峁玉器代表着的中国“玉教信仰”与“炎黄文化”已现融合,那么,《史记》却为何对“玉教信仰”的石峁竟一无所记?
(二)关于石峁遗址的历史定位
《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发表的《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表明,相关知名专家对遗址现世均感震惊,学界也联想多多。
1.对中国史前研究着力较深的河北师大沈长云先生,根据石峁遗址建造时间(距今4300年左右)距黄帝时期(距今约5000年前[9])不远,不能把作为“氏族部落首领”的黄帝具体人格化,且从黄帝死后葬于石峁附近的陕北子长县一带(并非古今认可的“黄帝陵”所在地陕西黄陵县)为据,认为石峁即“黄帝部族居邑”[10]。陕西学者杨东晨先生也认为,石峁文化系陕北“黄帝裔支部落文化”[11]。
2.烟台大学学者陈民镇先生反驳沈长云先生之说,认为石峁古城体现的是与传统“华夏文化”不同的“面向草原”的文化板块,有“石筑传统”,应不是持“土筑传统”的黄帝部族居邑[12]。虽此文标题《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仍显出某种“虚古”情绪,但它敏感地抓住“石筑”与“土筑”之别,较能服人。事实上,正如《神木石峁遗址座谈会纪要》披露的内蒙古专家所说,石峁的“石筑”与河套的海生不浪文化和阿善文化一脉相承[13]54。循此也许可能解开《史记》对它难着一笔之谜,因为不仅司马迁和石峁时代相距的时间与我们和司马迁相距的时间几乎差不多,而且他对“石筑传统”及其文化也确不熟悉。看来,《史记》对石峁古城的“失语”,应是中国古代“黄帝文化区”对另外一种“史前文化区”的“失语”所致。
3.杨雪女士则注目石峁“石筑”与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英国巨石阵等“石筑文化”的联系,认为石峁是龙山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标本[14]。似乎国内目前考古研究界还没有人以如此“全球眼光”看待石峁遗址,但从张光直先生曾费力从全球视野考察“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甚至把法国古洞中的美术图式与之联系的范例来看[4]361,以如此“全球眼光”看待石峁遗址也值得提倡,没准它会有点见解创新。不过,此思路仍然使我们又不禁想起作为黄帝族最早文化标志的银川一带人面岩画,那与石峁一样也是一种“河套石筑物”啊!两者关系是什么?
4.陕西师大朱鸿教授除呼应“玉石之路”假说外,还认定处于山顶的石峁古城应值大禹将治的洪水期,别解其为尧时“幽都”,即“北方的政令重镇”[15],也颇新颖。其思路与本文较接近,均把石峁遗址指向夏初大禹治水,是有道理的。虽然他只提及当时洪水围山,大禹部族需在高山筑守,未觉察到石峁是大禹敌手共工的都邑,亦即大名鼎鼎的“不周山”。其实,王国维先生当年就把“不周山”直称为“幽都”,且明言“幽都”地在朔方河套(见下文对王国维《冬夜读〈山海经〉感赋》的分析)。由此看来,按王国维思路,朱教授石峁系“幽都”之见,已经接近石峁即“不周山”之解,惜未最终破之。
三、石峁遗址即“不周山”的若干证据
此前中国古籍关于“不周山及共工”的所有记录和注释,均是在该故事发生之后很久随着文字能记录历史才出现的。几乎所有“体制内”的记录者和注释者均不知道石峁遗址,故其中不仅存在不同学派对同一史实完全不同的记录,包括对故事发生地点说法各异,相去万里,而且在不同版本中还出现了共工的对手分别为黄帝儿子颛顼(《淮南子·天文训》)、高辛(贾逵)、女娲(《三皇本纪》)、火神祝融及神农等情况,误差巨大,包括郭沫若先生、徐旭生先生、田昌五先生等根据文献对共工部落地处今豫晋陕交界一带的理解也需存疑。目前,笔者只能在“神话留有‘史影’”的信念下,择善而从,并据考古成果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一)神话学证据
1.共工“幽都”神话
王国维《冬夜读〈山海经〉感赋》写道:“黄帝治涿鹿,共工处幽都。古来朔易地,中土同膏腴。如何君与民,仍世恣毒痡。帝降洪水一荡涤,千年刚卤地无肤。唐尧乃嗟咨,南就冀州居。所以禹任土,不及幽并区。”[16]中国史前神话中的共工是与大禹对抗,而王国维眼中的共工却与黄帝斗争,是黄帝压服己臣,降洪水淹“幽都”。他指明其斗争就发生在“朔易地”,即今河套、晋冀一带,“黄帝治涿鹿”对应着“易”,而“共工处幽都”对应着“朔”。笔者特别看重王国维从远古“九州”之“幽州”地望出发,对共工“幽都”在“朔”的地理定位,这与石峁遗址地处河套正好对应。而按《山海经》等记载,共工“幽都”就是“不周山”(见下述),故可推知河套里的石峁遗址即“不周山”。王国维诗里说当时“幽都”被淹后“千年刚卤地无肤”,也与石峁遗址为“石筑”且周边荒凉相符。
王国维“幽都”说源头之一很可能来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尧欲传天下于禹,共工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幽州之都”应是较大都邑,也与今石峁规模相符。
2.《山海经》神话
根据《山海经》对“邢天无头”神话的记载,与今银川一带人面岩画中显示向西的一支其岩画的人面是四方形相符[8];以及对古泾河河谷“西王母”故事记载与今泾河河谷一直流传的“西王母”崇拜习俗也相符,且与史前作为男权社会的黄帝族迁徙途经泾河河谷而与“西王母”女权部族对峙的史实呼应[8],等等,推论《山海经》确以神话形式多少留下了陕甘宁晋一带某些远古“史影”,故它或许有助于破译石峁遗址奥秘。
一是《大荒西经》写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这一段记载,故事限于共工与大禹对抗,首先,点清了不周山地望在“西北”。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与共工对立者舜禹部落地处晋南,那么,《山海经》说明不周山地望在“西北”,就顺理成章了。这一段记载所谓“海之外”,鉴于当时“河”、“海”不清而不分,其意应指“河对岸”,因从晋南望不周山,它正在西北部黄河对岸。其次,说清了不周山的水景分“水西”和“水东”,实际点明了不周山东面的河水是正北正南流向,恰恰符合从今石峁看“黄河晋陕峡谷”的景况。再次,说明了不周山上有名为“黄兽”的石质或玉质刻品,也与今石峁出土大量石质或玉质神兽刻品情况一致。最令人注意且对本文论题有某种决定意义的是,这段话最终点明了“不周山”就是“共工国山”。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神话所谓共工“撞倒不周山”,实际是指共工与禹打仗,“禹攻共工国山”,结果是共工把自己部落的“国山”给“撞倒”了,实指自己毁了自己家园。古往今来,许多解说“不周山和共工故事”者,都少说此历史实况,误引人意,值得今天石峁遗址研究者引为鉴戒,认定不周山就在黄河西岸,且是一座军事城堡。实际上,今天的石峁遗址,正好呈现出军事城堡的许多特征,包括在石峁城址外城东城门附近发现了“马面1号”和“角楼1号”两处遗址,土石结构,石头包裹土层,保存完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土石结构城防设施实物。请设想一下,在今黄河西岸,从晋南看的西北方向,当时可以被视作强大的“共工国山”即不周山者,除今日石峁遗址之外,更有何址堪当?如果找不到别的遗址堪当不周山,那么,我们除了认定石峁遗址即不周山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思路呢?其实,虽然后来的《淮南子·天文训》把共工对手大禹换成黄帝儿子颛顼,但它无意中更细致地点清了不周山近处黄河流向,说共工“怒触”不周山之后,“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如果对着神木县地图,那么,你就会看到,《淮南子·天文训》在这里关于不周山附近河水呈东北—西南流向的描述,其实说的正是石峁附近的黄河。在陕北府谷和神木县境,黄河并非从正北流到正南,而是在今黄甫镇一带,开始从东北流向西南,一直流到佳县县城,又开始转向。正因黄河在不周山这里从东北流向西南,才会有《淮南子·天文训》关于共工撞山后“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笔者认为,这是今石峁遗址即不周山的又一有力的神话学证据。
二是《山海经·西次三山》载:“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临彼崇岳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爰有嘉果,其实如桃,其叶如枣。”这段话,首先,说清了不周山在黄河西岸。其次,说清了不周山颇高,从不周山上东看黄河,河水“浑浑泡泡”,简直就是“黄汤”。在中国,用“浑浑泡泡”四个字描写流在黄土高坡上的黄河水最形象。再次,说清了不周山上枣桃嘉果好吃。这些记载,均与今石峁遗址的地点、地势、水景、果类完全相符。
三是《大荒北经》载:“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山。其所歍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姓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海内北经》也写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两段所讲,均是共工与大禹斗争的一个片断,或许便是二者打最后一仗的某些情况。所谓相繇“九首蛇身”、“食于九山”、“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等,讲的都是相柳(相繇)作为共工族的图腾形状。据郭沫若先生和田昌五先生等考证,共工族势力强大,霸道九州,故以“九首”、“九山”等“九”数为图腾特征。其中一个记载细节说相柳“不敢北射”共工台,后者的蛇图腾头向着南方。这似乎说明相柳害怕北边的共工族,作为共工下属,不得不以洪水为屏障与大禹作战,致使战后该地五谷树木不生。大禹胜后,几经填土,在此造成了“众帝之台”。结合前述《山海经》所记,此“众帝之台”应即今石峁,因今石峁上玉制石制人像很多,堪称“众帝之台”。另外,今石峁遗址上留存的严密军事设施,也可佐证当年战争的血腥。大禹对共工城堡“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又正好与今石峁遗址里边长约90米的祭坛共三层相合,恐非偶合。
3.《国语》与《山海经》的联合证据
《国语·鲁语上》载:“共工氏之伯九有”,“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行,共工用灭。”这一神话,是从政治品德上把不周山故事引向对共工的否定,包括说他故意削平高丘、填塞洼地而堵河道,造水灾,害人民,只能走向毁灭。“伯九有”即“霸九州”。从这里看《山海经·大荒北经》以下描写,可能会对共工故事了解更全面:“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直目正乘,其暝乃晦,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在这里,“西北海之外”五字同于上述《大荒西经》对不周山基本方位的描述;关于“烛九阴”的描写,也同于《国语·鲁语上》所讲共工“霸九州”,故此说已隐隐指向不周山,唯“赤水之北,有章尾山”之说似乎又不是这样。但细看神木地图,在石峁遗址之南,有今秃尾河流过,此“赤水”应指今秃尾河。果真如此,则《大荒北经》对不周山上共工氏图腾的描写也就明确了:以红色蛇身人面而似乎蜿蜒不绝者为神祇,神祇竖立生长的眼睛正中有合成一条缝的眼皮,它闭上眼睛就是黑夜,睁开眼睛就是白天,而且它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只吃风喝雨,象征它能统治九州,此即“烛龙”。从这个神话的文化蕴含看,这条“烛龙”实际就是当年大禹族面对的滔天洪水的神话式形象表达。《山海经》最后一段话即记“洪水滔天”,“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九州”即《大荒北经》所讲的“烛九阴”。由此设想,当年大禹治水,不仅面对着自然界洪水灾害,而且面对着异族利用洪水挑战,天灾人祸并行。今黄河晋陕峡谷北边的共工部落,与在其南不远处治水的大禹部落之间,在治水前后展开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共工族失败,大禹治水成功。所谓“共工怒而触不周山”,应是对共工族在无奈和激愤中失败情绪的神话式描述。结合前述证据,由此推知,今石峁遗址就是被大禹征服过的“共工国山”,即不周山。
(二)文字学证据
1.“共工”与“洪江”的字源对应
夏禹治“洪水”的“洪”字,为什么是“三滴水”右边一个“共”字?依我们看,这可能是由“远古军事地理示意图”演变而来的汉字。中国古代地理图与今日地图方向坐标相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在此“远古军事地理示意图”中,“洪”字正好标示河的西岸,是“共工”部落的山头。这个示意,也完全符合当年“共工”部落盘踞黄河西岸大山头而倾泻滔滔黄河水企图战胜大禹部落的史实。很可能,当时大禹部落的人逐渐把这个“军事地理示意图”看成了可怕洪水的代号,遂有“洪”字和“洪水”一词的产生。在远古大禹部落先民心中,可怕“洪水”与“共工”部落就这样变成了一体。其实,中国汉字中,表示地图或地理环境的字不止一两个。
何新先生认为,共工上述故事实际“只不过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自然现象被人格化后的产物”,因为“‘共’字与‘洪’字相通,而‘工’字又与‘江’字相通,共工其实就是‘洪江’”,远古洪水“实际上正是共工触山这一神话的深层结构。而其表层结构,却转化为这种自然灾害的人格化形象——洪江被变名为叫‘共工’的天神”[17]59。此说虽完全无视远古神话蕴含的“史影”,但却把“洪江”二字的历史源头突现出来了,印证着笔者上述见解,值得重视。
2.“不周”臆解
以“不周”二字命名一山,其中“不”字尤其特殊,也值得一究。依方睿益先生之见,姬周王室使用的“周”字,是关中山川风水形胜的形象模拟[18]423,很有说服力。《山海经》称颂姬周,显然是两周文人所著。其《海内西经》说周人先祖后稷葬地“山水环之”,意指其风水形胜。而以“不周”二字命名石峁,我估计也是对其山川形势不合乎姬周风水模式的蔑称。试看石峁,既非“山水环之”,更非“前朱雀,后玄武”,而是无土石崖,黄汤流于东而石崖悬于西,可谓风水极不佳,故《山海经》等才以“不周”二字名之。
《史记·律书》记载,中国远古先民把各种风按方位分为若干类并分别命名,其中来自西北方向者被叫做“不周风”,曰“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史记》作者自称“世典周史”,他显然也按姬周风水思路审视西北不周风,甚至说它“主杀生”,可见“不周”二字确从姬周风水模式出发而含贬义。
(三)考古学证据
1.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公布,经碳14测定,确认石峁遗址最早处距今4300年左右,约在300年后的夏代毁弃。而李学勤先生从考古成果认定的大禹时期也在此前后,与尧舜禹时期密切相关的晋南陶寺遗址也发掘出距今4300年前和4100年前的“王”墓[13]35-37,这些都是大体同时期的石峁即不周山的时间证据。其中,石峁于夏代毁弃的时间结论,也与本文以上结论相符。
2.近代我国考古发现,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北方一系列河流(包括黄河干流及其支流,如湟水、洮河、洛河、伊河、沁河等)均出现洪水灾害;2002年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媭”上有98个字的铭文,其中包括“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13]50,与《尚书·禹贡》关于“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文献记载彼此呼应,从考古学上证明大禹治水确为史实,故推知与大禹治水相关的共工国“不周山”也应为真,它即今石峁遗址。
3.石峁遗址在规模上大于西安杨官寨遗址,也远大于同时期的浙江良渚遗址和山西陶寺遗址等,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且出土玉器6000件左右,人们只能承认它是当时一个强大部落的都邑。在当时当地,这个强大部落的都邑只能是共工的不周山。它建在高高的石崖山上,应与当时黄河沿岸滔天大水泛滥相关。在考古界于黄河西岸的陕北再发掘出新的其他大型史前遗址前,结合神话学证据看,对石峁遗址只能有这一种考古文化学解释,别的解释均似不妥。
[1]胡义成.西安“黄帝都邑”杨官寨遗址探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4):112-119.
[2]李韵.石峁入选世界重大考古发现[N].光明日报,2013-08-24.
[3]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N].光明日报,2013-03-25(《国学》版).
[4]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3.
[5]叶舒宪.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的形成[N].光明日报,2013-07-23.
[6]宋耀良.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M].上海:三联书店,1992.
[7]王天顺.河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胡义成.银川“萨满”进关中——关中黄帝族源探研[C]//胡义成,等.周文化和黄帝文化管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9]胡义成.西安古都史当在五千年以上——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新探[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5):92-104.
[10]沈长云.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N].光明日报,2013-04-15(《国学》版).
[11]杨东晨.黄帝与华夏文明——黄帝治理天下及其创造发明概述[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2):13-19.
[12]陈民镇.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N].光明日报,2013-04-05(《国学版》).
[13]国家文物局,等.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4]杨雪.哥贝克力石阵与石峁古城[N].光明日报,2013-09-23.
[15]朱鸿.石峁遗址的城与玉[N].光明日报,2013-08-14.
[16]王国维.观堂集林.缀林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
[17]何新.诸神的起源[M].北京:三联书店,1986.
[18]张亚初.商周古文字源流疏证: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